第一部:動盪童年
民國初年,在那個軍閥割據的動亂時代,我出生於安徽蕪湖。母親生了四個孩子,我是最小的女兒,有一個哥哥和兩個姊姊。相較於當時許多窮苦人家,我算是很幸運的,生長在富裕家庭,從小就有個非常疼愛我的奶媽,每天幫我綁辮子、照顧起居。奶媽身材修長、皮膚白皙、濃眉大眼、五官深邃,是個小腳美人。她是我最親密的人,不論搬遷到中國哪個地方,甚至奔走越南,她都不離不棄陪伴著我。直到後來我為了躲避共產黨迫害,必須逃到香港,才失去奶媽的音訊。
我的個性鬼靈精怪,家中老小都說我聰明伶俐,非常疼愛我這個「三姑娘」;如此集三千寵愛於一身,倒使得我有些驕縱了。有一天,母親要出門,我吵著要跟,母親拗不過我,只好把我帶出去。可是,我只顧著跟出去玩,卻忘了告訴奶媽,奶媽和父親遍尋不著,急得跳腳。回來後,暴怒的父親怒斥我一頓,我覺得很委屈,就把自己鎖在房裡三天三夜,任由母親和奶媽在外哭求也不出來。最後,父親不得不到房門口對我說:「鳳楨乖,開門吧,不然木匠可要把門鋸壞喔……爸爸錯了,爸爸對不起!」這時,哭得滿臉通紅的我才打開緊閉已久的房門。由此可見我有多麼剛烈倔強、恃寵而驕,想想也真難為我的家人了。
小時候,我先讀私塾,然後就讀新式學校。童年時光真是愉快,不論鬥蟋蟀、騎馬、繡花,還是讀書,奶媽都陪著我。我跟奶媽一起度過了許多幸福時光,甚至經歷過奇幻事件,因為我們竟然一同看見家裡的「狐仙」!
在這個富足的大家族裡,我無憂無慮生活著,一天天成長。直到日本侵略中國,美好的童年才驟然改變。
除了奶媽,全家最寵愛我的就是爺爺了;每當憶起這位和藹可親的老人家,心裡總是充滿溫暖與崇敬。
猶記得小時候,每天清晨我都會到爺爺房裡背誦《朱子治家格言》,提起毛筆寫三行小楷。爺爺邊吃著銀耳蓮子羹,邊看著我背誦經書、寫完小字,就會滿意地發零用錢給我;心情好的時候,還會多說個故事給我聽。看在旁人眼裡,我十足就是爺爺捧在掌心裡的寶貝。
每逢初一、十五,爺爺都會發放白米和三個銅板給家鄉的乞丐,殘障者加倍餽贈。過年期間,他還會委託當地米店,匿名贈送白米給每一戶清苦人家。
閒來無事的時候,爺爺會把醃豬肝切成薄片,邊餵著心愛的大黃貓,邊說故事給我聽。爺爺說的不是《三國志》或《西遊記》這些家喻戶曉的故事,而是縣府官員如何判案。每當說到一個段落,爺爺總是會問我:「這個李某某那麼可惡,害了那麼多人,妳說我們該打他幾下板子?」家中祖上曾任撫臺,爺爺說故事給我聽的時候,也喜歡討論法律案件。這種正氣凜然的精神從小就深植我心,難怪我一輩子充滿正義感、性格剛烈。
有一天,他老人家淡淡地交代父親:「你們這幾天都待在家,不要離開我。」父親聽了直嘀咕著:「上了年紀的人盡說些怪話……。」三個禮拜後,爺爺安詳仙逝,享壽八十四歲。慈祥爺爺留給後人的印象,盡是喜愛讀書、尊重法治、樂善好施,這些都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中,在漫漫人生路上引導著我。
成長於新舊交會的時代,不論好事壞事,其實都經歷了不少。回憶兒時最折磨人的兩件事,一是令人苦不堪言的「三日瘧」,另一件就是「纏足」。
在中國,女孩長出完美的小小腳丫,是每戶人家最重要的一件事。一千多年來,婆家品評媳婦的標準就是「進門看腳,出門看頭」:先看女孩的雙腳是否小巧,再看女孩的頭髮是否整齊。花轎轎簾的長度蓋下剛好露出女孩的雙腳,這是出身與家教的標準。
母親和奶媽都是小腳,她們希望我日後嫁得好,總是辛苦含淚裹住我的腳,我常常痛得淚水直流、嚎啕不已。有一天,母親和奶媽好不容易淚流滿面又滿頭大汗地裹好我的腳,我卻趁著大人不注意,喀擦一聲把裹腳布剪斷了。母親氣急敗壞地拿起雞毛撢子往我身上抽,我拚命哭鬧奮力反抗,奶媽則是哭著攔阻,幫我挨了好幾鞭。「打死我,打死我!打死我就不用再受罪了!」千年來每個家庭的辛酸戲碼,在我們家上演了好一段時間。
大人們忙亂的綑綁終究是徒勞無功,成堆的裹腳布被汗水和淚水濕透,也都被我剪爛了。最後母親終於放棄,奶媽也投降了,大家心裡嘀咕著:「不裹了,大腳就大腳吧!鳳楨日後的嫁妝加倍吧!」
數十年後,總算盼到回鄉探親。這次,我的眼淚不是滴在裹腳布上,而是滴在母親的墳頭上。哭號聲穿過樹梢,傳遍家鄉田野。這麼多年來,每每低頭望著變形的腳趾,到底是惆悵還是痛苦,我也說不清楚。
父親在蕪湖經營了一家百貨公司,放學後,我經常到那兒玩耍。
有一天,父母都不在公司,某個權貴手下剛好就在這天來到百貨公司「稽查」。那是個目無法紀的亂世,大隊人馬高聲叫嚷著要檢查有沒有偽劣品,是否哄抬物價。其實,當時的人們都知道,遇上這種「假稽查真找碴」,都要奉上銀兩才能「花錢消災」。但是父母親都不在,只有我這個女娃兒在。
帶頭的惡棍說話官腔官調,他們見今天出來應對的,竟然是我這個梳著兩條辮子的女學生,個個都樂壞了。百貨公司顧客與圍觀路人也都在旁議論紛紛,碰到惡煞上門,女學生該怎麼辦?
他們囂張地用手槍指著我的額頭,脅迫我跟他們走。這種舉動真的激怒了我,我大手揮開前額的手槍,飛出的手槍打中櫥窗,玻璃碎裂。我大聲喝道:「拿槍!」公司員工從四面衝出,拿著二十多挺機槍,團團圍住這群惡霸。雙方對峙僵持一陣子,帶頭的惡棍見情勢不對,大喊「撤退」;圍觀群眾則是爆出熱烈掌聲,歡送這些惡棍離去。
隔天,當地報載著頭條大新聞:「女學生喝退惡霸,百貨公司官逼民反」。權貴手下後來被移送法辦,人人稱快。多年後,我在台灣巧遇《蕪湖日報》記者吳碟,聊起這段火爆往事。吳碟驚呼:「妳,那個拿著機關槍的徐鳳楨,好厲害啊!」
不分亂世或治世,不論青春或年邁,我這嗆辣個性從沒改變過,朋友和家人常勸我別看政論節目,免得血壓飆高。我很喜歡做「大蒜燒雞」,噴香的大蒜、辣椒、醬油、糖和酒拌著雞肉,濃郁滋味融合得徹底又突出,像極了我的嗆辣性格。傳統安徽人稱這道菜為「乾鍋雞」,它讓人看著垂涎不已,吃第一口稍辣,吃第二口就欲罷不能!
大家都說,這「大蒜燒雞」就像我的熱辣基因,真是「菜如其人」,一輩子嗆辣到底。不過,這種「人敬我,我敬人」的態度,也使得我從「辣妹」到「辣婆」都挺直腰桿兒,一輩子問心無愧!
民國二十六年,日軍攻陷上海,我和家人遷居昆明,就讀當地寄宿中學。雲南生活充滿了青春洋溢的回憶,昆明美景則是令人魂縈夢繫;不過,經常讓我午夜夢迴的,卻是寄宿學校日復一日的米飯配醃黃豆。
抗戰期間,大家都挨餓受凍。在寄宿學校中,每個人都端著飯,就著面前一盆醃黃豆,用公筷夾醃黃豆到自己碗裡吃。只有醃黃豆,沒有其他東西,根本吃不飽。當時肺結核盛行,與眾多病患一同進食,非用公筷不可。生病的同學真是可憐啊,他們都好瘦好瘦,還常常吐血。公共衛生差,營養更差,病情根本沒有機會好轉。
教室都被敵機炸毀了,我們經常被迫在操場上課;為了躲避轟炸,在防空洞上課更是司空見慣。唉,餓得都沒力氣了,上課還要帶個小凳子跑來跑去。終於捱了一個禮拜,週末放假回家,我都會飛奔到豬腳麵攤大吃特吃,一次可以吃好幾碗,真的餓啊!
每次跟別人提起這段往事,看似在消遣自己,其實眼角都有點濕了。現在物質充裕,許多人吵著要減肥瘦身,很難體會我們當年的飢餓滋味;對大多數人而言,當年那樣的飢餓感,應該就是所謂的「白首宮女話當年」吧!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汪奶奶的人生廚房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汪奶奶的人生廚房
這不是一部食譜,而是一位不凡女性的酸甜苦辣人生。這不是百歲人瑞的頻頻回首,而是蕩氣迴腸的動盪時代傳奇。
這位大時代奇女子,熱情豪爽、廣結善緣,照料家人也熱愛朋友。數十年來,她的好手藝讓各方親友讚不絕口。她經常感嘆,飲食文化倒退即社會文化敗壞,因而興起述說自身故事之念。從兒時家鄉、日軍侵華、艱困求學、經商之路,到美食品味、生平趣事、養生之道、處世哲學,我們將這長達一世紀、跨越百年的點滴故事集結成冊,期盼她的人生智慧與精巧手藝得以傳承,大時代的傳奇得以見證。
本書以汪徐鳳楨女士的精彩點滴回憶為主,穿插介紹她的拿手家常菜,將這位百歲老奶奶見證過軍閥割據、對日抗戰、國府來台的壯闊歷史,以及她那令人回味不已的磅礡廚藝,以色香味俱全的方式端出來給讀者品嚐。歲月淹沒的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隨著各道佳餚的煎煮炒炸呈現出來,讓我們這些沒經過那段動盪歲月的後生晚輩體會當時的人生況味。我們不僅期盼汪奶奶的美食佳餚能滿足讀者的口腹之慾,同時衷心盼望,她那獨具見解的人生哲學也能刻劃在讀者的心版上,餘音繞樑、久久不散。
本書特色
一位不凡女性的酸甜苦辣人生;
一段蕩氣迴腸的動盪時代傳奇。
作者簡介:
汪徐鳳楨女士,又名徐海綸、黃美貞,親友稱她三姑娘、三姊、汪奶奶,晚輩暱稱她為「頗婆」。原籍湖南湘陰,民國六年生於安徽蕪湖,先祖曾任安徽撫臺。曾於上海求學,後因抗戰輾轉奔走雲南、越南和香港,後肄業於雲南法政大學。
汪徐鳳楨女士曾旅居香港四年,民國四十年代來台經商,胼手胝足經營著棉紗買賣與餐飲事業。後來放棄經商,與汪祖華先生結髮終老。婚後以創意巧思與豐沛熱情照料先生日常三餐,夫唱婦隨環遊世界。
TOP
章節試閱
第一部:動盪童年
民國初年,在那個軍閥割據的動亂時代,我出生於安徽蕪湖。母親生了四個孩子,我是最小的女兒,有一個哥哥和兩個姊姊。相較於當時許多窮苦人家,我算是很幸運的,生長在富裕家庭,從小就有個非常疼愛我的奶媽,每天幫我綁辮子、照顧起居。奶媽身材修長、皮膚白皙、濃眉大眼、五官深邃,是個小腳美人。她是我最親密的人,不論搬遷到中國哪個地方,甚至奔走越南,她都不離不棄陪伴著我。直到後來我為了躲避共產黨迫害,必須逃到香港,才失去奶媽的音訊。
我的個性鬼靈精怪,家中老小都說我聰明伶俐,非常疼愛我這個「...
民國初年,在那個軍閥割據的動亂時代,我出生於安徽蕪湖。母親生了四個孩子,我是最小的女兒,有一個哥哥和兩個姊姊。相較於當時許多窮苦人家,我算是很幸運的,生長在富裕家庭,從小就有個非常疼愛我的奶媽,每天幫我綁辮子、照顧起居。奶媽身材修長、皮膚白皙、濃眉大眼、五官深邃,是個小腳美人。她是我最親密的人,不論搬遷到中國哪個地方,甚至奔走越南,她都不離不棄陪伴著我。直到後來我為了躲避共產黨迫害,必須逃到香港,才失去奶媽的音訊。
我的個性鬼靈精怪,家中老小都說我聰明伶俐,非常疼愛我這個「...
»看全部
TOP
目錄
第一部:動盪童年
【三千寵愛珍珠丸子】【思念無盡梅菜扣肉】【千年辛酸鹽水雞塊】【嗆辣到底大蒜燒雞】【飢餓難耐可樂豬腳】
第二部:戰亂青春
【漫天砲火乾燒牛肉】【亂世佳人蓮藕丸子】【風雲詭譎肥腸三絲】
第三部:客居香江
【漂泊流離蘇式燻魚】【魂縈香江酥炸大蝦】【怡然優雅乾煎素鵝】【遠渡重洋清蒸鮮魚】
第四部:定居台灣
【克勤克儉蔥開煨麵】【初試啼聲三合鳳翼】【懷念家鄉雙冬烤麩】【門庭若市筍片牛肚】【眉飛色舞糯米燒賣】
第五部:快意人生
【有捨有得十香素菜】【情定一生紅燒牛肉】【過盡千帆鹹魚...
【三千寵愛珍珠丸子】【思念無盡梅菜扣肉】【千年辛酸鹽水雞塊】【嗆辣到底大蒜燒雞】【飢餓難耐可樂豬腳】
第二部:戰亂青春
【漫天砲火乾燒牛肉】【亂世佳人蓮藕丸子】【風雲詭譎肥腸三絲】
第三部:客居香江
【漂泊流離蘇式燻魚】【魂縈香江酥炸大蝦】【怡然優雅乾煎素鵝】【遠渡重洋清蒸鮮魚】
第四部:定居台灣
【克勤克儉蔥開煨麵】【初試啼聲三合鳳翼】【懷念家鄉雙冬烤麩】【門庭若市筍片牛肚】【眉飛色舞糯米燒賣】
第五部:快意人生
【有捨有得十香素菜】【情定一生紅燒牛肉】【過盡千帆鹹魚...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汪徐鳳楨
- 出版社: 美好事物 出版日期:2017-08-30 ISBN/ISSN:978986877857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60頁
- 商品尺寸:長:230mm \ 寬:170mm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傳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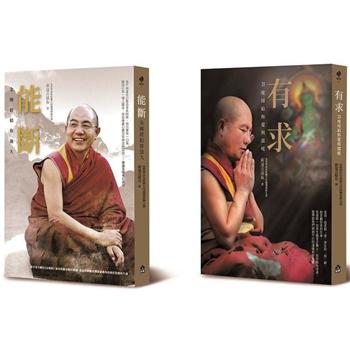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