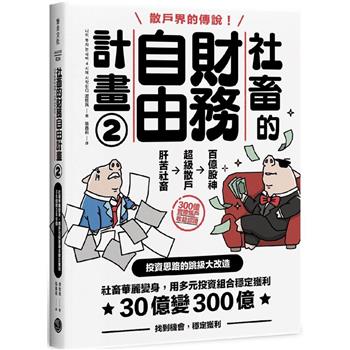圖書名稱:我睡不著的那一年
☾ 失眠苦主版《愛麗絲夢遊仙境》
☾ 亞馬遜四顆星推薦
☾ 輕巧且愉悅的的閱讀,有種永恆的寓言感,令人回味無窮——《衛報》
☾ 穿越失眠的噩夢,進入一處奇妙的無眠之境——《每日郵報》
「什麼時候睡眠成了一種信仰?」
當我不睡覺的時候,我是根本沒睡。
那些日子裡我並不全然是個不好的睡眠者,我是個不眠者。
我同時也是個不好的睡眠者,但睡得不好的夜晚都算是美好的夜晚,
因為至少有睡。
午夜、凌晨兩點、三點、四點、甚至五點,沒有差別
不管數了幾隻羊、燃起精油或助眠音樂,努力告訴自己不要在意
進入夢鄉的意欲依舊全無
而睡不著的夜晚是最長,最大,最像洞穴般深遠的事⋯⋯
關於失眠,你是否做過這些嘗試?
✘在正式進入睡眠前,提早一小時上床醞釀睡意
✘戒掉咖啡因和糖
✘正念減壓
✘找諮商師或是治療睡眠診所就診
✘針灸、或是各種預算能夠負擔的民俗療法
✘身心靈諮商溝通
✘✘✘✘✘✘✘……
但是這一切的努力,一點用都沒有。
無形的黑暗和思緒迷霧,在每個睡不著的夜晚裡,不斷蔓延;
而無法入眠的恐懼和焦慮,助長了失眠,彷彿老虎在場。
2016年,薩曼莎.哈維從即使處在壓力之下都能安然入睡的「睡眠無憂者」,成了——
難以入睡(擁有二到三小時睡眠)到完全沒睡的「無眠者」。
「我必須繼續做自己的考古學家,四處探尋,看看我是否能夠挖掘到問題並找出解決方案——但事實上,我害怕我自己,不是害怕會找到什麼,而是害怕一無所獲。」
哈維去找了諮商師,想了解潛意識中是否隱藏了什麼不安——如影隨行的死亡恐懼、15年前受創的陰影,還是只是,即將進入更年期的天賜之禮……。在這一年,哈維想盡辦法安撫自己的清醒,尋找幾乎不存在的睡眠,並且無所不用其極:藥物、運動、療法、放鬆技巧、飲食調整、改變生活上的安排,但,沒有任何幫助。
於是她寫作。寫下無眠夜裡的混亂思緒:表哥的死亡、信仰與科學的哲學思辨、對脫歐的憤怒……即使寫出來的東西看似雜亂無章,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開始在寫出的文字裡看見自己……
#關於失眠
「對我來說,現在,出現了一道謎題。那麼,是什麼助長了失眠——恐懼還是焦慮?焦慮,每個人都這麼說。我的催眠治療師說是焦慮,你躺在床上很安全,但心臟卻急速跳動,彷彿老虎在場。你必須學會根本沒有老虎。」
#關於不安
「心之所以會驕傲是由於無形的不安。」
#關於時間
「時間,不是生命,是我們的生活。時間,不是生命,是一種耗盡。時間將死亡推到我們可見之處,然後供予自身有限的保護。時間是恐懼和絕望的溫床。」
#關於信仰和科學
「宗教是神的信仰,科學是理性的信仰。我愈看這兩者,它們之間的差異就愈小。科學的信徒愈是將理性作為萬物的仲裁者,理性就愈像是被崇拜的神。理性是一種只證明自己的東西,如果你用理性來找出什麼是正確的,你會發現唯一正確的事是能夠藉由理性達成的事。這樣的事物我們稱之為「合理的」。」
#關於寫作
「寫作就是在作夢,並不是所有的夢都能夠得到解釋,而且,並非所有的解釋都會是正確的。而且,並非所有的解釋都會是有趣的。而且,夢就是事情本身。」
#關於再次入眠
「妳需要相信自己可以再次入睡。」
薩曼莎.哈維以混雜著寫實描述和非寫實小說體,創造出如夢似幻的詩意,任著意識跨越在清醒、焦慮和無聊之間,在天亮的幾個小時前—去經歷、去淘洗、去思考、去創作。如同一場失眠者的夢遊奇境。而深刻的失眠書寫所描述的痛苦、不安、憤怒、疲憊、恐懼和絕望,也在漫遊間得到自由。
進入無眠之穴不論可否歸因,那也許是宇宙多給你的重整之時,為自己梳理。
致那些晚上醒著的人:
這就是治療失眠的方法:沒有什麼事是恆長不變的。
一切都會過去,這個也是。
有一天,當你受夠了它,它會失去立足點並且消逝,
你將每晚入睡,不記得自己曾經覺得這是如何不可能。
我們曾經有過,但它終究會收場,
自始至終都在與一場獨特的努力相融相伴
要催開那朵存在於此的百萬花瓣花朵。
——菲利普.拉金
本書特色
失眠是現代人的文明病—是焦慮、憂鬱、不安全感的副產品。除此之外,失眠還有許多潛在原因,例如,環境改變、懷孕、經前症候群、更年期等等……近來心理相關出版多聚焦在焦慮憂鬱等情緒紓緩、厭世療癒等指南式/經驗分享;而「睡不著真的非常痛苦,我也想要被救」、但也不能算是精神疾病的化外民無眠者,其實也很需要被救援。(尤其隔天還要繼續當上班族戰士、或是上課的莘莘學子,拍拍,真是辛苦了。)
☀自我陪伴,允許狂亂☀
薩曼莎.哈維以世界上的初級無眠者起手式開始,嘗試各種方式解決失眠問題,但無一奏效。不同於先前市場上出版過的失眠書籍,哈維沒告訴你/妳,她最後如何再度進入睡眠,但是藉由允許自己的「不正常」、「睡眠失序」、「歇斯底里」,有一天妳就是會好,你/妳必須相信這點,她便是如此。
☀文筆詩意,敘事精準☀
哈維的小說家、創意寫作講師背景,使書寫失眠筆觸頗具詩意,書中以多種具象事物描寫失眠的疲倦、無助感、憤怒,相信失眠過的人讀了都會會心一笑。
☀結構獨特,如劇本的流動感☀
沿著思緒漫遊,探討的議題範圍也擴及過往創傷、人類學、科學與哲學思辨、脫歐、穿插短篇小說創作,以介於散文、小說之間的敘事體,呈現失眠期間的所思所想。夾敘夾議又抒情的文字風格,讀起來有如觀看劇本書的流動感,跟著哈維的失眠路徑漫遊在無眠時空,失眠也能是匯聚靈感的培養皿。
作者簡介
薩曼莎.哈維(Samantha Harvey)
現任巴斯思巴大學的創意寫作碩士班資深講師(2012年至今),教授小說及散文寫作。課程指導學生從事哲學小說、思想小說、文學小說、敍事小說等方面的創作,關注於體驗時間及記憶。
除了教學與寫作外,她到處旅遊。在日本居住任教過,並曾居住於愛爾蘭及紐西蘭。最近與人共同創立了一家環境慈善機構,目前居住在英國巴斯。
她的第一本小說《原野》(The Wilderness),是一部關於阿茲海默症的作品,入圍了2009年柑橘小說獎(現稱百利女性小說獎)、2009年布克獎,並獲得2009年貝蒂.特拉斯克獎(Betty Trask Prize),並於2010年獲The Culture Show評為英國12大新銳小說家之一。
作品、書面評論、文章、散文散見於《衛報》、《獨立報》、《時代》、《每日電訊報》、《蘇格蘭人》、《每日郵報》、《紐約客》、《華盛頓郵報》。
譯者簡介
李伊婷
1980年生,高雄人。
曾任知音文創產業國外行銷主管。
喜愛文學,瑜珈及旅行。
現為自由工作者及譯者。
譯作有《聖殿騎士懸疑系列之一聖殿之劍》。
聯絡方式:stellayiting@gmail.com


 2020/08/19
2020/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