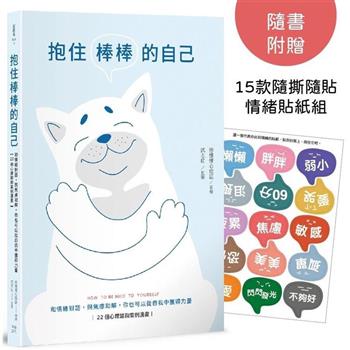【第一章】盧梭:沒有朋友的「人類之友」
(節錄)
我尤其想聚焦在「告訴人類該如何處世的知識分子們」的道德與判斷力。他們自己的人生過得怎麼樣?他們對親友與夥伴誠實正直到什麼程度?他們處理情欲與財務是否公允?他們說的、寫的都是真實的嗎?以及,他們的思想體系在經歷時間與實踐的考驗後,是否還站得住腳?這項調查從盧梭開始,他在這些現代知識分子當中居首位,是他們的原型,在許多方面也是影響力最大的一位。雖然比他更年長的知識分子如伏爾泰,早已開始進行推翻聖壇與尊崇理性的工作,但盧梭是結合現代普羅米修斯所有顯著特質的第一人:他主張自己有權利全然反對既存秩序,相信自己有能力根據他設計的原理,將既存秩序改頭換面,同時,也相信這一切能透過政治手段達成。以及最特別的,他承認本能、直覺與衝動,對人類行為的影響甚鉅。他相信自己對人類有一份獨一無二的愛,並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天賦與洞察力,使他的言詞得以精彩巧妙。在他的生前身後,以他對自己的評價來看待他的人,數量出奇地多。他的影響力無論從時間遠近來看,都很巨大。在他死後的那個世代,他的地位達到神話等級。他死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十年前,然而,當時許多人認為,促成法國大革命及歐洲舊制度垮台的人就是他,路易十六與拿破崙也這麼認為。
(節錄)
盧梭為後人留下的思想寶藏,以及他對於文化演進的相關想法,後來受到馬克思等人的攫取繼承。對他來說,「自然」指的是「原始」或「文化出現以前」,由於個人與他人的關係會誘發人類的邪惡傾向,因此所有文化都會帶來弊端:如同他在《愛彌兒》中所寫,「一個人所吐出來的氣息,對其同胞是致命的」。因此,人類文化本身便是一個會不斷發展的人造結構,會規範人們的行為舉止,而你可以透過改變文化,同時改變產生這些文化的競爭因素,確實又徹底地改善人類的行為──這得靠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盧梭要建構的這些概念是如此廣泛,幾乎光是概念本身,便是現代思潮的百科全書。
當然,這些概念並非全都出自盧梭。他博覽名家:笛卡爾(Descartes)、拉伯雷(Rabelais)、巴斯卡(Pascal)、萊布尼茲(Leibnitz)、貝爾(Bayle)、豐特奈爾(Fontenelle)、高乃伊(Corneille)、佩托拉克(Petrach)、塔索(Tasso),以及他尤其喜愛引述的兩位哲學家,洛克(Locke)與蒙田(Montaigne)。德.斯戴爾夫人(Germaine de Staël)認為盧梭有著「最令人崇敬的稟賦」,她表示:「他沒有發明任何東西,不過,他為一切點燃了火苗。」更確切地說,簡單、直接、有力與發自內心的熱情,讓盧梭作品中的見解,看起來多麼生動又清新,許多讀者因此大開眼界。於是,這個人成為了擁有卓越力量的道德與智慧導師。而他又是怎麼得到這些的呢?盧梭是瑞士人,在日內瓦出生,被養育成一個喀爾文主義者。
其父艾薩克(Isaac)是製錶商,但生意並不太好,反而經常惹是生非,頻繁涉入暴力與暴動。其母蘇珊娜(SuzanneBernard)則出身富裕家庭,但生下盧梭之後沒多久,就因為產褥熱而過世。儘管他雙親都不是來自於統治日內瓦的寡頭政府,或是與組成二百人理事會(Council of Two Hundred)、二十五人內部理事會(Inner Council of Twenty-Five)關係緊密的家族,但他們享有最高的投票權與法律上的特權,盧梭也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優越地位,這使他出於利益(而非出於智識的信念)自然而然成為保守派人士,也使他終其一生,都藐視沒有投票權的群眾。他家裡也算是有錢。盧梭沒有姐妹,但有一個大他七歲的哥哥。痛失妻子的艾薩克特別疼愛盧梭,因為他長得像母親。艾薩克對他的態度,擺盪於哀憐的情感與恐怖的暴力之間,但即便他受寵,卻曾經公開譴責他父親扶養他長大的方式,他後來在《愛彌兒》中寫道:「為人父者的野心、貪欲、專橫與錯誤的先入為主,還有他們的疏忽與殘酷的無動於衷,比起為人母者欠缺思慮的心軟,對孩子的造成傷害更勝百倍。」不過,父親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是哥哥,一七一八年,他因為父親的請求被送入少年感化院,理由是他的頑劣屢教不改。一七二三年,他逃走了,就此音訊全無,也讓盧梭成了實質上的獨子,他對許多當代的知識分子領袖就是這麼說的。不過,儘管多少會覺得自己幸運,但他從孩提時期便有強烈的被剝奪感,以及自哀自憐──後者或許是他最為人所知的個人特質。
死亡很快地奪走他的父親與養母,他不想做版畫學徒,於是他十五歲時(一七二八年)逃走,並皈依天主教,以獲得法國安訥西(Annecy)的華倫夫人(Françoise-Louise de Warens)保護。《懺悔錄》中盧梭早年職涯細節的記錄並不可信,但他的私人書信,以及「盧梭產業」龐大的資料,已經被用來建立一些沉默的真相。
華倫夫人依靠法國王室撥給的退休金度日,而且似乎是法國政府與羅馬教廷之間的密探,盧梭與她同住,靠她吃穿,從一七二八年至一七四二年,度過了最美好的十四個春秋。在這段時間裡,他們倆有一段時間是戀人,但也有幾段時間他自行離開對方。到他安然邁入三字頭的年紀以前,他都過著失敗且依賴的生活,尤其是依賴女人。他換了至少十三份工作,雕刻匠、僕役、神學院學生、音樂家、公務員、農夫、家庭教師、出納員、樂譜抄寫員、文書與私人祕書。
一七四三年,他成為法國駐威尼斯大使蒙太居伯爵(Comte de Montaigu)的祕書,雖然這個差事看起來合他意,但他做了十一個月後就被解雇並且馬上逃之夭夭,以免被威尼斯大議會逮捕。蒙太居聲明(相較於盧梭的說法,人們更相信這個版本),他的祕書因為「卑劣性格」與「難以形容的傲慢」,導致「狂悖」與「自命不凡」而注定窮困潦倒。
有幾年盧梭自認是天生的作家,他用字遣詞技巧一流,尤其自認在寫信時特別出色,但他在尊重事實方面卻不怎麼嚴謹。確實,他如果是律師應該會很優秀。(蒙太居是個軍人,他這麼厭惡盧梭的理由之一,是因為這位大使在口授書信時,費力想著該怎麼拿捏措辭,盧梭卻時常誇張地打個大呵欠,甚至遛躂到窗戶旁邊。)一七四五年,盧梭認識了年輕的洗衣女泰蕾茲(Thérèse Levasseur),她比盧梭小十歲,答應長期做他的女傭。這為他漂泊的生活帶來些許安定。與此同時,他也認識並結交了狄德羅(DenisDiderot),後者是啟蒙運動的重要人物,後來主編了《百科全書》(L’Encyclopédie)。狄德羅和盧梭一樣是工匠之子,靠自身努力成為作家的典範。他寬容大度,對人才的照顧不餘遺力,盧梭欠他很多人情。盧梭透過他認識了聲譽卓著的德國文學評論家暨外交官格林(Friedrich Melchior Grimm),格林帶他參加霍爾巴赫(Baron d’Holbach)的激進派沙龍,這個沙龍便是知名的「哲學領班」(le maître d’hôtel de la pralosophie)。
法國知識分子的力量才剛發端,並在這個世紀的下半葉穩定地拓展開來,但在一七四○與五○年代,他們身為社會評論家的地位還不夠穩固,政府如果覺得自身受威脅,依舊可能導致突發的政府暴力行為。盧梭後來大肆抱怨他所受的迫害,但實際上與同時代的人相比,他的遭遇輕微許多:伏爾泰因為得罪一位貴族,被其僕役公開鞭打,並在巴士底監獄(Bastille)服刑了快一年。販售禁書者則可能要在槳帆船上服刑十年。
一七四九年七月,狄德羅因為出版一本為無神論辯護的書遭到逮捕,並被單獨囚禁在法國樊尚(Vincennes)的堡壘中三個月。盧梭前去樊尚探監,途中他在報紙上看見一則公告,是第戎科學院(Dijon Academy)的論文比賽邀請函,寫著「科學之重生,和對提升道德有所貢獻之藝術」。
這件事發生在一七五○年,是盧梭一生的轉捩點。他受到啟發,覺得自己該做點什麼事。其他的參賽者不意外地會為藝術或科學辯論,他則將主張自然的優越性。突然間,就像他在《懺悔錄》中所說的,他堅信自己對「真實、自由與美德」有著無比熱忱。他自我宣告:「美德,真實!我會越來越大聲呼喊,真實,美德!」他補充說,他的背心「被不自覺流下的淚水浸濕」。溼透的背心可能是真的,因為他哭點很低。可以確定的是,盧梭立即決定要寫一篇論文,這種方式後來成為他的原則要素: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贏得比賽,一夕成名,這個目前仍就失敗、滿腔怨恨,渴望成名的三十九歲男人,至少正合時代所需。那篇論文寫得拙劣薄弱,今天看來幾乎不值一讀,當我們回頭去看這樣的文壇事件,似乎很難解釋,如此不可取的作品,怎麼會製造這麼大的名氣?確實,知名評論家勒美特(Jules Lemaître)說盧梭的瞬間神化,「為人類的愚蠢提供了強力的證據」。
(節錄)
一七六二年,隨著《愛彌兒》出版,眾人對盧梭的崇拜開始激增,他在這本書裡提出了各式各樣的想法,「論自然以及人類如何回應自然」成了浪漫主義的主旋律,但之後變成討論「未開發的原始狀態」。這本書為了確保能擄獲最多讀者,因此過於精心設計。某種程度來看,盧梭太知道如何對自己有利了。一部分是他的感染力越來越強,在宣揚真實與美德時指出了理性的侷限,為宗教在人類內心深處留下一席之地。所以他在《愛彌兒》收進《信仰這一行》這個章節,譴責啟蒙時代與他同夥的知識分子,尤其是無神論者或自然神論者。盧梭批評他們傲慢又武斷,「即便他們自稱是所謂的懷疑主義,卻無法通曉萬事」,也批評他們破壞信仰的行為,對正派的男女信眾所造成的危害:「他們毀滅、踐踏了所有人的敬畏,偷走了他們從宗教中所獲得的對苦難的慰藉,奪走了對權力、財富的追求唯一的抑制力量。」這說法相當有力,但為了平衡,盧梭覺得也有批評國教之必要,特別是天主教對奇蹟的狂熱,對盲目崇拜的鼓勵。這絕非明智之舉,尤其盧梭為了打擊盜版,甘冒在著作上簽名的風險,他老早就被法國教會人士盯上,被懷疑是雙重叛徒:曾皈依天主教,後來又為了恢復日內瓦公民資格回歸喀爾文教派。因此,由楊森教派(Jansenist)所把持的巴黎高等法院(Parlement),強力反對《愛彌兒》中反天主教的觀點,在司法宮(Palais de justice)前焚燒此書,並發出對盧梭的逮捕令。他及時收到高官友人的警告逃過一劫,此後,他做了幾年亡命之徒。由於喀爾文教派也反對《愛彌兒》,讓他在不受天主教管轄的境外之地,也被迫不斷遷移居所。但他從來不缺有力人士的庇護,在英國(一七六六至一七六七年間居留了十五個月)與法國(一七六七年之後)皆然。在他餘生的最後十年,政府不再關注他,他的主要敵人都是同輩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伏爾泰。為了回應這些人,盧梭寫了《懺悔錄》──一七七○年他終於落腳巴黎之後,在此處完稿。他沒有冒險付印,但卻在上流社會的家族裡發送,因此傳閱甚廣。一七七八年他過世時,他的名聲正是新一波高潮的前夕,並在革命者接管巴黎後,達到完美的巔峰。
然後,盧梭享有他生前未曾想過的成功。從不帶成見的現代角度來看,盧梭似乎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但他可是文學史上最愛抱怨的人之一,他堅持自己的一生充滿不幸與迫害。他抱怨得如此頻繁、痛苦與反覆,以致於有人覺得有義務要相信他。有一點他非常堅持:他長期苦於不健康。他是「受病痛所苦的可憐蟲……我有生之年的每一天都在痛苦與死亡之間掙扎」。他「受失眠之苦長達三十年」,他還補充道:「大自然塑造我來受苦,給了我證明能對抗病痛的體質,讓我再難受也不會氣力衰竭,或許我的身體覺得自己的氣力,一直都這麼強吧。」
更確切地說,他的私處一直有毛病。在一七五五年他寫給友人特羅尚醫師(Dr Tronchin)的信中,他提到「某一器官的殘疾,從我出生就有」。他的自傳作者萊斯特.克勞克在仔細診斷後寫道:「我相信盧梭一出生就罹患了尿道下裂,這是一種陰莖的殘疾,尿道的開口在陰莖腹側。」
成年後,這變成一種限制,讓他不得不痛苦地使用導尿管,對心理與生理都造成問題。他一直覺得自己需要排尿,而這會讓他在上流社會維持生計變得困難:「我還是一想到就發抖,」他寫道:「被一群婦人簇擁,強忍到某些話題結束……當我終於找到一處敞亮的樓梯間,總有另一個貴婦拖住我,接著滿院子不斷移動的馬車準備把我擠死。貴婦的侍女們盯著我,排成障壁的僕役們嘲笑我。我找不到符合我用途的一面牆或可憐的小角落。總之,我只有在一一見過每一個人,或某些穿著白襪高貴的腿之後,才能小便。」
這段文章是自哀自憐,有其他大量證據表明,盧梭的健康沒他寫的這麼糟。他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偶爾會強調自己身強體壯。他的失眠在一定程度上是幻想,因為有不同的人作證聽到他打鼾。大衛.休謨(David Hume)陪著他航行到英格蘭,寫道:「他是我認識的人裡面最活蹦亂跳的。他能在最凜冽的夜晚待在甲板十個小時,那裡的水手都快凍死了,他卻一點事都沒有。」
不管動機正不正當,他自憐最初始的樣子就是不斷憂慮健康,用來掩護、餵養他生活裡的每一個片段。他從年輕就養成一個習慣,告訴別人他所謂的「內情」以博取同情,特別是出身名門的貴婦。他自稱「最不幸的將死之人」,曾說過「殘酷的命運糾纏著我」,宣稱「像我流這麼多眼淚的男人,世間罕見」,並堅決地認為「我的命運多舛,慘到沒人敢提,也沒人肯信」。他真的經常這麼說,很多人也信了,直到他們更了解他的個性。甚至真的了解之後,還是繼續同情他。艾丕內夫人(Madame d‘Epinay)是他的資助人,雖然她已經察覺到盧梭對她態度惡劣,卻還是說:「他用簡單而原始的方式講述他的不幸遭遇時,我還是會被感動。」盧梭像是軍隊裡「老兵」,一個老練的心靈騙子,有個發現毫不意外,他年輕時寫了幾封討錢的信,有一封還留存在世。收信者是薩伏依公國的統治者,內容要求給付撫恤金,因為他罹患了可怕的、會損毀外貌的疾病,而且很快就會死掉。
在盧梭的自憐背後,是令人難以忍受的自大,他認為自己所受的苦、自己的本質,都不同於凡夫俗子。他曾經寫過,「你的不幸怎麼可能跟我一樣?我的處境舉世罕見,從古至今沒聽說過……」、「平心而論,能愛我如我愛自己的那個人,還沒出生」、「沒人比我更有愛的天份」、「我生來就是實際存在過最好的朋友」、「如果我認識比我更好的人,我會疑懼不安地離開人世」、「你找給我看看,有誰比我更好、更忠誠、心更軟、更多愁善感……」、「後代子孫會尊敬我……因為我值得」、「我對自己深感欣喜」、「……我的慰藉存在於我的自尊」、「……如果歐洲找得到一個開明政府,他們會設立我的雕像」。難怪伯克會說:「自負只是他的瘋狂行徑中,程度最輕微的小缺點。」盧梭的自負,有部分是出於他認為自己的基本情緒運作不太正常。「我感覺自己優秀到不會有恨」、「我太愛自己了,以至我無法恨任何人」、「我從來不知道憤恨是什麼感覺,嫉妒、惡意、報復未嘗進駐我心……偶爾生氣,但我從來不狡猾或積怨」。實際上,他太常積怨,而且狡猾地追逐這些憤恨,很多人也注意到這件事。盧梭是第一位公開表明自己是所有人類之友的知識分子,而且他多次這樣表明。但他所說的愛,是泛指全人類,他培養出一種強烈癖好,喜歡譴責特定的個人。他早先的友人,日內瓦的特羅尚醫師就是其中一名受害者,他曾提出質疑:「全人類之友怎麼會沒朋友,或幾乎沒有?」盧梭的回應,是捍衛他自己有權決定誰值得鞭策:「我是人類之友,人類到處都有。真誠之友還會發現,惡意到處都有──我其實不用說得太多。」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所謂的知識分子:那些爆紅的時代人物,與他們內心的惡魔(上、下冊不分售)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3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61 |
二手中文書 |
$ 615 |
世界人物傳記 |
$ 615 |
Social Sciences |
$ 648 |
Social Sciences |
$ 648 |
Others |
$ 722 |
中文書 |
$ 738 |
社會人文 |
$ 738 |
讀書共和國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所謂的知識分子:那些爆紅的時代人物,與他們內心的惡魔(上、下冊不分售)
保羅.約翰遜最受推崇、也最多爭議的經典大作
──一部現代人必看的「除魅」之書──
★暢銷多國三十餘年,是最具批判力道的人文巨著
★作者獲頒美國最高榮譽,受總統乃至知識分子的大力盛讚
★《紐約時報》暢銷書、美國亞馬遜暢銷書
「在我的經驗裡,除了說謊成癖者外,最忘恩負義、最難應付的病人就是知識分子。」──榮格
►自戀病、雙重標準,與「特殊性關係」,造就了改變世界的知識分子
‧為什麼盧梭自稱「全人類之友」,卻連一個朋友都沒有?
‧為什麼托爾斯泰大談「博愛」,卻連自己的家人都不愛?
‧為什麼高談「自由」的易卜生,卻犧牲了他人的人生?
因為,他們是這世上最會說故事的人……
你一定聽過書中的人物,他們推動人類進步、急於改變世界,包括盧梭、雪萊、馬克思、易卜生、托爾斯泰、海明威、布萊希特、羅素、沙特等。這些知識分子至今仍深具影響力,言論思想既嚇人又迷人。他們的生活特立獨行,個個精通虛張聲勢、情緒勒索、欠債不還。他們眼光遠大,甚至遠到看不見自己的缺點。
《所謂的知識分子》是一部非典型的人文巨著,作者將在本書中抽絲剝繭,將這些偉大心靈的另一面攤在聚光燈下,而你將看見思想的誕生,也將知道他們的崇高理想是否為空談,以及最重要的──他們是否配得上「知識分子」的光環。
►歷史表明:知識分子不可輕信!
兩百年前,知識分子儼然成為了人類的嚮導與良師。他們肩負重大的道德任務,也因此需要獨特的洞察力,替人類看清真相。然而,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教訓,就是要小心知識分子。他們曾經為了謀求人類的進步,居高臨下指使別人,卻犧牲數百萬條無辜的性命。
本書挑選出當代最有代表性的十多位知識分子,細細檢視他們的私人生活。你將發現,他們的眼光常常失準,也常常自相矛盾。他們表裡不一、極度虛榮、欺騙成性、性關係複雜,多數拋家棄子,極端的行為甚至害慘了整個社會。
這是一本知識分子的「除魅之書」,現代人將從中得到借鑑──要當心知識分子的言行、所屬團體,也要懂得質疑他們,因為他們常常忘記一件最重要的事:「人」遠遠比他們崇高的理念來得重要。
各界好評
「保羅.約翰遜在他的著作中,展現出淵博的知識和清晰的道德觀,深刻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美國前總統小布希
「這是一部很獨特的作品,任何人拿起這本書就很難再放下。」──《紐約郵報》
「約翰遜先生揭露了這些偉大思想家們邪惡的一面,而這也顯示本書將饒富興味。」──《紐約時報書評》
「充滿生命、活力與迷人的細節,對現在來說多麽適切,任何拿起這本書的人,都很難放下。」──《紐約郵報》
「珍貴且充滿娛樂性,是一部心靈冒險者的入獄檔案照。」──英國小說家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
「這本書對往後幾年的西方文學與文化,應該具有淨化的影響力。」──《富比士》雜誌發行人,邁爾.康富比士(Malcolm Forbes)
「這些對傑出知識份子予以重擊的人物側寫,尖鋭、帶有偏見、激發思考,讀起來迷死人。」────《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對於知識份子的傲慢、自大與惡意,辛辣且往往搞笑的仔細分析。」────美國藝術評論家金貝爾(Roger Kimball)
作者簡介:
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最高榮譽歷史學家
英國影響力最大的歷史學家之一,曾獲頒美國象徵平民最高榮譽的「總統自由勳章」,寫過多本暢銷的通俗歷史書,完整涵蓋人類所有活動。
著作超過四十本,包括《文藝復興》、《其實我沒有砍倒櫻桃樹──華盛頓傳》、《邱吉爾──樂在危險的人生》、《新藝術的故事》、《創作大師的不傳之秘》等,同時也是《旁觀者》與《富比士》的專欄作家。
譯者簡介:
周詩婷
曾任商業書編輯,現為專職文字工作者,譯著有:《銷售的科學》、《失控的銀行》、《反對思考》與《伊斯蘭國》(合譯)。
章節試閱
【第一章】盧梭:沒有朋友的「人類之友」
(節錄)
我尤其想聚焦在「告訴人類該如何處世的知識分子們」的道德與判斷力。他們自己的人生過得怎麼樣?他們對親友與夥伴誠實正直到什麼程度?他們處理情欲與財務是否公允?他們說的、寫的都是真實的嗎?以及,他們的思想體系在經歷時間與實踐的考驗後,是否還站得住腳?這項調查從盧梭開始,他在這些現代知識分子當中居首位,是他們的原型,在許多方面也是影響力最大的一位。雖然比他更年長的知識分子如伏爾泰,早已開始進行推翻聖壇與尊崇理性的工作,但盧梭是結合現代普羅米修斯所有顯...
(節錄)
我尤其想聚焦在「告訴人類該如何處世的知識分子們」的道德與判斷力。他們自己的人生過得怎麼樣?他們對親友與夥伴誠實正直到什麼程度?他們處理情欲與財務是否公允?他們說的、寫的都是真實的嗎?以及,他們的思想體系在經歷時間與實踐的考驗後,是否還站得住腳?這項調查從盧梭開始,他在這些現代知識分子當中居首位,是他們的原型,在許多方面也是影響力最大的一位。雖然比他更年長的知識分子如伏爾泰,早已開始進行推翻聖壇與尊崇理性的工作,但盧梭是結合現代普羅米修斯所有顯...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致謝
▼上冊
【第一章】盧梭:沒有朋友的「人類之友」
「他的醜陋足以嚇壞我,而愛情並未讓他增添風采。但他是個可憐的傢伙,我用仁慈與溫柔待他。他是個有趣的瘋子。」──烏德托公爵夫人,盧梭的情婦
【第二章】雪萊:追求「理想狀態」的絕情詩人
「他不介意任何年輕男子,只要他能接受,就可以跟他老婆上床。」──罕特,雪萊的友人
【第三章】馬克思:偽造科學的災難預言家
「馬克思不信神,但他很相信自己,並讓每一個人都會為他所用。他心中盈滿的不是愛而是仇恨,以及些許對人類的同情。」──巴枯寧,無政府主義者...
▼上冊
【第一章】盧梭:沒有朋友的「人類之友」
「他的醜陋足以嚇壞我,而愛情並未讓他增添風采。但他是個可憐的傢伙,我用仁慈與溫柔待他。他是個有趣的瘋子。」──烏德托公爵夫人,盧梭的情婦
【第二章】雪萊:追求「理想狀態」的絕情詩人
「他不介意任何年輕男子,只要他能接受,就可以跟他老婆上床。」──罕特,雪萊的友人
【第三章】馬克思:偽造科學的災難預言家
「馬克思不信神,但他很相信自己,並讓每一個人都會為他所用。他心中盈滿的不是愛而是仇恨,以及些許對人類的同情。」──巴枯寧,無政府主義者...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2023/09/21
2023/09/21 2021/11/14
2021/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