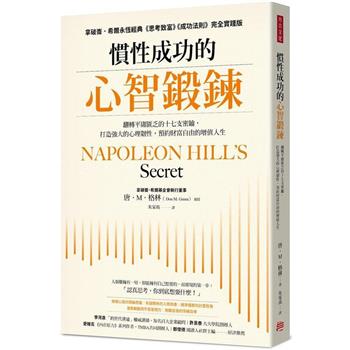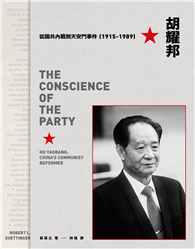一
「姓陸的!」
有夥計見陸照陽來了,便開口高喊道:「你那小孩呢?」
「他日日夜夜地跟你,可累壞了人,你怎麼就捨得那一身細皮嫩肉,你好歹給一句話,憐惜一下,要不然——」
「怕是和別的人跑了!」
「欸喲!是這個理!」
說完,全都混帳般地哄堂大笑。
這些渾人瞧不得陸照陽這樣的人,皆因他們是泥裡跑出來的糙人,最嫌那陸照陽不搭眼的高傲氣,像面鏡子,倒把他們映襯得入不得尋常人的眼。於是便絞盡腦汁地想,這陸照陽憑什麼瞧不起人?憑什麼與他們不同?想著想著,他們便死心塌地地覺得同樣是個煙燻火燎、滿泥臭汗的人。論高貴,那是都城裡貴人們的事,即便是高貴,那也要看天高不高興,免得高貴到了頭,就到了泥潭裡。
人。
該認命——掙不上幾分銀錢,掙掙扎扎一輩子,或許能討得個舒心的媳婦,傳宗接代,方不辜負投胎來的人道,在世上走上一回。
這陸照陽就理不通,是傻人,很不得人喜歡。
陸照陽面無表情地順了他們一眼,只往裡去。這時聽得外頭一聲驚呼,他的小孩——夥計們嘲諷的——就從外面探了個腦袋出來,被最壯的給揪著拉了進來。
小孩瘦弱,被風吹得像片落在人們眉梢上的不起眼的雪粒,流落到了鎮上。穿的是衣裳,卻不得體,光著腳,白晃晃般亮的肉,跟妓館女人的細肉有得比。
鎮上的人交頭接耳,因此得出個高深的結果:這樣的白膩若沒個金銀珠寶,上好脂香來養個十年八年,可不得這些勾人的顏色。
高門大戶果真與平頭百姓不同,養的玩意都比村頭的癩頭狗金貴。——他們笑了。
夥計存著要陸照陽難堪的意思,這小孩離了人,就活不下去,所以是用了什麼見不得人的狐媚法子,糾纏住了陸照陽,才沒被趕走。
小孩呼痛,眼裡噙了滴滴答答的淚水,抓著他的夥計心道乖乖,這哪像個男人,倒成了個小娘子了。
手裡抓的細腕子上冒出點紅的,那夥計唬了一跳,改抓為拎,可怕這一碰可別染上什麼不乾淨的病。縱然鬼迷心竅,捨不得那細滑的手感。
高壯夥計假意問小孩叫什麼名。
小孩抬頭先瞧了眼在那的陸照陽,隨後輕聲細語地如實道:「阿雪。」
高壯夥計酸倒了牙,又問年歲,阿雪說二十了,說完又低下了腦袋。
「這可不像二十的,倒像十三四的。」
餘下的人圍過來,阿雪往後退了一步,說:「奴……我真的二十了。」說完還看了陸照陽一眼,不知他聽沒聽到,陸照陽十分厭煩阿雪自稱奴,打從陸照陽第一次聽見,後來阿雪每說一次,便抽一下他手心。最嚴重的一次,阿雪手心被抽得皮肉紅腫,只能夜裡躲在一旁呼著手哭上一會。
到這才知,不是什麼狐媚法子,不過是著人厭煩的跟蹤乞求。陸照陽一時心軟,由著心裡那股憐憫,才收留了他。可憐憫心不易得,阿雪哭哭啼啼的作樣,早已惹了陸照陽厭煩不已,只差某日發作起來,將人徹底趕出去。
這些人見陸照陽不管不問,算盤打錯,面上過不去,心裡也過不去,皆像是被陸照陽羞辱了一番,對著阿雪便立馬換了方才那些勁,眼裡浮現的那些厭,比之陸照陽有過之而無不及。阿雪心思細弱膽怯,更有一人手腳不乾淨,將阿雪看作那妓館裡的女人,可隨意拿捏,掐在了屁股上。
阿雪驚怕地淚水漫起,低頭不敢動。這裡的人,包括陸照陽,都冷漠可怕得很,哪裡願意幫他一句,連個動作也不肯。阿雪不敢說,因他沒讀過書,一個字都不曾識過。
到底不是個正常人。
阿雪屏息忍耐,等那人摸了許久,心滿意足了,他才敢逃跑,他狼狽地摔在地上,連頭也不敢回。
他只聽鋪子裡的嘲笑聲傳了很遠,直至有個聲音呵斥他們。
阿雪悶頭跑著,被人撞著,被罵了聲不長眼,好大聲響,引了別人張望是誰這般倒楣,攔了一頓臭駡。
不講理的人要抓住他,好罵出個道理來,臨到頭又萬分嫌惡,高高的牌坊在心中立著。
有人怪覺得可憐,略勸了幾句,說這孩子瘦弱不堪,少說上一句,和和氣氣便得了。
嘿喲!我呸!我家那幾個小潑辣就是小,也知道撞了人該說聲對不住!只有那外頭來的——她上下橫了一眼阿雪,「沒爹沒娘的,才不會對不住。」
「哦喲喲,越說你越得勁了,欸,你快道個歉,這事就這麼完了。」
阿雪木愣愣的,什麼話也不說,給人急得再三催促:「愣著做什麼!還不快說對不起,趕緊走了?」
他臉一白,喃喃說了聲道歉,十分拿不出手,這罵人的也頓時提不起勁了,嘀咕幾句,越想越氣。
阿雪走遠了還能聽到勸她的——「你生什麼氣,那地方出來的,無人教養,還指望是個什麼人才不成,到我們這村上別添惹出什麼風流事來,便是燒高香,祖上保佑了!」
「哼,依我看就該趕出去才罷,那姓陸的居然還要給他添戶籍,咱們這地雖小,但就一樣清白,百年沒出過這樣的人!」
「嘿喲喲,瞧你這說的,鎮上那妓館,你還能燒了不成?」
女人們碎嘴了幾句,阿雪靜靜聽了片刻,面紅耳赤,雙腿乏軟。避著人,往無人的小道上走。他走出經驗來了,大路人多,回頭指指點點他的人也多,回頭望望,再露出指點後的笑。
後來連院子籬笆外都有小孩好奇地張望,不過是東西倒地的聲響,明兒或許就傳出那陸照陽和新來的那個在屋子裡顛鸞倒鳳,白日宣淫。
話盡是讓他們都說全了,說過癮了。
阿雪是個新鮮物什,突然到了這太平小村裡,夾著不堪的驚天過往,突兀給人一個棒槌。
怎麼會有他這種被調教出來的玩意。
又嫌又惡,又奇又驚,乾淨的兒郎們多看一眼,家中父母就要尖聲訓斥起來,女郎們躲在門簾後,幫了下忙,那手帕子必定立馬要燒個乾淨,同時要對神仙念上幾句保佑,好像是亂了朝綱的妖精,只是這裡不敢稱朝綱,也沒妖精,是一塊再正常不過的小地方。
阿雪進了籬笆門,房子很小,陸照陽分了他一半的床,平日裡兩個人擠擠挨挨,往往要陸照陽讓出大半的位置來,可憐他那高個,得讓給阿雪。
他歪在床上,身體乏累,心道只睡一小會。待睜開眼睛,已是滿堂霞夕,阿雪一驚,從床上了滾下來,慌張站起來,才想起驚恐失落下還有一份事要做。他今兒原合計著出去再試著找點事做,陸照陽要他有自力更生的本事,因此這些時日他都去鎮上轉轉,看可有什麼活要他的。
只是成效不好,此間種種阿雪不想回憶。每晚躲著人,一想到那些話,就哭了幾次,幾次下來,找不到能幹的,就跟著陸照陽,遠巴巴綴著。
他總從陸照陽黑沉的眼裡看到些不明情緒。可恨他沒讀過書,不識字又不機靈,這些光怪陸離的東西,叫他一腳踏進來,沾了滿身的腥,這是什麼,那又是什麼,這話是如何意思,那些話又是如何的,他已然招架不住,兜來兜去,被撞來撞去,早看不見那眼神中的失望了。
陸照陽再不喜,但卻恪守承諾——既答應了人,留他下來,便不反悔,只有一樣,求這人不要添麻煩,也不要一件事也做不好。
可偏偏今日,阿雪既沒幫忙燒水,甚至外頭晾曬的衣服也沒收,這全是陸照陽囑咐過的,若他回來了,能做的,便幫忙做了。
阿雪白著張臉,急匆匆收了衣服,不會疊便一股腦塞進木櫃子中,心想著藏起來,待明日等陸照陽去了鋪子,再拿出來疊。
說到燒水,他又不知怎麼辦了。愣了半時,才想起自己是該去舀水。可水缸水沒了,得去外頭打水,村口有口井,家家都去,又能順帶著聊聊,井邊最多的就是各家的娘子們,一個個氣也不喘,通通兩下,扁擔一抬,就健步走了。
阿雪嬌,卻又不是正當的嬌,是一身好皮肉的嬌。
打水的事是怎麼也不肯幹的,稍稍一想,井邊的那些人,是吃人的怪物,他就再也不想出這門了。
也許他該雇個人,幫忙打個水,只要給錢就行了,只要給了錢,何愁沒人去做這些事?
阿雪急忙去屋裡翻出自個身上那點碎銀子,這是他身上僅存的一點家當,他都拿了起來,藏進袖子裡。
他提著桶,茫然地望著,事實上,也並沒有很多人一直關注著阿雪,有些甚至連看也不看,是他終於鼓著勇氣叫了幾聲,如同貓叫,那幾個大漢回頭啊了一聲,他倒把自個嚇了一跳。
阿雪磕磕絆絆地說,其中一名漢子問,那你要給多少?
他不知,沒數,實話說了,他總低著頭,那漢子明顯也不知這人如此,阿雪以為對方不耐,可再不打水回去,怕是陸照陽就要回來了。
他說就只有這些錢。
那漢子一瞧,便道:「咱們幫你打水,幹的可是力氣活。再者,誰家的水缸是一回就能打得滿的,你這點錢可不夠使。」
「那……」阿雪皺著眉,他只有這麼點錢了,不能花陸照陽的。
「你沒錢,咱們可是不幹的。」
「不要打滿,只半缸,這點錢也不成麼?」阿雪盯著手裡的銀子,急切地問,心裡卻有些不捨,若他能以己力打上水,這些銀子就能留下來。
「行了,逗他做什麼,吃酒賭錢輸了,打別人銀子的主意了?」
「這不是逗逗他,誰曾想真信了我們的話,這也太好騙了。」
阿雪抬頭,瞧見是其中一斯文人,見他瞧過來,便笑了笑,「你別在意,這夥人見你好欺負,說渾話,也不要什麼錢,我替你打了去。」
漢子們說:「不愧是讀書人,就比咱們會講道理。小郎君,咱們說笑的,你可別往心裡去!」
斯文人讓他們快滾,那些漢子嘻嘻哈哈,鬧將跑了。
阿雪聽到別人口中說他是讀書人,心裡便覺得讀書人果真都是好的,他沒讀過書,但幹過藏小書的事,他原本也是個想讀書的人,只是院子的主人不准他們識字讀書,他便只能看話本上的畫,有的只畫了鬍子的士人,又有畫美麗神女的,他就盯著那些畫,夢裡都笑了起來。
斯文漢子說自個姓陳,阿雪叫了聲陳郎君。
陳郎君問他叫什麼名字,阿雪回了。
陳郎君說:「你只有名字?姓什麼?」
阿雪說沒有姓。
不過倒很想說上一句,想姓陸。
他怕陸照陽,卻自然地賴上了人家,即使有時委屈生氣,阿雪也不知道這死心塌地的由來,愚笨的腦子裡只知要盡力活著了。
〃
陳郎君替他抬了幾桶水,來回幾次,直到水缸倒滿了,阿雪面紅,過意不去,覺得這陳郎君不似他人,是頂難得的大好人。
阿雪說要給他錢,陳郎君笑道:「咱們鄉里鄰里,不拘這些,以後你也別這樣,錢要仔細收好,若是給別有用心的人撞見,你這些錢不光被騙走,連水都沒了。」
阿雪聽了一段似懂非懂,陳郎君便知他腹中無一點墨,空白得可怕,都已是說明了,卻還是不明白。
也不知陸照陽這圖什麼。陳郎君此般疑惑。不過阿雪想他是大好人,倒不是錯意。陳郎君更願信自個的眼,也就想通了。一來,陸照陽與人本就不合,為人過分冷漠,有心人看不慣便說些風言風語也是有的,二來——陳郎君不著聲色地打量了阿雪一番,此人實在愚鈍,卻並非無可救藥之人,陸照陽大有可能心軟。
他讀聖賢書,雖與常人一樣鄙夷賣笑之人,但又懷有君子常說的憐憫之心,既然阿雪已經離開魔窟,那麼就是迷途知返,他幫助弱小又有何不可?
陳郎君問他,在這可待得習慣,阿雪歪著腦袋,不說好,也不說不好,沉默了下。
正當此時,陸照陽回來了。
他看向院中二人,向陳郎君點頭後,回了屋子,阿雪本想請他吃些茶涼涼再走,只是見了陸照陽回來,這會便顧不上了,陳郎君會意,叨擾已久,叫阿雪不要送。
阿雪回了屋子,陸照陽只偏了頭問他怎麼回事。
「我請陳郎君幫忙打個水。水缸沒水了。」
這話引得陸照陽回頭看他,阿雪又忙道:「我本想給錢的,沒想讓人白幫忙!」
「你給他了?」
「他沒要,說都是鄉鄰,不需要給錢。」
陸照陽嗯了一聲,阿雪奇怪他居然沒發火,一時反轉不過來,擱在平時,他要做了什麼事跟他說了,必定要被訓上一番,阿雪被說慣了,可偶爾卻覺得也沒多大錯,是他小題大作了,陸照陽訓多少,他仍舊是改不掉,照做不誤。
久而久之,陸照陽便懶怠說了,將阿雪扔至一旁,二人無緣無故,他做什麼好人?
「你不說我?」阿雪問。
陸照陽褪去上衣,露出精壯的身子,他每日都要換衣裳,扔進木盆中,當日就要洗。阿雪泛著臉紅,大著膽子道:「他還叫我以後不要這麼做,會被人騙。」
「是麼?」陸照陽神色冷淡,拉開櫃子,剛那被胡亂塞的衣服就倒了下來,阿雪臉更紅了,一把端起木盆,說要去洗衣裳。
他抬不動木桶,就拿木勺從水缸舀水倒進盆裡,一聽陸照陽腳步聲,埋頭將衣服搓洗得更厲害了。
他還是會洗衣裳的,這是他到陸照陽家來唯一沒出錯的事。
但洗個衣服的功夫,人就受不住,只覺得胸悶,頭暈眼花。
阿雪晾好衣服,跑進廚房邀功,「我洗好了,也沒破。」
「那。」陸照陽站在灶邊,讓他把菜給洗了。
阿雪拎了盆進來,蹲在陸照陽旁邊洗菜,一邊洗一邊哈氣,說冷。
陸照陽哪裡管這些,仗著血熱,冷秋裡還打赤膊。
阿雪洗了一遍,陸照陽瞥了眼說不乾淨,他又洗了第二遍,陸照陽還說不乾淨,他就有些不服了。
陸照陽燒著熱水,霧氣綿延地轉,剛擦洗過的身又滲了汗,正是燥的時候,阿雪洗了兩次,站著偏不洗第三遍。
陸照陽晾著他,已是極大的好耐性,換了幾年前的脾性便是不幹就滾,連個機會都吝嗇給。
「我說錯了?你那淘兩下的功夫就叫洗菜了?」
阿雪盯著腳尖,灰撲撲的,難看極了。
「你拎不動東西,又不會下地。這段時日,也找不到活,連最簡單的衣服不會疊,洗菜也是這樣。不過說你兩句,就委屈了?」
「我不會這些。我沒做過。」
阿雪幾下眼淚,著實煩人,陸照陽壓住火道:「這不會那不會,掉眼淚倒是勤快。」
陸照陽看不上他矯情姿態,只要說上一兩句不如意的話,他便掉眼淚,好似天大的委屈,不止在陸照陽面前,他在所有人面前都這樣,受欺負了就哭,找不到活幹也哭,說他一兩句還是哭。
眼淚眼淚,掉了那麼多便覺得萬分廉價。
他不會讓人覺得可憐,反倒是覺得可恨。
「別哭了!有誰在意你哭?你若待不下去就滾,滾回你原來的地方,那裡好吃好喝的,供你玩供你樂,你只需榻上一躺便齊活了!」
「我沒有!」
「沒有什麼?」陸照陽轉頭看他,淚珠子還往下滾,滾不盡,哭不盡,聲聲纏纏繞繞,極是惱人,惱動人的肝火。陸照陽不知怎麼,往日任他哭去,眼一閉,幹不了就叫他滾遠點閉嘴,落個清靜便是,就今日油倒了水,三年多沉寂的炮仗脾氣全冒了出來,他將阿雪往外拖著走,阿雪吃痛,手腕子感覺要被捏碎了,但顧不得疼,陸照陽是要將他趕出去了,阿雪哀叫一聲,蹲下身,求著別把他趕走。
陸照陽紅了眼,道:「不趕你走做什麼?教你白吃白喝,我這可沒什麼富貴日子,你不還想著那些錦衣玉食?既如此,我便當這個好人,送你回去不好!」
「沒有!沒有!我錯了,我洗,我洗,是我沒洗乾淨!是我錯了!」
阿雪往前一滾,被拖出了門檻,接著他使出力氣抱住了陸照陽的腿,他只會這麼做了,滿臉的汗,滿眼的淚,他怕極了,勾住陸照陽不讓他動,「你別這樣,別扔我,我怕,我真的怕——你要是不解氣,打我,抽我,怎樣都行!」
「我打你做什麼?」陸照陽停下來問。
阿雪拼命搖頭,死死扒住,又不說話了。
身體一顫一顫的,早是被嚇破了膽,陸照陽喝了一句抬頭,他不敢不照做,滿面可憐可憎的狼狽。
陸照陽嘆了口氣,只叫阿雪站起來,徑自回了廚房,阿雪不敢問,胡亂抹了兩把眼淚,也跟了進去,蹲回原處將每根菜葉都洗了一遍。
陸照陽突然開口:「你去買個雞蛋。」
阿雪抿唇,但站起身往身上擦手,聽陸照陽說:「你去東娘子那裡,不遠,其他人家不要去。」
阿雪說好,陸照陽又叫住了他,叫他等著。過會,塞給他幾枚錢,又拿了乾淨的布往他臉上胡亂擦去,便轉過身說走吧。
阿雪眨眨眼,心下平靜起來,又說了聲好,比方才大了音量。
他未見過東娘子,但陸照陽叫他去那,估摸這東娘子不像別個人,會無理為難人的。
這般想著,他放了心。
不多時,便有一名年輕女郎過來應門,「小郎君何事?」
阿雪伸出手,給她所有的銅板,輕聲道:「買雞蛋。」
女郎叫他稍等,過不久便拿了三顆雞蛋出來,阿雪急忙伸出手,緊緊地捧在手心裡。
女郎道:「有顆我送的,瞧你面色不好,正好今日家裡母雞多下了蛋,便送你了。」
阿雪靦腆地笑笑,一路走回家去。回家後,低著頭將手往前一伸,陸照陽也不問多餘的一顆怎麼來的,只接了過去,道了聲謝。
晚飯仍舊是簡單地做了麵食,阿雪胃口極小,常是陸照陽從碗裡分出一點來給他。今晚他碗裡還多了份蛋,陸照陽在他開口前就先堵住他話,生硬地叫他吃。
阿雪不敢多問,吃了一半,將蛋全吃了,肚子漲漲的,隱隱不大舒服。
陸照陽皺眉看他還剩了一點,阿雪低頭說:「我真的吃不下。」
「我知道了。」陸照陽道,「你無事便先去睡吧。」
阿雪不敢多言,他還未擦身,也不敢說要熱水,咬咬牙,便拿了院子裡的冷水簡單擦拭了下,打著抖鑽進了被子。他揉著肚子,好叫它不要那麼疼,但手腕子也疼,上頭掛了瘀青,他再次想起了方才暴怒的陸照陽,這一想又覺得眼睛一酸,阿雪趕緊擦掉,怕人聽見。
他這小腦袋瓜裡自打離開那逼仄的院子後,便塞滿了各式各樣的事,眼裡看見的,耳裡聽見的,都是不曾接觸過的新鮮物什。他人的醜陋骯髒,他瞧不明白,只好悶在心裡,像墊了沉沉的擔子,一條壓著一條,而他成了一個存擔子的地方,只知道有時會覺著莫名愁苦和酸意。
陸照陽發怒,讓他仿徨失措,一個勁地往自個身上攬錯,以為這樣或許對方就會減輕怒意,他是這般如此天真地想。
阿雪感覺無所適從,好像從頭髮絲兒,鼻子眼睛到腳趾間,都是怪的,在大太陽底下原形畢露。
說來到底,種種都變成了害怕、可怖。
最後迫使他成了不敢、不聽、不說之人。
門一響,阿雪趕緊閉上眼裝睡,陸照陽坐到床邊,伸進拽得緊緊的被子裡,拉出一條瘦喇的膀子。
阿雪僵著手,以為陸照陽要把他的手給砍下來,等了半日不見疼,就睜開眼,便見陸照陽要給他塗藥。
陸照陽彷彿後腦勺長了眼一樣,叫他醒了就別裝睡,「手抖來抖去,怕我發現不了你醒著?」
阿雪抿唇,只覺得不好意思,往外挪了挪,「你在給我塗藥嗎?」
陸照陽冷淡地給他看了眼手上的膏藥,細細地塗勻開來,阿雪的手指尖軟了下來,任他拿捏。
「我以為你要砍我的手。」
「你的手是金子?」陸照陽冷哼一聲,可讓阿雪到這今日的恐懼全消了,並不怎麼怕他了。
「陸——郎君……」
「嗯?」
「你別趕我走,成嗎?」
陸照陽停下來,阿雪慢吞吞道:「我知道強迫你讓我待在這,讓你很不開心,你說的對,我有點懷念吃穿不愁的日子,可我還是不想回去。我都出來了,等以後久了,我衣服會洗會疊,什麼活都可以幹,話也會說得很利索。你說什麼都行,我做錯事,你生氣就打我、罵我都成,就是不要趕我走。」
陸照陽收了藥,才說:「我不會打你。我沒那趣味。不過日後,你自個好自為之吧。」
阿雪道:「謝謝。」鼻頭一酸就埋進了被子裡。
「你想好要姓什麼了麼?」
「我,還不清楚。」
「罷了,問你也問不出什麼來。」
陸照陽站起身,阿雪看著他上了床,合上眼,不再說一句話。
阿雪還睜著眼,望了一會兒人,便突然想到陸照陽雖然做著打鐵的營生,常常滾汗,但從未在他身上聞到異味,相反甚是愛乾淨,便是讀書的陳郎君也比不過。阿雪曉得,看得出來,更有種種習慣上,行為上的不同,猜出陸照陽想必出身好,卻不知為何落到這步田地,他難不成是與自個一樣流落在外?
阿雪又想了想,否決這個想法,陸照陽不與他說,他猜也是沒用,這人從不說自個的事,早出晚歸,也就今日鬧了大了,才多說了話。這還是他倆頭次貼近,讓阿雪心裡有股熨帖。
〃
還剩下兩個雞蛋,阿雪本想表現一下,水燒開後就打了下去,應該是水泡蛋,蛋液四濺,一半落了地,一半進了滾燙的沸水,又一攪,蛋白四分五裂,只剩下蛋黃的固體悠悠蕩蕩。
阿雪很快地將兩顆蛋黃撈了出來,又仔仔細細將四散的蛋白也撈了起來。
他端上桌,陸照陽剛洗了臉,滿身的霜氣,見阿雪一臉討好相,站在一旁,只可惜這水泡蛋的的賣相還不如陸照陽做的。
阿雪強調說熟了,又給陸照陽遞筷子,他抿著嘴,可疑地看著碗中寡淡極了的東西,這寡淡相就如阿雪給人的印象,又淡又弱。
實在不像個正常的人。
陸照陽舀起蛋黃,一下口,蛋液便流了出來,他躲之不及,一下子流出了下巴滴在了衣襟上,阿雪漲紅著臉,忙挾了袖子往他臉上擦去,又擦衣襟上的,這下他的袖口也髒了。
「行了。」陸照陽皺著眉撥開他的手,阿雪揪著手,眼睛亂眨,這般模樣看在陸照陽眼裡,便知那阿雪又是嚇破了膽,不敢動了。
他難得解釋道:「無事,這是流黃的,不是沒熟。」
陸照陽敲敲桌子,嫌他站著礙事,趕緊吃。
阿雪坐下了,極小心地咬開,吸了一口,忍不住咂嘴:「好吃。」
陸照陽道:「不能咂嘴。」
「哦。」阿雪小心翼翼地又吸了一口,含在嘴裡小心地咽了下去,又忍不住咂嘴,趕緊張了嘴又立馬合上。隨後瞥眼陸照陽,陸照陽不想理睬。
飯後,陸照陽洗了碗,準備去上鋪子,阿雪站在門口看他,他問有事?
這孩子搖頭,搖了頭後又跟個木頭一樣傻愣著。
陸照陽走到門口,回頭說:「你今天去鎮上嗎?」
阿雪略略糾結,最後點頭。
陸照陽卻道:「你今天就在家待著吧。」
「要做什麼嗎?」阿雪問。
接著又趕緊說:「我會把衣服洗了,早上弄髒的,還有在你回來前會把熱水燒好的。真的。」
陸照陽說:「隨你吧,你不要裹亂就是。還有,你從今以後別再趁著我走了後又跟上去。」
阿雪道好,有些不大高興。
陸照陽走了,籬笆靜了,阿雪跑過去將籬笆門關好。過會,他趴在籬笆上看陸照陽有沒有走遠,人已見不到了,走遠了,他又想跟上去,便將籬笆門打開,摸了滿手的晨露,腳底下也浸了月下的露水,阿雪驚過來,將滿手的水擦了,又回去了。
他蹲在院子裡洗陸照陽的衣服,給他襟口搓得乾乾淨淨,又過了兩遍水,生怕洗不乾淨,這下半缸的水又沒了。
阿雪見水這麼快就要用完了,想不用幾天又要去抬水了,若是院子裡就有個水井多好,這樣就不需請人幫忙,也不必去外頭見那些人。
只是打水井需取得陸照陽同意,就在這想水井也是個夢。
阿雪頭次想要陸照陽打上那麼個井,有了這個多好呀,還不用跑個幾趟才放滿水缸。
他洗完了,將衣服晾在竹竿上,腰都快直不起來,緩了一陣才罷。
做完了後,發了會呆,又生出想去鎮上的念頭,可是去了做什麼呢?陸照陽不要他跟,鎮上的人又鮮有好臉色的,一見他這樣弱不禁風的,連個小娘子也不如。再問他會些什麼,他又支支吾吾答不上來,人家便會說你是哪裡來搗亂的?揮手就將他趕走了。
阿雪嘆了口氣,更是垂頭喪氣不說,又想到昨日那頓火,指不定陸照陽說到做到,不管他了。
他掰著手指頭想,還有什麼可做的,直到聽見外頭小童們嘻嘻哈哈的笑聲,他好奇地循聲,在籬笆邊上見到幾個小孩。原是秋天到了,拿了風箏來放,好大一條蜈蚣被放到天上,呼啦啦威風極了,在稀薄的雲上和鳥兒一起,騰起騰下,幾對足撥著淡雲,飛得越來越高。
阿雪羡慕極了,他和院子裡的人也這麼放過一個風箏,不是蜈蚣的,是個小小的,極平常的一個風箏,連個花樣也沒有,那是趁著富商去了外省,帶了別人陪,才剩下他們的,這才能偷偷弄個風箏回來。
光是拿銀子賄賂看門的人便花了許多,其實他也偷藏過錢,只不過如今都沒了,他被半路拋棄至此地,想必連東西也一同丟了,他倒是希望留著,一丁點也行,讓還被困在院子裡的人拿走。日後有條生路,去了外面不必走投無路。
阿雪閉上眼,紅了鼻子,想到或許這世上再沒第二個陸照陽能這樣收留人了,那些與自個同樣遭遇的,到時可怎麼辦?會被騙嗎?會落到更不堪的境地嗎?
他們連個字也不識,若遇不到好心人,是不是就會淪落到那些風月地方,可或許也是條出路。畢竟無需像現在這般,處處招人惡。
想至此,阿雪突然渾身發冷,扇了自個一下,罵道自己糊塗了,這些算來算去,又誰比誰好?
阿雪整個人都沉浸在巨大的一種傷感中。要是給陸照陽知曉了,必定會說他自個不知能做什麼,卻還想著別人。
阿雪決定咽下去,冷靜了一會。
他正自顧著想事,方才放風箏的小童們跑過來叫他幫忙,原來蜈蚣風箏掉進院子裡去了。
阿雪嚇了一跳,因村裡的一些小孩早被大人叮囑過,總繞著自個走。不想這幾個像是不知情一樣,還叫他哥哥。他從未見過如此乖巧的孩子,心裡一熱,說不出的感動,就如昨夜給他上藥的陸照陽,從沒讓他感到這麼開懷。
他立馬拾了風箏給他們,還被邀請跟他們一起玩,阿雪臉都紅了,激動得不知怎麼該好,慌忙說著我沒糖,不能送你們糖吃。
小童們被逗笑了,快點讓他出來一道玩。
阿雪跟著他們,到了湖邊,那地空曠,可以跑來跑去,讓風箏飛得更高。起先阿雪放得不好,小孩們就笑他,說風箏也不會,臊得阿雪不知如何是好。過了幾趟才在小孩們七嘴八舌的尖叫下,成功了一個,各個渾身一把汗,玩得跟泥人一樣,連哥哥也不叫了,只叫他阿雪。
阿雪一個激動跌進了湖裡,吃了一頭的水,狼狽地站起來,一邊摸臉一邊笑,又繼續跑起來瘋叫。
此刻阿雪心裡極為敞亮,許久未感到的快樂,連時間也忘了,只想著若是明兒、後兒,再後面的日日如此,該有多好。
他感到無比愜意,若是這樣,他便不用苦惱那些事,可正當他如雲端輕渺,便被一杆打落水裡,只聽見更為尖細的聲音罵著那些小孩:「尋了半日,可倒好,跟這人在一道,不怕皮膚爛了,生了病長了爛瘡!」
阿雪頭暈眼花,頭悶眼悶,又覺額上一痛,原是磕到了石頭,流血了。
岸上的小孩被教訓得一句話不曾講,那推他的女郎不知哪家的,瞪眼瞧著瘦巴巴的阿雪,一見這麼個大男人磕了,見了自個連屁都不敢放,居然還哭了眼,當下噁心滿貫,也不管動作粗俗,將孩子們都帶走了。
他渾身都濕了,覺得累,心上也說不出的冷,蓄滿了滿腔的悲。好一會才爬起來,一邊哭一邊抽搭,哭那好端端的夢就被打碎了,哭這蕭索的秋日,最後也不知道哭什麼。
陸照陽回了家不見阿雪人,當下便起了火。見著人終於回來,阿雪渾身狼狽,面上已是哭過一番,跟挖出來的泥人一般,陸照陽只好壓下火問,他這次又怎麼回事。
阿雪不敢說,又驚又怕,陸照陽逼問了幾次,才知道他跑出去玩,結果又被一個小娘子欺負了,被人推進水裡。分明自個占理的事,還成了罪該萬死了。
陸照陽將人給拎到房裡,扔了藥瓶子在阿雪懷裡,叫他收拾好,阿雪抽噎一會,只想連陸照陽都不想理睬他了。他上了藥,換了衣服,顫顫巍巍地去見了陸照陽,那陸照陽卻恨他這無比懦弱的模樣,連句話也懶怠再說一句,更是一句責備也無。
阿雪提心吊膽,想起早間答應的事一件未做,更不敢開口。至了晚間一場秋雨潑下,寒氣不竭,落在籬笆上,屋子也是冷極了人,他想到被雨濺的那片湖,他的風箏也落在那裡了。
見陸照陽吹滅了蠟燭,他趕緊閉上眼,只希望這雨這夜趕緊地過了。
可去了夢裡也不安生,哪都疼,一會受了驚,一會心思沉沉,一會冷風陣陣,一會隆隆聲響,這邊來,那邊也來,一隻大手捉住他的腳,捉住他的人,上下搖晃,左右開打。
忽然整個人魂沒了,嘴一張就吐了出來。
此後幾日都是不安生的妖魔景象。
阿雪病了,燒得厲害,也胡話得厲害。眼睜不開,也聽不見聲音,以為就剩下他孤零零地躺在這,眼角始終滲著淚。
陸照陽忙乎幾日,給阿雪熬藥、找大夫,不說那人睜不睜眼,身體也不爭氣,這會還哭了。一想這幾日不上工,那老闆又是如何抓著小辮子扣錢,滿嘴地胡吣,他人見了笑話又樂了幾日。
不出所料,現今又是一朝流言,說這陸照陽冷心冷面,不知掛了多少女郎的面子。現在為個東西卻是錢也不要,鋪子也不去,大夫還找了幾回。
陸照陽閉上眼,不與他們分說,只想讓這不省心的麻利地滾起來才是。
他推推阿雪的臉,冷硬道:「既然醒了就別裝死。」
阿雪眼睫微顫,才睜了眼,裹了一片淚下來,直愣愣地看著人,又忍不住皺起臉,猛地哭出來,這會哪裡想得到陸照陽實在厭煩他的哭聲,陸照陽被折磨久了,這會倒是計較不起來,叫他別哭了,帕子糊住阿雪的臉,哭聲才漸漸消下去。
陸照陽冷笑:「怎麼不哭了?」
阿雪趕緊搖頭,一搖頭眼前一黑,喘不過氣。
「行了!」陸照陽皺眉,「都跟你似的,連活都不要做了。一生個病要死要活,滿嘴胡話。」
阿雪不敢回嘴,這般沒用的模樣看在陸照陽眼裡,一點辦法也沒有,「不過幾個小孩,就傷心成這樣,又不是人都死絕了,不會打回去?」
聽到裡頭的冷意,阿雪心道,自己未曾這麼做過,反倒是不間斷地被打才是真的。說這些事,難保陸照陽不心生鄙夷。
陸照陽更是冷哼一聲,憶起以往,事事遵循著性子,叫人害怕,說他傲,目中無人,絕無此等人犯到跟前,他臉色一變,因阿雪想起陳年舊事,不免又想到別的,當下沒了好臉色。
阿雪不明,以為是因他哭,陸照陽才不爽快了,他屢教不改,多少讓人不爽。阿雪想讓他開心,因此說起風箏的事,跟那些小孩是如何相處融洽,又是如何突然受了刁難。
這些微不足道的小心思惹得陸照陽發笑,而對阿雪來說卻是極重要的,「你說就跟我給你上藥那般?」
「我會記一輩子的。」阿雪道。
陸照陽微微一動,心道此次就不為難他了,倒也不是一點可取之處也無。
阿雪又睡了過去,到了晚上才覺得好點,吃了藥又躺下,陸照陽說他那落戶的事已解決,「那我日後是不是就是良民了?」
阿雪以前連個戶籍也沒,那買了他的富商,在被父母出手後,那戶籍便不存在了,連個賤籍也沒。院子裡的人都是黑戶,又不識字,極易拿捏。
阿雪聽到這個消息滿心滿眼的熱,陸照陽還告訴他,日後便叫陸雪,阿雪一愣,不知該說什麼好,激動之餘抱住陸照陽,悶聲哭起來。
陸照陽立馬撥開他,叫人躺好,又告訴他一壞消息,原來是不肯讓他這麼不清不白的人落到這來的——但陸郎君熱心腸,咱們感動萬分,也不是這麼不講理的。陸照陽便知了,回去思了幾日,一想此事本無意,為何要管他人的死活,二想卻又被逼了回來,他早年性子雖渾,卻從不失信他人,他拿了銀子孝敬,又說不可,拿東西換了更多的銀子,才說可,獻了多少銀子才換了一張戶籍。
從此以後,這陸雪和陸照陽便是一根繩上的螞蚱,人們背後裡早已笑開了。
可偏巧這阿雪是個不靈光、不爭氣、可恨可惡的人。
陸照陽隱去笑,他將隨身的玉佩當了,此生再無機會給贖回來,頓覺索然無味,便離了床邊,阿雪仍沉浸在這消息中,更有從此以後隨姓了「陸」,恍然覺得是與陸照陽的長久緣分。
他見陸照陽面色冷淡,小心小意起來,問道:「是不是我又做錯什麼了?戶籍你不願意麼?」
陸照陽未回頭,但他聽出來話中的平淡,似乎這只是一件平常事。
「我很開心的,謝謝。」
「和我無關,你睡吧。」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死生(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9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死生(上)
阿雪又躊躇了,陸照陽握住他的手,在紙上寫下兩人的名字。
阿雪覺得手指頭快被捏斷了,捏得軟掉了,但又不覺得疼,只知道是化開成了別的,眼裡心裡只在陸照陽手底下一筆一字寫出的鋒利刀霜,將旁的陸雪二字也染上風雨同去的勁狀,即便配上陸照陽三個字也會不失了臉面,是能同高的了。
作者簡介:
喜食年上。腦洞是零錢罐,每天存一塊。筆名是一句話故事:在孩子的庭院裡和貓開宴會。
章節試閱
一
「姓陸的!」
有夥計見陸照陽來了,便開口高喊道:「你那小孩呢?」
「他日日夜夜地跟你,可累壞了人,你怎麼就捨得那一身細皮嫩肉,你好歹給一句話,憐惜一下,要不然——」
「怕是和別的人跑了!」
「欸喲!是這個理!」
說完,全都混帳般地哄堂大笑。
這些渾人瞧不得陸照陽這樣的人,皆因他們是泥裡跑出來的糙人,最嫌那陸照陽不搭眼的高傲氣,像面鏡子,倒把他們映襯得入不得尋常人的眼。於是便絞盡腦汁地想,這陸照陽憑什麼瞧不起人?憑什麼與他們不同?想著想著,他們便死心塌地地覺得同樣是個煙燻火燎、滿泥臭汗的人。...
「姓陸的!」
有夥計見陸照陽來了,便開口高喊道:「你那小孩呢?」
「他日日夜夜地跟你,可累壞了人,你怎麼就捨得那一身細皮嫩肉,你好歹給一句話,憐惜一下,要不然——」
「怕是和別的人跑了!」
「欸喲!是這個理!」
說完,全都混帳般地哄堂大笑。
這些渾人瞧不得陸照陽這樣的人,皆因他們是泥裡跑出來的糙人,最嫌那陸照陽不搭眼的高傲氣,像面鏡子,倒把他們映襯得入不得尋常人的眼。於是便絞盡腦汁地想,這陸照陽憑什麼瞧不起人?憑什麼與他們不同?想著想著,他們便死心塌地地覺得同樣是個煙燻火燎、滿泥臭汗的人。...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