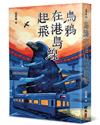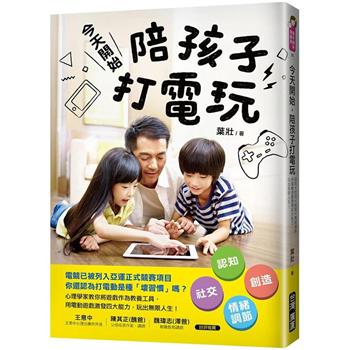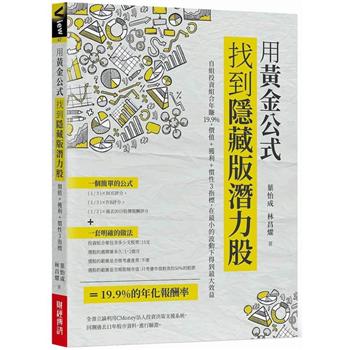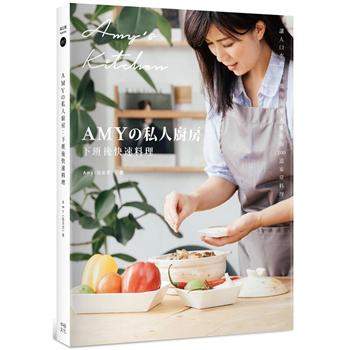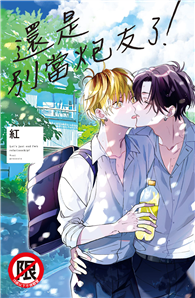序
海市
如何書寫香港,這對每個在地作者都是一個重要命題。
成長於斯是一種寫法,珠玉在前,如西西、也斯等作家,皆有佳構傳世。而作為外來書寫者,似乎又多了一重考量。縱觀一九三〇年代以降的南來作家。如出身上海的馬朗,其將「過去中國大陸春野上的經驗,與香港現實的經驗互相重疊 」。記憶與現實融合,造成兩種氣息截然的影像之交迭。徐訏居港三十年間,創作甚少涉及香港地景,亦以回憶重築鄉土書寫。即使關涉香港敘事,適夷等為代表的作家,則多以異鄉人自居,以故鄉記憶作為範式來選擇「觀看」視野。張愛玲書寫香港的《傳奇》數篇,卻可見頗具地方感的清晰表達。換言之,張氏言明「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進而打破橫亙在「外來者」與「在地者」之間的壁壘,實現對這座城市更為開放的文學建構。
程皎暘作品《烏鴉在港島線起飛》亦致力南來主題,近年而觀,可謂箇中新生佳作。其響見當代一端,亦稱為「港漂」。此詞為近年參考「京漂」、「滬漂」說法而盛行,就淵源而言,時見論議,不應者認為其含有自我異質化的傾向,似乎亦包涵了身分歸屬層面的焦慮。而就另一層面,「漂」含有了流動感的指涉,就人群的狀態而言,直觀且生動。程皎暘選擇的,大約是這樣一種角度。〈細雪〉與穀崎潤一郎名篇同名,卻另沽一味。不再流連於關西望族的舊日風土,卻聚焦香港聖誕時節人造雪景的幻境與北國凜冽現實的殘酷。空間的流轉伴隨著記憶痛楚的隱現,在此地亦在他鄉。〈深水炸彈〉亦然,如同〈細雪〉故事中都有一個在主人公漂泊生命中缺席的父親。不倫感情的歸宿,或許是對這種缺席的無聲反抗或代償。以中國人的生命觀,強調「安土重遷」、「葉落歸根」,都是植根於穩定大勢,在地理隱喻的層面,不期然地指向陸地,甚而北望於中原。〈另一種空間〉,卻由此提出問題:何談「另一種」?以及空間在哪裡?顯然,「漂」的生命取向,對北方的「來處」是不信任的,甚而失望的。那麼「漂」的終點,如非大陸,又當指向何處。〈金絲蟲〉在某種意義上,嘗試提供答案。港漂主人公在經濟大蕭條中被裁員,順理成章地離棄大城市的主流生活,進而實現成為小說家的夢想。 「在這炎熱繁忙的週一早高峰,我在傾斜入侵的日曬下,浸泡在司機手機裡不斷響起的語音信箱裡,倍感煩悶,直到四周高低起伏的大廈逐漸消散,車子進入跨海大橋,心情才舒暢起來。」這離棄的終點是一座「遠離市區的人工小島」。此處「島」的意象可堪回味。作為島城的香港,在漂流者的目光中已趨同於主流。遁逃方法是漂向另一座島外之島。而在這島上所發生故事,又近乎於魔幻與現實之間。主人公作為小說作者的身分,賦予其奇妙的後設意味,使得「虛構」本身的虛弱質地,也帶有一絲無奈的反諷。而值得重視的,是作者對於美涯灣作為「人工」 地景的強調。這幾乎構成了整本小說集的另一條閱讀的線索。或許出於對晦暗現實和人性的徹底失望,作者數度將救贖之光寄託於「人工」、「人造」等元素,但似乎由此指向了更深度的無望。首篇〈非人〉以AI孩童開宗明義,其後「易空間」、「水晶球」、「鏡面騎士」、「紙皮龜宅」、「完美戀人演繹館」無不以科幻甚至奇幻元素拷問人世間的煙火日常。而在其間,尤為矚目的是人類情感的肉身,也一次又一次暴露在人工智慧冰冷的寒光中,並被鞭打至於創痕累累。不期然,有一座海市冉冉而生,折射這城的另一種真相。
〈歲末夜晚的紅色氣球〉或許是這本書中最接近作者「本我」的文字。在清寒的夜晚,這城市有無數夜歸的人,他們或醉或醒,或靜或動,但心底總有微渺的願望,在不遠的前方,有個等待著的、溫暖而孤寂的守夜人。
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