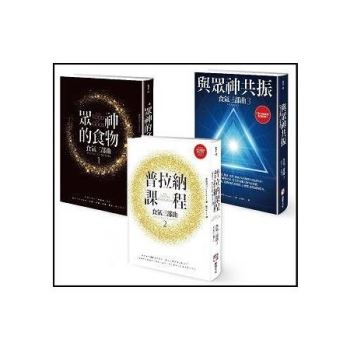本書由“人”的角度切入,就人的體氣、飲食、男女、家庭、社會關係、天人關係、歷史意識、思維模式、感性世界、德業擔當、文化實踐等各層面,說明古代文化在這些方面如何處理,其所形成之文化,在與世界其他文化的比較中,又顯示了甚麼型態、有甚麼優缺點。對於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出現的一些誤解,則正本溯源,說明其致誤之由來。對華夏文明在現代變遷異化後之再生的可能,也有一些期許。
本書採用學術講座的風格,有意保留講課的口氣和生動的文風,有“講”的現場感,比較親切、有趣。
本書的擬想讀者主要是青年,適合社會上一般讀者作為提高文化素養的普及性讀物;如果用作大學通識課教材,教員上課時可以參照其框架和基本內容,再加補充發揮;或者預先指定學生閱讀某些章節,上課時組織學生討論。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中國傳統文化十五講的圖書 |
 |
中國傳統文化十五講 作者:龔鵬程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5-1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中國歷史 |
$ 396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傳統文化十五講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龔鵬程
祖籍江西,1956年生於台灣,博士、教授。曾任報社主筆、書局總編、政府公職人員等等,創辦過三所大學、一些研究機構。兼通三教,博涉九流。著作六十餘種,主編圖書數百種。以弘揚中華文化為職志,現在大陸講學。
龔鵬程
祖籍江西,1956年生於台灣,博士、教授。曾任報社主筆、書局總編、政府公職人員等等,創辦過三所大學、一些研究機構。兼通三教,博涉九流。著作六十餘種,主編圖書數百種。以弘揚中華文化為職志,現在大陸講學。
目錄
序論
第一講 體氣:感諸萬物
一 不以形體為崇拜對象
二 不以人體為審美對象
三 不以心體為二元對立
四 知覺體驗與氣類感通
第二講 飲食:禮文肇興
一 上古文明的性質
二 特重飲食的文明
三 飲食思維的傳統
四 飲食文明中的人生與宗教
五 飲食文明中的政治與禮教
第三講 男女:人倫漸備
一 兩性關係的想像
二 姓氏與祖先崇拜
三 始祖高禖與上帝
四 性別思維的特色
第四講 封建:立此家邦
一 敬人神
二 立制度
三 厚人倫
四 辨中西
第五講 道術:內聖外王
一 封建禮教
二 郁郁乎文
三 禮本太一
第六講 天人:通乎神明
一 特殊的神人關係
二 非超越性的天帝
三 非奉誡待救的人
四 自然自在之天道
第七講 王官:理性的禮制社會
一 諸子出於王官之學
二 王官本於宗法禮教
三 理性化的支配型態
四 社會變遷下的官學
第八講 史學:史官與歷史意識
一 “舊法”世傳之史
二 舊法世傳之“史”
三 舊法“世傳”之史
四 歷史性的思維
第九講 用思:思維模式與方法
一 思維的模式
二 思維的方法
第十講 抒情:氣感愉悅的世界
一 風氣聲樂以生萬物
二 聲歌舞踴以成君子
三 君子興詩感情成樂
第十一講 憂患:德業政治的擔當
一 天下:受命於天的帝國
二 革命:應順於民的政權
三 國家:參錯於家族的邦
四 治國:異於家政的國務
第十二講 周公:文化實踐的聖王
一 思想史上的周公
二 “軸心期”之謎
三 集大成的創制者
四 中國觀的確定者
五 禮樂文德的教化
第十三講 畫歪的臉譜:孟德斯鳩的中國觀
一 想像遠方的“異類”
二 貶損“異類”的道德
三 中國國情特殊論
四 亞洲社會停滯論
五 中國觀的新典範
六 精神發展的譜系
七 孟德斯鳩在中國
八 由歷史發現歷史
第十四講 由法律看西方對中國文化的認知
一 西方的中國法律觀
二 總評:中國法律之性質
三 分論:法律的實施狀況
四 超越偏見與誤解
第十五講 華夏文明的異化與再生
一 演化、變化、異化:文明轉變與發展的模式
二 變動中的文化:當代中國的文化處境
三 流動的傳統與再生的文明
四 大陸、台灣、海外:全球化與華夏文明的新動向
後記
第一講 體氣:感諸萬物
一 不以形體為崇拜對象
二 不以人體為審美對象
三 不以心體為二元對立
四 知覺體驗與氣類感通
第二講 飲食:禮文肇興
一 上古文明的性質
二 特重飲食的文明
三 飲食思維的傳統
四 飲食文明中的人生與宗教
五 飲食文明中的政治與禮教
第三講 男女:人倫漸備
一 兩性關係的想像
二 姓氏與祖先崇拜
三 始祖高禖與上帝
四 性別思維的特色
第四講 封建:立此家邦
一 敬人神
二 立制度
三 厚人倫
四 辨中西
第五講 道術:內聖外王
一 封建禮教
二 郁郁乎文
三 禮本太一
第六講 天人:通乎神明
一 特殊的神人關係
二 非超越性的天帝
三 非奉誡待救的人
四 自然自在之天道
第七講 王官:理性的禮制社會
一 諸子出於王官之學
二 王官本於宗法禮教
三 理性化的支配型態
四 社會變遷下的官學
第八講 史學:史官與歷史意識
一 “舊法”世傳之史
二 舊法世傳之“史”
三 舊法“世傳”之史
四 歷史性的思維
第九講 用思:思維模式與方法
一 思維的模式
二 思維的方法
第十講 抒情:氣感愉悅的世界
一 風氣聲樂以生萬物
二 聲歌舞踴以成君子
三 君子興詩感情成樂
第十一講 憂患:德業政治的擔當
一 天下:受命於天的帝國
二 革命:應順於民的政權
三 國家:參錯於家族的邦
四 治國:異於家政的國務
第十二講 周公:文化實踐的聖王
一 思想史上的周公
二 “軸心期”之謎
三 集大成的創制者
四 中國觀的確定者
五 禮樂文德的教化
第十三講 畫歪的臉譜:孟德斯鳩的中國觀
一 想像遠方的“異類”
二 貶損“異類”的道德
三 中國國情特殊論
四 亞洲社會停滯論
五 中國觀的新典範
六 精神發展的譜系
七 孟德斯鳩在中國
八 由歷史發現歷史
第十四講 由法律看西方對中國文化的認知
一 西方的中國法律觀
二 總評:中國法律之性質
三 分論:法律的實施狀況
四 超越偏見與誤解
第十五講 華夏文明的異化與再生
一 演化、變化、異化:文明轉變與發展的模式
二 變動中的文化:當代中國的文化處境
三 流動的傳統與再生的文明
四 大陸、台灣、海外:全球化與華夏文明的新動向
後記
序
序論
坊間談傳統文化的書汗牛充棟,但本書與眾不同,別有立場與方法。
一、立場
我是個生在台灣的江西人。傳統文化,本來在我幼時的生活中,就是街坊鄰里的揖讓進退、閒話桑麻,是生活裡具體存在著的體驗。人人悲喜愉泣,俯仰於斯,誰也很難說甚麼是傳統甚麼是“我”,傳統並不是“我”之外的一個東西。
可是據說社會進步了,傳統(其實也就是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生活)也就要拿來檢討檢討了。我們,於是就站在傳統之外,對它品頭論足了起來,覺得它好,覺得它壞,覺得它有精華也有糟粕。
那時,台灣政府正在推動現代化,而反對政府的自由派學者則更為激進地主張現代化,揚“五四”之餘焰,為時代之鼓吹。不贊成如此激進現代化者,便漸漸形成了一股被名為文化保守主義的陣營,與之交鬨,史稱“中西文化論戰”。但其實,無論是講心性論的當代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或言超越前進的胡秋原,大抵也只是說傳統文化亦有優點,不可徑棄而已。由時代的大趨勢上看,政經社會體制的改造,已重新創造了一種新的生活,那原先與我們生活生命相聯結相融貫的傳統文化,早就渾沌鑿破。新時代的哪咤,正在剔骨還父、割肉還母,期望新的蓮花化身。故僅餘的那幾聲文化保存之呼喊,聽來宛若驪歌。雖然情意綢繆,矢言弗忘,可是行人遠去,竟是頭也不回的了。
然而歷史如長川大河,從來不會一瀉入海,總有曲折縈迴。台灣的“中西文化論戰”烽火未熄,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倒已是遍地硝煙了,批孔揚秦,其勢既遠勝於“五四”,亦非在台倡言現代化諸君所能望其項背。此時,無論從政治策略或文化需要上說,台灣似乎都應起來保衛傳統。於是,成立孔孟學會、發起文化復興運動、中學生都要讀《文化基本教材》(也就是四書,以《論語》、《孟子》為主)等等,乃蔚為新的人文景觀,與政經體制之現代化“並行不悖”起來了。
五六十年代“從傳統到現代”的命題,遂漸次轉變為七八十年代的“傳統與現代”。前者是要揚棄傳統,後者則想融合並行之。但其融合之道,乃是以新時代之現代化要求為取捨。故金耀基曰“我贊成現代化,但只有在它不妨害現代化發展的前提下贊成”(《中國現代化的航向》序),文崇一曰“把傳統和現代劃為對立兩極,這正是早期現代化討論所犯的重大毛病。其實,兩者是相互為用的,好的傳統可以幫助現代化,壞的傳統可以阻滯現代化”(《現代化的模式在哪裡?》)。也就是說:傳統文化是為現代化大業服務的。凡不符時代之需求者,皆宜棄去,如同啃不動的雞骨頭就應該吐掉那樣。
我成長於以上這個社會脈絡中,親身經歷了五十年來“傳統/現代”這些論題的爭論與發展,感慨萬端。然此處非發感慨的地方,故謹綜述我主要的觀點如下:
“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這個題目中的A、B兩項,原本就是全然相斥的關係。因為“現代化”從定義上就是說一個社會要拋棄傳統以轉型成現代社會,傳統文化乃是現代化之障礙,是需揚棄之物。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我國走的都是這個路子。
把兩者解釋為非相斥關係,是修正現代化理論者的傑作。這些人都是捨不得把傳統文化丟了的,所以各自發展了一些論述策略,欲修正現代化理論。
其一是說:社會固然要現代化,但傳統文化也有好的一部分,可以保留,不必倒澡盆水時把嬰兒也倒了。因此,此一派便有“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論”、“現代社會仍須講倫理道德論”、“傳統文化不礙現代化論”、“以傳統文化為中國特色之現代化論”等說。其二則稱:傳統文化其實無礙於現代化,也可開展出現代化。歷史上未見開出,並不代表它在質性上不能開,只要經過“良知的自我坎陷”等加工,它也是能開展出自由民主科學的。此說已較第一路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二者不僅非相斥關係,更是同一關係。第三說比第二說還要強勢些,謂傳統文化可以積極促進現代化。80年代“東亞儒學與經濟發展”的論調即屬此,認為韋伯講錯了,儒學也可以發展資本主義,且可能比西方老牌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更好。
這些修正主義的基本問題是:都不敢攖現代化之鋒,都承認現代化的價值與必要,所以要以傳統文化無礙於或有助於現代化為說。換言之,看起來是傳統文化的護衛者,其實是拉傳統文化去做現代化的拉拉隊。傳統文化有沒有價值,要以現代化為標準來估量。既如此,這些修正論者又怎麼可能真正動搖、修正得了現代化論?傳統文化不正透過現代性的價值重估而被揚棄被轉化了嗎?現代化論者對此類說法嗤之以鼻,良有以也。
因此,這些修正論都是虛軟的論述。真正要面對現代化理論,是要問:現代性真是種好東西嗎?現代社會真是人所需要、符合人性的嗎?我們犧牲文化傳統以追求現代化,值得嗎?亦即:現今我們需要的,不是追求現代化而是批判現代化。
自有現代化,即有批判它的思潮。20世紀初,西方文學藝術上的現代主義,便不是教人去追求現代,而是要揭露現代人奇特的精神處境,例如喪失了信仰、離開了家庭、活在科層體制和都市水泥叢林中、人與人的關係疏離而陌生、孤立的個我遂成為失落了意義的無根浮萍等等。厥後各派理論奇峰疊起、賡續發揮,不勝枚舉。如生態論者,大力批判現代社會的機械宇宙論、竭澤而漁的發展觀、宰制自然之科技工業等,形成了自然生態主義。哈貝瑪斯認為現代社會的理性觀,只是工具理性之擴張,但價值理性、道德實踐理性明顯不足,故提倡溝通理性以濟現代化之窮。丹尼.貝爾講後工業社會,則是說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存在著內在的文化矛盾:它由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所促動,可是發展下來,卻成為刺激慾望、鼓勵消費、消耗資源的型態,與新教倫理的入世禁慾精神恰好相反。故後工業社會所應強調的,不再是現代性,反而是宗教精神。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則全力去瓦解理性所倚賴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二元對立的形上學。其他批判現代社會中科層宰制、科技災難等,林林總總,實已蔚為大觀。至於馬克斯.韋伯一路思想,包括後來的世界體系依賴理論、全球化理論,更都指明了東亞國家之現代化並非其文化內部產生了變遷的需要,而是複雜的國際因素使然。
對於這些學說,我們也均予以介紹過,或批發,或代理,或零售,各有名家,但依樣畫葫蘆,學舌一番而已,殊少抓住其總體精神。總體精神是甚麼?就是對現代文明的不滿,而籌思改善之道。
我們的情形恰好相反,我們對現代文明是豔羨的,希望自己能早日擁有這份(西方人大力抨擊唾棄的)現代文明。所以包括那些批判現代性的學說,我們都把它當成西方現代文明來擁抱,以促進現代化。
這種總體精神方向上的差異、文化處境上的不同,也讓我們根本無法體會到:傳統文化之不同於、扞格於現代文明之處,或者才正是它有價值的所在。相對於二元對立、人天破裂、宰制自然的形上學,中國本來所講的天人合一、陰陽相濟,不就是當代西方批判現代的生態自然主義者所想要發展的思想嗎?相對於現代社會張揚工具理性,而道德理性、價值理性不足,中國原本所強調的倫理精神,不是恰可藥此頑疾嗎?過去被認為是封建、宗法、保守、落伍的那些東西,透過西方後現代情境中一些思想的反思,不是已讓我們驚覺到中國傳統文化其實含有豐富的“先後現代性”(pre-post-modernity)嗎?
如此說,當然不是挾洋以自重,而是要告訴仍在講現代化的先生們:現代化是落伍的論調,現代社會是有缺陷的居所,現代文明是要批判超越的。批判並超越之,其資源就在中華傳統文化中。
二、方法
但由於現代化運動推動已及百年,政經社會總體已遭改造,我們事實上都在過著一種新的生活,器用層面、制度層面、精神價值層面均已發生了具體的文化變遷。
時至今日,老實說,中國在感情上誠然仍是中國人的家園;但在理解上甚或精神旨趣上,當代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其心靈的故鄉,卻大有可能不在中國而在歐洲、在美國。除了技術器用層次、制度層次之外,在精神、信仰、知識層面,也早已離開了中國。
以哲學為例。目前整個中國哲學研究,因對傳統已極隔閡,對文獻又不熟悉,對其美感品味亦不親切,對古人之人際相應態度也甚為陌生,故研究已導向一套新的典範,研討的問題和接受答案的判準也改變了。幾乎所有人都只能採用西方哲學或科學的思考方式、觀念系統、術語、概念來討論中國的東西。碰到這個新“範式”所無法丈量的地方,便詬病中國哲學定義不精確、系統不明晰、結構不嚴謹、思想不深刻等等。
這樣的研究,看起來頗有“新意”,論者亦多沾沾自喜。但實質上是甚隔閡、甚不相應的,令我這種讀者讀來頗有聽洋牧師講說佛經之感。
可是學界仍不以此為警惕、仍不滿意,仍在覃思中國哲學應如何現代化。但依我觀察,無論是就哲學這門學科的內涵與外延之認定,或由我們討論哲學的方法等各方面看,中國哲學研究之現代化,可說早已完成了。目前已不會再有人用傳統的表述語言、思維工具來討論“哲學”了。談哲學的人,對於中西方哲學,並不視為不同的兩種東西,而覺得它們都是“哲學”,也都可以用同樣的表述、思維方式、關心方向去要求它。
許多人把西力東漸,中國人開始接觸並學習西洋哲學思想的情形,模擬為魏晉南北朝佛教之傳入中國,並認為目前的主要課題,即在於“譯經”、在於有系統地介紹西學、在於消化之。但實際上,現在的情況與佛教傳入中國之際是不同的。佛教進入中國時,中國人對佛教無知,故以其所知、已知之儒道思想去知之,此稱為“格義”。現在卻往往是對中國哲學一無所知,故用已知之西方哲學來說明未知的中國哲學。這種情形,與“格義”雖完全一樣,但卻掉轉了一個方向。
如此反向格義,確實也能令研究中國傳統學術者眼界大開,使得中國傳統思想,在西洋哲學觀念、術語、理論之參照與對比之下,讓現代人更為了解。而且原先中國所無之各色理論譯述介紹進來,豐富我們的文化、開拓我們的視野,也是頗有功勞的。正如中國菜固然佳妙,但外國烹調亦自有其傳統、有其特色。異饌者不同味,自應介紹來令國人也都能嚐嚐。國人之所以負笈西方,習其烹飪之技者,亦以此也。海通以還,西餐東來,西班牙、意大利、法蘭西、俄羅斯、印度、緬甸、泰國,殊方絕域之異味佳餚,畢陳於我中華,正賴於此。吾輩亦因此乃得大飽口福、大快朵頤。因此,除非是口味格外古怪、別有胃腸,相信沒有人會對西餐東來抱持反感,堅決不吃洋餐,且批評西餐東來遂令我華人口味墮落,不再能欣賞中餐之美了等等。
這些道理是不待辯說的。但是,假如現在做中餐的師傅只能用製洋餐之方法去烹調,不會中菜的刀法、不能用中式廚房、不擅鍋鏟炒氽之技,而皆僅能以煮意大利麵之法煮麵,然後說此即中華古麵式也,您以為如何?
西力東漸以來,中餐是少數尚能維持其風味與傳統的領域,尚未遽遭異化。哲學研究若不想繼續被異化,實不妨參考中餐館的存續發展之道。
中餐各系菜色,如淮揚菜、川菜、廣菜、魯菜,在西力東漸,西餐洋食來挑戰時,採取甚麼方法呢?是用西方觀點與方法來炒中國菜嗎?是通過理解西方烹調,以求“中西會通”嗎?是以西方菜式為“普遍菜式”,而要求中國菜據此為標準嗎?是據西方菜式以評價中國菜嗎?又或是以西方做菜的歷史為發展階段來解說中國烹飪史嗎?
顯然都不是!在討論烹調時,若有人如此主張,一定會令人笑破肚皮。可是,在談到中國哲學時,卻恰好相反。人人似乎都覺得非用西方觀點與方法來解析中國哲學不可;非通過理解西方哲學以求中西會通不可;非說哲學就是哲學,無中西型態之不同不可;非說中國哲學以西方哲學衡之,有邏輯性不足、體系性不完備、概念不清楚等毛病不可;非用西方上古中古近代或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等發展階段來解說中國哲學史不可……不如此,學界就覺得你保守、無新意、不預流。因為整個潮流正是如此的,因此誰也不覺得如此甚為荒謬。
中餐則完全不曾採取這種方式,而只是平實地由其本色菜法中推陳出新。參酌西餐之處,亦非沒有。例如進餐時的情調氣氛、餐點的佈置陳設、餐廳的花飾搭配等,盡可採酌西式。某些西餐之用料或是烹調技法,也不妨擇用。如乳酪起司的運用、做酥皮湯、用奶油煎菇之類。但這些都是在中餐的基本法式中參用的。此外皆以本門刀法、火候、工夫、用料等等為主,研練而推出新款。
西方哲學之發展,何嘗不是如此呢?當代諸哲學新流派,誰不是通過重讀其哲學傳統,以發展出新理來?為甚麼西方哲學不以用東方觀點與方法解釋西方哲學為時髦,不強調要通過理解東方哲學以求中西會通等為職事,我們卻必須以此為樂?
面對這樣的窘境,豈不也應像中餐或西方哲學那樣,由其古代及中古哲學中不斷發展出新的哲學理論與學派,不斷對其傳統做反芻與反省;然後,再以傳統的或新發展出來的理論、思致、方向、形態為“已知”,去觀看對方,發展我們對世界的解釋,一如西方哲學家以其傳統的或新發展出來的觀念及方法來解釋世界那樣。唯有如此,東西兩方才能共同結構成一個對話的情境。否則,即只不過是一方發聲,一方聽受之、學習之而已。
所以,中國哲學在現代的道路,就在於應切實反省過去不恰當的“現代化”作為,老老實實“歸而自求”,好好清理中國的學術傳統,勿徒以他人之眼光視己,亦不當自慚形穢,認定老幹已無法在現代開花,非得“接枝”或“變種”不可。如此方能使中國哲學在現代社會重新出發,重新被認識。
換言之,真正懂得吃中餐的人,大抵也才能懂得或欣賞西餐,既不會用製葡國雞、烤馬加休魚的方法及口味來要求廚子依其法做武昌魚,也知道武昌魚須如何處理才能真正讓湖北佬認為道地。至於專治西庖者,當然也同樣會有此態度。諸君皆知味者,必不以吾言為河漢!
三、體例
由於認定了批判並超越現代化之資源就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在研究傳統文化時,又不採用以西餐方法來烹調中國菜之模式,所以本書之論次有縱有橫。
縱,是指章節次序的安排。全書由中國人對“人”的基本認定講起,故第一講為體氣。有此體氣,就有生命存養的問題,故第二講說飲食。有人,人要生存下去,就又有男女婚媾之事,故第三講談男女。有男女夫婦,便會有家庭、成社會、建邦國,而中國在這方面最著名的即是封建,所以接著第四講論封建。封建既關聯於家又關聯於國,封建之禮教,既用以修身又用之治國,內聖外王通為一體,《莊子》所謂古道術,或《大學》所述修齊治平之道,都是這樣的格局,故第五講明道術。道術不僅要通內外,還希望能究天人,於是第六講論天人,說明中國人與古希臘古希伯來人不同的天人關係。究天人之際以後,當然仍得通古今之變,是以第七、八講談王官之學的內涵與流變。此一變,亦是先秦學術發展之關鍵,而且“舊法世傳之史”所關聯的史官與歷史意識,乃是中國社會與中國人意識上迥異於古希臘古印度之處。講完歷史意識,接著第九、十、十一講就接著闡明中國人思維與心理之特點,論思維模式、抒情感性與憂患意識。孔子曾讚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有憂患意識才有德業之擔當,有此擔當,才能有文化實踐的願力,故第十二講便以周公為例,說這樣的聖王如何開中國的禮樂文德之教。
以上十二講,選的材料、引述的史事,都在孔子以前,也就是春秋前的中國傳統文化狀況。描述中國這個文明,如何在飲食、男女、用思、抒情等各方面建立其面貌、發展其文化方向。依我看,中國傳統文化之大綱大維,大抵在那時就確定了,後來老子、孔子以述為作,只是踵事增華,並非變本加厲。因此把源頭說清楚了,嗣後的發展也就弄明白了。
今人對傳統文化當然頗不明白,故批評東批評西、說三道四,自以為居高臨下,可以揀擇區判其到底是糟粕還是精華。可是今人常不知自己所用以批評傳統文化的那些觀點和語詞,往往只是拾人牙慧,學著洋人在說話。因此第十三、十四講著重說明這種中國觀是怎麼形成的。十三講,以孟德斯鳩為中心,介紹歐洲從崇仰中國文化到鄙夷的過程,論析中國國情特殊論、亞洲社會停滯論、中國禮教不如歐洲法制論等論調之內涵及其訛謬。十四講,再以法律為例,說明西方對中國法制體系之誤解。兩講互相印詮,一從某個人的主張說,一從某個領域的認識說,其餘即可以隅反。
這兩講是“破妄”,前十二講是“顯正”,最終一講則是結語,傷華夏文明之異化而冀其再生也。
本書縱的條理,大約如此。橫的條理,則是指本書每一講主要都採取一種橫向比較之論析方法,具有比較哲學或比較文化史的意味。
第一講,由比較中國人的身體觀如何不同於古希臘古印度,又不同於佛教希伯來宗教開始。第二講,論中外飲食思維之不同如何構建了不同的文明。第三講,論在性別思維方面中西方有甚麼差異。第四講,論中西封建之殊,及因封建倫理形成的中西文化之分。第五講,論關懷型文化和西方驚異型知識系統的差別。第六講,論中西方不同的神人關係、天人關係。第七講,辨明周代文官制度為何已是理性的法制型社會。在歐洲,此等社會之出現,乃是工業革命以後的事。第八講,論中國人歷史意識與希臘印度之不同。第九講,談中國人思維方法之特點。第十講,論中國人如何興於詩、成於樂,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降“言辯證成”的教育體系有何不同。十一講,比較中西方群體組織之歷史與觀念,說明其政治經濟思維上的差異。十二講,反對軸心時代(Axial Period)的說法,辨明中國觀與一般民族自認為居住在世界中心的態度有何不同。每一講都對比中西,旁及印度蘇美希伯來,以見優劣。
我從來不假撇清,騙人說我的研究是客觀中立的云云。人文研究,哪有中立客觀這回事?由於人文研究本質上乃是在研究價值,價值必然涉及判斷,必然會有取捨,大部分更關聯著興趣、愛好、習慣、美感等等。我的比較,旨在說明中國文化為甚麼好。而方法便是藉由比較來看清中國究竟與其他文明有何不同,此種不同為何又不只是不同,更可能具有價值上的勝義。
這是我的目的,當然也就是我的偏見所在。讀本書者,敬祈留意,勿被我的偏見所惑。
三四十年前,初讀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便萌發了也要寫本中國文化史的念頭,即或寫不成,也準備以文化史為此後治學之領域。這當然是年少輕狂時的呆想,但未嘗沒有些俠義心腸。古詩《獨漉篇》云:“雄劍掛壁,時時龍吟。不斷犀象,羞澀苔生”。在我看,中國文化現今就彷彿這柄原是神兵利器,可以斬犀斷象的寶劍,無端遭了冷落,瑟縮在牆角裡生苔長蘚。美人落難、明珠蒙塵,皆是世上大不堪之事,非由我出來搭救不可。
懷此呆想,遊於上庠者亦數十載矣。解人頗不易得,而我自己對文化史的創獲竟也有限,年光飄忽,不免神傷。曾於1983年試講此課於台灣淡江大學,並動手寫了一部講稿。對於文化史之範疇與研究方法,粗有釐析;對於中國文化之分期與變遷,略有衡定。後卻不能終篇,殘稿輯入業強版《思想與文化》中。當時主要氣力,用於探討文化變遷。專就周秦之際、漢魏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晚清民初等幾個關鍵的變革期抉微闡幽,欲通古今之變,並為“五四運動”以來之文化變遷找到些對比勘照的模型,以經世濟民。所以文化史雖未寫成,對那幾個變革期的研究,卻令我辦了不少會議、寫了不少相關論文。近年逐漸輯刊的《漢代思潮》、《唐代思潮》、《晚明思潮》、《清代思潮》,大抵就代表了這一階段的產物。
1991年以後,我涉世歷事越來越雜,又是公職,又是辦學,又是社會活動,文化史的寫作遂越來越不可能了。但任公職、辦學校等經歷,對我的文化認知卻也不無助益。因為我早期所論,其實只是思想文化之史,於文化之制度與器用層面,研究不免粗略。正因為有此一段涉世歷事的經驗,才能深入了解典章制度及人倫日用是怎麼回事。1997年我出版的《文化美學綜論》,即可以顯示這個新的方向,欲由生活世界重開禮樂文明。
可惜辦學實在太忙了,辦了南華大學之後又辦佛光。到2003年,我校長任期屆滿。為了選新校長,董事會的行事引起了一些非議。我在爭鬧中開始寫《中國思想史》。事情鬧了幾個月,我也就草成了幾十萬字。在胡適、馮友蘭、勞思光、牟宗三諸前輩之外,另闢蹊徑,由上古黃帝開始講起,寫到了周公。此下因為要寫老子、孔子,有些畏難,才暫時先擱下了。
適巧當時北大湯一介先生主辦蔡元培、湯用彤兩講座,邀我赴講。於是就把稿子的前四章(言、象、教、字)拿來講了。合併舊作論文化符號學者數篇,輯為《文化符號學導論》,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北大的講會,聽講者甚為熱切,不覺竟感染了我的情緒,所以就趁勢請了長假,住到北大,以避囂塵。溫儒敏先生怕我太閒了,即邀我為學生講中國文化史一課。一切都是如此當機、如此順緣,實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就把其餘的稿子略作修整,一一宣講之。如此講了兩過,並在珠海聯合國際學院也講了一次。學生反應甚佳,以為前所未聞。溫先生說:那就出書吧。本擬以學生錄音整理為之。因我事忙,一直無暇核校,所以最終還是用了舊稿。原稿本是思想史,改名文化史,不盡妥切,故僅稱為中國傳統文化十五講。
為甚麼本來是思想史而居然可稱為“傳統文化十五講”呢?
我有一妄見,謂邇來講中國哲學的先生們,重點只在心性論與存有論,其餘各種思想多不注意。論思想,又只注重一些關於道、氣、性、理、仁、心等的抽象概念,對這些觀念是在甚麼樣的人文生活場域中浮顯出來,卻欠缺具體的了解,也不明白這些觀念和具體的人文活動有何關聯。以致哲學研究常只是抹去時空的概念編織,用沒有時空性的知識框架去討論活生生的歷史人文思想活動。而且他們往往是概念太多而常識太少,對整個文化的基本性格捉搦不住,只能孤立而抽象地談天道性命等觀念,所以這種危險就更為顯著。我寫思想史,前面本來就為了力矯此弊,所以作了許多類似文化導讀的鋪墊,希望讀者能明白中國哲學是在一種甚麼樣的文化中生長起來的。這一部分,抽出改稱為“傳統文化十五講”,豈不是因緣巧合嗎?
以上是說緣起,具體談到此書的內容,則另詳序論。本書在寫作時,綜攝了許多前輩與時賢的見解,但因起草時已處在風波紛擾之中,此後數年又浪跡禹域各地,無法檢書核查,故亦不及一一註明。而綜攝之後形成的我的見解,又不免有許多疏漏,這些,都是要請讀者見諒的。從前《碧岩錄》曾說道:“大凡扶持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眨眼的手腳,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捲舒齊唱、理事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著,建立第二義門,直下截斷葛藤。”我確有殺人不眨眼的手腳,此書卻未能立地成佛,並且只是權說,意在接引,故未極理趣使然,識者鑒之。最後,要謝謝溫儒敏先生和艾英,他們通讀數過,且提示了許多修改意見。
2006年處暑
於北京小西天如來藏
坊間談傳統文化的書汗牛充棟,但本書與眾不同,別有立場與方法。
一、立場
我是個生在台灣的江西人。傳統文化,本來在我幼時的生活中,就是街坊鄰里的揖讓進退、閒話桑麻,是生活裡具體存在著的體驗。人人悲喜愉泣,俯仰於斯,誰也很難說甚麼是傳統甚麼是“我”,傳統並不是“我”之外的一個東西。
可是據說社會進步了,傳統(其實也就是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生活)也就要拿來檢討檢討了。我們,於是就站在傳統之外,對它品頭論足了起來,覺得它好,覺得它壞,覺得它有精華也有糟粕。
那時,台灣政府正在推動現代化,而反對政府的自由派學者則更為激進地主張現代化,揚“五四”之餘焰,為時代之鼓吹。不贊成如此激進現代化者,便漸漸形成了一股被名為文化保守主義的陣營,與之交鬨,史稱“中西文化論戰”。但其實,無論是講心性論的當代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或言超越前進的胡秋原,大抵也只是說傳統文化亦有優點,不可徑棄而已。由時代的大趨勢上看,政經社會體制的改造,已重新創造了一種新的生活,那原先與我們生活生命相聯結相融貫的傳統文化,早就渾沌鑿破。新時代的哪咤,正在剔骨還父、割肉還母,期望新的蓮花化身。故僅餘的那幾聲文化保存之呼喊,聽來宛若驪歌。雖然情意綢繆,矢言弗忘,可是行人遠去,竟是頭也不回的了。
然而歷史如長川大河,從來不會一瀉入海,總有曲折縈迴。台灣的“中西文化論戰”烽火未熄,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倒已是遍地硝煙了,批孔揚秦,其勢既遠勝於“五四”,亦非在台倡言現代化諸君所能望其項背。此時,無論從政治策略或文化需要上說,台灣似乎都應起來保衛傳統。於是,成立孔孟學會、發起文化復興運動、中學生都要讀《文化基本教材》(也就是四書,以《論語》、《孟子》為主)等等,乃蔚為新的人文景觀,與政經體制之現代化“並行不悖”起來了。
五六十年代“從傳統到現代”的命題,遂漸次轉變為七八十年代的“傳統與現代”。前者是要揚棄傳統,後者則想融合並行之。但其融合之道,乃是以新時代之現代化要求為取捨。故金耀基曰“我贊成現代化,但只有在它不妨害現代化發展的前提下贊成”(《中國現代化的航向》序),文崇一曰“把傳統和現代劃為對立兩極,這正是早期現代化討論所犯的重大毛病。其實,兩者是相互為用的,好的傳統可以幫助現代化,壞的傳統可以阻滯現代化”(《現代化的模式在哪裡?》)。也就是說:傳統文化是為現代化大業服務的。凡不符時代之需求者,皆宜棄去,如同啃不動的雞骨頭就應該吐掉那樣。
我成長於以上這個社會脈絡中,親身經歷了五十年來“傳統/現代”這些論題的爭論與發展,感慨萬端。然此處非發感慨的地方,故謹綜述我主要的觀點如下:
“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這個題目中的A、B兩項,原本就是全然相斥的關係。因為“現代化”從定義上就是說一個社會要拋棄傳統以轉型成現代社會,傳統文化乃是現代化之障礙,是需揚棄之物。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我國走的都是這個路子。
把兩者解釋為非相斥關係,是修正現代化理論者的傑作。這些人都是捨不得把傳統文化丟了的,所以各自發展了一些論述策略,欲修正現代化理論。
其一是說:社會固然要現代化,但傳統文化也有好的一部分,可以保留,不必倒澡盆水時把嬰兒也倒了。因此,此一派便有“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論”、“現代社會仍須講倫理道德論”、“傳統文化不礙現代化論”、“以傳統文化為中國特色之現代化論”等說。其二則稱:傳統文化其實無礙於現代化,也可開展出現代化。歷史上未見開出,並不代表它在質性上不能開,只要經過“良知的自我坎陷”等加工,它也是能開展出自由民主科學的。此說已較第一路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二者不僅非相斥關係,更是同一關係。第三說比第二說還要強勢些,謂傳統文化可以積極促進現代化。80年代“東亞儒學與經濟發展”的論調即屬此,認為韋伯講錯了,儒學也可以發展資本主義,且可能比西方老牌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更好。
這些修正主義的基本問題是:都不敢攖現代化之鋒,都承認現代化的價值與必要,所以要以傳統文化無礙於或有助於現代化為說。換言之,看起來是傳統文化的護衛者,其實是拉傳統文化去做現代化的拉拉隊。傳統文化有沒有價值,要以現代化為標準來估量。既如此,這些修正論者又怎麼可能真正動搖、修正得了現代化論?傳統文化不正透過現代性的價值重估而被揚棄被轉化了嗎?現代化論者對此類說法嗤之以鼻,良有以也。
因此,這些修正論都是虛軟的論述。真正要面對現代化理論,是要問:現代性真是種好東西嗎?現代社會真是人所需要、符合人性的嗎?我們犧牲文化傳統以追求現代化,值得嗎?亦即:現今我們需要的,不是追求現代化而是批判現代化。
自有現代化,即有批判它的思潮。20世紀初,西方文學藝術上的現代主義,便不是教人去追求現代,而是要揭露現代人奇特的精神處境,例如喪失了信仰、離開了家庭、活在科層體制和都市水泥叢林中、人與人的關係疏離而陌生、孤立的個我遂成為失落了意義的無根浮萍等等。厥後各派理論奇峰疊起、賡續發揮,不勝枚舉。如生態論者,大力批判現代社會的機械宇宙論、竭澤而漁的發展觀、宰制自然之科技工業等,形成了自然生態主義。哈貝瑪斯認為現代社會的理性觀,只是工具理性之擴張,但價值理性、道德實踐理性明顯不足,故提倡溝通理性以濟現代化之窮。丹尼.貝爾講後工業社會,則是說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存在著內在的文化矛盾:它由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所促動,可是發展下來,卻成為刺激慾望、鼓勵消費、消耗資源的型態,與新教倫理的入世禁慾精神恰好相反。故後工業社會所應強調的,不再是現代性,反而是宗教精神。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則全力去瓦解理性所倚賴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二元對立的形上學。其他批判現代社會中科層宰制、科技災難等,林林總總,實已蔚為大觀。至於馬克斯.韋伯一路思想,包括後來的世界體系依賴理論、全球化理論,更都指明了東亞國家之現代化並非其文化內部產生了變遷的需要,而是複雜的國際因素使然。
對於這些學說,我們也均予以介紹過,或批發,或代理,或零售,各有名家,但依樣畫葫蘆,學舌一番而已,殊少抓住其總體精神。總體精神是甚麼?就是對現代文明的不滿,而籌思改善之道。
我們的情形恰好相反,我們對現代文明是豔羨的,希望自己能早日擁有這份(西方人大力抨擊唾棄的)現代文明。所以包括那些批判現代性的學說,我們都把它當成西方現代文明來擁抱,以促進現代化。
這種總體精神方向上的差異、文化處境上的不同,也讓我們根本無法體會到:傳統文化之不同於、扞格於現代文明之處,或者才正是它有價值的所在。相對於二元對立、人天破裂、宰制自然的形上學,中國本來所講的天人合一、陰陽相濟,不就是當代西方批判現代的生態自然主義者所想要發展的思想嗎?相對於現代社會張揚工具理性,而道德理性、價值理性不足,中國原本所強調的倫理精神,不是恰可藥此頑疾嗎?過去被認為是封建、宗法、保守、落伍的那些東西,透過西方後現代情境中一些思想的反思,不是已讓我們驚覺到中國傳統文化其實含有豐富的“先後現代性”(pre-post-modernity)嗎?
如此說,當然不是挾洋以自重,而是要告訴仍在講現代化的先生們:現代化是落伍的論調,現代社會是有缺陷的居所,現代文明是要批判超越的。批判並超越之,其資源就在中華傳統文化中。
二、方法
但由於現代化運動推動已及百年,政經社會總體已遭改造,我們事實上都在過著一種新的生活,器用層面、制度層面、精神價值層面均已發生了具體的文化變遷。
時至今日,老實說,中國在感情上誠然仍是中國人的家園;但在理解上甚或精神旨趣上,當代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其心靈的故鄉,卻大有可能不在中國而在歐洲、在美國。除了技術器用層次、制度層次之外,在精神、信仰、知識層面,也早已離開了中國。
以哲學為例。目前整個中國哲學研究,因對傳統已極隔閡,對文獻又不熟悉,對其美感品味亦不親切,對古人之人際相應態度也甚為陌生,故研究已導向一套新的典範,研討的問題和接受答案的判準也改變了。幾乎所有人都只能採用西方哲學或科學的思考方式、觀念系統、術語、概念來討論中國的東西。碰到這個新“範式”所無法丈量的地方,便詬病中國哲學定義不精確、系統不明晰、結構不嚴謹、思想不深刻等等。
這樣的研究,看起來頗有“新意”,論者亦多沾沾自喜。但實質上是甚隔閡、甚不相應的,令我這種讀者讀來頗有聽洋牧師講說佛經之感。
可是學界仍不以此為警惕、仍不滿意,仍在覃思中國哲學應如何現代化。但依我觀察,無論是就哲學這門學科的內涵與外延之認定,或由我們討論哲學的方法等各方面看,中國哲學研究之現代化,可說早已完成了。目前已不會再有人用傳統的表述語言、思維工具來討論“哲學”了。談哲學的人,對於中西方哲學,並不視為不同的兩種東西,而覺得它們都是“哲學”,也都可以用同樣的表述、思維方式、關心方向去要求它。
許多人把西力東漸,中國人開始接觸並學習西洋哲學思想的情形,模擬為魏晉南北朝佛教之傳入中國,並認為目前的主要課題,即在於“譯經”、在於有系統地介紹西學、在於消化之。但實際上,現在的情況與佛教傳入中國之際是不同的。佛教進入中國時,中國人對佛教無知,故以其所知、已知之儒道思想去知之,此稱為“格義”。現在卻往往是對中國哲學一無所知,故用已知之西方哲學來說明未知的中國哲學。這種情形,與“格義”雖完全一樣,但卻掉轉了一個方向。
如此反向格義,確實也能令研究中國傳統學術者眼界大開,使得中國傳統思想,在西洋哲學觀念、術語、理論之參照與對比之下,讓現代人更為了解。而且原先中國所無之各色理論譯述介紹進來,豐富我們的文化、開拓我們的視野,也是頗有功勞的。正如中國菜固然佳妙,但外國烹調亦自有其傳統、有其特色。異饌者不同味,自應介紹來令國人也都能嚐嚐。國人之所以負笈西方,習其烹飪之技者,亦以此也。海通以還,西餐東來,西班牙、意大利、法蘭西、俄羅斯、印度、緬甸、泰國,殊方絕域之異味佳餚,畢陳於我中華,正賴於此。吾輩亦因此乃得大飽口福、大快朵頤。因此,除非是口味格外古怪、別有胃腸,相信沒有人會對西餐東來抱持反感,堅決不吃洋餐,且批評西餐東來遂令我華人口味墮落,不再能欣賞中餐之美了等等。
這些道理是不待辯說的。但是,假如現在做中餐的師傅只能用製洋餐之方法去烹調,不會中菜的刀法、不能用中式廚房、不擅鍋鏟炒氽之技,而皆僅能以煮意大利麵之法煮麵,然後說此即中華古麵式也,您以為如何?
西力東漸以來,中餐是少數尚能維持其風味與傳統的領域,尚未遽遭異化。哲學研究若不想繼續被異化,實不妨參考中餐館的存續發展之道。
中餐各系菜色,如淮揚菜、川菜、廣菜、魯菜,在西力東漸,西餐洋食來挑戰時,採取甚麼方法呢?是用西方觀點與方法來炒中國菜嗎?是通過理解西方烹調,以求“中西會通”嗎?是以西方菜式為“普遍菜式”,而要求中國菜據此為標準嗎?是據西方菜式以評價中國菜嗎?又或是以西方做菜的歷史為發展階段來解說中國烹飪史嗎?
顯然都不是!在討論烹調時,若有人如此主張,一定會令人笑破肚皮。可是,在談到中國哲學時,卻恰好相反。人人似乎都覺得非用西方觀點與方法來解析中國哲學不可;非通過理解西方哲學以求中西會通不可;非說哲學就是哲學,無中西型態之不同不可;非說中國哲學以西方哲學衡之,有邏輯性不足、體系性不完備、概念不清楚等毛病不可;非用西方上古中古近代或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等發展階段來解說中國哲學史不可……不如此,學界就覺得你保守、無新意、不預流。因為整個潮流正是如此的,因此誰也不覺得如此甚為荒謬。
中餐則完全不曾採取這種方式,而只是平實地由其本色菜法中推陳出新。參酌西餐之處,亦非沒有。例如進餐時的情調氣氛、餐點的佈置陳設、餐廳的花飾搭配等,盡可採酌西式。某些西餐之用料或是烹調技法,也不妨擇用。如乳酪起司的運用、做酥皮湯、用奶油煎菇之類。但這些都是在中餐的基本法式中參用的。此外皆以本門刀法、火候、工夫、用料等等為主,研練而推出新款。
西方哲學之發展,何嘗不是如此呢?當代諸哲學新流派,誰不是通過重讀其哲學傳統,以發展出新理來?為甚麼西方哲學不以用東方觀點與方法解釋西方哲學為時髦,不強調要通過理解東方哲學以求中西會通等為職事,我們卻必須以此為樂?
面對這樣的窘境,豈不也應像中餐或西方哲學那樣,由其古代及中古哲學中不斷發展出新的哲學理論與學派,不斷對其傳統做反芻與反省;然後,再以傳統的或新發展出來的理論、思致、方向、形態為“已知”,去觀看對方,發展我們對世界的解釋,一如西方哲學家以其傳統的或新發展出來的觀念及方法來解釋世界那樣。唯有如此,東西兩方才能共同結構成一個對話的情境。否則,即只不過是一方發聲,一方聽受之、學習之而已。
所以,中國哲學在現代的道路,就在於應切實反省過去不恰當的“現代化”作為,老老實實“歸而自求”,好好清理中國的學術傳統,勿徒以他人之眼光視己,亦不當自慚形穢,認定老幹已無法在現代開花,非得“接枝”或“變種”不可。如此方能使中國哲學在現代社會重新出發,重新被認識。
換言之,真正懂得吃中餐的人,大抵也才能懂得或欣賞西餐,既不會用製葡國雞、烤馬加休魚的方法及口味來要求廚子依其法做武昌魚,也知道武昌魚須如何處理才能真正讓湖北佬認為道地。至於專治西庖者,當然也同樣會有此態度。諸君皆知味者,必不以吾言為河漢!
三、體例
由於認定了批判並超越現代化之資源就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在研究傳統文化時,又不採用以西餐方法來烹調中國菜之模式,所以本書之論次有縱有橫。
縱,是指章節次序的安排。全書由中國人對“人”的基本認定講起,故第一講為體氣。有此體氣,就有生命存養的問題,故第二講說飲食。有人,人要生存下去,就又有男女婚媾之事,故第三講談男女。有男女夫婦,便會有家庭、成社會、建邦國,而中國在這方面最著名的即是封建,所以接著第四講論封建。封建既關聯於家又關聯於國,封建之禮教,既用以修身又用之治國,內聖外王通為一體,《莊子》所謂古道術,或《大學》所述修齊治平之道,都是這樣的格局,故第五講明道術。道術不僅要通內外,還希望能究天人,於是第六講論天人,說明中國人與古希臘古希伯來人不同的天人關係。究天人之際以後,當然仍得通古今之變,是以第七、八講談王官之學的內涵與流變。此一變,亦是先秦學術發展之關鍵,而且“舊法世傳之史”所關聯的史官與歷史意識,乃是中國社會與中國人意識上迥異於古希臘古印度之處。講完歷史意識,接著第九、十、十一講就接著闡明中國人思維與心理之特點,論思維模式、抒情感性與憂患意識。孔子曾讚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有憂患意識才有德業之擔當,有此擔當,才能有文化實踐的願力,故第十二講便以周公為例,說這樣的聖王如何開中國的禮樂文德之教。
以上十二講,選的材料、引述的史事,都在孔子以前,也就是春秋前的中國傳統文化狀況。描述中國這個文明,如何在飲食、男女、用思、抒情等各方面建立其面貌、發展其文化方向。依我看,中國傳統文化之大綱大維,大抵在那時就確定了,後來老子、孔子以述為作,只是踵事增華,並非變本加厲。因此把源頭說清楚了,嗣後的發展也就弄明白了。
今人對傳統文化當然頗不明白,故批評東批評西、說三道四,自以為居高臨下,可以揀擇區判其到底是糟粕還是精華。可是今人常不知自己所用以批評傳統文化的那些觀點和語詞,往往只是拾人牙慧,學著洋人在說話。因此第十三、十四講著重說明這種中國觀是怎麼形成的。十三講,以孟德斯鳩為中心,介紹歐洲從崇仰中國文化到鄙夷的過程,論析中國國情特殊論、亞洲社會停滯論、中國禮教不如歐洲法制論等論調之內涵及其訛謬。十四講,再以法律為例,說明西方對中國法制體系之誤解。兩講互相印詮,一從某個人的主張說,一從某個領域的認識說,其餘即可以隅反。
這兩講是“破妄”,前十二講是“顯正”,最終一講則是結語,傷華夏文明之異化而冀其再生也。
本書縱的條理,大約如此。橫的條理,則是指本書每一講主要都採取一種橫向比較之論析方法,具有比較哲學或比較文化史的意味。
第一講,由比較中國人的身體觀如何不同於古希臘古印度,又不同於佛教希伯來宗教開始。第二講,論中外飲食思維之不同如何構建了不同的文明。第三講,論在性別思維方面中西方有甚麼差異。第四講,論中西封建之殊,及因封建倫理形成的中西文化之分。第五講,論關懷型文化和西方驚異型知識系統的差別。第六講,論中西方不同的神人關係、天人關係。第七講,辨明周代文官制度為何已是理性的法制型社會。在歐洲,此等社會之出現,乃是工業革命以後的事。第八講,論中國人歷史意識與希臘印度之不同。第九講,談中國人思維方法之特點。第十講,論中國人如何興於詩、成於樂,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降“言辯證成”的教育體系有何不同。十一講,比較中西方群體組織之歷史與觀念,說明其政治經濟思維上的差異。十二講,反對軸心時代(Axial Period)的說法,辨明中國觀與一般民族自認為居住在世界中心的態度有何不同。每一講都對比中西,旁及印度蘇美希伯來,以見優劣。
我從來不假撇清,騙人說我的研究是客觀中立的云云。人文研究,哪有中立客觀這回事?由於人文研究本質上乃是在研究價值,價值必然涉及判斷,必然會有取捨,大部分更關聯著興趣、愛好、習慣、美感等等。我的比較,旨在說明中國文化為甚麼好。而方法便是藉由比較來看清中國究竟與其他文明有何不同,此種不同為何又不只是不同,更可能具有價值上的勝義。
這是我的目的,當然也就是我的偏見所在。讀本書者,敬祈留意,勿被我的偏見所惑。
三四十年前,初讀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便萌發了也要寫本中國文化史的念頭,即或寫不成,也準備以文化史為此後治學之領域。這當然是年少輕狂時的呆想,但未嘗沒有些俠義心腸。古詩《獨漉篇》云:“雄劍掛壁,時時龍吟。不斷犀象,羞澀苔生”。在我看,中國文化現今就彷彿這柄原是神兵利器,可以斬犀斷象的寶劍,無端遭了冷落,瑟縮在牆角裡生苔長蘚。美人落難、明珠蒙塵,皆是世上大不堪之事,非由我出來搭救不可。
懷此呆想,遊於上庠者亦數十載矣。解人頗不易得,而我自己對文化史的創獲竟也有限,年光飄忽,不免神傷。曾於1983年試講此課於台灣淡江大學,並動手寫了一部講稿。對於文化史之範疇與研究方法,粗有釐析;對於中國文化之分期與變遷,略有衡定。後卻不能終篇,殘稿輯入業強版《思想與文化》中。當時主要氣力,用於探討文化變遷。專就周秦之際、漢魏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晚清民初等幾個關鍵的變革期抉微闡幽,欲通古今之變,並為“五四運動”以來之文化變遷找到些對比勘照的模型,以經世濟民。所以文化史雖未寫成,對那幾個變革期的研究,卻令我辦了不少會議、寫了不少相關論文。近年逐漸輯刊的《漢代思潮》、《唐代思潮》、《晚明思潮》、《清代思潮》,大抵就代表了這一階段的產物。
1991年以後,我涉世歷事越來越雜,又是公職,又是辦學,又是社會活動,文化史的寫作遂越來越不可能了。但任公職、辦學校等經歷,對我的文化認知卻也不無助益。因為我早期所論,其實只是思想文化之史,於文化之制度與器用層面,研究不免粗略。正因為有此一段涉世歷事的經驗,才能深入了解典章制度及人倫日用是怎麼回事。1997年我出版的《文化美學綜論》,即可以顯示這個新的方向,欲由生活世界重開禮樂文明。
可惜辦學實在太忙了,辦了南華大學之後又辦佛光。到2003年,我校長任期屆滿。為了選新校長,董事會的行事引起了一些非議。我在爭鬧中開始寫《中國思想史》。事情鬧了幾個月,我也就草成了幾十萬字。在胡適、馮友蘭、勞思光、牟宗三諸前輩之外,另闢蹊徑,由上古黃帝開始講起,寫到了周公。此下因為要寫老子、孔子,有些畏難,才暫時先擱下了。
適巧當時北大湯一介先生主辦蔡元培、湯用彤兩講座,邀我赴講。於是就把稿子的前四章(言、象、教、字)拿來講了。合併舊作論文化符號學者數篇,輯為《文化符號學導論》,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北大的講會,聽講者甚為熱切,不覺竟感染了我的情緒,所以就趁勢請了長假,住到北大,以避囂塵。溫儒敏先生怕我太閒了,即邀我為學生講中國文化史一課。一切都是如此當機、如此順緣,實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就把其餘的稿子略作修整,一一宣講之。如此講了兩過,並在珠海聯合國際學院也講了一次。學生反應甚佳,以為前所未聞。溫先生說:那就出書吧。本擬以學生錄音整理為之。因我事忙,一直無暇核校,所以最終還是用了舊稿。原稿本是思想史,改名文化史,不盡妥切,故僅稱為中國傳統文化十五講。
為甚麼本來是思想史而居然可稱為“傳統文化十五講”呢?
我有一妄見,謂邇來講中國哲學的先生們,重點只在心性論與存有論,其餘各種思想多不注意。論思想,又只注重一些關於道、氣、性、理、仁、心等的抽象概念,對這些觀念是在甚麼樣的人文生活場域中浮顯出來,卻欠缺具體的了解,也不明白這些觀念和具體的人文活動有何關聯。以致哲學研究常只是抹去時空的概念編織,用沒有時空性的知識框架去討論活生生的歷史人文思想活動。而且他們往往是概念太多而常識太少,對整個文化的基本性格捉搦不住,只能孤立而抽象地談天道性命等觀念,所以這種危險就更為顯著。我寫思想史,前面本來就為了力矯此弊,所以作了許多類似文化導讀的鋪墊,希望讀者能明白中國哲學是在一種甚麼樣的文化中生長起來的。這一部分,抽出改稱為“傳統文化十五講”,豈不是因緣巧合嗎?
以上是說緣起,具體談到此書的內容,則另詳序論。本書在寫作時,綜攝了許多前輩與時賢的見解,但因起草時已處在風波紛擾之中,此後數年又浪跡禹域各地,無法檢書核查,故亦不及一一註明。而綜攝之後形成的我的見解,又不免有許多疏漏,這些,都是要請讀者見諒的。從前《碧岩錄》曾說道:“大凡扶持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眨眼的手腳,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捲舒齊唱、理事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著,建立第二義門,直下截斷葛藤。”我確有殺人不眨眼的手腳,此書卻未能立地成佛,並且只是權說,意在接引,故未極理趣使然,識者鑒之。最後,要謝謝溫儒敏先生和艾英,他們通讀數過,且提示了許多修改意見。
2006年處暑
於北京小西天如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