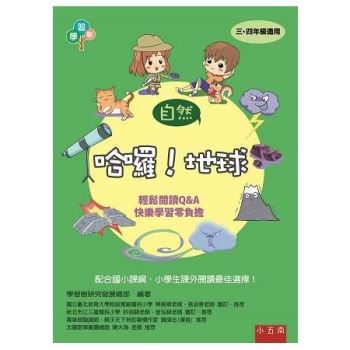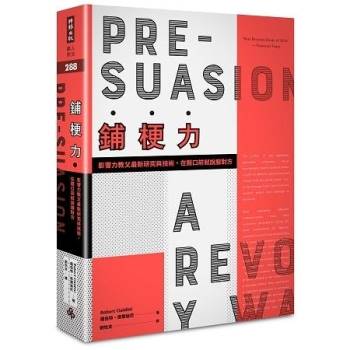壽衣不能提前做
夏天和冬天最容易死人了,一般死的都是老人。冬天還無所謂,天冷死人也不怕冷。可夏天不行,死人怕熱啊,尤其是四十多度,三天下來,滿屋子裡都是臭味。現在有冰棺材了,以前可沒有,就是拿兩盆冰放屍體下面。那個時候連個電扇都沒有。我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我跟著我爸來到一家。那是一個老太太,可能有八十多歲了,特別的胖,心臟病死的。老太太的壽衣是幾年前就準備好的,可他們忘了一點,老太太又胖了。難免的,家裡一有人死,人就慌裡慌張的。
我從頭說啊,中午吃過午飯,老太太說睡一會兒,後來就沒有醒,睡過去了。老太太這一沒有醒,全家人就都慌了。我爸爸那會兒也正在睡午覺,我放暑假,看電視,正演《西遊記》三打白骨精那集,他們家就來了。也不遠,我爸爸就喊上我,我們和串門一樣,溜達著就去了。
到了他們家,所有人都站著迎接我們的到來,老太太就和睡著一樣躺在床上,旁邊放著幾件衣服。此時老太太的兒子過來,對我們說:「這是我媽媽自己準備的衣服,她以前就交代過,死的時候,要穿自己親手做的衣服。」
「行!那是你們給你媽穿還是我們給穿?這天太熱,要穿就快點兒,一會兒人就容易發起來。」我爸對那兒子說,我爸是有職業經驗的。
「哦哦。對對,發起來,那你們給穿吧,這樣是不是也能快點兒。」那兒子說發起來的時候,眼裡全是恐懼。不知道為甚麼我突然想到一糰麵。
「那行!你們過來兩個人,幫幫忙。有剪子嗎?給我,我們先把老人的衣服剪開。再給我拿一瓶白酒、一塊乾淨的毛巾過來,給老人擦洗乾淨。」我爸話說完,至少有三十秒沒有一個人動,三十秒以後屋子裡的所有人又全部動起來。二十幾分鐘以後,已經都擦洗完,酒瓶也空了。行了,可以穿壽衣了。我爸多有經驗,拿起壽衣一看,又看了看老太太,就開始搖頭。
「這衣服做得太瘦了,你們自己看看。」我爸用手把衣服打開,我一看,心想,這老太太手真巧,給自己做了三件旗袍,其中一件還是夾棉的。她做的時候可能是冬天,也許以為自己能在冬天死,怕自己凍著。
「師傅,我媽媽是南方人,嫁給我爸爸才來的天津。您看看這怎麼辦呢?」那兒子更慌了。
「現在改也來不及了,也沒有這個時間,你們幾個也別閒著,看看去哪裡弄點兒冰塊,大塊的那種。快去!」我爸全身都是汗,衣服都貼在身上了,跟剛洗完澡似的。
「師傅,那您看怎麼辦?我媽媽就這一個遺願。」兒子已經哭了。
我爸也急了,說:「你們幾個女的都給我過來,先把這衣服裡的棉花都給我掏出來。快點!」
此時衝過來兩個女的,都五十多歲的樣子,拿起剪子就把衣服剪了一個大口子,兩個人四條胳膊,伸手往外掏棉花。頓時,她們兩個成雪人的樣子。反正當時也顧不上那麼多了。很快又過來兩個人,她們一起掏,有的掏袖子的,有的掏後邊的。我想如果老太太看到這個情景,能活過來也說不定。屋子裡全是棉花,像下了雪一樣,加上大家又都出汗,棉花遇到汗都黏在手上身上臉上頭髮上。這可是八月最熱的伏天啊,場面太詭異了。還有一個老太太只蓋著個床單,等著要穿她這輩子最後的一件衣服。
最後四五個「雪人」可算把棉花都掏出去了,壽衣也被剪得都是口子。我爸說這哪行啊,縫好了啊。「雪人」們又開始縫,這又過了快一個小時,再看縫好了的衣服,誰看了都傻眼,各種顏色的線,縫得亂七八糟的。一件好好的旗袍壽衣,這可是老太太的遺願,最後成了一件乞丐服。我爸叫過來剛才那兒子,問他:「你確定,要把這件衣服給你媽穿嗎?」
兒子也頂著一頭棉花,拿衣服看了又看,當時也猶豫了。我爸說:「你要快點兒決定,老人那裡還等著呢!」兒子想半天說:「我和家裡人商量商量。」他拿著衣服走了。不一會兒工夫來了幾個人,都同意還是這件。
我爸爸深深地點了一下頭,說了聲:「那好!你是兒子,你就是孝子。我要先把衣服一件一件給你穿上,然後你再脫下來,一起給老人套上。」說完,我爸一使勁,只聽「呲啦」一聲,一隻袖子被撕下來了,然後是另一隻。那兒子剛要急,我爸說:「我不撕你媽不可能能穿進去。」然後一件一件讓他穿。都是旗袍啊,我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看到一個男人,一次穿三件旗袍。穿好以後,我爸像個裁縫一樣,從身後面,把衣服一下子剪開,三件連在一起的旗袍成了左右兩個部分。然後我爸讓我幫忙扶著分左右兩部分給老太太穿好。袖子也是在後面剪開再套上。從表面看,根本看不來任何破綻。蓋上一層蒙臉布,又蓋上壽單,壽被被我爸直接省去了。
包子是誰吃的呢
你們都覺得我爸厲害,其實我媽才叫厲害呢。這可不是我聽說的,是我親眼看見的。小時候,我們家住五棟,前面還是後面的,我記得是十二棟。那天夜裡下大雨,我爸喝多了,怎麼都叫不醒。有人大半夜敲我們家門,說他們家有人上吊了,就因為兩口子吵了兩句。我媽一看,只能她去了。這和醫生一樣,大了救死扶死,都是要命人家才求你來的,不能拒絕。不是錢的事兒,再說那會兒也沒有幾家壽衣店,大了也少。都是鄰居,我媽媽也不好意思說,下雨了我們不想去。只能去,沒有辦法,把我叫醒了,跟著。我也習慣了,醒了揉揉眼穿上衣服鞋就跟著走。我啊,那個時候上小學三年級左右,也沒多想,從小這樣習慣了。我和我媽都穿著雨衣,那個時候我家還沒有雨傘。
我看到有個人躺在床上,據說救護車剛走,說沒有救了。我媽問:「她丈夫呢?」不知道誰回答:「被救護車拉走了,嚇得神志不清了。」我媽說:「那來吧。你們誰能說了算?」此時站出一個人來說:「你有甚麼事情可以和我說。」我媽說:「咱們大晚上的先不要鬧,把人先安頓好。穿好衣服。明天一早再通知大家,搭床板甚麼的也明天早晨再說。你們覺得行嗎?」大家紛紛點頭。用敬佩的目光看著我的母親。當然我也是。
我媽不胖不瘦,不黑不白,平時也不愛說話,但只要她說話別人就必須聽。我媽媽走到上吊的女人身邊對著她說:「你說你,沒事上甚麼吊?看你這眼珠子,都快跑出來了,還不捨得閉上,幹嘛呀?捨不得誰?還是有甚麼委屈?那你現在也說不出來了吧?誰讓你沒有事上吊的。來,閉上眼睛。」我媽用手把她的眼睛合上。這個鏡頭我也在電視上看到過。人民解放軍死了,只要聽見:「我們會替你報仇的。」眼睛就閉上了。我也以為,我媽媽說半天,怎麼也給個面子,可那個女人就不閉眼。我媽最後就拿手按著她的一隻眼睛,按了很長時間,有一點點效果,但還是不能完全閉上。眼睛都閉不上,怎麼給她穿衣服?所有人都看著我媽。但是她一點兒也不著急,對著屋裡的人說,看看家裡有蘋果饅頭甚麼的嗎?一會兒有人拿來兩個包子,不好意思地問我媽:「就有兩個包子,行嗎?」「拿過來吧。」我媽把包子按在眼睛上,一隻眼睛按一個,兩個包子在一張臉上。估計很長時間,屋子裡的人都不打算再吃包子了。後來我就在椅子上睡著了。沒有睡多會天就亮了。我一醒過來就想起我睡前那兩個包子,不知道起作用了沒有。我看到上吊的女人,蓋著單子。
我問我媽:「她閉上眼睛了嗎?」我媽點了點頭,我看到桌子上一個碟子裡放著一個包子。
「媽!!怎麼只剩一個包子了,不是兩個嗎?」我拉住我媽問。我媽不慌不忙地說:「不知道被誰吃了。不過我肯定,不是昨天晚上在這裡的人。」
給我每人兩頭牛
這是前兩年發生的事。有時細想想,有的人就是很怪,老人活著的時候,不孝順,一定要死了以後才發孝心。這個老人有五個兒子兩個女兒。老人活著的時候,在每個孩子家住一天,正好七天。老人患有老年癡呆症,總以為老伴還活著,看見個人就問:「玉華回來了嗎?怎麼還不來看我啊?」
老人一百零二歲,他孩子最大的也七十多了。他們家個個比著有錢,生怕自己在兄弟姐妹面前沒有面子,這我第一次去就發現了。他們本來是請我爸去,但我爸已經退休了,這才勉強同意我去。我們不怕有錢的,就怕沒錢的。有錢願意當冤大頭我們熱烈歡迎。有一次老人進了醫院,他們就把我叫去,和我談葬禮細節。談了好幾次,老人卻好了,出院了。其實我知道,他們是想藉老人去世,把多年送出去的禮錢都收回來。搞得越大型人來得越多,禮錢就越多。
為了老人去世,他們特意租了一套房子,表面說是人多,其實他們每個人都不想讓老人死在他們自己家中。死去的老人從醫院被直接拉到了租的房子裡。我去的時候,沒有人哭,都忙著打電話,每個人都在打電話。意思都差不多:我爸今天早晨剛剛過去了……去世了……走了……找我媽媽去啦。整得場面和記者招待會一樣。我就坐在老人身邊,看著他們每個人打電話。他們也沒有人注意我。我和剛死去的老人成了隱形人。
這個葬禮從第一天開始就像是一場大型鬧劇。有人還在門口空曠的地方請了一個樂隊。說是完全按照老人老家的傳統來。我這個大了其實就是個擺設。他們個個都是大了。我只管最後拿錢就行。但這畢竟是我的工作,我找到一個管事的,和他商量送路的事。
「不用商量,給我最貴的那個檔次。電視,冰箱,洗衣機,手機,甚麼電器都要有,還有房子,汽車,轎子都要。還有馬要十四匹。牛有嗎?給我兩頭!不行,每人兩頭,也十四頭,每個人兩頭。你不知道,我爸爸就喜歡吃牛肉!」他說得太認真,我都不忍心打斷他。
「您知道牛是幹甚麼用的嗎,大爺?不是用來吃的!那是讓牛幫著喝下去世之人生前浪費掉的水。做這個用的。不是吃的!我的大爺!」本來我對活人的耐心就遠遠沒有對死人多。大爺告訴我:「這是我們家辦喪事,我們說了算,小伙子,你要聽我們的。我們要的越多,你不是掙錢越多嗎?你別管我們要多少。我們要多少,你給我們多少,不就完了嗎?」
尾聲
有一回我爸高興,我就問他:「爸,有個事兒,我一直就想不明白。我小時候,您為甚麼總帶著我去當大了?」
「讓你跟著我是為了讓你從小就習慣適應,習慣了就不知道害怕。人天生就害怕死去的人。所有的動物我們都怕活的,就是人,我們怕死的。人一死就是植物了,從動物變成植物啦!死人又不會吃人咬人的,怕甚麼呢?大家不是怕死人,是害怕死,怕和死人一樣。覺得離死人遠一點,就能活得時間更長一點。」我爸說:「做大了做了一輩子,整天就是給死去的人穿衣服,讓他們走好,聽到最多的就是哭。但是這一輩子白事讓我知道,人應該怎麼活。」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死亡筆記:禮儀師的生死見聞的圖書 |
 |
死亡筆記:禮儀師的生死見聞 作者:自然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7-1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40 |
二手中文書 |
$ 316 |
人生故事 |
$ 316 |
NatureScience & Mathy |
$ 360 |
中文書 |
$ 360 |
人生故事 |
$ 360 |
科學‧科普 |
$ 360 |
宗教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死亡筆記:禮儀師的生死見聞
看清楚了死,才能更明白地活。
人們在直面死亡時,恐懼往往會大於悲傷。那是一個有去無回的世界,沒有任何過來人可以給你指明方向。
“殯葬禮儀師”是接觸死亡最多的人,他們賦予死亡莊重的儀式,妥善送走死者,同時目睹那些由死亡折射出來的人間百態:在自己葬禮上教學生直面死亡的老師,臨死前堅持要穿上壽衣自拍並把照片放上網的老太太,深夜去鐵路旁找孩子屍體殘肢的父親,葬禮上鬧事的酒鬼朋友,把六歲女兒的葬禮辦成攝影展的年輕父母……
作者用黑色幽默的語言,以超脫的姿態講述了四十餘篇禮儀師的親歷故事,這些故事或驚心動魄、或荒誕不經、或催人淚下、或啼笑皆非,引發人們對生與死的思考:凡人皆有一死,在死亡來臨前,應該如何活著?
本書特色:
死亡是個嚴肅而又沉重且相對禁忌的話題,但作者通過幾十個故事,展現了或荒誕或溫情的一面。
殯葬禮儀師親身經歷故事,真實,引發人們思考。
故事短小好讀,貼近人情。
作者簡介:
自然
生於70年代,現居天津。從2015年11月起在豆瓣閱讀寫作,迄今已發表作品《白事會》、《凡人皆有一死》和專欄《白事會:第二季》。
TOP
章節試閱
壽衣不能提前做
夏天和冬天最容易死人了,一般死的都是老人。冬天還無所謂,天冷死人也不怕冷。可夏天不行,死人怕熱啊,尤其是四十多度,三天下來,滿屋子裡都是臭味。現在有冰棺材了,以前可沒有,就是拿兩盆冰放屍體下面。那個時候連個電扇都沒有。我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我跟著我爸來到一家。那是一個老太太,可能有八十多歲了,特別的胖,心臟病死的。老太太的壽衣是幾年前就準備好的,可他們忘了一點,老太太又胖了。難免的,家裡一有人死,人就慌裡慌張的。
我從頭說啊,中午吃過午飯,老太太說睡一會兒,後來就沒有醒,睡過去了。...
夏天和冬天最容易死人了,一般死的都是老人。冬天還無所謂,天冷死人也不怕冷。可夏天不行,死人怕熱啊,尤其是四十多度,三天下來,滿屋子裡都是臭味。現在有冰棺材了,以前可沒有,就是拿兩盆冰放屍體下面。那個時候連個電扇都沒有。我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我跟著我爸來到一家。那是一個老太太,可能有八十多歲了,特別的胖,心臟病死的。老太太的壽衣是幾年前就準備好的,可他們忘了一點,老太太又胖了。難免的,家裡一有人死,人就慌裡慌張的。
我從頭說啊,中午吃過午飯,老太太說睡一會兒,後來就沒有醒,睡過去了。...
»看全部
TOP
推薦序
代序
大了(dà liǎo),曾經是天津人對婚喪嫁娶組織者的稱呼。現在的大了,專指從事白事的組織者。
在你看這些文字的時候,也就是此時此刻,正有人閉上眼睛,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而你正在閱讀,呼吸均勻,意識清醒。想到這些,你或許會突然產生一種恐懼、壓力和緊迫感。你會不會下意識地珍惜今天?可能你會在網上給自己買下心儀很久的高跟鞋,下頓吃點兒好的,不再為了一點點的小事就氣得肝顫……反正你會暗自慶幸,自己還活著。
好像在一輛公車上,司機師傅大聲地提醒你:「我們車上有個小偷,希望大家看管好自己的物品!」你會立刻...
大了(dà liǎo),曾經是天津人對婚喪嫁娶組織者的稱呼。現在的大了,專指從事白事的組織者。
在你看這些文字的時候,也就是此時此刻,正有人閉上眼睛,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而你正在閱讀,呼吸均勻,意識清醒。想到這些,你或許會突然產生一種恐懼、壓力和緊迫感。你會不會下意識地珍惜今天?可能你會在網上給自己買下心儀很久的高跟鞋,下頓吃點兒好的,不再為了一點點的小事就氣得肝顫……反正你會暗自慶幸,自己還活著。
好像在一輛公車上,司機師傅大聲地提醒你:「我們車上有個小偷,希望大家看管好自己的物品!」你會立刻...
»看全部
TOP
目錄
代序
壽衣不能提前做
包子是誰吃的呢
給我每人兩頭牛
後備廂的鐵鍁
結婚第三天
屋子大有甚麼用
哭了看不清
大師也怕嗆
一天之內
人死了不還是人嗎
斑馬線
司機師傅都長點心吧
穿壽衣發個朋友圈
奶奶的白頭髮
猴子派來的狐狸精
你恨我嗎
別鬧,我們正辦喪事呢
白色生死戀
參加白事的基本素質
如果可以飛檐走壁找到你
泰森的葬禮
耳語
我不讓你死
這個路口是我爸的
死神,你好
除夕夜的鐘聲
歲月是個好裁縫
好像身體少了一部分
陽光
當愛已成往事
太平間的婚禮
對不起,買不起
回家
走在人群中才發現
也是...
壽衣不能提前做
包子是誰吃的呢
給我每人兩頭牛
後備廂的鐵鍁
結婚第三天
屋子大有甚麼用
哭了看不清
大師也怕嗆
一天之內
人死了不還是人嗎
斑馬線
司機師傅都長點心吧
穿壽衣發個朋友圈
奶奶的白頭髮
猴子派來的狐狸精
你恨我嗎
別鬧,我們正辦喪事呢
白色生死戀
參加白事的基本素質
如果可以飛檐走壁找到你
泰森的葬禮
耳語
我不讓你死
這個路口是我爸的
死神,你好
除夕夜的鐘聲
歲月是個好裁縫
好像身體少了一部分
陽光
當愛已成往事
太平間的婚禮
對不起,買不起
回家
走在人群中才發現
也是...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自然
- 出版社: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7-12 ISBN/ISSN:978988846609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32開
- 商品尺寸:長:200mm \ 寬:142mm
- 類別: 中文書> 心理勵志> 心靈雞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