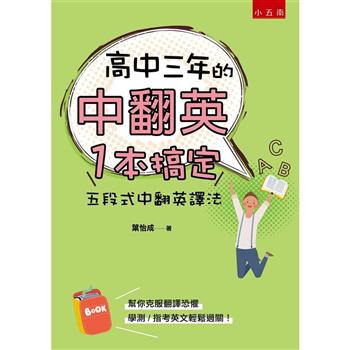序
山高水長,斯人千古伯駒先生是上世紀我國文化界的一種異數和一段傳奇。在民國四公子中,他所綻放的文化光輝、貢獻的異珍奇寶及所體現的高風亮節,無人能及,幾可與司馬遷《史記》中的戰國四公子分鑣並轡,各有千秋。
伯駒先生出身名門,博精諸藝,詩詞歌賦,唾手成章,書法戲劇,無不精妙。尤重書畫收藏,為國存寶,不惜傾家蕩產。劉海粟先生稱:「他是當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從他那廣袤的心胸湧出四條河流,那便是書畫鑒藏、詩詞、戲曲和書法。四種姐妹藝術,相互溝通,又各具性格。堪稱京華老名士,藝苑真學人。」啟功先生以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下民間收藏第一人。」周汝昌先生則云:「一是先生所捐獻於國家者,重於黃金百倍千倍不止。蓋黃金有價,而先生所獻者無價…… 二是先生異代相賞於這些歷史誕生的文墨藝匠的無以倫比的藝術才情,正如杜少陵之於先賢宋玉所謂,『蕭條異代不同時』,『風流儒雅亦吾師』,彼此有精神境界之投契。」又云:「他為人超拔, 是因為時間坐標系特異, 一般人時間坐標系三年五年, 頂多十年八年, 而張伯駒的坐標系大約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觀雲起, 笑看落花, 視勛名如糟粕,看勢利如塵埃。」一點不錯,正
是這種情懷與定力,成就了他的藝術人生。
誰能想到,這樣的大收藏家,晚年會是一貧如洗。記得1977 年過年時,竟困難到無以度歲的程度,還是承燾先生讓我給他送去500 元勉強維持。然而老人依舊笑談待客,不以為苦。據《叢碧書畫錄》記載,其所收一等書畫達118 件之多。在故宮設立表彰書畫捐獻者的《景仁榜》上,頂級書畫中近一半為伯老捐獻,皆為價值連城的異寶奇珍。1936 年為防止溥心畲所藏西晉陸機所書《平復帖》流入日本人之手,他請傅增湘先生出面,千方百計以四萬大洋購回。1945 年日本投降,長春偽滿州國流出上千件文物,日美諸國覬覦已久。為此,伯老緊急倡議由政府出資購回交故宮保管。並云:「如果資金不足,可代為周轉。」而腐敗的政府竟不加理睬,乃決心個人出面,盡力搶救。再如傳世最早的青綠山水隋代展子虔《遊春圖》索價800 兩黃金,伯老因財力不足,無奈之下將自己最後一處花園住所—弓弦胡同一號「叢碧山房」,以220 兩黃金出售給輔仁大學,而後以此款購回這一稀世國寶。並於1956 年5 月捐獻給故宮博物院。沈雁冰部長頒發獎狀云:「化私為公,足資楷式,特予褒揚。」
伯駒先生護持國寶的大節高風,深深感動着年輕學者榮宏君,他決心為先生立傳,以彰天地之清氣,而立文化之標高。榮君從零開始,千方百計搜集資料,孜孜汲汲,十有餘年。訪遍南北萬里,書採數百餘家,事事核實,字字推敲,乃成就洋洋四十萬字的巨著。我挑燈批覽一過,深佩作者不遺巨細而成此鴻篇。考核既嚴,判斷尤精。資料之豐贍,行文之流美,令我這個在伯老晚年追隨身後的弟子,驚喜連連,備受感動。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迄今有關伯駒先生最翔實最深刻的一部著作。比如傳主伯老的身世,過去很不清晰,通過《年譜》的記述,就一目了然了。其父張鎮芳,光緒十一年舉人,十八年進士,官至一品署直隸總督,實為其裔父。生父張錦芳,是晚清廩生,曾任度支郎中、道尹等職。其祖父張瑞楨為光緒二十年舉人,家中藏書數萬卷。而其姑母,則是袁世凱的長嫂。如此顯赫的背景,對於其人生道路,影響自然是巨大的。
《年譜》的另一特點是,補錄了伯老大量未收的佚詞、詩聯及散文,皆榮君從各類名人筆記、報刊雜誌上收錄得來,應超過百首以上。如1936年所填《木蘭花慢》「鬱巫閭莾莾,鍾王氣,定幽燕」,以及《蝶戀花》「十里城西楊柳路」、《人月圓》「戍樓更鼓聲迢遞」、《浪淘沙.京陵懷古》等詞作。另如1952 年夏為畫友惠孝同所藏《魚村小雪圖》書七言古風:「三年樓居對西山,日日憑窗看雲烟。…… 咫尺之間見天地,晷刻以內即神仙。」為作者罕見之長調,過往傳著亦未見收錄。甚至如1977 年6 月賀葉帥八十律詩:
杖朝杖國仰群黎,百歲韶華壽域躋。
早有功名揮日返,猶多英氣望天低。
陰山不度空胡馬,漢社全傾除牝雞。
霜葉滿林秋更好,明霞燦爛映紅旗。
此等傑構,幸賴此而得以傳世。至於伯老與當代名家,如郭則澐、黃公
渚、黃君坦昆仲,唱和詩詞,不下百首,亦賴此而存一綫,可謂斯文之幸。
《年譜》涉及當時上層的動態,尤其值得注意與研究,如1920 年9
月,伯老陪父親張鎮芳拜訪張作霖。作霖為報答鎮芳當年排摒掉段芝貴而扶植其上位之恩,任命伯駒為奉軍總稽查。翌年張作霖又出手幫助擺平因「復辟事件」而被吳鼎昌掠奪的鹽業銀行股權問題。再如《鄧之誠文史札記》所言:伯駒云,「袁世凱稱帝受英、德慫恿,歐戰既起,英、德無力東顧,日本乘之,而段、馮因之倒戈。又言宣統復辟,徐世昌謀以孫女為后,而自居輔政,密遣曹汝霖詢日本公使意向,日使言必反對,徐遂袖手。」又云,「護國軍之起,蔡鍔受日本助款二百萬,則湯薌銘為我言之。中國何時始能獨立自主乎?」如此等等,事關政局秘辛,值得認真研究。
《年譜》還記錄伯駒先生與毛澤東主席,與陳毅、葉劍英元帥的親切交往,體現了國家領導人對老專家學者的關愛,令人感動。在伯老的牛棚日記中詳細記錄了他的心得,在《看不慣知識份子》中寫道:「十幾年來存在着封建時代的士大夫四舊生活,與一些封建餘孽聚飲、填詞、聚飧、聯吟、猜詩謎、打詩鐘,春日看杏花、夏日賞荷、中秋賞月、重陽登高賞菊、看紅葉。在社會主義中還像六十年前之歲月,落後到何等地步。」又云:「五三年我愛人潘素與北京老畫家合畫冊頁,祝毛主席五九大慶。蒙毛主席春節賞賜禮物…… 這樣的恩遇。…… 我五三年呈獻毛主席唐李白《上陽臺帖》蒙辦公室賜予回信。我列入右派後,毛主席秘書(田家英)還說:『張伯駒還是有功國家的』。」這些記錄表達了老人劫難中的心聲,真令人不勝唏噓。《年譜》還記錄了他和陳毅元帥難得的對話。1961 年10月2 日,陳帥於中南海紫光閣為伯老餞行,問他:「到吉林教什麼?」伯老說:「到藝專教書法史、繪畫史、詩詞等。」陳總說:「這是你的專長。」又問:「右派帽子摘掉了沒有?」伯老說還沒有摘掉。陳總說:「你是舊文人,難免情緒孤僻,新事物知道又少。或為人所不諒。你的一生所藏書畫精品都捐給國家了,你還會反黨嗎?我同他們說給你改改好了。」伯老說:「我受些教育,對我很有好處。」陳總說:「你這樣說很好。我謝謝你。」今日讀來仍暖透心窩,使人感佩!
《年譜》對天下第一票友伯駒先生的戲劇功力,更有精彩生動的記錄。1937 年3 月4 日先生四十壽,於隆福寺全福館賑濟河南旱災義演,京劇名家老宿集體出動。壓軸大戲《空城計》由伯老飾諸葛亮、王鳳卿飾趙雲、陳繼仙飾馬岱、余叔巖飾王平、楊小樓飾馬謖、陳香雪飾司馬懿、錢寶森飾張郃等,可謂盛況空前,絕無僅有之樂事。《民國雜誌》云:張
伯駒飾孔明,在四大名伶所飾各將環護下,飄然升帳。「羽扇綸巾四輪車」
數句引子,臺下真疑為全場有二「余叔巖」出現。「若將此班人馬,搬來
滬上演出,則恐又將鬧翻上海矣。」關於伯老戲功高卓,陳巨來在《安持
人物瑣記》中云:是年伯駒欲串演二戲,自「問樵」至「出箱」一氣呵成,
毫不費力。出箱用鯉魚打挺而滾出的,內行亦不敢輕於嘗試也。天下第一
名票,決非虛譽也。
伯駒先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護神。關於國畫藝術的現實意義,伯
駒先生與悲鴻先生看法有異,二人曾產生過一場論戰,據《年譜》:1947
年10 月中旬徐悲鴻先生在《大公報》上連續發文,揚言「要打倒八股山
水」,不要仿古,而應摹寫人民的生活,並解聘了秦仲文等三教授。10 月22 日,伯駒先生發表了《我對文化藝術創造之意見》,指出「吾中華民族藝術之表現,為雍容和平,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風度精神…… 每隨時代遞嬗創造,而其一貫之精神聯繫不斷。」又云:「近感於徐悲鴻氏發言,謂該校一年級學生畫,即比董其昌、王石谷為好之一語。易啟學生對藝術輕易之心…… 。建議教育部規定文化藝術發展之方針與途徑,則藝術之爭自息…… 仍希望徐氏善自謙抑,勿意氣用事。」云云。其遠見卓識、諄諄告誡,真令人欽敬。其對傳統藝術之態度,與畢卡索有異曲同工之妙。1956年張大千去巴黎拜訪畢卡索,他說:「我不懂中國人為何要到巴黎來學藝術?中國畫真神奇。齊先生畫水中的魚兒沒有上色,一根綫去畫水,卻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了水的清香。」(《環球人物》)
伯駒先生酷愛傳統文化,特別是詩詞,已經融入他的呼吸和生命。伯老晚年最關心的事是籌建韻文學會。他認為詩意是一切古典藝術的靈魂,一生為之奮鬥。早在1956 年夏間,就曾邀約葉恭綽、朱光潛諸位韻文學會籌備委員商議此事,決定與章士釗、葉恭綽聯名上書周總理,並獲得總理的認可。無奈反右事起,遂被擱置。直到改革開放以後,伯老復聯絡夏承燾、唐圭璋、任二北、王力、程千帆以及趙樸初、周谷城、鍾敬文等一批巨擘,聯名上書中宣部部長王任重,報請成立韻文學會事宜。1980 年2月8 日,寫信告訴我約青年詞家座談章程問題;6 月14 日寄書上海唐雲、謝稚柳諸老商議籌建韻文學會問題。同年6 月,夏承燾、張伯駒、周汝昌三老上書文化部黃鎮部長云:「經呈中宣部申請成立中國韻文學會,聞已批覆貴部,擬向您面呈梗概。」12 月6 日致函天津詞家告知韻文學會已獲批准,並附有創刊號目錄,同時函告我草擬韻文學刊啟事,並商議開成立會問題。1981 年初囑我以張、夏二老名義代擬至周巍峙部長函,催辦韻文學會之事。8 月26 日伯駒先生致函王任重、賀敬之部長,談及韻文學會成立的困難,建議附屬於全國文聯或文化部藝術研究院諸事。11 月17 日函告我云:「文化部通知韻文學會須於12 月內成立,請與統一速到我家面談,持我信與文化部周部長接洽為要。」終因掛靠問題未能落實而拖延下來。伯老已是垂暮之年,為創建韻文學會,仍事無巨細,親力親為,費盡心血,令人感動。1982 年2 月8 日,伯老病倒入住北大醫院大病房。我
聞訊後於11 日前往探視,老人昏昏沉沉,狀態不佳。當我把敬之同志關於韻文學會將採取掛靠實體學術單位的想法告訴他時,他已不能對話,頷首而已,令人淒黯不已。此後在敬之部長的關懷下,伯老入住高幹病房,神志漸趨清爽。2 月25 日(農曆正月廿二),老友張大千先生令孫張曉鷹前來探視,老人精神好轉,頭腦清晰,即興口述七律一首,末句云:「還期早息鬩牆夢,莫負人生大自然。」諄諄以祖國和平統一,順應自然法則為囑,立意何其高遠。另填詞《鷓鴣天》:
以將干支斗指寅,回頭應自省吾身。莫辜出處人民義,可負身教
父母恩。儒釋道,任天真,聰明正直即為神。長希以往昇平世,
物我同春共萬旬。
伯老這首辭世之作,充分展現了老人爐火純青的藝術才華與完美崇高的思想境界。上片回顧平生,以為尚沒有辜負人民的厚愛與父母的養育之恩。下片筆鋒一轉,提出一個哲學命題:儒釋道聖賢立說,無非是聰明正直、本色天真。我最嚮往的去處,就是一個人與自然界能夠同享萬年春光的彼岸!這不就是上報四重恩、下濟眾生厄的博愛情懷與華嚴境界嗎?如此灑脫、超邁,可謂深沃道心、悲智雙運之傑作。這就是老人為我們留下的極寶貴的謝世遺言。
山高水長,斯人千古,伯駒先生值得我們永遠紀念!
戊戌盛夏門人周篤文盥手拜書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張伯駒年譜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張伯駒年譜
张伯駒先生(1898年2月12日-1982年2月26日)是20世紀中國文化界的一段傳奇。他出身名門,博精諸藝,詩詞歌賦,下筆成章,書法戲劇,無不精妙;尤重書畫收藏,為國存寶,不惜傾家蕩產,晉陸機《平復帖》卷、隋展子虔《遊春圖》、唐李白《上陽臺帖》、杜牧《贈張好好詩》卷等均由他捐獻國家。
本《年譜》係學者榮宏君耗時十餘年,廣搜旁證,編纂而成。作品資料豐贍,考證翔實,準確而細緻地勾畫了張伯駒先生風雲跌宕的一生,集學術性、史料性、可讀性於一體,對於學術界、文化界、一般大眾較為完整、清晰地認識張伯駒先生,必然大有裨益。
作者簡介:
榮宏君,畫家,文化學者,1973年生於山東曹縣。現任全國青聯常委,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北京城市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張伯駒潘素文化發展基金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出版有多種著作,包括:《丹青典藏──榮宏君卷》(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2008年),《世紀恩怨──徐悲鴻與劉海粟》(北京同心出版社,2009年),《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實錄》(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季羨林說佛遺稿彙編》(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徐悲鴻與劉海粟》增訂版(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文博大家史樹青》(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竹墨留青──王世襄致范遙青書翰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成龍•收藏人生》(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國寶傳奇──張伯駒》(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張伯駒牛棚雜記》(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
作者序
序
山高水長,斯人千古伯駒先生是上世紀我國文化界的一種異數和一段傳奇。在民國四公子中,他所綻放的文化光輝、貢獻的異珍奇寶及所體現的高風亮節,無人能及,幾可與司馬遷《史記》中的戰國四公子分鑣並轡,各有千秋。
伯駒先生出身名門,博精諸藝,詩詞歌賦,唾手成章,書法戲劇,無不精妙。尤重書畫收藏,為國存寶,不惜傾家蕩產。劉海粟先生稱:「他是當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從他那廣袤的心胸湧出四條河流,那便是書畫鑒藏、詩詞、戲曲和書法。四種姐妹藝術,相互溝通,又各具性格。堪稱京華老名士,藝苑真學人。」啟功先生以為:...
山高水長,斯人千古伯駒先生是上世紀我國文化界的一種異數和一段傳奇。在民國四公子中,他所綻放的文化光輝、貢獻的異珍奇寶及所體現的高風亮節,無人能及,幾可與司馬遷《史記》中的戰國四公子分鑣並轡,各有千秋。
伯駒先生出身名門,博精諸藝,詩詞歌賦,唾手成章,書法戲劇,無不精妙。尤重書畫收藏,為國存寶,不惜傾家蕩產。劉海粟先生稱:「他是當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從他那廣袤的心胸湧出四條河流,那便是書畫鑒藏、詩詞、戲曲和書法。四種姐妹藝術,相互溝通,又各具性格。堪稱京華老名士,藝苑真學人。」啟功先生以為:...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 錄
卷一 少年遊 001
光緒二十四年至民國十五年 (一八九八— 一九二六)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一歲 003
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辛丑) 四歲 005
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六歲 005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甲辰) 七歲 005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八歲 006
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九歲 006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十歲 006
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十一歲 007
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己酉) 十二歲 007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辛亥) 十四歲 008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壬子) 十五歲 011
一九...
卷一 少年遊 001
光緒二十四年至民國十五年 (一八九八— 一九二六)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一歲 003
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辛丑) 四歲 005
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六歲 005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甲辰) 七歲 005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八歲 006
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九歲 006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十歲 006
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十一歲 007
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己酉) 十二歲 007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辛亥) 十四歲 008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壬子) 十五歲 011
一九...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