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沉默有如玻璃上的裂痕,細微隱匿卻足以瓦解一切……
「故事生動卻也使人不安,一讀就上癮;一路朝著毀滅性的結局讀下去,無法喘氣。」
──S. J. 華森,《別相信任何人》
◆ 出版史上,最沉默的轟動!!驚人的口碑效應,讓亞馬遜書店總監直呼出版奇蹟!
◆ 妮可‧基嫚讀後大為驚豔,立刻買下電影版權,並製作主演!
◆ 構思十年的絕響作品,張妙如、張國立、貴婦奈奈、宅女小紅、吳若權、劉黎兒、女王等國內外知名作家競相推薦!
「一個女人為了保有自己擁有的事物,願意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優雅沉靜的她,怎樣也料想不到,幾個月後,自己會成為殺人兇手……
住在芝加哥海濱高級公寓的裘蒂和陶德,原本過著優渥自在的日子,但這樣的生活變得岌岌可危,因為兩人正一步步邁向一樁悲劇。裘蒂與陶德在一起多年,他老是偷腥,她總是包容;他活在雙重世界,她則用沉默理解。他決定孤注一擲,她則是來到了底線……
以「她」和「他」的觀點穿插敘事,訴說一段支離破碎的關係、一對走向毀滅的伴侶、無法做出的讓步,以及無法保守的承諾。作者精心計量的細節、耐心營造的氛圍,儘管一開始就得知結局,情節發展卻依舊讓人大吃一驚。全書挑戰你走出自己舒適圈的能耐,進入一個任何事都可能發生的世界。你,準備好了嗎?
作者簡介:
A. S. A. 哈莉森 一顆新星的殞落,出版史的一頁傳奇
加拿大籍作家,是名前衛的藝術家,喜歡解構再結構大家慣以為常的觀點。曾出版四本非文學類書籍,同時也是藝術雜誌編輯。創作力源源不絕的她,於2004年開始寫小說。儘管屢遭退稿,仍維持高度紀律,督促自己交出更好的作品。她甚至在寫作時會戴上工業用耳罩,阻隔零零雜雜的小噪音,專注經營自己的小說世界。
《沉默的妻子》是她初試啼聲的文學作品,但在創作後期卻發現自己罹癌,當時的她以為能安然度過考驗。書稿完成後,立即獲得企鵝出版社的青睞,接著是全球20多國重量級出版商的競價。電影圈也開始打電話給她。試讀本送出後,多位知名作家驚嘆她的降臨,紛紛期待這本書的出版。然而,死神最終沒有放過她,哈莉森於2013/4/14病逝,距離自己的第一本小說上市只差了兩個月。
在沒有作者宣傳、豪華行銷的情形下,《沉默的妻子》締造了出版史的奇蹟。讀者驚人的口碑效應,讓亞馬遜書店總監直呼:「除了《格雷的五十道陰影》,很難再找出另一本靠自己賣起來的小說了。」
企鵝出版社的資深編輯柯爾回憶,哈莉森交稿後,自信《沉默的妻子》將受到讀者的認可,但沒想到竟然是如此強大的迴響。企鵝出版社為了她的逝去感到遺憾,認為她是一位「偉大的女性與難能可貴的天才作家」。
過世前,她還不放棄第二本小說的創作。她的先生,視覺藝術家約翰•梅西說:「她一直說要打破生命的框架,她辦到了。」
譯者簡介:
劉嘉路 任職出版社十數年。認為譯者如同詩人,都是「帶著腳鐐跳舞」,在限制和規範中如何翻新、保留意象就是樂趣所在。近期譯作包括:《說不出的故事,最想被聽見》(圓神出版)。
章節試閱
1 她
時序剛入九月。裘蒂.布瑞特在廚房準備晚餐。多虧了這間公寓的開放式設計,她的視線毫無阻礙地穿過客廳,朝面東的窗戶望去:夜色已將天空和湖泊暈染上了藍色。地平線如一抹深藍細線,近在眼前,彷彿伸手就可觸摸。裘蒂很喜歡這道弧線,感覺自己被圈了起來,而這也是她喜歡住在二十七樓摩天公寓的原因。這裡是她的空中王國。
儘管已經四十五歲,裘蒂仍自認年輕。她不會將希望寄託在虛幻的未來,反而是積極活在今日,珍惜當下每一刻。她直覺地認為世間的事情肯定不能盡如人意,但也足可讓人接受而繼續走下去。換句話說,她並沒有體會到自己的生活、青春和活力已經走到碎裂前的最後階段,也沒有察覺到她和陶德.吉伯特這二十年來的婚姻已逐漸腐鏽,更沒想到她對自我的認識,以及對自己行為的約束力會如此脆弱,因為短短幾個月之後,她竟然成了一名殺人兇手。
如果現在就有人告訴裘蒂這項事實,她肯定不會相信。她的生活根本不會出現「謀殺」兩字,那是虛渺的名詞—那種她在報紙上讀到不認識、也永遠不會遇見的陌生人的事故主題。她尤其很難相信會有家庭暴力,日常生活中的摩擦怎麼會擴大到這種可怕的地步?如果先把裘蒂自我約束的習性撇開不談,她缺乏對這些事情的體認其實有跡可循:她不是理想主義者,相信好事和壞事同時依存;她不會主動挑起事端,也不會輕易掉入爭吵的陷阱。
當裘蒂在砧板上忙碌時,一隻黃金獵犬在她腳邊蹲坐著,全身的金毛光滑柔亮如絲緞。裘蒂三不五時朝狗兒丟一片胡蘿蔔,狗兒張開嘴接住後,開心地用臼齒磨碎。從她把當時還是圓滾矮胖的小狗仔帶回家之後,一人一狗就開始了這個晚餐前的小儀式,雙方也頗能自得其樂。小狗仔轉移了陶德年過四十突然想要孩子的渴望,這種渴望彷彿在一夜之間湧出擴散,怎麼也抑止不住。裘蒂把小狗仔取名「佛洛伊德」,這樣她才好找機會取笑那位跟小狗仔同名、奉行男權主義的傢伙—她在大學時可是被迫認真學習了他那套理論。佛洛伊德放屁了!佛洛伊德翻垃圾桶了!佛洛伊德追著牠的尾巴轉哪!這隻黃金獵犬也是天生好脾氣,絲毫不介意自己成為她取笑逗樂的對象。
她把心思全放在烹飪上:挑揀蔬菜、剁碎各類香草。她喜歡烹飪的緊湊感:爐火蓄勢待發、計時器標示流逝的時間、結果好壞立刻揭曉。她能感覺到廚房後方的安靜氣氛,手邊所有的事情即將趕赴終點,而終點就在她聽見他轉動門鎖裡的鑰匙當下,那是整段過程她最享受的一刻。她仍認為替陶德準備晚餐是件大事,仍然為命運把他離奇撞入自己的生命而感到驚異。那原本只該是一次「不會再有下次」的意外,更不會期待兩人一起品嘗美味佳餚的未來。
***
等到她聽見他進來時,湖泊和天空已經蛻成光滑柔軟的暮靄。她關掉頭頂上方的燈,留下間接照明燈的柔和光暈,解下了圍裙,手指沾些口水,梳理太陽穴旁的髮絲。她全然期待著,仔細聽著他在玄關的一舉一動。他逗弄了狗,掛好外套,掏出口袋裡的東西放在玄關桌上的銅缽裡。當他檢視郵件時,安靜了一會兒。她把煙燻鱒魚擺到盤子上,搭配疊成扇形的餅乾。
他是個身材高大的男人,有著沙色頭髮、青灰色眼睛,全身充滿了活力。當陶德.吉伯特走進室內,所有的人彷彿都醒了過來—如果有人問她,她愛他哪一點時,她就會這麼回答。而且,他隨時都能輕鬆逗弄她笑出聲。跟其他男人不一樣的是,他可以同時做許多事情。因此就算他在講手機,還能同時幫她繫上項鍊或是教她如何使用兩段式開瓶器。
他用手指輕輕滑過她的額頭,繞過她身旁,來到櫥櫃拿出雞尾酒杯。
***
「告訴我,你在想什麼?」她說道。
他的眼皮眨了幾下,朝她微笑。「這味道真是好極了。」他說。他伸手拿起半滿的酒瓶,重新斟滿兩人的酒杯。「妳覺得這瓶酒味道如何?」
他喜歡談論酒。有時候,光是他們當晚喝的酒都可以變成整頓晚餐的主題。但在她還沒來得及回答之前,他用手掌用力拍了頭一下,說:「我忘了告訴妳,這週末要釣魚。有幾個朋友想參加。」
「釣魚?」她說。
他已經吃完兩份厚片牛排,正在用麵包抹乾盤子上的肉汁。「星期五下班後出發,星期天回來。」
陶德從來不釣魚,而且就她所知,他那些朋友也沒人對此有興趣。她立刻明白了——一絲懷疑也無——他是委婉地用「釣魚」來暗喻某些事情。
「你要去嗎?」她問。
「我還在考慮。」
她依舊切著牛肉,但是速度加快了。她進食的方式,對他的耐性是一大考驗—取一小口放進嘴裡,然後像是關囚犯似地含著不動。她知道這一點。她吞下半咀嚼過的肉塊,結果卡在喉嚨裡,反倒引起嘔吐反應。她開始說話困難、喘不過氣,他立即起身在她背上拍打。最後,那塊引來麻煩的碎肉迸射而出,落進她的手裡。她看也不看地把它擱在盤子邊緣。
「你決定好了再跟我說。」她一邊用餐巾擦擦眼角,一邊這麼說著:「如果你要去,我可能會送地毯去清洗,再做些橘子果醬。」
她其實並沒有計畫要做上述任何一件事,只是找些話來說罷了。她總覺得他不會對她撒謊是件好事,這表示他不會過度渲染自己的事情,胡亂加些變成謊言的具體細節。這裡的問題不在於他用遁辭說話,而在於他從來不會在週末到外地,他以前根本不會做這種事。
「對了,」他說:「我買了禮物給妳。」
他走出飯廳,回來時多了一個包裹:平扁的方形,大約是平裝書的大小,用牛皮紙包裝起來,還用隱形膠帶固定。他把它放在她碟子旁邊的桌面上,再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來。他時常買禮物送她,這讓她非常開心,但當禮物是用來安撫時,她可就沒那麼歡喜了。
「有什麼特殊原因嗎?」她問道。
「沒有啊。」
他的臉上還帶著笑容,但是和樂的氣氛已開始瓦解。她應該把各種東西砸在飯廳裡,彼此應該要發瘋似地相互甩頭怒罵。但她只是拿起包裹,發現它幾乎沒啥重量。
2. 他
他喜歡一大早起床,開始一天的作息。這些年來,他已簡化早上作息。沖冷水澡,減低逗留的欲望。刮鬍組同時結合刮鬍泡和安全刀片。他在半漆黑的臥室裡穿衣,避免吵醒睡夢中的裘蒂和小狗。有時候,裘蒂會睜開眼睛說:「你的襯衫已經從洗衣店拿回來了。」或是「那件褲子越來越鬆垮了。」他則回應:「繼續睡吧。」他用柳橙汁吞下綜合維他命,橫向刷牙(儘管方法不對卻很快速)。起床後三十分鐘,他搭上電梯,前往停車場。
七點不到,他已經坐在辦公室裡,那是在南密西根大道一棟四層樓建築的四樓,位於羅斯福地鐵站下方。這棟大樓是他經過十年拆房歷練後,第一個大手筆改建的案子。
他第一通電話是打給熟食店,請他們照例送早餐過來—兩份三明治和兩大杯咖啡。等待期間,他從書桌抽屜拿出一個菸草舊鐵盒,撬開蓋子,把裡面的東西倒在桌面上:喇叭手捲菸紙、一盒火柴,以及一小袋乾燥的花瓣草葉。他以前沮喪的時候,發現抽些大麻可以轉換淡漠的心情,幫助自己專心投入工作。他現在已經習慣捲菸、點菸的儀式,也喜歡以陶然的好心情開始新的一天。他拿著大麻菸走到窗戶邊,把煙霧往外吹入流動的大氣中。倒不是說抽大麻是什麼天大的秘密,他只是覺得「陶德•吉伯特有限公司」不應該聞起來像是年輕人聚會場所。
以前從他的窗戶可見到廣闊的藍天,如今他見到的只是一小片不規則的藍色塊,漂浮在街道上的公寓高樓之間。這也總好過什麼都看不到吧,何況他可不想唱衰建築業的榮景。總之,他把注意力放在公車站等車的人群。即使今天早晨晴朗暖和,仍然有些人站在堆滿垃圾的候車亭裡。他認出一些眼熟的通勤族:戴著大耳機和背包的吊兒郎當男生,戴著棒球帽、老是菸不離手的瘦皮骨老傢伙,穿著印度紗麗、牛仔外套的懷孕女子。幾乎每一個人都專注著路況,伸長脖子看清楚驅近的公車。一如平常,總會有一、兩個人走下人行道緣石,站到馬路中央好看清楚些。等到公車終於出現在遠遠一端時,緊張的氣氛才明顯舒緩下來,彷彿眾人是同心連氣。而當公車臨近時,原本鬆散四處的人群匯聚成焦躁不安的縱隊。當然,他在好幾個街區外就看見了那班公車。有時候他覺得上帝就在四樓的窗戶外,與他同在。
熟食店的服務生把他的早餐放在書桌上,取走壓在紙鎮下方的早餐錢。他大口吃著早餐,發現吐司有些濕軟,不過培根倒很酥脆。等他吃完兩個三明治、喝完一杯咖啡,便又繼續打電話。這一次,他連絡的是他的不動產仲介,對方已經幫他找到潛在買家。這是好消息。公寓型住家大樓只是過度期間的計畫,如果必要,他寧願持有這棟樓,只出租房間。不過原先計畫是把它賣出去,利用賺到的錢繼續下一個冒險—規模更大的辦公大樓,超越自己的頂級案子。
史黛芬妮在九點二十分抵達。她先花點時間整理、歸檔,在三十分的時候才帶著記事本、檔案夾走入他的辦公室,拉過椅子在他面前坐下。史黛芬妮儘管三十五歲了,仍然帶著女孩氣,蓬鬆的頭髮紮成馬尾。他總是饒有興味地看著史黛芬妮就坐:若直接坐在他前面,他只能看見腰部以上;若坐在他右手邊,她會把手臂擱在書桌上做筆記,還會習慣性翹腳。橢圓形的桌面立在長方形的底座上,底下有充裕的空間讓腳伸展。因此不管是什麼理由讓她伸展雙腿,他就會認為當天是他的幸運日。如果她穿牛仔褲,他就得以欣賞她的胯部和大腿;如果她穿裙子,他就會欣賞她的膝蓋和小腿。她不會調情,但也不在乎他會注意她的坐姿。她今天穿牛仔褲,坐在稍遠一點的位置,所以他只能注意緊貼在她上衣鈕釦下方的雙峰。她的身高不滿一百五十公分,這也是她胸部何以特別引人注目。
***
他看了時間,動手打了電話。話筒彼端傳來的「喂」帶著濃濃睡意,他驚異的同時也升起一股愉悅感,喚醒了他的生殖器。
「妳該不會還在床上吧?」
「嗯哼。」
「妳不是要上課嗎?」
「等一會兒才過去。」
「妳這被寵壞的懶豬。」
「我倒希望如此呢。」
「妳身上穿什麼?」
「你以為呢?」
「一絲不掛。」
「你為什麼想知道?」
「妳為什麼認為我想知道?」
「這是認真的問題?」
「不算是。」
「你說的唷。」
他們就這樣你來我往地談了好一會兒。他想像住在北克萊蒙分租公寓的她,躺在狹小臥室、凌亂床單裡的模樣。他在兩人交往初期去過那裡一次,她那時身上還有幾處地方沒讓他碰觸。事後在廚房裡,她的室友問了一堆惱人問題,多數跟他的年齡和他的妻子有關。在那之後,他們開始約在麥迪遜街上的皇冠飯店,那裡的員工懂分寸、不饒舌。
他跟她說話的同時,仍感到各種奇異的感覺撞擊著,讓他不禁懷疑自己不是陶德,而是另一個男人趁他過去幾個月沮喪神遊的時候潛入他的身體。在那一小段他遇見她的日子裡,她讓他拾回生命。他欠她這份生命禮物,她讓他重新體認當男人的感受—不光只是愛,還有渴望、情欲,以及野心⋯⋯既豐富又狂亂的命運。即使是他的心急也是一份禮物,希望和她偷歡的焦急就這樣整天騷動著他。即使是他的忌妒也是一樣禮物。他知道她有權利挑一個年輕許多的情人,也擔心她早晚會明白這一點。儘管痛苦,至少他還站在「活著」這一邊。
忌妒對他來說是新鮮事。他慣於周旋在女人之間而感到自信。根據裘蒂的說法,這種自信來自於一個全心奉獻的母親澆灌在獨生子身上的愛。儘管經濟困窘,母親情願只當兼職護士,也要把多數時間留下來照顧他,以彌補從事建設工程的酒鬼丈夫對孩子的漠視。當他還是高中生時,就學著到處賺錢、負責任,擔起母親經濟供養者的角色。也由於如此,不光是他的母親,連他母親的朋友、他的老師,以及他認識的女孩都對他多所稱讚。女人喜歡他。她們喜歡他是因為他知道如何關心她們。他關心娜塔莎,純粹是因為她的年輕、引人遐想,以及不知足,而非她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不過娜塔莎有種危險性,讓他警覺到自己老去的年齡和搖搖欲墜的活力。
當史黛芬妮拿著一疊支票要他簽名時,他還在講電話。他來回走呀走的,來到了窗戶邊停住。她把支票放在桌上,等著。他知道史黛芬妮明白他跟娜塔莎之間有那麼一回事。儘管娜塔莎只來過這裡一次,但套句史黛芬妮說的話,她當時的神情彷彿想一口把他吃下肚似的。有哪個助理會用這種口吻跟上司說話?而且這一陣子,史黛芬妮都會在他們講電話的當下正巧走進來。他只能尷尬唐突地掛上電話,就跟現在一樣。她把手裡的鋼筆用力推給他,彷彿兩人是在比劍擊一樣。
離開辦公室之前,他打了電話給裘蒂,說他不回家吃晚飯了。這是禮貌性的提醒,她早就知道他今晚會跟狄恩見面,但他喜歡讓她知道自己還是顧慮著她。他是幸運的男人,也清楚眼前的事實:儘管她喜歡窩在家裡,但是纖細的身材與深色的頭髮仍活脫是個大美人。她知道他不可能每天晚上都待在家裡不出去。他有些朋友必須回家吃晚飯,有些人甚至連喝杯啤酒的自由也沒有。還好,他交遊廣闊,很多人不是單身就是已離婚,所以他總能找到人陪他喝幾杯。必要時,他也不介意消磨一整晚。
他和狄恩.柯法克在高中就認識了。狄恩是他認識最久的朋友,也是唯一認識他父親的朋友。當他形容自己的父親是個刻薄的老王八時,狄恩能完全體會。狄恩就像是自己的家人,像個兄弟。不過他也是娜塔莎的父親,這一點以後可能會是個麻煩。也或許不會。如果狄恩知道他們兩人之間的事情,很難說他會有哪一種反應。他當然會很震驚,但是等到他冷靜後,誰知道會如何?他們或許能幽默以待,他可以稱呼狄恩「爸」或「岳父」,狄恩還可以叫他滾一邊去!十之八九事情都會順利解決的。至少他不需要自己跟狄恩說起這件事,這是娜塔莎的事情。兩人當初決定好,等她認為時機成熟的時候,自己告訴他。
***
回市區的路上,他打了電話給娜塔莎,期盼她會出來跟他吃午飯,不過她正巧吃著三明治。
「我們講話的時候,妳就吃著三明治?」
「我才剛打開包裝紙,正要咬一口。」
「放著吧,我們到法蘭西絲卡去吃飯。」
「我沒辦法,還要去上課。」
「我下班後,妳可以跟我見面嗎?」
「我四點到七點要當保母。」
「那我過去。」
「這不太好。」
「妳知道我再晚一點就得忙了。」
「我們明天一塊吃午餐吧。」
「這樣子我今天就見不到妳了。」
「你想你熬得過去嗎?」
「妳在吃哪種三明治?」
「裸麥薩拉米香腸。在曼尼那裡買的。還特別加了芥末。」
「妳坐在哪裡吃三明治?」
「我說過了,我在上課的路上。」
「妳現在走路去上課?」
「我在摩根街上,朝北走。剛經過圖書館。如果你再不讓我掛電話,我就要遲到了。」
「告訴我,妳今天穿什麼衣服。」
她裝出生氣的樣子,但他知道她心裡是歡喜的。她喜歡這些小殷勤裡的性暗示。他描繪著她沉甸甸的後背包、套在她肩膀的背包肩帶、陷進疊滿肉腸三明治的潔白牙齒。她今年大四,明年春天就要自歷史系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她還沒想到工作的問題,她想要的是結婚,建立一個家庭。關於這一點,她已經告訴過他,他會是很棒的爸爸。他因這暗示感到鼓舞,這表示她不會為了更年輕的男人而甩掉他。但他還沒想過兩人的未來,只除了私下承認他與娜塔莎之間的感情很特殊,不是一時的激情放縱而已。激情對他來說像是一種運動、一種消遣,不會侵占你的生活方式或讓你不知所措。然而,這段感情卻幾近混亂、要求很多、令他上癮,還讓他時時擔憂。有時候,他發誓要改邪歸正不再繼續下去,但多數時候,他覺得自己像是在愛情浪花裡苦苦掙扎的人。
週末度假屋是她的點子。她發現了這間在狐河邊的鄉村旅館,有十七畝的林地、溫水泳池,以及法國主廚。她先預訂了房間,再來說服他答應。他們可以在早餐後再回到床上去,晚餐前一起洗澡。他們可以在樹林裡漫步,在和煦的空地做愛。相較於平常只能偷偷尋歡片刻,他們可以悠閒地好好享受這些過程……諸如此類。
「或者你寧願跟裘蒂待在家裡?」她問道。
他希望她不要把裘蒂扯進來。他跟裘蒂的生活屬於一個跟她互不相關的世界,相互平行:那裡的生活一切平穩,也將會如此繼續;無可挑剔的歲月甜蜜地記錄著過去,也會如此延伸至未來。有一次,他不小心告訴娜塔莎,裘蒂在床上像一條死魚。他並不想要貶低裘蒂,只是想讓娜塔莎安心。他是個寬宏大量的人,可以輕鬆接納不完美的世界—特別是跟女人有關的時候。他有這樣的天賦去接受事物原本的面貌,與之共存。跟裘蒂在一起如此,跟娜塔莎在一起也如此。
他能容忍裘蒂的一個原因是她的高學歷。不像娜塔莎只會拿到一個學士學位,裘蒂有一個博士以及兩個碩士學位。他不介意她腦袋靈光,他討厭的是年輕男孩老是藉此戲弄他,說裘蒂比他優秀多了。這不是說,他真相信高學歷有什麼了不起的價值。接受教育是為了掌握權力—威脅在於,如果你不上學,你以後就會淪落到麥當勞打工。在美國,聖杯指的是金錢而不是教育。
***
他在一家英國風味的酒吧吃午餐,抗拒點啤酒的渴望。等他回到辦公室,史黛芬妮交給他先前交代的報價資料,以及他需要打電話連絡的事項清單。他在沙發上伸直身體,打了電話;之後,睡了午覺。他醒來已經四點半,前往健身房。
上健身房是近來的事情。一開始是要對抗他的沮喪憂鬱,醫生告訴他充分的運動可以釋放腦內啡,天然的體內止痛劑。他起先並沒有感覺到腦內啡,每次想到去健身房就會抗拒,直到他遇見了娜塔莎。他現在跟著一位教練練習,使用啞鈴而不是健身機器,他還開始穿戴護腕、健身手套和背心。
敦促自己健身一小時後,他再度有了活力,還有些性渴望。等到沖澡、擦乾身體,他把毛巾圍在腰上,也不管在擁擠的更衣室裡根本不可能安靜說話,就撥了電話給娜塔莎。事實上,他也得克制自己腦裡的畫面,他可不想在那裡勃起,對著一屋子光著身體的人招展。
他等她連說三次「喂」才出聲。
「你是變態嗎?」她問道。
「一點也沒錯。」他回答。
「你知道我可以在來電顯示上,看見你的名字和電話吧。」
他決定,下一次要用公共電話。
***
他把保時捷交給泊車小弟,走進德雷克酒店的休息室,一眼便瞧見狄恩.柯法克坐在吧檯邊。這間帶復古風格的夜店俱樂部有著酒紅皮椅、閃亮的原木和舊世界既有的陽剛之美,是他另一個舒適卻也誘人的家。現在擠滿了下班後報到的人潮,嘈雜聲此起彼落,他在人群中穿梭前進,在狄恩背上重重拍了一下,在他左邊的空椅坐下來—較像是扶手椅,而不像高腳椅。
「嘿,老弟!」狄恩一口喝光生啤酒,說道:「抱歉,沒等你就先喝了。」
「你這傢伙,」陶德說:「你欠我一杯。」
「老弟,我總是欠你一杯酒啊。」狄恩說。他對酒保揮揮手,舉起兩根指頭。狄恩的體重不斷上升,再加上他的圓臉和雙下巴,看起來就像個胖寶寶。他穿了一套夏天的藍色西裝,雖然裡面的免燙襯衫在腹部撐開了,但總比露出白色汗衫的時尚絕症還好一些。他的手巾從胸袋裡探出頭招展著。過去十二年來,他在一家塑膠公司擔任業務主管,對這份工作挺滿意的。
酒保在他們面前放下兩品脫的酒。陶德好好痛飲一杯,用手背擦去嘴邊的酒沫。健身過後的疲倦感讓他只想靠在椅子上,被動地消化酒精和周邊的氣氛。狄恩是天生的業務員,陶德只要問他關於利潤的事情就能讓他滔滔不絕。「上次我見到你,你提到利潤縮水,」他放出了魚餌。狄恩順勢說了市場占有率和目前的競爭狀態,陶德也就心不在焉地聽著,也藉此放鬆。他寧願聽產品和現況的發展,就算是塑膠業也有吸引人之處。不過,狄恩對目標、價格、利潤和市場預測更有心得。
陶德一年大約會見到狄恩兩到三次。一向都是狄恩打電話約時間,但如果狄恩沒動作,陶德就會主動約。儘管他們在不同的世界,但是共同的過去將兩人緊緊連在一起。他們一起在芝加哥西南邊的阿什本市長大,一起念柏根中學,一起加入曲棍球隊,一起吸食迷幻藥,甚至一起失去童貞。失去童貞這件事發生在狄恩父親的露營車裡面,他們兩對情侶進行四人約會。狄恩兩杯酒下肚,一定會說起這件往事。這對狄恩來說別有意義,因為他跟陶德分享了那次性體驗,無意間聽見了陶德從男孩轉成男人的聲音。陶德也在那裡分享了狄恩經歷的一切。儘管這對陶德也深具意義,但他不希望酒吧裡的每個人也知道這件事。為了避免這發生,他要了菜單,讓狄恩專心想晚餐該吃什麼。
吃完漢堡,他們從啤酒換成烈酒。這時候,狄恩就會開始回憶過世十年的妻子。
「別告訴我,她不是每個男人都夢想擁有的完美妻子。」狄恩說:「一輩子只會遇見一次的好女人。」他挺直腰桿強調,下意識點著頭,就像那些搖頭公仔一樣。「一次,」他把手指關節重重敲在吧檯上,重複說道:「如果他幸運的話。」
「她是個好女人。」陶德同意說道。
「這女人真是他媽的女神啊,」狄恩說:「我根本就是崇拜這女人。你知道的。」
他等著陶德的附應,這一點陶德從沒讓他失望過。陶德認為,狄恩此刻的感性和他過去在妻子在世時就已緋聞不斷的事實之間,沒有什麼矛盾之處。
「她知道你有多愛她。大家都知道。」
「沒錯。」狄恩說:「我崇拜這女人,現在還是一樣。你知道我是說真的,因為如果是假的,我早就再婚了;但我並沒這麼做。」
近幾年狄恩交往了一連串的女友,沒有一個比得上他過世的妻子,沒有一個有希望取代她的位子。狄恩對此也感到滿意,他喜歡追求征服的遊戲,也喜歡成功挑起女人的興趣後那種權力在手的滋味。
狄恩喝完他那一杯,血脈賁張的興奮取代了感性。人潮退了一些,高聲叫嚷轉為嗡嗡低語,狄恩的心思遊蕩著。他在高腳椅上低頭轉來轉去,目光盯住了一個約莫他女兒年紀的年輕女孩。她剪了鮑伯頭,塗著鮮豔的口紅,在那裡大談闊論著。不時假裝注意著陶德,彷彿他想要對她做什麼或是他想要她對他做什麼。隔著一段距離與嘈雜對話中,她毫不知道狄恩鎖定了自己。倒是其他那些在聽力範圍之內的人注意到了,紛紛轉過頭看著狄恩。
同時,陶德已經溜進自己的世界。他那慷慨的本性膨脹了,擴散到整間夜店。他的大度雅量讓他不去評判或驅逐任何人,不管是狄恩或是狄恩這會兒忙著製造的敵人。在場的每個人都被納入他的善意之中。陶德喝了酒就是這樣,他會如牧師般沉靜,寬恕和修復所有的人性。
狄恩對那紅唇女孩失了興趣,現在將注意力轉向坐在他右側的女人。她身材微胖,年紀跟他相仿。在酒精催化的昏沉魔力下,她很可能會狄恩產生興趣。然而,她正忙著跟坐在另一側的男伴說話,那男伴根本沒注意到狄恩這號人物。狄恩的嘴朝女人的左胸,用舌頭做著隔空舔食的動作。對方發現了,嫌惡地瞪了他一眼,要他滾開,並把高腳椅挪開些。狄恩聽到「滾」字,回她一個猥褻的動作。這使得那女人和戴著設計師眼鏡的滑頭男伴站了起來,互換位子。這男人現在擋在狄恩和女人中間,不過他沒對狄恩說什麼,反倒是狄恩「很有原則地」戳了他的背部。
「嘿,兄弟,」他說:「我不過是在行使身為男性物種的權利。」
「對啦,你何不到別的地方去行使這個權利?」那男人回話。
狄恩轉過來對陶德說:「我只是在行使男性物種的權利,這是個自由的世界,不是嗎?」
1 她
時序剛入九月。裘蒂.布瑞特在廚房準備晚餐。多虧了這間公寓的開放式設計,她的視線毫無阻礙地穿過客廳,朝面東的窗戶望去:夜色已將天空和湖泊暈染上了藍色。地平線如一抹深藍細線,近在眼前,彷彿伸手就可觸摸。裘蒂很喜歡這道弧線,感覺自己被圈了起來,而這也是她喜歡住在二十七樓摩天公寓的原因。這裡是她的空中王國。
儘管已經四十五歲,裘蒂仍自認年輕。她不會將希望寄託在虛幻的未來,反而是積極活在今日,珍惜當下每一刻。她直覺地認為世間的事情肯定不能盡如人意,但也足可讓人接受而繼續走下去。換句話說,她並沒有體會...

 6 則評論
6 則評論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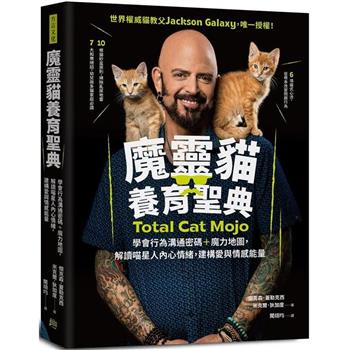









“沉默”原來是對自己殘酷,面對丈夫不斷的偷腥,卻視而不見的包容,其實是不想讓自己陷入可悲,令人同情的弱者。 陶德的變心不是他最大的過錯,要離開二十年盡心盡力沒有對不起他的女人卻不願回饋一絲該給對方的道義及尊嚴,這是讓我唾棄的,也是激起裘蒂殺他念頭的主因,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當狠下心、情不再時,當初的承諾與誓言都變成利刃,千刀萬剮著彼此。 撇開懸疑與推理的角度,這本書更刻劃著人心的深層,這是讓我從一開始進入故事後,就不想罷手的理由,一方面想探索裘蒂的內心世界,一方面也想從陶德這個角色了解出軌男人的心理。 最後再補充一開始拿到這本書的感覺,封面的設計簡單有吸引力,內頁像是用再生紙的感覺,我個人超喜歡,整本書拿起來很輕鬆很舒服,內容也讓我愛不釋手,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