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全球最知名搖滾團體U2,全球賣出超過1億7000萬張專輯
榮獲22項葛萊美獎殊榮,史上贏得最多座葛萊美獎的樂團
迄立音樂界超過三十年、首次唯一授權自傳
2006年英美首度同時出版精裝版,2009年12月平裝新版上市
2011年繁體中文版搖滾上市!

※出版即獲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滾石雜誌名列U2為「百年百大音樂家」中的第22位。
※主唱Bono曾被Q音樂雜誌推崇為「樂壇50位最具影響力人士」的榜首。
※主唱Bono曾獲《Times》選為時代年度風雲人物,並多次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iPod於Video機上市時,更趁勢推出限量U2紀念版以饗廣大樂迷。
※2009年10月25日在美國加州的現場演唱會,透過YOUTUBE向全球樂迷直播內容,成為YOUTUBE一大盛事。
※非常擅於運用歌詞表達對政治、時局、社會的看法,立志「以搖滾樂改變世界」。U2長期援助非洲貧民,發起「免除外債」,打破貧富階級;支持環保運動,多次提出減碳議題;為愛滋病及弱勢國家問題,強力遊說梵蒂岡當局;在強力搖滾當中毫不避諱,大量使用「教會專有名詞」,打破流行音樂與教會音樂的圍牆……多次在演唱會中提除拆除原子彈:拆除人與人之間的原子彈,拆除國與國之間的原子彈,拆除神與人之間的原子彈……以其廣大影響力,在全球樂迷間造成正面影響力。
※《U2 BY U2》一書由一九六○年代開始,以第一人稱方式,由四位樂手開始說起自己的故事,與音樂的連結、透過生活啟發的創作、對於週遭環境社會的關注,對於全球年輕樂迷不只帶來在音樂上更是在社會意識上的影響。一個劃時代的搖滾樂團背後最真摯的情感。
※除透過四人各自第一人稱撰寫文章,以及彼此對話記錄外,更搭配大量相關照片包括幼時照片、組團後表演時、平日生活及與樂迷互動等,為U2樂迷的最佳收藏。
史上最撼動人心的搖滾樂團
Bono、The Edge、Adam Clayton、Larry Mullen, Jr.
四個搖滾靈魂,秉持著對搖滾的忠誠信仰、30年堅固情誼,
建構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搖滾王朝,
聽過U2,你就會知道搖滾樂的偉大。
首度完全披露U2樂團每一張專輯、甚至每一首歌的創作過程
真實展露自1970年代成團以來四位團員間既赤裸又感動人心的互動《滾石雜誌》形容U2是當今唯一最重要樂團,他們驚人且永不枯竭的創作力被譽為「來自上帝的恩賜」;經典專輯『The Joshua Tree』48小時內創下白金銷售,打破英國唱片工業有史以來「銷售速度最快的專輯」紀錄;成軍至今創造全球逾1億7千萬張唱片銷售,拿下22座葛萊美獎音樂奇蹟;主唱Bono還曾為名導文溫德斯的電影「百萬大飯店」(2000年柏林影展銀熊獎[評審團大獎])主導製作原聲帶;Bono積極實踐「搖滾樂改變世界」的雄心壯志,為消弭非洲負債愛滋病等課題,奔走於各國政要之間;2004年Apple iPod在全球推出U2限量版iPod機型……似乎所有的不可能都在他們身上變可能了!
U2創團以來的樂團經理及摯友保羅.麥吉尼斯Paul McGuinness表示:「曾有人這樣告訴我,在美國你往往一次只能因為一件事情而出名,但這個理論在Bono身上並不適用。」
Bono說過:「
流行音樂常常說萬事OK,搖滾樂則是聲明萬事很不OK,
但你可以改變它,搖滾就是有一種公然挑戰的性格,讓你在每天早上找到一個起床的理由。」
《U2 BY U2》一書由一九六○年代開始,以第一人稱的方式,由四位樂手開始說起自己的故事,與音樂的連結、透過生活啟發的創作、對於週遭環境社會的關注,對於全球年輕樂迷不只帶來在音樂上更是在社會意識上的影響。一個劃時代的搖滾樂團背後最真摯的情感。
2001年主唱Bono的父親Bob因為癌症去世,Bono與父親之間的冷戰關係成了他永遠修復不了的破洞。Bono因此創作出〈Sometimes You Can't Make It on Your Own〉懺悔與父親的關係,並且在葬禮上演唱這首歌曲,Bono曾在這首歌的音樂錄音帶註明:「我真希望能更了解他就好了。」
作者簡介:
※從愛爾蘭都柏林開始,1975年教堂山中學四位高中同學在一場廚房試奏會中,在毫無專業音樂基礎但憑著一股熱情下組成了樂團:主唱波諾Bono、吉他手艾吉The Edge、貝斯手亞當Adam Clayton、鼓手賴瑞Larry Mullen, Jr.,以及樂團經理保羅Paul McGuinness開始長達超過三十年從未解散、從未更換團員的持續合作
※風靡全球IPod於Video機上市時,更趁勢推出限量U2紀念版以饗廣大樂迷。
※榮獲22項葛萊美獎殊榮,是當今的紀錄保持樂團。
※滾石雜誌名列U2為「百年百大音樂家」中的第22位。
章節試閱
開場白
波諾
有些時候,我真覺得我加入U2是為了要拯救世界來的;同時也是為了拯救我自己。走在路上,我會遇到一些人把我當成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般崇拜。
每當有人說:「嗨,和平大使!」我就可以聽到賴瑞憋著氣偷笑:「算你走運,他沒有給你來一記頭槌。」樂團其他人不太能了解為何我如此執著於非暴力(non-violence),因為他們知道沒有人可以比主唱更深入體會歌曲。他們了解我之所以被這些歌曲的特質、主題所深深吸引的原因──因為我的生活、我的性格,和這些歌曲所表達的可以說是迥然不同。我內心裡是有一把無名火,但這把火並非沒來由地亂燒,而是其來有自。我已經很擅於掩飾這個部份了。
我現在是好多了,但演唱會結束後通常還是很難跟我說上話,因為我會極度亢奮個一個小時左右。而且,假使演唱會的狀況不太理想,我會有受騙上當和不完美的感覺。和一般搖滾演唱會比較起來,U2演唱會的後台更像是拳擊賽、或者足球賽結束後的選手休息室。你要記得,對U2來說,每場演唱會都必須是最棒的。假使它不是最棒的,那其中一定有什麼原因。我們設下了非常高的標準,我們也一直都很清楚是誰付薪水給我們。我們的觀眾值得享受最棒的曲目組合,我們可不是像自動點唱機那樣一首唱過一首就能出來混的。我可以感覺到台下觀眾們是不是開始降溫了,如果是的話我就會丟個爆點給台下,那個爆點可能就是我自己。反正就是把導火線給點了,看會發生什麼事再說。
要唱這些歌、飆這些高音,是需要極度的專注與投入的。你必須融入這些歌曲、與它們同在。所以,當你在唱〈血腥的星期天〉(Sunday, Bloody Sunday)時,你就是站在德里(Derry)的事件現場 ;或者當你在唱〈以愛之名〉(Pride in the Name of Love)時,你就是金恩博士(Dr. King)在孟菲斯(Memphis)的人權集會中的一員;我就在那裡。你的朋友正在用成袋的海洛因摧毀他自己的人生──那是〈壞〉(Bad)。你要在這些情緒當中。我想這個樂團很能了解我是在那樣的狀態裡的。有些時候,這對他們來說一定很辛苦,因為他們的主唱會一直在那些情緒裡頭。
本性是很難改變的,這得要花上很長的時間。然而在你精神生活上最特別的轉變,不是你的缺陷消失了,而是它們開始為你工作,原來的缺點現在變成了優點──你原本是個多嘴的人,後來你成了歌手;你本來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後來你成了需要掌聲的表演者。我聽過很多生命改變、奇蹟出現的例子,有些人在一次禱告後就成功戒了毒癮,也有夫妻在「放手、順從上帝的指引」之後挽救了婚姻。但這些都和發生在我身上的不同。與其說「我曾經迷失過,但我已經找回我自己」,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我曾經完全迷失我自己,但此刻我已經不像以往那樣茫然了」。我正在一點一點地找回我自己。對我來說,我的精神生活就像是──每隔一段時間,看看使用手冊上的小字,讓電腦重新啟動、重新開機。這讓我能夠慢慢地重建一個更好的形象。雖然這得花上好一段時間、而且還沒完沒了。
艾吉
搖滾樂是這個時代特別的產物,在音樂史上前所未見,因為它完全是靠「電」玩出來的。
當你在錄音間裡彈弄電吉他時,把你馬歇爾(Marshall)音箱音量盡量調大,等音量大到已經無法準確重現原有的音色時,你就製造出壓縮聲音的效果了,感覺就好像聲音是從喇叭當中爆出來的一樣。你會覺得所有一切都在你身旁轟然倒下,實際上這就是你的耳膜受到巨響刺激之後會有的反應──它會自然而然中止運作。這種聲音帶來的快感就是人們之所以著迷於搖滾樂的原因;這不是民謠吉他可以帶給你的。
電吉他的音色確實有種神奇的魔力。不管品牌是斯特拉托開斯特(Stratocaster)、泰勒開斯特(Telecaster)、雷斯保羅(Les Paul)、還是探索者(Explorer),電吉他的長相不都是一節木頭、上面有個琴頸(neck)、幾根絃、再加個拾音器(pick-up)嗎?不過事實上,這中間有很大的不同,每一款電吉他遇上不同的效果器、音箱都會產生不同效果。我並不特別鍾情於哪一支電吉他,我還沒那麼神經質;我只是看到這些電吉他各自展現了不同潛力。我對於這些聲音、還有現代科技加諸在這些聲音上所形塑出來的效果,特別感到心醉神迷。
現在看起來,我似乎是沒辦法想像沒有音樂要怎麼過日子。不過說老實話,假使不是U2讓我相信這是有可能的,我還真不知道自己會走上專業音樂人這條路。我們幾個長大之後就一直在一起,這四個一九七五年就決定要組團的男人可以說展現了無比的團結與向心力。這個樂團在過去之所以被人們認為成功的種種因素,到今天仍然沒有改變。我們現在還是會一起創造偉大的音樂、激盪出新的創意,造就充滿感情、激情、靈性、與無限可能的演出。
就某種程度來說,U2是個功能失調的樂團。我們之所以成為這樣的樂團,是因為我們都不是什麼太出色的樂手。別人的曲子我們玩不來,所以我們必須自己動手寫歌──這種音樂上的失能還是常常出現在我們身上。有時候我們走在路上,聽到自己以前的歌,我會一邊抓著頭在想,「我那時是在彈什麼啊?聽起來很怪,我到底是怎麼彈的?」不過我們已經懂得怎麼樣化缺點為優點了。或許我們算不上搖滾史上音樂成就最高的樂團,但我想我們會是其中最有原創性的。
我們每個人各有不同的人格特質。波諾是「超限表現者無名會」(Over-Achievers Anonymous)的主持人兼創辦人 。他追求成功的動機非常強烈,而且熱愛生命。他渴望能經歷生命中所有的一切,不過也就是這一點,讓他很容易受到傷害。我有時候會擔心媒體讓大家對他以及他的信念形成一種迷思,我希望這些誇大的報導不會讓大家忘了其實他也是一個平凡人、一個努力想找回自我的平凡人。每個人內心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掙扎,試著要去釐清自己正在做什麼或想往哪裡走。U2寫了一些關於這種掙扎的歌曲,但我們自己其實就跟所有人一樣困惑。
我呢,我所追求的方向和波諾不太一樣。我心裡頭的那股好奇心會不斷驅使我,讓我想去找出一些方法,創作出最新的歌曲。而且在清楚地了解我們的目標和方向在哪裡之前,我是不會輕言放棄的。假使波諾參加的是「超限表現者無名會」,那我恐怕得去上「工作狂無名會」的十二步驟課程 。我們兩個都從彼此的意志力、專注力、和幹勁上得到很大的鼓舞。
亞當和賴瑞跟波諾和我是完全不一樣的人。亞當有著非常高尚的情操,他是我們樂團的良心。早些年,我們幾個人對基督教一派狂熱時,亞當的寬宏大量與仁慈證明了他是我們當中最具有基督教精神的。就某些方面來說,因為他是我們當中比較不需要煩惱歌曲或歌詞怎麼寫的人,他反而有更多的自由投身在你想都沒想過的事物上,或是拋進一些天外飛來的想法。他是我們的「外卡」(wild card) ,他是天生的前衛派。賴瑞則是整個樂團的基本要素。他務實、可靠,是一個非常小心謹慎的人,總在我們激動過頭的時候適時踩一下煞車。每當我們這艘船快要撞上石頭的時候,賴瑞會負責穩住船隻、我會拿起望遠鏡指出該去的方向、波諾鬆開船索、亞當則會氣定神閒地待在動力室裡頭。
我們是一起長大的,也一起學習怎麼樣玩音樂。有時候,我們的念頭是會有心電感應的。波諾在唱的時候,我可以感覺到他希望這個音要怎麼和;甚至當我獨自在寫歌的時候,我一邊寫也好像可以邊聽到他在唱的聲音。不過真正有趣的地方是,當這些歌發展到下一個階段,也就是亞當和賴瑞加入我們一起演奏的時候──全新進化的歌曲誕生了。我想,到頭來,你能夠集四個完全不同觀點之大成於一身,這就是樂團的力量。它所能成就的絕不是我們任何一人獨力可以達到的。
亞當
我從以前就一直想當個搖滾明星。打從我十五歲拿到第一把貝斯的那個時候起,那就是我的夢想。我這輩子也沒什麼其他好說的。
假使U2沒玩起來,上帝會指引我去處。我從來沒替這檔子事擔過心,因為我把大量的企圖心和精力,都投入在讓自己變成我心目中理想的那樣的人。我逆來順受,一旦機會出現,我就絕不放過。後來我的人生繼續前進,我的想法有了很多改變,也拋棄了不少過去的生活方式。我安於和我的人生伴侶蘇西(Susie Smith)之間的關係。我發現,我其實是個遠比自己過去想像中來得簡單、而且低調的男人。我也意識到,讓我在這條道路上持續前進的動力並不是「搖滾樂」這個標籤,而是音樂本身,以及和同志之間的革命情感。
我不會說U2是什麼好玩的事;那是工作。我們每回相處並非總是充滿歡笑。波諾常嫌棄我們有多爛──這個「我們」當然也包括他自己。錄音室裡經常圍繞著緊張的氣氛。我們必須很快做出評估,假使這個音樂稱不上出色,那它就上不了檯面。那不是一個輕鬆的工作環境,因為當你的點子受到挑戰時,你必須隨時準備好要捍衛自己的論點,或是跳開來從其他角度進行思考。創作的過程非常累人。感覺上好像我們在確定最後版本之前,必須要嘗試過各種可能性才行。我們從A開頭的歌挑到Z開頭的歌,然後常常還要再從頭走一遍。我們會試著找出一些難以捉摸的歌,一些可以代表我們現在在情感上、身體上、心靈上的狀態,卻又夠新鮮、夠激動人心的歌曲。假使我們拿出來的不是最棒的,何必自找麻煩呢?
毫無疑問,波諾是我們團隊的動力。你很難拿什麼字眼來形容波諾,因為他絕對不只是你所形容的那個樣子而已,或許說他是一團矛盾的組合還貼切點。他絕頂聰明,是個邏輯超清楚的策略家,但是他不曉得要怎麼做水煮蛋。那倒沒關係,我想他對做水煮蛋也沒什麼興趣。他就像人們所謂的「男子漢大丈夫」;他清楚知道自己渴望的是什麼,而且他會為了這個目標義無反顧。在他眼裡沒有極限,只有無盡的可能。就某部份來說他就像是U2的靈魂,他象徵了我們每個人都有的那一部份。
艾吉也很有企圖心、很積極,但是除非你跟他夠熟,否則你可能會因為他的仁慈與慷慨而看不到這個部份。他總是把別人擺在第一位。好比說他雖然正在熬夜趕他的工作,但只要你請他幫個什麼忙,他都會放下手邊的事來全力幫助你解決問題。他是很棒的朋友,也是很棒的同事,頭腦非常敏銳。波諾是成果導向的人,而艾吉就比較重視細節,兩個人加起來就形成了我們超強的創意組合。
賴瑞是個心思非常細密的傢伙,是非常忠實的好朋友。他也很一板一眼。他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就跟他打鼓一樣──你拍子沒打準就是沒打準;沒什麼有點準又不會太準的。順帶一提,拍子不準的通常是我。話說回來,賴瑞真是一個天生的鼓手。你很難解釋他是怎麼辦到的,因為你看到的就是他現身,然後打鼓。他可能會從健身房運動完後直接過來,在他的位子上坐定,接著就開始演奏。看起來完全不費他吹灰之力。
我說不上來我給U2帶來了些什麼──也不見得就是我彈的貝斯。有時候艾吉會彈貝斯,波諾也會,那不是我的專利。只要是好的點子,不管是誰想的,它就會被留下來。不過當整個樂團在一起共同演出的時候,就會有一些不同的東西出現。那些東西是無法被量化的,但總是會讓我激動萬分。就是我們之間這種激動與能量所迸發的火花成就了U2,我們四個人,缺一不可。
賴瑞
對於成名這一類的事情,我從來都不是感到太自在。我不喜歡自己太受注目。
要說我入錯行,那也沒錯。就打鼓和在錄音間裡搞創意這兩件事讓我沉迷。一旦我開始做這些事,我就覺得當什麼搖滾巨星這種事很可笑。
我看過很多關於U2的八卦報導。有時候我看到我們幾乎被奉為天神、或者被稱為命運的主宰,我就會大笑不止。搞U2就好像是在駕駛一列失控的火車,你得使出吃奶的力氣緊抓著它不放。
多年來,我們經常苦於音樂表現上的缺失,光是一起合奏就是一大挑戰了。現場演出的確就像是一場障礙賽,場上摔倒的事也是有的。所以我努力穩住自己。我會想,縱使大家在演奏時亂了腳步,他們也會知道,身為鼓手的我會想辦法控制住局面──只是這說的比做的容易。
亞當和我一向是相依為命。艾吉在舞台上總是有很多好忙的,他得按很多按鈕、變出很多不同的聲音。波諾可能會忙著爬上鷹架、然後跳到觀眾群裡頭去──有時候我們也不知道他人在哪裡。偶爾只有我和亞當在舞台上,所以我們已經學會怎麼樣和對方互動、溝通,大部份樂團的節奏搭檔是不會這麼做的。
你可以說U2是一個民主團體。我們做決策的過程,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過,只要能夠出聲辯論、爭取、表達意見的人就能佔上風。話說回來,假使你待的團裡有像波諾這樣健談、好辯、又有口才的人,我們其他人想佔上風也很難。
我們四個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人,各有各的性格。不論是在專業領域或私領域,我們每個人的需求都不一樣。我們是一個團體,但我們絕對不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假使要說U2有什麼特別的,那和我們個人一點關係也沒有,只有當我們一同站在舞台上或在錄音間裡才會發生。這很難形容,更別提要怎麼解釋這一回事了。然而,這是我們仍然在搞U2的唯一理由。當我們一起玩音樂的時候,就是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開場白波諾有些時候,我真覺得我加入U2是為了要拯救世界來的;同時也是為了拯救我自己。走在路上,我會遇到一些人把我當成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般崇拜。每當有人說:「嗨,和平大使!」我就可以聽到賴瑞憋著氣偷笑:「算你走運,他沒有給你來一記頭槌。」樂團其他人不太能了解為何我如此執著於非暴力(non-violence),因為他們知道沒有人可以比主唱更深入體會歌曲。他們了解我之所以被這些歌曲的特質、主題所深深吸引的原因──因為我的生活、我的性格,和這些歌曲所表達的可以說是迥然不同。我內心裡是有一把無名火,但這把火並非...
目錄
目錄:
1960-75 // 男孩們的故事 stories for boys
1976-78 // 時過境遷 another time another place
1978-80 // 凝視太陽 staring at the sun
1980-81 // 進入中心 into the heart
1982-83 // 唱首新歌 sing a new song
1984-85 // 以愛之名 in the name of love
1986-87 // 發光時刻 luminous times
1987-89 // 外邊美國 outside it’s America
1990-93 // 追求表象的遊戲人生 sliding down the surface of things
1994-98 // 日子有好有壞 some days are better than others
1998-01 // 最後的搖滾巨星 the last of the rock stars
2002-06 // 直到世界末日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
目錄:
1960-75 // 男孩們的故事 stories for boys
1976-78 // 時過境遷 another time another place
1978-80 // 凝視太陽 staring at the sun
1980-81 // 進入中心 into the heart
1982-83 // 唱首新歌 sing a new song
1984-85 // 以愛之名 in the name of love
1986-87 // 發光時刻 luminous times
1987-89 // 外邊美國 outside it’s America
1990-93 // 追求表象的遊戲人生 sliding down the surface of things
1994-98 // 日子有好有壞 some days are better than others
1998-01 // 最後的搖滾巨星 the la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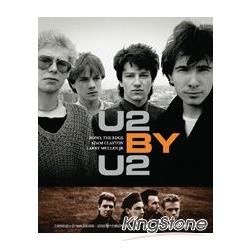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