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羅網中
1
長方形的屋子裡,光線黯淡。
第一扇窗戶被打開了,淡黃色的光照射進來,排列成行的桌子依稀可辨。第二扇窗戶又被打開了,屋子裡明亮多了,這裡的一切已經可以看清。教室前面的黑板,右上角用白色的粉筆寫著一九╳╳年╳月╳日一行字,黑板下面的溝槽裡,用過的粉筆頭和掉下的粉筆灰堆在一起。當第三扇窗戶被打開,屋子裡更明亮了。講課用的講台在黑板的右側,椅子被推進講台,上頭擺了黃褐色的粉筆盒和紅色的花瓶,裡面插著暗紅色的茵比拉花,花瓣已經謝了,無力地垂在花瓶上;光線照射進來,將投在講台上的玻璃花瓶影子添上了一層淡紅色調。教室後面的一角,靜靜地站著裝垃圾的簍子、掃帚和撢子,這個角落上方是剛被打開的最後一扇窗戶。
小提琴聲輕輕地傳了過來,並不是什麼美妙動人的曲子,只是初學者拉出來、高高低低的音符而已。在早晨,一片寂靜的早晨,小提琴聲遠遠地從教職員宿舍飄了過來……
發打開所有的門窗之後,走出了教室──這是今天早晨他必須整理完的最後一間教室。這兒總共有十六個房間,其中包括十二間教室、三間教職員辦公室、音樂教室、工藝教室和醫務室。有個房間有五個窗戶、兩扇門,每天早餐和晚間時分他都必須開關好門窗,他所做的一切是規定好了的,已經成了習慣。
他從教室大樓走下來,沿著大樓周圍的水泥甬道,拐到樓後的七個大水罐附近,打開水龍頭往橢圓形的鐵皮桶裡放水;水滿以後,關好龍頭,提著水桶和抹布又向教室走去,爬到樓上,用力擦著地板。他跑來跑去,把樓上的走廊地板擦完了,然後又去換水,擦樓下的走廊,完成後再轉去擦另一間教室大樓樓上走廊的地板。這裡只有樓上鋪的是地板,樓下是水泥地(是學生們星期五開會用的)。
地板擦完以後,他把水桶和抹布放回水罐旁,然後回到樓裡,進了校長休息室,打開放在緊挨著校旗旁邊位於校長辦公桌後面的玻璃櫃,櫃子裡陳列著銀製的獎盃和錦旗,這是從很多次的比賽獲勝得來的。發從櫃子的下層拿出國旗,搭在肩上然後關好櫃子,下了樓,來到學校前面的旗杆旁,把國旗繫在旗杆底部的繩子上。旗杆基座以水泥築成,外圈用磚頭砌成圓形,在兩者間種著仙丹花,綠葉之中正開著橘黃色的花朵。
今天早晨陽光和煦,晴朗宜人,發卻感到有些悶熱,他背上的衣服已被汗水溼透了。
學童們身著灰白色的衣服,自四面八方陸續抵達學校。他們拖著零亂的書包,有的還帶了飯盒……
達品老和尚以及當師兄手捧著缽盆從椰子園中走出來,穿過學校前方的草地,正要返回佛寺,廟童們則提著飯盒跟在後頭。發放下手中還沒繫好的國旗,蹲在那裡向路過的和尚雙手合十,之後再站起身,把雙股的繩子拴在旗杆的底部。
佛寺的大鐘急促地響著,最後三響卻有些間隔,就像收音機報時一樣,告訴大家現在是早晨八點鐘。日上三竿,愈來愈多學生從四面八方抵達,從城裡搭車來的老師已經到了,住在教職員宿舍的老師還沒有來,家裡離此處不遠的校長也還沒有到。
如果是雨季,發會站在擺有洗腳缸、通往教室的樓梯邊監督著學生,因為總有人不洗腳就提著書包和飯盒就這麼跨進教室。有些學生是提著鞋子來學校的,不到校門口他們是不想穿上的。學校有個新規定,每個學生,特別是五到七年級的學生必須穿鞋。在那個季節,田園的道路十分泥濘,走路的時候腳上免不了要沾上許多爛泥,有些學生不慎會跌得滿身泥漿,到了學校,走進教室之前是必須洗乾淨的。
但此時還是涼季,所以洗腳的事也就不過分要求了。
笛聲、琴聲和咚咚的鼓聲雜亂地響了起來,大家自顧自地吹奏、拉彈、敲打自己的部分。七年級學生是群音樂家,他們正在音樂教室裡試著自己的身手,為早晨列隊做操做準備。一位對音樂有所涉獵的新進老師提議將早操配上樂隊,校長和老師們也無一不表贊成,其中的意思無非想表明,這所鄉村學校的程度並不比城裡的學校差。學生們已經練了很長時間,從現在起,唱國歌的時候要有笛子、琴和鼓聲伴奏;走進教室的時候,也要有音樂伴奏,讓學生踩著鼓點、一二一二地踏著步。這也是學校和小鎮正在興旺發達的一個象徵,要不了多久,大概就會有小提琴加入,因為音樂老師每天早晚正在勤奮練習著呢!
太陽愈升愈高,一切都愈發顯得紛繁雜亂,差不多有三百名學生在草地上,樓前樓後玩耍著。身穿白襯衫、藍裙子和黃褐色褲子的學生到處跑著、跳著、追逐著。人聲鼎沸,嘈雜成一片。
鈴聲響了起來,身穿白衣的、藍裙的、黃褲的一下子突然都停住了,他們有的走著、有的跑著向旗杆處靠攏。大孩子排起隊總比低年級的小孩子快,年紀小的孩子還在那裡你擠我、我推你,隊伍好像條蛇,班導師手執教鞭在一旁督促著。樂隊站在最前面,樂隊之後是一年級,後頭依次排列到七年級為止。敲第二響鐘聲的時候,學生的隊伍就都排得整整齊齊的了,還不夠安靜的只有最小的孩子們。
國歌聲響了起來。
念經的聲音。
隊伍行進的鼓聲響了起來……
一隊隊的學生隊伍走進了教室,三五成群,邊走邊談的老師是最後的一批,後頭只剩下空曠而碧綠的草地。
兩座教室大樓又像清晨一樣安靜了,不同的是教室裡有了學生和老師,他們正各盡其責。
發來到樓上,走進校長休息室,每個早上他都得來聽候命令。校長正坐在辦公桌前看報,年齡大約四十出頭,圓圓的臉龐,上唇稀疏的髭鬚修剪得整整齊齊,這使他整張臉顯得莊重而有魅力。見到發進來,他雙手將報紙一闔,只用一隻手疊了起來,隨手將報紙往桌上扔。
「吃飯了沒?」校長問道。看來這句問話是無需回答的,就像人們打招呼常用的「要去哪兒」一樣。
「等一下去把學校前面的土翻一翻,要離水泥甬道一公尺遠,長度就像走廊那個樣子,挖成四塊,中間留些間隔,把土翻鬆,準備種彩葉草,種點花草樹木可以美化一下環境,說不定,城裡的大人物會來檢查。」他停頓了一下,然後問道:「今天能做完嗎?」──這才是需要回答的問話。
「我想可以。」
「好吧,加把勁。」他朝發笑了笑,「噢,還有一件事,巴里查老師告訴我,今天早晨他去洗澡的時候,你老婆敞開胸口讓他看乳頭,不管怎麼樣,你總得管管老婆呀!喂,她到底是不是你老婆?」校長齜牙笑著問。發沒有回答。他接著說:「住在教職員宿舍的老師都是從別的地方來的,別搞得太難看,壞了我們小鎮的名譽。」校長大概再也想不起什麼,於是便說道:「啊,好了,你去忙吧,不然事情做不完了。」他重新拿起報紙,接著往下讀。
發轉身走出屋子,沿著走廊走著,教室裡老師站在講台上正給學生上課,他覺得大家的眼睛好像都在盯著他,好像每個人都知道了巴里查老師看到了「良」乳頭的事。(「良」是發對繼母頌鬆的稱呼,他不知道叫她什麼才好。當父親在世的時候,他和她說話的次數完全數得出來。父親去世以後,他和她生活在一個屋簷下,說起話來總得有個稱呼。要叫她「媽」嘛,但他本來就沒有媽媽,也不會喊任何人為媽媽;叫「後媽」吧,但頌鬆的年齡幾乎比父親小了一半,「大嬸」、「阿姨」、「大姐」都行不通。她不是他的親戚,他也沒有親人,於是只好叫她為「良頌鬆」,但這種叫法又把本來應該親近的關係變得疏遠了,叫習慣了,便只剩下「良」一個字,但聽在別人的耳朵裡,似乎又帶著點親暱的味道了,好像是發把父親妻子的名字「頌鬆」故意改成了「良」①,目的是占有寡婦頌鬆最私密的那個部位而不至於害臊一樣。)
發打開樓梯下面放雜物倉庫的門鎖,把鑰匙塞進褲子口袋,拿起鋤頭、鐵鍬和一團繩子,向校園前面走去。他將繩子拉成一條直線,便動手翻起土來。
佛寺裡吃齋的鼓聲響了起來,他抬頭看了看太陽,看看校園前面的草地,樹木青蔥翠綠,孩子們玩耍的草地中央的土地是一片白色,又帶點粉紅,草皮幾乎全被踩死了。六七個男孩經過他的身邊向佛寺跑去,這些孩子是廟童,他們必須去侍候和尚;而發是學校的人,他有義務去侍候教職員們。他把視線從草地上移開,看著自己剛剛翻起的土地,好像到處泛著閃閃爍爍的金光。他站起身,讓眼睛適應一下強烈的陽光,之後就把鋤頭和鐵鍬收進倉庫,繩子留在原地,以便下午回來時再接續著幹活。
學校後方,大水罐裡的冷水沖去他一身的燥熱和溼黏。他用雙手接滿了一捧水,將臉浸在水裡,一上一下擦洗著,再用手輕輕地敲著後方肩頸,像是能消除疲勞,感覺舒服點似的。他關上水龍頭,兩隻手溼答答地在胳膊上抹了抹,好像用身體擦手。清風吹拂過來,未乾的皮膚感到一陣涼意,當他走到校門口的時候,身上附著的小水珠就全乾了,而他身穿的黃色卡其布衣服卻仍舊留著水的痕跡。
發走上樓梯,在每間屋子門口等著老師們午餐點餐的紙條。校長是回家吃的,尼帕老師自己帶飯菜,剩下的七位老師發會替他們買炒飯、什錦燴粿條、醬油炒米粉還有一些別的。小店就在佛寺後方,那裡也是雙排座小型私人巴士的停靠站。
他穿過校園前方的草地,鑽進佛寺後面的椰林,急匆匆地踏上了兩旁高度及膝、凌亂灌木叢的小路。這條路一向沒什麼人走,人們常走的是寺院後方的大路,發走這條路是因為可以順道經過他的家,而且也比大路近得多。
發順便回了家一趟,打算把早上良袒胸讓巴里查老師看乳頭的事情問個清楚,但茅屋裡沒有人,只好走出家門轉向沙石大路奔去。走了一會兒,向右一拐,在馬路的盡頭有四五家賣生活日用品的小商店。發走近賣粿條的小店,門前一輛藍色飾有白線條的雙排座小巴士停在那裡等乘客。他把老師點餐的單子送給在灶前忙著的車大媽,然後便躲到汽車後面的一張桌子旁,坐在那裡等著,眼睛看著坐在小店裡等車的三個人。
「要去城裡呀?琪!」他問道,被叫了名字的那個人點了點頭。然後他向小店裡頭望望,年輕的司機正坐在桌旁和一個叫達珉的長髮青年下象棋。
「發不發車呀,格留?你他媽的還要摸多久!你從城裡回來,人不是擠得滿滿的嗎!是在怕賠錢喔?」坐在車裡著急得快冒火的老先生、老太太們也表示同意。
「等一下啦,我十二點一定準時開車,耐心點,下車來喝杯冰咖啡、冰開水什麼的……你也……」年齡比琪小一點的司機高聲喊著回答,然後又低頭看著棋盤。琪從車裡下來,坐在旁邊,微聲地抱怨著。
「你這個死傢伙,十二點不走我一定踹你!」
「一言為定,……你來幫我看看,我快輸了。」格留把琪的注意力引到了棋盤上。
「誰說你會輸?他才要輸了呢!這麼走你看看怎麼樣!」達珉出車將了一軍。
「哎呀,我下不過你,你也來一盤吧!」看到琪搖了搖頭,格留便把棋子收進盒子。小店立刻安靜了下來,過了一會兒,格留轉過臉開玩笑地問發:
「你要去城裡嗎?我可以等你。」發搖搖頭。
「我去幹嗎?」
「嘿,去開開眼界呀,現在那裡有『茶室』了,知不知道『茶室』呀?」格留追問著,就像下棋的人要逼得對方走投無路一樣。
「不知道。」發直楞楞地回答,他不知道這個年輕人想弄清楚什麼。
「你不想喝點茶嗎?那可是燒滾滾的茶呀,喝了會出汗,爽死了。」
「嘿,我常喝呀!」發自豪得很,自己並不落伍,不必到市場去,他每天都泡茶喝,在他出家當沙彌的時候就開始了。
「那你繼母呢,她也跟你一塊喝嗎?」格留笑瞇瞇地問,轉過臉來衝著琪笑,好像在演一齣鬧劇,逗等車的乘客開心,消磨消磨時光。
「當然呀,怎麼不一起喝!」發提高了聲調,覺得自己占了上風,──看看這些人,坐車進城就是為了喝杯茶,這些傢伙看樣子神經有點不大正常。
「那你喜歡在什麼時候喝茶?」
「有空就喝,不太一定。我每天睡前都會喝,喝了喉嚨會很舒服。」發剛把話說完,格留便哈哈大笑起來,笑到前翻後仰。聽了這一語雙關的話,旁邊的人也忍不住偷笑起來。
「舒服,真的舒服嗎?還真是舒服咧!」格留還在笑。
「嘖嘖,奇怪咧,有什麼好笑的,就是喉嚨舒服呀!你是沒喝過茶嗎?」發的語調帶有瞧不起對方的意思。
「意思是,你一天和繼母喝好幾回囉?」
「是呀,你問這要幹什麼?」發才感覺這些話不太對勁,似乎有其他意思。
「沒事,隨便問問。你說和繼母喝茶喉嚨舒服,我問你是不是常常喝,這沒什麼呀!」這時候,格留大概注意到了發眼神的變化。
發的神情像是在聽格留說話,但他卻全然不知道對方在說什麼,他心裡想著,為什麼喝茶的事他們要笑?昨天說到中午喝粥的事情他們也笑。這些傢伙實在很怪,明明還是些小毛頭卻要和他平起平坐。不理他們也不好,自己已經沒有可以說話的人了,還是和他們聊聊吧。他們老愛開玩笑,中午喝粥他們笑,睡覺前喝茶也笑,這是不是和良有關係呢?想到這裡,發的臉色明顯地表現出不滿的情緒,但他盡量忍耐,靜靜地坐那裡不說話,眼睛看著小店外頭,讓格留這小子一個人在那兒傻笑。
聽到車大媽叫他,他才轉過身來走進店裡。
「好囉,發!」
拿了飯趕快往回走,經過自己的家又繞去看看。她還沒有回來,打開飯鍋的蓋子看看,飯還是早晨那麼多。他立刻返身向學校奔去。午休時間已經到了,一群群穿白衣的孩子正湧出校門,有的已經圍住了學校旁邊的小攤子。
「唉喲喂,快餓死了,你怎麼這麼慢啊?」
「做好了就立刻趕來了。」
「哪包是我的?」
「這是我的。」
「這不是你的嗎?沒有雞蛋的。」
「欸,怎麼沒拿點辣魚露回來?」
每個人急急忙忙地拿著自己那份塑膠袋,然後把飯菜倒到盤子裡,沒有人注意發了。他走了出來,還要把剩下的另一些飯菜送到另一棟樓的教師休息室去。
「快點,快點!」看到發拎著飯菜走來,瑪尼老師揮手叫著。
「都在這裡了。」他把一袋袋的飯菜和找回來的錢一併放在桌上。
「哪包是醬油炒米粉?」
「都放在一起了,您打開看看。」
「──這個是醬油炒米粉!」吉迪老師推來一包米粉說。
「好了,發,謝謝。」看到每個人都各得其所,正準備吃飯,瑪尼老師信口說了這麼一句。
發從教師休息室出來,回了家,還是不見頌鬆的人影,不知道她又到哪裡去了。他在學校周圍找了半天也沒找著,廟前的亭子也沒有。他又來到佛寺的院子,看到她在戲棚那裡,坐在戲台上,做出像是要跳舞的姿態。發用慍怒的聲調高聲喊著:
「良,你不打算吃飯嗎?」頌鬆聽到喊叫,回過頭來看見是發,便咧嘴笑笑,又轉過身去看看舞台,捂著嘴說:「官人,奴家來也!」
發看到她這個樣子真想笑出聲來,來時的火氣也消了大半。「走吧!」頌鬆十分聽話,輕手輕腳地跟在發的後面。兩個人從廟的後方往家裡走,一路上發沒有再跟她說什麼。
他們回到家裡,發趕快動手生火,然後把水壺放在爐子上,當木柴紅紅的火舌舐著漆黑的壺底、發出吱吱響聲的時候,學校的鈴聲傳了過來,這表示學校午休的時間已經結束了。發搧著火,想讓火燒得更旺些。
他把熱水澆到盛飯的盤子裡,用勺子把黏成了坨的米飯撥散開來,再拿刀切開一枚鹹鴨蛋,遞給頌鬆一半,自己留一半,還有早晨剩下的半條煎鹹魚,就這麼吃了起來。
「早上巴里查老師洗澡的時候,你給他看乳頭了,是不是?」發的眼睛盯著頌鬆,手裡的勺子停在空中。
「在什麼地方?」頌鬆抬起臉問。
「別裝蒜,是不是真的?」
「根本沒那回事!」
「別想說謊!」發做出凶相威嚇道。
「就那麼一點點,就是這樣呀──」說著就解開領口,露出白皙的皮膚,已經可以看到乳頭旁紅褐色的乳暈。
「欸!」發立刻把頌鬆的手按住,不讓她再把衣服拉下來。
「以後不可以這麼做了,如果妳不聽話,我就把妳趕走!」頌鬆的臉立刻現出了愁容,「還有,不知道告訴過妳多少次了,不能叫我『丈夫』,如果妳再叫一次,我鐵定把妳趕出去,懂了嗎?」他提高嗓門問著。
「知道了,知道了。」她連聲答應。
發放下盤子和勺子,用水瓢舀了點水喝。「等一下妳去把盤子洗一洗,把床收拾乾淨。」發吃飽了,走出茅屋,留下頌鬆一個人在那裡細嚼慢嚥。
發連跑帶跳,才剛鑽出椰林走進學校操場,就看到校長早已站在翻土的地方了。發走過去,剛想問問挖的寬度夠不夠,可是校長卻先說話了。
「怎麼這麼晚?」
「剛吃完飯。」
「還幹別的了吧?」
「什麼?」
「嗯,就是跟老婆『來一下』呀,新婚生活不嫌多呀!」校長笑咪咪地說,像是個性情很好的人。
「唉,校長,別鬧了,我從沒做過那種事!」發的聲音有點惱怒,察覺以後立刻緩和下來,不自然地笑了笑,「真的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這種事,做太多不好,傷身體吶……」校長自顧自地繼續說著。「挖好以後,傍晚四五點的時候澆點水!」他用手指指著那塊地,然後緩緩地朝另一棟樓走去。
發拿回工具,繼續上午沒有做完的活。陽光已經把學校這座建築物的影子趕到後面,發在午後灼熱的陽光下翻著土,不一會兒衣服就被汗溼透了,索性把衣服脫下來,掛在走廊窗戶插銷上。
發的身材算是比較矮小的,在當兵的時候,每次排隊他無法像那些大個子一樣站在排尾,但那時候的他要比現在壯實多了。
每當黧黑的雙臂舉起鋤頭的時候,他的肋骨總隆起一大片,渾身淋漓的大汗使他的皮膚又黑又亮,已經完全不像他穿袈裟的時候那樣容光煥發了,人家談起他的時候都說:「他不會享福,如果在佛寺裡待下去哪會吃這種苦。」
發渾身的力氣變成了翻過的土地,不斷地伸展著,最後終於做完了。
發把衣服搭在肩上,提著鋤頭和鐵鍬到後頭,將黏在工具上的泥土洗乾淨,也把臉和身體洗了洗,這回渾身感到輕鬆多了。又回去把繩子捲好收起,再把這些工具收拾進樓梯下面的庫房,穿好衣服以便到樓上見校長。校長又提醒他休息一會兒以後,別忘了傍晚的時候要澆一次水,他答應以後走了出去。
勞動,能給他安寧和幸福的勞動,完成了。
發又回到他的茅屋。他要頌鬆洗的盤子和碗還是亂七八糟地放在竹床上,根本沒有收拾。告訴她的話就好像沒說一樣。頌鬆不在屋子裡,很可能在佛寺那邊閑逛,自得其樂著呢。他不得不自己動手收拾盤碗,把竹床擦乾淨,做著中午交代頌鬆做的事。
忙完了這些事以後,他又回到學校,在校園裡到處奔波去撿拾那些廢紙和香蕉葉。
放學的鈴響了,學生們自教室湧出來,跑到操場上集合。這次的隊伍並不像早晨按班級站了,而是按回家的方向排。離家最遠的七年級學生是每路的路隊長,如果誰在途中不守紀律,將會被記下名字,第二天早晨要受紀律處分。但路隊長通常都不會報告值班老師的,孩子們都很熟,誰也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夥伴受罰。
學生們排好了隊,值日老師開始講話(也是為了等候打掃教室的值日生,好讓他們一起回去),告訴學生走路要保持隊伍整齊,回到家裡要給父母敬禮、幫家裡幹活、完成家庭作業等等。
一切妥當之後,隊伍便按各自的方向走出了校門。
剩下的只有老師了,他們談談天、開開玩笑,之後就各自回家。
學校空了,再度沉浸在寂靜之中。兩幢房檐塗成白色、樓身為天藍色的教室大樓靜靜地矗立著。門窗全都敞開,白色的窗簾隨風飄動,甬道上的廢紙被風吹起、飄舞著。除了走在後樓樓下走廊的雜役發一個人之外,這裡再也看不到一個活的生物了。
發曾讓頌鬆來學校幫忙,後來卻覺得反而招來麻煩,因為她喜歡把教職員休息室和教室裡的諸如茶杯、粉筆、本子、紙張、花瓶等東西帶回家裡,這些東西對她也沒任何用處,無非是在小屋子裡藏來藏去。發不想為這些事生氣,於是就一個人做著,他覺得這工作反正也不重。
等他把八十扇窗戶、三十二扇門全都關好,又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兩幢大樓全沒了聲息,這意味著他一天的工作算是結束了──但是還沒有……
他回到茅屋,看到頌鬆已經在家了,發要她生火做飯,自己到汽車站的小店裡買點菜。如果是佛日或者在入夏節②的期間,他們就不用做飯,因為佛寺裡的飯菜多到得天天倒掉,他們拿這些東西填飽肚子就行了。在雨季,村民會輪流供給和尚飯食,剩餘的菜餚也是很多的。
可是現在,雨季已經過去,村民只會在佛日的時候才給和尚的僧缽塞得滿滿的,平日的布施不多,所以發和頌鬆必須自己開伙。
忙到將近六點鐘,兩個人才坐下來吃飯。飯後,他讓頌鬆去收拾,自己坐在茅屋裡,看著她洗碗、掃地。忙完以後,就邀頌鬆一起到學校的草地上散步去。
廟童和佛寺附近的孩子正在學校操場上踢足球,兩個住在宿舍的老師也一起加入。黑白相間的足球在碧綠的草地上滾動著,球滾到哪裡,孩子們便追逐到哪裡,好像一塊磁鐵吸引著他們。趕得上的就踢上一腳,有的踢得到,有的踢不著,人群時分時合。球滾遠了,就重新追上去。老師盤到球就餵球給學生射門,孩子們不夠分,便拉著老師的臂膀或褲子讓老師動彈不得,一陣哈哈大笑。
發和頌鬆站在那兒看了一會兒,便走過教室大樓,兩個人又給大樓周圍的花木澆了一遍水。澆完水以後,降下國旗,上樓把它放進校長休息室的櫃子裡,雜役一天的事情總算完成了,他和頌鬆一起回家。
黃昏籠罩了周圍的一切。小提琴的聲音響了起來,和早晨一模一樣,嘶啞的低音和尖聲拉氣的高音長長地混在一起。太陽正在隱沒,對面的天際現出淺藍色,灰黃的雲彩擴散開來,抹染了一大片的天際。暮色降臨,孩子們依依不捨地解散,是該回家了……
發從佛寺裡提來一桶水倒到屋後的缸裡;這水是供日常用的,也是為頌鬆洗澡所準備的,他自己是在寺裡洗的。
佛寺裡洗澡的地方有個水泥砌成的水槽,幾口特大的水缸並列排成一排,和尚、廟童和老師(住在宿舍裡的)都在這兒洗,水是從佛寺裡的汲水唧筒打上來的。發到那兒洗澡的時候,天已經黑了,三名教師也拿著水瓢和浴巾徑直地走來。
「怎麼樣,發?好個大洗特洗呀!」看到發把手插進圍身布洗下體的時候,巴里查老師打著哈哈。老師們衝著他笑,解開身上纏著的浴巾,只剩下一條底褲,把浴巾和毛巾堆放在水缸蓋上,從裡頭舀著水嘩嘩地往身上澆。
「早上你老婆打開衣服讓我看乳頭,有沒有吃醋?」巴里查老師齜著牙笑著,發也對他笑了笑,搖著頭。
「您別見怪,她有點瘋瘋癲癲。」發把肥皂放到肥皂盒裡。
「什麼腫③了?」吉迪老師也湊過來大開玩笑。
「什麼瘋瘋癲癲我不知道,但早上我看到的那東西可是又白又『腫』喔。」巴里查老師轉過臉對吉迪老師說。
「腫了是不是因為捏的,發?」吉迪老師問,發只是呵呵地笑著,並沒有回答。
看發不想答話,老師們只好各洗各的,等發洗完離開了。瑪尼老師說道:
「我們開他玩笑的時候,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
「噯,開開玩笑有什麼大不了的!」
「發大概不會生氣吧,說個兩句而已。讓主人看僕人老婆的乳房,我看他是吃醋了。」吉迪老師說完,哈哈地笑著,邊舀著水沖去身上的肥皂泡沫。
這三位年輕的教師是這個學期剛來的,兩個人是頂替調走的老師,另一個老師的職務是校長新提出增加的,三個人的年齡差不多都是二十歲剛出頭。
他們剛來的時候,發給他們各方面的幫助,像是提東西、搬行李、釘書架等零零碎碎的木工活兒,還幫他們買東西。發對他們很恭敬,雖然發的年齡要比較大些。發的父親達富曾對他們說:「有什麼要辦的事盡量使喚他,有什麼做不好的也盡量說出來。」有時夜裡,發到他們宿舍裡聊天,從發的口中他們了解了不少這個小鎮的人情世故。沒過多久,他們之間就混得很熟了,他們信任發到了這樣的程度,如果要拿東西就把鑰匙交給發,讓他到自己宿舍房間裡去取。
達富死的時候,他們還參加了超度死者亡靈的儀式,鄰人們也來幫助料理,但人數不多。他們從村民的口中知道發是個好人,達富也曾經是個好人,雖然晚年娶了個像自己女兒一樣的年輕老婆,但是加減乘除一番,值得稱道的優點還是不少的。
死者入殮以後,發和他們的往來就不像從前那樣密切了,但不時還是會去會會他們,時間隔的比較長罷了。而當發收留了繼母頌鬆以後,就更疏離了他們,不再到他們的宿舍去了,在學校裡他們才會見著,要不就是在晚上洗澡的時候碰面。
發和他繼母的事,在他們的心目中那是別人的事,只是生活的一個「插曲」而不是「基調」。他們還有不少自己的事要去想,比如工作呀、前途呀、父母呀等等。當然,發和繼母有染的桃色新聞,是他們在緊張工作之餘尋求消遣和樂趣的一種談笑材料。
發向自己的茅屋走去,天空已經完全變成了藍黑色,高大的椰子樹的葉片的暗影在空中搖動著,佛寺裡的發電機噠噠噠地響起來,僧舍被照亮了。他沿著看上去有些發白、彎彎曲曲的小路走著,不一會兒就看到了自己茅屋黑黝黝的影子,屋子裡還沒有點燈。發繞到屋後,想打點水沖沖腳,好上床睡覺。但他聽見到嘩嘩嘩的澆水聲,頌鬆正在洗澡。頌鬆背對著發,不知道後面遠遠地站著人,她解開筒裙上面的帶子,把裙子退到腰間,然後用肥皂擦洗上半身,白白的脊背在黑暗中依稀可見。發咳了一聲想提醒頌鬆,卻見她轉過身來,不但沒有遮掩,還朝著他咧著嘴笑。在她塗肥皂的時候,一對乳房上上下下地抖動著,在朦朧的暮色中看上去是那麼柔軟而富有彈性。
頌鬆轉身和他打了個照面,這使得發大吃一驚,那雙抖動的乳房近在咫尺,雖然在黑暗之中,仍然可以看見。他趕緊把目光移開,看著水缸,用顫抖的手心慌意亂地從缸裡舀了一瓢水,心噗通噗通地直跳著。他從未見過光著上身的女人。打完水立刻走進了茅屋,竟忘了告訴她別這樣洗,但轉念一想,現在正是黑夜,他們的茅屋又在佛寺的後面,不會有什麼人經過的,她想怎麼洗就讓她怎麼洗吧。
黑暗中銀光一閃,當火燒到了柴薪的時候,火焰變成了紅色。他點燃以罐頭盒子做的油燈燈蕊,火焰由小變大,上頭升起了一縷青煙,飄到空中旋即消散。
發點著了爐子,燒了一壺水,然後又拿來椰子殼薰起煙來驅趕蚊子。頌鬆拿著水瓢走了進來,縷縷青煙飄散在屋子裡,宛如在霧中行走。上床之前她又沖了沖腳,然後走到屋角她的床鋪旁邊。當她在屋角的黑暗當中坐下來的時候,竹床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響,身上散發的粉香混合著煙味。頌鬆解開盤著的長髮,任其披散下來,然後悠閑地梳理著。身後巨大的黑影投射在牆上,隨著她的動作晃動。一支歌曲從她嘴裡哼了出來,這是她的小夜曲,發聽不出這是什麼歌曲,從前也沒聽過這種曲調,他只知道她現在大概覺得愜意。
發把開水倒到茶壺,蓋上蓋子悶著。然後起身拍打幾下床鋪,放下蚊帳,一連串習慣性的動作,他默默地做著,沒有和頌鬆說話。
剛剛看到的她的那對乳房的畫面還沒有從心中消散,這對乳房使他覺得自己和她成了陌生人,他為此感到羞愧──為何要有這種東西呢?莫非每個人都需要捏捏它、撫摸它、吮吸它不可?……唉!他責備自己。
弄好了蚊帳,便坐下來一個人默默地啜飲熱茶。不一會兒,頌鬆下了床,輕輕地坐到了他身旁,一股粉香鑽進他的鼻孔。她只裹了條低胸裙,在油燈的光線下,可以看到她豐滿突起的乳房輪廓。
「妳怎麼不穿好衣服呢?」發的語調表明他的內心仍然很不平靜。
「我很熱呀。」頌鬆轉過臉回答。
發起身躲開,把爐火和地上的火弄熄。鼓聲和鐘聲從佛寺裡傳來,這表示在經堂裡的和尚已念完了晚經,大概是晚上八點多鐘。狗聽到鐘聲也汪汪地叫著。他相信這是狗看見了吊死鬼來分享和尚念經所帶來的福分,此外也許還有無親無故的鬼、孤苦伶仃的鬼、餓死鬼──大概不包括父親在內吧,因為他每逢佛日都會去滴法水。
發上床準備鑽到蚊帳裡睡覺,但他覺得茅屋中似乎還缺少點什麼。
「呃,妳怎麼還不放下蚊帳呢?」
「我想和你一起睡。」頌鬆像孩子似地微笑著,但發卻覺得她的臉和往日不同。
「不行!」他生硬地說,「把蚊帳放下來!」
頌鬆起身走到自己的床鋪那裡,發看著直到她鑽進了蚊帳,他才吹熄了燈,然後摸黑掀開自己的蚊帳,躺了下去。一個世界──他的蚊帳以外的世界結束了。
然而蚊帳裡的世界卻開始了。他躺到蓆子上,骨頭和蓆子同時發出了響聲,他伸手向枕邊摸了摸,看看手電筒還在不在,有時夜裡狗叫得凶,他得爬起來拿著手電筒去學校周圍察看一下,這也是他的份內工作。
為了通風,茅屋開了扇窗戶,月光從這兒照射進來,所以屋內並不像下弦月的夜晚那樣漆黑一片。夜裡,昆蟲振翅鳴叫,聲音十分清晰。其實這種聲音在此之前並非沒有,只是他沒有聽見而已;燈火熄滅、夜色籠罩一切的時候,周圍一切的聲音格外清晰,讓他可以分清是什麼東西發出來的。頌鬆翻了一下身,竹床晃動著,發出吱吱呀呀的聲音,發仍靜靜地躺在那裡,讓心頭的思緒隨意漂流……
想到白天他翻過的土地,校長說要種上彩葉草,但要上哪兒去找種子呀?他家裡也就那麼幾棵,真看不出美在哪裡!嗯,但倒比種花好一點,因為得看顧著才能免於孩子們去攀折。真是糟糕!頌鬆也喜歡花,特別是紅色的仙丹花,見了非摘不可。不知道她是什麼毛病,說她瘋了嗎也不像,她不吵不鬧但卻讓人無法放心。她腦子裡想著些什麼呢?怎麼會解開衣服讓人家看乳頭呢!今晚還要和我一起睡,真是不像話。嗯,不過大概不是那麼回事,也許她想做那件事了吧?父親死了一個多月了,聽人家說那種事是會上癮的,如果嘗過了滋味,不是輕易就能忍得住的。唉,慾望……她是不是色迷心竅了呢?她如果真的這樣那我該怎麼辦?!唉!爸爸,你真是給我留下了個枷鎖。如果沒有她,我就會為父親還願出家去了,不會像今天這樣遭受精神上的折磨。我的名譽掃地了,一掃而盡了……霸占繼母……毫無辦法!沒有一個人願意相信我連碰都沒碰過她,父親不是知道我從沒有和她有任何瓜葛嗎?那為什麼沒人相信我呢?連校長也不相信!頌鬆的嘴我也管不住,還和拉邁姑娘吵架,竟然說我是她的丈夫,不知她怎麼說出口的,真是丟人,唉──(發長嘆一聲)如果找別的女人做老婆大概也沒什麼,最令人煩惱的是她是父親的妻子!要不然把她趕出去好不好呢?還是把她騙進城去,然後自己偷偷跑回來以示清白,辭掉學校雜役的工作,出家永不還俗如何?嗯,好哇……如此村民們就會說,你睡了她然後一腳踢開,讓她流離失所,無依無靠,還可憐兮兮的,這反而更傷人吧!好吧,假設我把她趕走了,村民們會不會相信我和她毫無瓜葛呢?頌鬆今天說這種話是因為她精神不太正常,你倒想撇得一乾二淨了!你看看頌鬆吧!你坐車回家她會坐在店裡等你,天黑了你還不回來,店家要關門能不攆走她嗎?坐得太久人家也會趕的。頌鬆走出店來,東瞧西望,到處找你,行人你來我往,亂成一團,她扯這個、拉那個都以為是你,她推這個、拉那個的,還不是跌跌撞撞的,她心裡何嘗不害怕?她到處跑,東找不著,西找不見,精疲力盡,汗流浹背,像大熱天高樓林立的巷子裡伸著舌頭喘氣的狗一樣。夜裡你要她去哪兒睡?睡在馬路邊上嗎?不能洗澡也無法換衣服,你給她的錢能用幾天?說不定這口袋裡的錢還會為她招來橫禍。你想想看,這樣過了一兩個星期,人會髒成什麼樣?衣服骯髒,破爛不堪,滿身汙泥,一股汗臭味,身體能不紅腫潰爛吧?!頭髮會像亂麻雜草般結成硬塊,攪成一團還散發餿味,誰見了都會躲!她大概只能靠撿飯館的殘羹剩飯活著,要是顧客覺得噁心,店主還能不趕她嗎!你要她到哪兒去吃飯?像路旁的狗一樣翻垃圾堆嗎?床鋪在馬路邊,飯菜在垃圾桶裡!她是人啊不是畜生,你光養她一個人會怎麼樣嗎?飯菜有的是從寺裡取來的,想趕她走是為了證明你自己的清白,還你一個好人的名聲,所以他人的死活你就不管了?(發翻來覆去想著趕走頌鬆的事,最後他下定了決心)──我不能這麼做!我還不知道她是從哪裡來的!每次問她,她只是說從曼谷來,從克薩善那一帶來的。曼谷、克薩善……為什麼她的兄弟姐妹不來看看她呢?或許她根本就沒有兄弟姐妹?
發長嘆一聲,翻身側臥了過去,灑在竹床上的月光漸漸短了起來。
別想了,夜深了,睡吧,明天還要早起。他讓呼吸鬆弛下來,同時在心裡默念著:睡吧──睡吧──,安撫著自己,試圖拉回紛亂的思緒,但要不了多久又像脫韁的野馬奔騰起來……
村民們的結論實在草率,誰也沒有親眼看見我和頌鬆做過那種事,為什麼他們一口咬定而且深信不疑呢?從前他們喜歡我、稱讚我,可現在他們卻憎恨我、嘲諷我,好像過去的我已經死了,留下的只是個無可救藥的新的我,可是我的為人並沒有變呀!他們是依憑什麼來判定的?只因為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同住在一個屋子裡,就非得做那種事不可嗎?或者換作是他們自己,他們必定會這麼做嗎?唉,算了!誰想說就讓他去說吧,反正我沒做過他們說的這些事!總有一天他們會明白的!可是要等到哪一天呢?哪一天才能真相大白,才能爬出這個地獄呢?看不到還有哪條路能走!要不然我真的按照他們說的那麼做,讓大家都知道,如何?可是,這麼做的苦果你已經嘗到了,人們口中議論的「幸福」,你根本沒沾上邊啊!
「……啊,不,爸爸,我只是想想而已!」(他不由自主、自言自語了起來,為這一閃而過的想法感到羞恥,不知道這是不是他真正的想法。)──為什麼你會有這種可恥的想法呢?為什麼你只想些骯髒勾當,不想想好事呢?這樣想對嗎?你沒有做過人們所議論的那種事就落得如此下場,要是變成事實,你不就是名副其實的下流胚子嗎?現在,至少自己心裡是清楚的,你沒有做過那種事,事實會像朋友一樣安慰著你;但如果真的向下沉淪,你還剩餘什麼呢?
發翻了個身,仰天躺著,右手放在額頭上,頌鬆的鼾聲從她的蚊帳裡響起來。
怎麼會睡不著呢?若是睡著了就不會想那麼多了,睡吧!睡──吧!睡──吧!爸爸幫幫我!我睡不著……睡──,睡──,他再次誘導著自己。睡吧,如果我總是這樣睡不著,會不會變神經病呢?從前我當兵的時候是睡得很沉的,那時候也許太累了吧,唉,但現在何嘗不累呢!為什麼睡起覺來變得這麼難呢?唉,都是別人讓我睡不著的啊!那逃往別處去行不行?但你能搬到哪裡去呢?你去過什麼地方、認識過誰、要靠什麼過活?或者還是把她趕走,但她能做什麼,怎麼過日子?──你為什麼要可憐她?各管各的吧!不行!不行!這麼想不行!這份苦是父親留給我的。我想出家,想待在佛門,爸爸做這種事的時候從沒替我設想,如果他稍微考量過,就不會把頌鬆留下來了,這大概就叫色迷心竅吧,做了這種事的奴隸無力自拔。但我從來沒成為色慾的奴隸呀,我為什麼要吃這種苦頭呢?父親並沒有吃過苦頭呀,和頌鬆一起生活的時候,他成天眉開眼笑,不是很幸福嗎!那麼苦楚從何而來呢?來自於別人。所以你應該在別人面前解決!但解釋了卻沒人相信,沒有人相信我!他們自以為是,然後就替我下結論,我一定是這樣的──我一定像他們想像的那樣,沒有別的可能……
想到這裡,一種孤立無援的心情抓住了他。
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時代,和父親同睡戲棚的一個蚊帳裡,那是多麼溫暖,多麼幸福啊!他總是比父親先睡著,但卻比父親晚起,有時他朦朦朧朧地睡了去,卻能感覺父親在清晨時分給他蓋好被子。他還記得,從小到大都是和父親睡在一個蚊帳裡,這種幸福感他從不陌生。在他出家當了沙彌以後,就再也沒和父親同睡在蚊帳裡了。童年的生活情景浮現在記憶中,這段、那段卻連不起來,意識已經有些有點模糊不清了。
他覺得自己大概快睡著了,回過頭來再想想自己剛才都想了些什麼,他卻想不起來了,這證明睡意即將來臨了。
快要睡去的時候,他感到身體一下子離開竹床飄到了空中──又開始了,又來了……但他無法制止,身體一下子急速衝上前方天空,一會兒又栽了下來。肚子錐心般地痛,他拚命念著經,想把這疼痛趕走,可是沒有用,他還是像在無邊無際的高空飛行。他想動動手臂,讓自己恢復正常,手臂卻沉如千鈞重,根本抬不動,連動動小拇指也做不到,彷彿被緊緊纏繞,旋即從高空跌落下來,墜入下方的深淵。他拚命想掙脫,但是身體就像是被黏在高空中,飛了很久很久。他忍受著折磨,簡直快斷氣了,冷不防一下子驚醒了過來。
發憋得難受,深深地吸了幾口大氣,再緩緩地吐出來,這才感到暢快了些。他的眼睛睜得老大,睡意頓時全被趕跑了。他又睡不著了,各種紛亂的思緒捲土重來,翻來覆去攪在一起,他不知道時間過去了幾個小時,到了下半夜的時候他才睡了一會兒。
發的一天,十分漫長的一天結束了。
是呀,墜入苦痛深淵之人的一天當然會比幸福美滿之人的一天要漫長得多……
────────────────────────
注釋:
① 譯注:「良」通譯為「娘」,這裡為避免混淆,譯為「良」(在泰話中音nang),是女人、女性之意,也是已婚女子名字的前銜,在正式場合使用居多,為「女士」之意。(以下皆為譯注)
② 泰國男子多在入夏節(雨季)前出家。
③ 泰語中「瘋瘋癲癲」的另一個意思是「腫」,在此有一語雙關之意。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Chart KORBJITTI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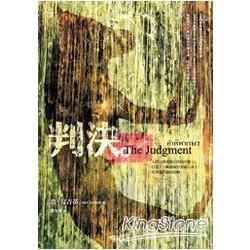 |
$ 180 ~ 246 | 判決-小說精選
作者:查.勾吉蒂(Chart KORBJITTI) / 譯者:欒文華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9-01-23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36頁 / 14.8*21.0 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2 則評論 2 則評論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判決
‧1982年東南亞文協獎首獎作品/2004年泰國文化部Silpathorn Award文學類首屆得主
‧泰國現代文學永遠的先驅者查.勾吉蒂代表傑作
他想,人的一生也夠奇怪了。
生下來,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有了生命,就要為了生活奔波,死了,一切也就結束了。
人並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死,死在哪裡,而且不知道死了以後會到哪裡去。
活著的時候,就像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瞎子。
──《判決》,第一部:羅網中
沒有什麼可失去了。
命運之前,該低頭沉默或者起身反抗?
熱天午後,尋常泰國小鎮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查.勾吉蒂 ชาติ กอบจิตต/Chart Korbjitti
1954年出生於泰國沙沒沙空省,童年時光都在農村度過。中學時代立志投身寫作,畢業後進入工藝學校學習。1979年以〈失敗者〉獲得泰國作家協會短篇小說鼓勵獎;隔年的中篇小說《走投無路》(No Way Out)出版後旋即引起廣泛討論,為當時低迷的泰國文學注入新氣象。1981年,長篇小說《判決》(Th
章節試閱
第一部 羅網中1 長方形的屋子裡,光線黯淡。 第一扇窗戶被打開了,淡黃色的光照射進來,排列成行的桌子依稀可辨。第二扇窗戶又被打開了,屋子裡明亮多了,這裡的一切已經可以看清。教室前面的黑板,右上角用白色的粉筆寫著一九╳╳年╳月╳日一行字,黑板下面的溝槽裡,用過的粉筆頭和掉下的粉筆灰堆在一起。當第三扇窗戶被打開,屋子裡更明亮了。講課用的講台在黑板的右側,椅子被推進講台,上頭擺了黃褐色的粉筆盒和紅色的花瓶,裡面插著暗紅色的茵比拉花,花瓣已經謝了,無力地垂在花瓶上;光線照射進來,將投在講台上的玻璃花瓶...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查.勾吉蒂 譯者: 欒文華
-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1-23 ISBN/ISSN:9789570833706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6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其他各國文學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2009/03/12
2009/0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