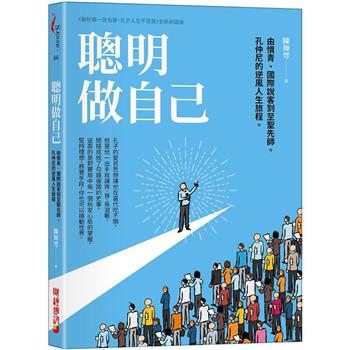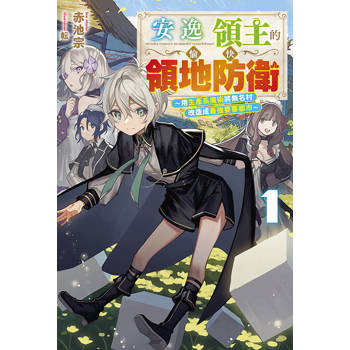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Crystal Tsai的圖書 |
 |
$ 82 ~ 342 | 活出率真:本來的你,就很好
作者:福森伸 / 譯者:Crystal Tsai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5-25 語言:繁體書  共 1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位於鹿兒島的「菖蒲學園」成立於一九七三年,
是一所提供智能障礙者及精神障礙者交流聚會、生活的福利機構。
他們不論於工藝、藝術作品乃至於音樂活動都備受海內外肯定讚揚,
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過程,才得以成就現在的榮景。
究竟需要什麼,才能真正地發揮人類能力的同時,還能自由自在地生活。
讓我們重新審視人們「原本應有的生活方式」是什麼。
對那個人來說,如果是做讓自己開心的事就能夠持續一直做下去。
只要在這裡,會讓你重新思考何謂理所當然。
本書作者為菖蒲學園的園長,長年致力為這些智能障礙者打造自由自在的天地。
菖蒲學園以藝術活動為主軸,打破一般人對智能障礙者的成見,讓他們的作品成為真正的藝術。
學員縫紉出的布製品,曾被巴黎的藝術收藏家收藏;
音調不和諧、節拍不一致的演奏,還曾為日本知名服飾品牌「niko and…」的廣告所用。
福森伸透過本書,分享他的心路歷程、與智能障礙者的相處及想傳遞的理念給讀者,是一本非常真實、珍貴且具有教育意義的書。
作者簡介
福森 伸
一九五九年生於鹿兒島。自一九八三年任職於「菖蒲學園」,現任提供智能障礙者支持服務的社會福利機構菖蒲學園的統括設施長。自學木材工藝設計,設立「工房菖蒲」。其中以二○○○年起以縫製物品為主軸的企劃「nui project」所製作的作品於海內外廣受好評。此外還有聲音表演「otto & orabu」、傢俱專案飲食空間異業企劃等,將「衣食住+交流」作為理念,融入工藝、藝術、音樂等,以新「SHOBU STYLE」之名製作許多讓患有智能障礙的人們,藉以參與各種各樣的創作活動與社會多方交流的企劃。
譯者簡介
Crystal Tsai
生長於台灣台北。輔仁大學畢業後學習日語多年,曾住日本一年,並於東京日本語學校長沼學校學習商用日語,現同時精進日文口譯。合作信箱:tsaitienwe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