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Darrin M. McMahon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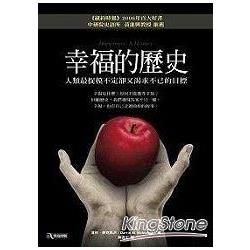 |
$ 199 ~ 396 | 幸福的歷史:人類最捉摸不定卻又渴求不已的目標
作者:達林.麥克馬洪(Darrin M. McMahon) / 譯者:陳信宏 出版社:究竟 出版日期:2007-11-2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96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紐約時報》2006年百大好書
◎中研院史語所黃進興教授推薦
幸福是什麼?如何才能獲得幸福?
回顧歷史,我們發現答案不只一種;
幸福,也有自己迂迴曲折的故事。
現代人認為幸福是一種權利,是天賦的人權,本書所談的,正是西方人怎麼產生這項信念的歷史故事。在希臘羅馬哲學與基督教信仰裡,幸福極為罕見,只屬於「幸運的極少數人」。啟蒙時代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概念,把幸福視為一種所有人在此生中都能追求的目標。自此以後,幸福不再是神的贈禮,不再是命運所玩弄的把戲,也不再是傑出表現的獎賞,而是人類與生俱有的能力,是所有男女老少都可以達到的目標。
回顧歷史,幸福也有自己迂迴曲折的故事。本書內容旁徵博引,遍及藝術與建築、詩詞作品與宗教經典、音樂與神學,乃至文學與神話。呈現出來的結果,便是一部磅礡的智識史,記述了人類最捉摸不定卻又渴求不已的目標。
啟蒙時代,狄德羅編纂的法國百科全書裡,「幸福」這個條目寫道:「所有人難道不是都有幸福的權利嗎?」由先前一千五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來看,這個問題顯然極為不尋常:幸福的「權利」?但這項主張在十八世紀中葉已經見怪不怪,到了世紀末更是廣為普及。人類顯然有幸福的權利,問題只是該怎麼做才能達成俗世的喜樂。
十八世紀的作家為這個問題所提出的答案,數量委實前所未見。實際上,探討這個議題的著作從來不曾以這麼高的頻率和數量出現過。在法國、英國、低地國家、德國、義大利,以及美國,探討幸福的論著不斷湧出。俄國在一七七五年簽訂了一紙和平協約之後,凱薩琳大帝就舉行了一場慶典。這場活動找來了一千名表演者,參與規模盛大的演出。在這一片狂歡當中,幸福女神是中心主角,搭乘一部由四頭白牛所拉的戰車,駛往龐大的「幸福殿堂」。自從羅馬帝國以來,幸福女神就不曾受到如此盛大的崇拜,也很少有人花費這麼大的精力追求幸福女神在俗世間的贈禮。
「啊,幸福,我們生存的終點與目標!
我們為了你而活下去,也因你而敢於踏上死亡的路途……」
──詩人波普(Alexander Pope)
「幸福在哪裡?所有人都尋求幸福,卻沒有人能夠找到。」
──盧梭
「唯有激情能夠帶你達到幸福。」
──薩德侯爵
作者簡介:
達林‧麥克馬洪(Darrin M. McMahon)
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及耶魯大學接受教育,並於一九九七年在耶魯獲得博士學位,著有《啟蒙的敵人》(Enemies of the Enlightenment)。他曾在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與紐約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現任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教授。他著述探討歐洲史及美國史的文章共二十篇以上,刊登於《華爾街日報》《波士頓環球報》與《德達羅斯》(Daedalus)等刊物。
譯者簡介:
陳信宏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曾獲全國大專翻譯比賽文史組首獎、梁實秋文學獎及文建會文學翻譯獎等翻譯獎項,目前為專職譯者。譯有《我愛身分地位》《幸福建築》《微型殺手》(先覺出版)、《品牌思考很簡單》《100個創造歷史的故事》《不可不知的100位思想家》《101個兩難的哲學問題》《非暴力抗爭》(究竟出版)等書。
引言:幸福的悲劇
第一部:一套現代信仰的誕生
1 最高的善
2 恆久的喜樂
3 從天堂到人世
4 不證自明的真理
現代儀式
第二部:傳播福音
5 質疑證據
6 自由主義與社會不滿的現象
7 建構幸福的世界
8 喜樂的科學
結語:幸福的結局
- 作者: 達林‧麥克馬洪 譯者: 陳信宏
- 出版社: 究竟出版 出版日期:2007-11-26 ISBN/ISSN:9789861370897
-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心理勵志> 心理學理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