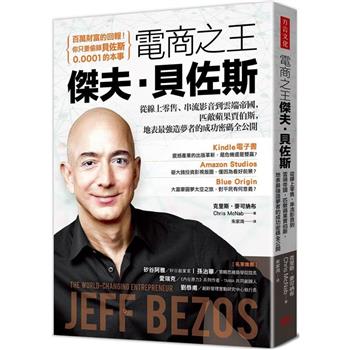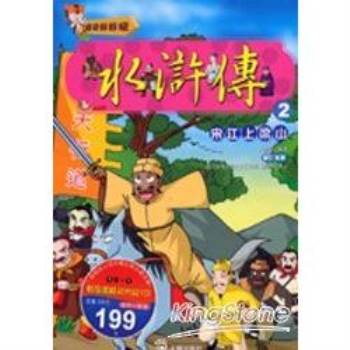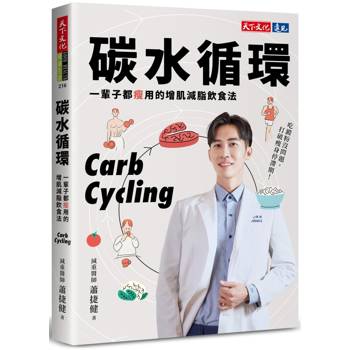他們為何殺人?
這些兇手是瘋子,還是天生壞胚子?
對罪行有什麼感覺,以及有自覺嗎?
怎樣的心理歷程、精神症狀,或是適應不良,
讓他們一步步偏離常軌,選擇了暴力犯罪。
這些兇手是瘋子,還是天生壞胚子?
對罪行有什麼感覺,以及有自覺嗎?
怎樣的心理歷程、精神症狀,或是適應不良,
讓他們一步步偏離常軌,選擇了暴力犯罪。
「連環殺手」、「弒母」、「殺嬰」,有關暴力與行為異常等駭人聽聞的事件,背後通常有個藏在頭條新聞底下、我們所不知曉的真實人物。心理健康問題不該與危險畫上等號,但有些危險行為必須從精神病學切入了解。
從事司法精神醫學工作超過二十年,塔吉.納森醫師透過經手的奇特案件,探討暴力行為背後的心理歷程。
※妄想症患者賽伯:他深信眼前的媽媽是個冒牌貨,還綁架了真正的母親,他必須戳破這個騙局,用刀刺殺她……
※嚴重情感缺失的艾米特:他刺殺兩個家人,卻無法解釋原由。他感受不到別人的痛苦,哭泣不是為了失去家人,而是事件對自己造成影響。
※人格疾患患者娜琳:在女兒的飲品中加料,最終致死。她只是想帶女兒去醫院,透過拍照上傳網路、博取關注,讓她感受到與他人的連結。
※性施虐症患者保羅:他不諱言會因為想到他人受苦而感到性興奮……當他掐住對方,看見她那恐懼的神情,就再也回不了頭。
本書作者曾擔任上百起案件的專家證人,他實際接觸書中十位犯罪者,細膩呈現與他們的對話過程,並以令人信服的醫學角度分析這些「病患」,讓我們得以一窺在監獄、法庭與病房中的這些人,是如何受到童年創傷或社會與文化影響,才選擇往危險行為靠攏。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