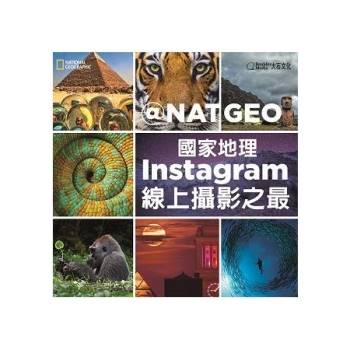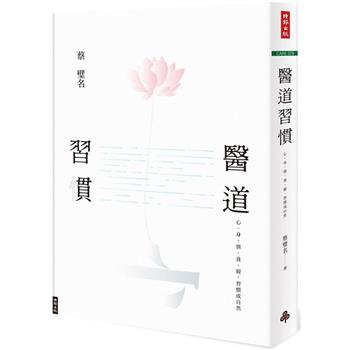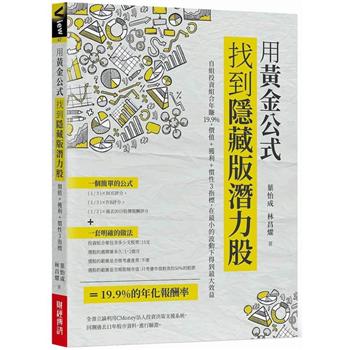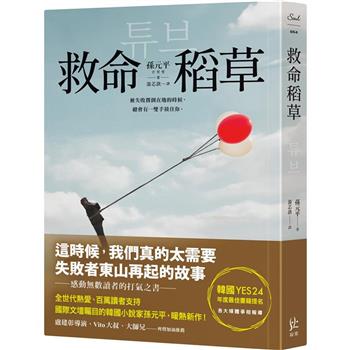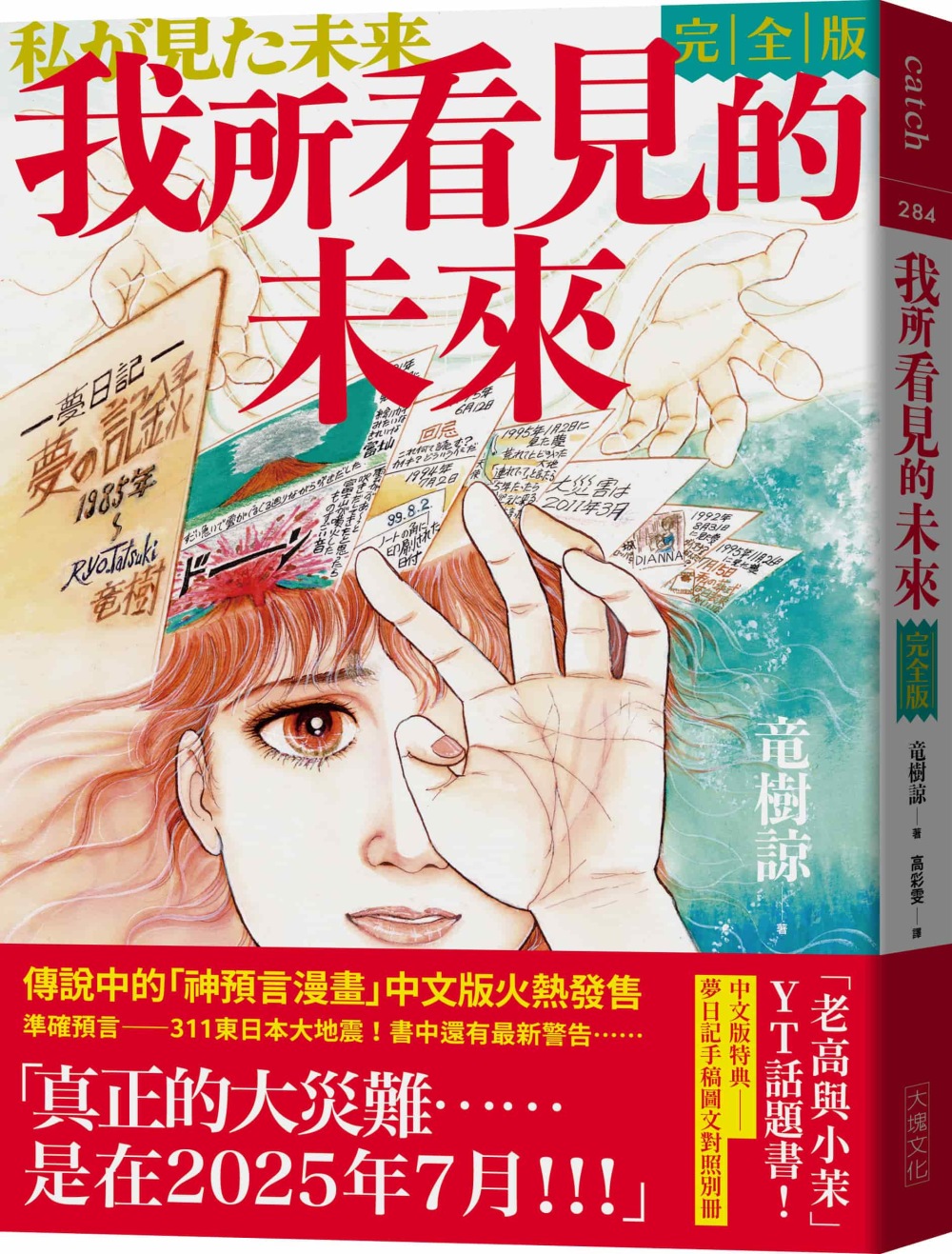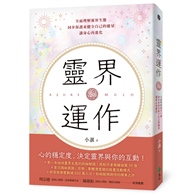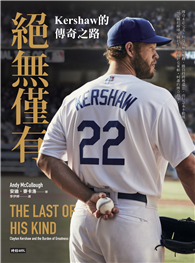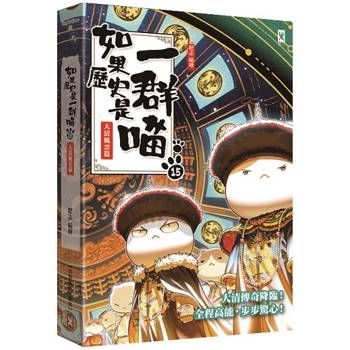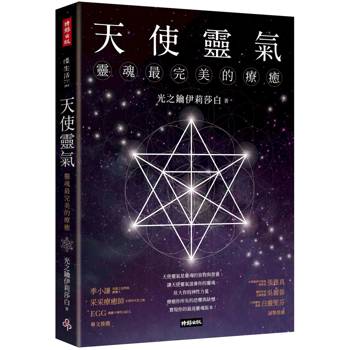中華在他方,它會是「他者」(autre)嗎?
我們在語言上和歷史上都觀察到這個「他方」。至於「他者性」(altérité),我們要耐心地在中華文化和歐洲文化之間建構它,這兩種文化在很長時間裡各自發展,但沒真的接觸。
法國哲學家兼漢學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一本論著又一本論著地,或說,一路做來,致力於建構該他者性。朱利安不假設有原則上的「他者性」或「同一存有本體性」(identité);為了提供一些概念以認識中華,也為了從中華外部回頭來質問哲學以重振哲學。
藉著這本《他者眼中的他者:歐洲與中華思想的研究》,作者以平易手法介紹他所走過的研究歷程、或說他的「治學之道」,及其取得的成果。他因此呈現了如何從文化之間的互相揭露面貌出發去打開「人的自我反思」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Franois JULLIEN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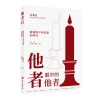 |
$ 323 ~ 361 | 他者眼中的他者: 歐洲與中華思想的研究
作者:作者:朱利安(Franois JULLIEN)/譯著:卓立/審訂:翁文嫻、蔡林縉 出版社:成大出版社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他者眼中的他者:歐洲與中國思想的研究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
擁有三個學術標簽:哲學家、希臘學學者和漢學家。他在中華思想和歐洲思想之間開闢耕耘的研究工地上深思文化間距論並提出暢活存在哲學。迄今已經出版了五十本論著,已有34個國家有他論著的外文翻譯,他更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外文翻譯的當代思想家之一。朱利安曾榮獲德國漢娜.鄂蘭政治思想獎以及法蘭西科學院哲學大奬。
譯者簡介
卓立(Esther Lin)
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巴黎索邦大學比較文學博士。長期定居法國,資深翻譯家,主要翻譯人文學術論著和文學作品。其譯作當中包括台灣小說家舞鶴的《餘生》法譯本,以及多種朱利安論著的中譯本。現任職於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
審訂者簡介
翁文嫻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香港新亞研究所文學碩士、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方語文系博士。研究專長:現代詩 、「間距」詩學、《詩經》的現代轉化。
蔡林縉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文化學系博士。研究專長:現當代華文文學、華語電影、現代詩學。
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
擁有三個學術標簽:哲學家、希臘學學者和漢學家。他在中華思想和歐洲思想之間開闢耕耘的研究工地上深思文化間距論並提出暢活存在哲學。迄今已經出版了五十本論著,已有34個國家有他論著的外文翻譯,他更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外文翻譯的當代思想家之一。朱利安曾榮獲德國漢娜.鄂蘭政治思想獎以及法蘭西科學院哲學大奬。
譯者簡介
卓立(Esther Lin)
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巴黎索邦大學比較文學博士。長期定居法國,資深翻譯家,主要翻譯人文學術論著和文學作品。其譯作當中包括台灣小說家舞鶴的《餘生》法譯本,以及多種朱利安論著的中譯本。現任職於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
審訂者簡介
翁文嫻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香港新亞研究所文學碩士、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方語文系博士。研究專長:現代詩 、「間距」詩學、《詩經》的現代轉化。
蔡林縉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文化學系博士。研究專長:現當代華文文學、華語電影、現代詩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