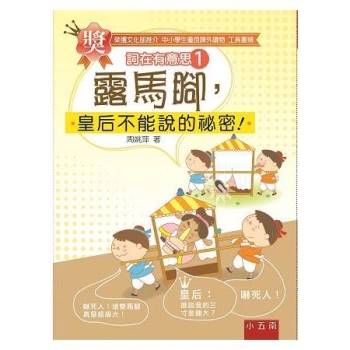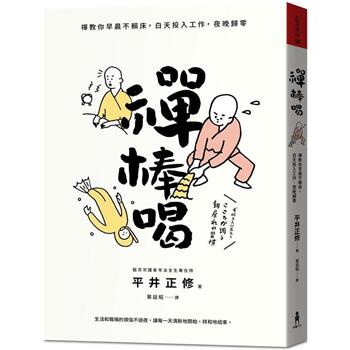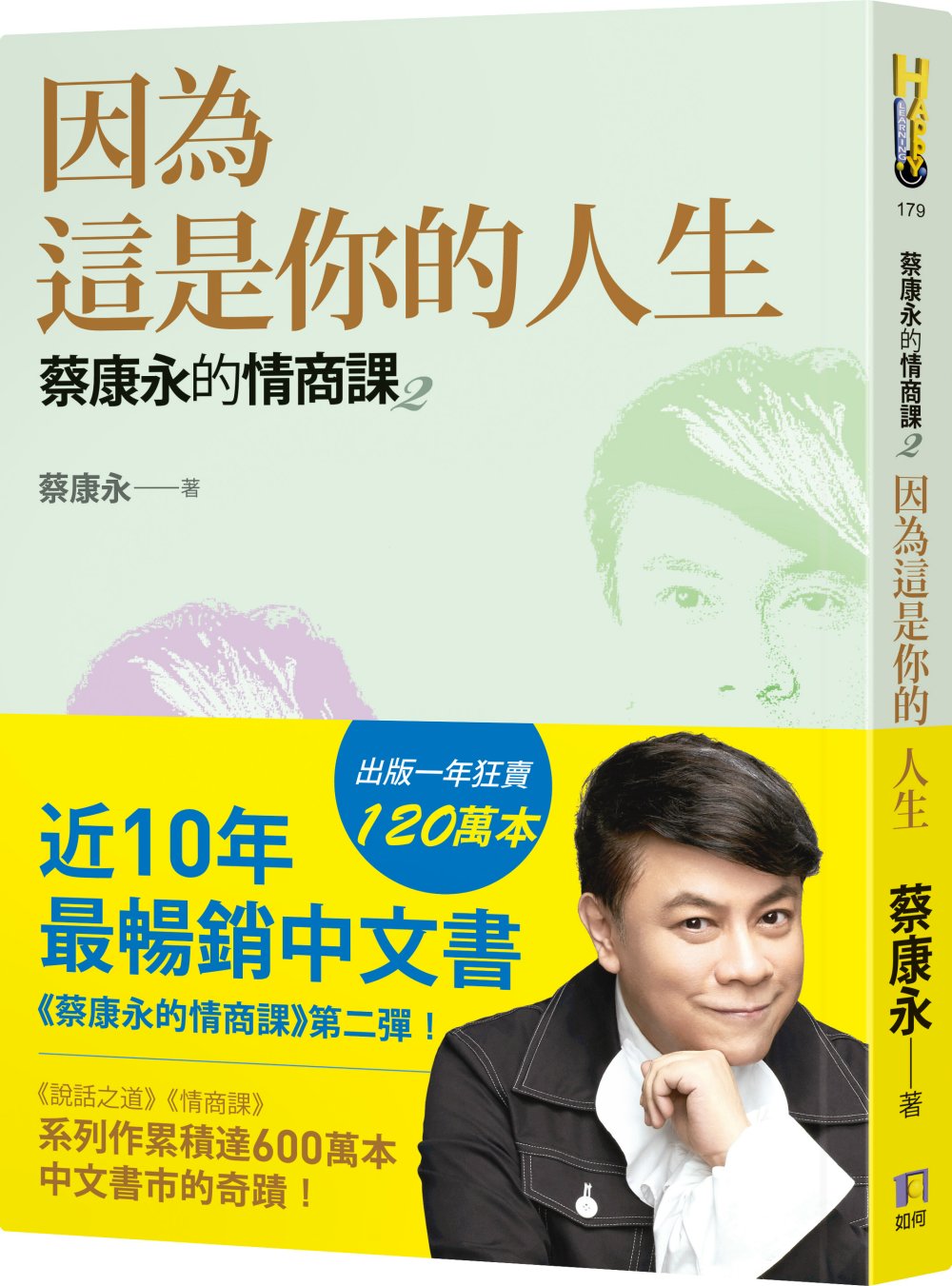1980 年 4 月 30 日,兩個小女孩─一個 7 歲、一個 4 歲──死於交通事故,死於駕駛人粗心。這則在報紙媒體上只有一天壽命的消息,卻是母親一輩子無法逃離的夢魘;消失,是生者所能承受的最大的磨難,把這一切寫出來,可能是唯一的救贖……。
我在醫院裡讀著這份書稿,妻在生產過後的虛弱中休息,每隔三小時哺餵母乳;我則在醫院固定而短暫的探視時間,每天做兩小時的父親,隔著玻璃窗看著新生的女兒,不管她是哭鬧還是安睡,我都聽不到她的聲音。
相比起來,這份可以觸及的書稿則顯得真實許多─
至少,我可以用指尖撫觸碳粉的突起,紙張也沾上了我的體溫,因而升越一種奇突迷離的感受:
女兒會哭會鬧,無時不在成長,此刻卻顯得虛幻;而這份書稿─一份關於死亡的記錄、一則己經結束的故事─卻是可觸及而真實的。
幾乎有一種馬勒《悼亡兒之歌》的不祥。
《潛水鐘與蝴蝶》的作者被禁錮在肉身驅殼之中,與外界幾乎失去聯繫;而這本書的作者─一位驟然失去兩個女兒的母親─則是被悲傷囚禁起來,失去了與世界相處與聯繫的能力,向著黝暗的深淵緩緩陷落....。
悲傷的力道是如此之大,作者要過了十三年之久,藉由文字─透過與友人的書信─才逐步舒緩糾結的心、柔軟堅硬的傷痂、逐步打開記憶的牢籠,向著光亮的水面浮去,整個事件,連同身為母親與作 家的細膩感受,在讀者眼前開展。
在這個時刻,我慶幸自己只是一個讀者,隔著安全的距離想作者生命杯的滋味,也提醒自己去發掘,蘊含在「擁有」這件事情本身之中,那種單純的魅力與幸福。
每一行、每一句無不碰觸到你的心靈....一本無與倫比的著作。─《世界報》(Le monde)
出色的文字令人心情為之起伏;充滿智慧與洞見力。─《她》(Elle)
優美、婉轉的書信,簡單的文句載著無法承受的重量。─《費加洛週刊》(Madame Figaro)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