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文壇大師米蘭.昆德拉最喜歡的冰島小說
「在這部小說中,你會發現一位偉大的歐洲小說家用無比微妙和獨特的方式捕捉住一個青春期少女的存在困境。」——米蘭.昆德拉◇ 1991年「冰島文學獎」得獎作品
◇ 1992年「北歐協會文學獎」提名
九歲的小女孩因為偷竊而被送到鄉下農場工作,農村中的一切對於從海邊來的女孩來說是如此陌生且神秘,在這片壯闊、永遠不變的風景中,她發現一羣人游移在古老傳統和新的態度之間,左右為難。農村生活並不是田園詩歌,她必須面對許多嶄新、孤獨以及恐懼的感覺,也得正視她內心和周遭陌生環境中的未知,並運用自己的荒誕的「奇想」來解讀她所不理解的事物。而傳說農村當地山上有一頭怪獸會化身為天鵝的形體,並對看見牠的人唱出他的性格和命運。漸漸地,在承受許多鄉村生活的限制和苦難後,小女孩決心動身前往山上尋找那傳說中的天鵝……
猶如電影《羊男的迷宮》成功結合幻想、現實與寓言,描述童年孤獨與異想的奇妙之作
博格森為一位偉大的歐洲小說家,其藝術靈感泉源源自於一種對「存在」的探索,這也讓他的小說立於現代小說的中心。本書不僅具有現代主義的風格,同時也帶有魔幻寫實的手法,書中怪誕、美麗和滑稽的情節呈現出強烈對比,讀來卻又莫名地和諧。米蘭.昆德拉讚博格森在本書中使用無比微妙和獨特的方式捕捉住一個青春期少女的存在困境,那在童年與青少年間遊走的界線,是一個時時走在幻想迷霧中的年齡,而透過此本小說我們得以重新體現。
作者簡介:
古博格.博格森
1932年出生於冰島濱海小村格林達維克,曾在冰島與西班牙求學,獲得巴塞隆納大學文學學位,著作種類廣泛,如詩集、兒童文學及小說。他於30歲時出版第一本著作,之後的現代主義作品《暢銷作家:湯瑪士.強森》使他躋身冰島大師級作家行列,此後幾十年來創作不斷,並多次獲得重要文學獎項肯定,其中《天鵝之翼》更因受到文學大師米蘭.昆德拉的讚賞,被譯為英、法文而進入國際文壇。博格森同時也是著名的冰島翻譯家,譯過多位世界知名作家——例如塞凡提斯、波赫士和馬奎斯等人的作品。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天鵝之翼》是一本別具獨創性與特質的小說。」——《獨立報》
「在這部小說中,你會發現一位偉大的歐洲小說家用無比微妙和獨特的方式捕捉住一個青春期少女的存在困境。」——米蘭.昆德拉《新觀察家》
「這是一本五星級小說,絕絕對對的精彩。」——《年輕世界》
「這部訴說哀愁與慰藉、蛻變與魔法的小說,將是這個秋天最美麗的出版品之一。」——《德國國家廣播電台》
「《天鵝之翼》是描述一個小女孩的精彩故事,她的靈魂是一處無法量測的深淵。這是一個很棒的故事,讀者的收穫遠遠超過數小時閱讀所帶來的樂趣。」——《冰島國家廣播電台》
「博格森創造出一部神奇的小說。」——《南德意志報》
「這是一趟靈魂的文學出航,充滿了神奇和冒險。」——《北德廣播公司》
「混合了諷刺和單純、憂鬱和距離,以及最重要的,濃濃的氣氛,共同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氛圍,並提升了這個故事,使它成為藝術品。」——《柏林早報》
媒體推薦:「《天鵝之翼》是一本別具獨創性與特質的小說。」——《獨立報》
「在這部小說中,你會發現一位偉大的歐洲小說家用無比微妙和獨特的方式捕捉住一個青春期少女的存在困境。」——米蘭.昆德拉《新觀察家》
「這是一本五星級小說,絕絕對對的精彩。」——《年輕世界》
「這部訴說哀愁與慰藉、蛻變與魔法的小說,將是這個秋天最美麗的出版品之一。」——《德國國家廣播電台》
「《天鵝之翼》是描述一個小女孩的精彩故事,她的靈魂是一處無法量測的深淵。這是一個很棒的故事,讀者的收穫遠遠超過數小時閱讀所帶來的樂趣。」——...
章節試閱
長途巴士出發的那一刻,女孩就開始思念起岩石和大海了,而當他們來到鳥鳴草長、河水流動、水塘和沼澤被陽光照得閃閃發亮的地方以後,她的失落感也變得更為加劇。當她坐在車窗旁,看著沿途飛逝而過的草原,讓她一直回想起那個夏天她獨自一人時候的大海。灰色的雲影掠過青草,瞬間就讓草色變成了墨綠,再恢復正常的顏色。之後有一絲絲的哀傷悄悄滲進陽光中,而這點哀傷又被雲影、平坦的原野和廣大無邊所擴大。這廣大不是大海的寬闊,而是大地的廣袤,愈來愈大而無邊無際,因為一片土地會接上另一片土地,而巴士似乎在這些高山、沼澤和河流間前行,卻永遠也抵達不了目的地。巴士駛在一條路上,這路會變成另外的、無數的路。有些路穿過高高的橋,這時她就會試著很快地往橋下水面看去,只見那水會打轉成為小漩渦,並且變得好深,使得她心中充滿恐懼。她閉上眼睛,感受那深深的水潭,再立刻把眼睛睜開,免得自己消失在車輪和橋面下方的河裡。
當她離家時,她母親陪她到客運巴士站,並且說:「這次是你第一次離開家到鄉下,離開你的父母親,所以盡量要去喜歡那裡的事物。對每個人都要有禮貌,要行為端正,這樣你就會忘掉你做過的事。等你回到家以後,其他所有人也都會忘掉了。」
然後母親把她摟在懷裡,低聲說:「我們喜歡忘記,就和我們喜歡記得一樣,我親愛的。」
這天早晨她父親去工作以前,他們頭一次一起換衣服的時候,他對她說:「如果你給人留下好印象,那裡的農夫或許會讓你這整個冬天都留下來幫忙,還會付你工錢。」
他才剛說了這些話,她的嘴巴和喉嚨裡就塞滿了柔軟而乾的石頭,這是一種奇怪的石頭,她得費很大的勁才吞得下去。
之後他們直率地說起她在鄉下會如何的成長發展、那裡空氣比城裡健康、那裡的人自在又好脾氣。
「就算不完全是那樣,你也應該相信都是一樣的。」她父親說。
女孩既放了心,又感到哀傷。她在車上可以感覺得到這種情緒,她在車子駛過房舍之際深深吸氣,之後她低聲自言自語,因為這趟旅程是一個無止盡的道別時刻。長途巴士在路上愈走愈遠,她眼神裡悄悄有一種自己正逐漸死去的感覺。
同時她也開始透過窗戶向她最後一次看到的東西道別。她感覺自己正在陽光下枯萎、垂死,而小片小片的雲正飛掠過大地。她就懷著這種感覺一路從大海的海浪坐車到青綠起伏的山丘。
車開得越遠,這是一條不歸路的態勢就越清楚了。從半開的窗子吹進來的風裡,海水的濕氣已經消失。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春天最初的跡象:地面已經是綠色,一陣陣的風傳送出一種帶有土壤溫熱、沒有鹹味的奇特濕氣。放眼看去,只有大地的寧靜安詳,而沒有那種熨貼人心的神祕嘆息聲,那是在過完狂濤巨浪的冬天後,厚實的春天寧靜散佈在海上時,大海所發出的聲音。大地在春天復甦,但大海卻在同時間死去,或者說是冬眠了。它變得像是一頭藍色、一直在動的流體動物,平靜地臥著。然而它的眼睛仍然觀測周遭,隨時準備好要發出低聲撲向岸上。
突然間她開始啜泣。她對著她看到的一切事物哭泣。無聲而長的啜泣,她用手心掩著嘴,彷彿她在唱歌一樣;她望著鄉間、農場和草地,這些地方是屬於某些人的,而且只屬於他們。擁有它們的人稱做農夫。可是大海卻是每個人都可以分享的,沒有一個人可以住在上頭,或是把他的牲口趕過去吃草。沒有人可以擁有大海,因為它不停歇地流向天空,再經過太陽曬和雨水落下的方式流回到自己身上。
某些時候車會停下。有人下車,有人上車,坐一小段路。狗兒從農場跑下斜坡和草地,不是作勢咬人就是要歡迎下車的人。看到狗兒那毫不收斂的歡喜,女孩並不歡喜。她知道當她終於抵達她的目的地後,不會有人歡喜,連隻狗兒也不會高興。
女孩知道,就算她直接回家,走到海邊,也不會有魚游到岸邊,拍動尾巴歡迎她到來。沒有任何東西,會對走到海邊的人表示歡迎之意。任何走到海邊的人,對於能夠再次見到之前離開的那大片水域,只會在自己胸中有歡迎的感覺。
「這是海洋和陸地不同的地方。」她想道。
※ ※※
坐在她前面的一名乘客開始大聲唱起一首歌,關於鄉間、太陽和土壤的歌,而一位美麗的女子喝著麥酒。從前她只在教科書上看到的詩和故事,此刻就在她眼前,並且突然間讓她的耳朵也聽見了。她正置身在詩詞的景色中。要是她永遠不需要到達她的目的地,也不用在一個不熟悉的地方和那裡的陌生人打交道,那麼她透過窗子所見的,配上這些音樂,還真是不錯。
她身上罩著一層昏暗的山色,這團暗影出人意料地帶著哀傷,在這個頭一次離家的人心中某處爆發開來。旅途中剩下的時間裡,她就一直掩在這片暗影下方。
巴士停了,司機回過頭,眼神空洞地望著她說:「這裡就是你下車的地方了。有人會來接你。」
聽到這句話,她往車外看去,於是第一次看到了這個農夫。他一個人等在路邊,附近看不到半間房子,他身後就只有一條車道,迤邐消失在兩座低矮的山丘之間。
她兩腿僵硬的下車,一下車就聽到鳥叫聲,還有種說不出來、緩慢的植物聲音。她從沒聽過的生命從遠處的湖泊和草原上發出迴響,到處都是。它似乎是從地面和天空中、從四面八方同時傳來。
司機比她先跳下車,匆忙地把她的行李從行李廂裡拖出來,碰的一聲放在路邊。他做每件事都很急躁。他把行李丟在農夫腳邊。
「皮箱,這裡。」司機說,然後急促地上了車,搖搖晃晃把車開走了。
農夫穿著工作時候的衣服:一套藍色「毛裝」,外套褪色得比長褲嚴重。外套後背幾乎都成了白色。他彎腰做活時,陽光把衣服顏色都曬掉了。然後他問:「你可不可以自己提皮箱?」
「可以,」她說,「可是我提不遠。」
「那麼你算是強壯的了。」他說,並且從口袋裡拿出一條繩子,把皮箱綁起來,雖然皮箱鎖鎖得很穩。然後他不費什麼氣力的就把皮箱放到背上,再稍稍往上調整到肩膀上。
「喔,不重嘛。」他說,一邊露出笑容,彷彿很高興有人給他一個重擔扛在背上。
「你跟著我走,」他說,「回去的路不遠,而且這裡沒辦法開車。我們就走回去。」
女孩開始希望這條路是沒有盡頭的,這樣她就永遠也不會離開這條路,前去農場;她希望路永無終止之處,而她的旅程只是一本素描簿上的一幅素描:她、農夫、狗群、太陽、母羊、農場房舍和四周的鄉間。如果是的話,她會立刻把它擦掉。可是他們卻穩定的一步一步接近房舍。不久後路上什麼也沒有了,只有一個手又冷又濕黏的女人來迎接他們。
「哈囉,」她說,「你就是那新來的女孩囉?」
「你怎麼不開車去接她?」女人問,並且帶女孩進到一間有兩張床的房間。
下午慢慢過去,女孩大部份時間是坐在床上。她試著平靜的呼吸,以免把那寧靜嚇跑。農夫和他的妻子像是死掉了一樣,到處都看不到他們的影子。在沒有一丁點生命跡象的情況下,時間一點一點過去。她小心翼翼偷偷走到窗邊,看到那隻狗也睡了,牠的鼻子搭放在一雙腳掌上。時間用靜態的方式前進。她可以從她的手錶知道時間過去,而太陽也經過這屋子的兩側。她聽到車子逐漸駛離的聲音。農夫和妻子突然去了哪個地方了,留下她一個人。她想:「這地方隨便它要怎麼樣,我才不在乎哩!」
然後她開始換衣服,心思又在睡和醒之間徘徊於空中。當她從她的飛行中返回,在睡著之前,她決定要夢到自己的家。她決心以後都要在她夜晚睡覺時待在老家,即使白天她醒著的時候都必須工作,也許以後一輩子都如此。
※ ※※
第二天,女孩就立刻被派到沼澤去牽一匹農夫說是藍灰褐的馬。她不知道這是什麼,不過她猜藍灰褐是一種顏色,只是她怕被認為很笨,所以沒有問。
於是她慢慢出發,心中帶著疑問,肩上掛著馬勒走在草地上。這是她頭一次離開家鄉,她也很期盼能獨自一個人,希望答案在開放的原野中要比在屋子裡更容易出現,如果那是一種顏色,那就會像閃電一樣的進入她心中。
馬匹們在老遠的沼澤地上吃草。在這麼遠又耀眼的陽光下看過去,那些馬兒很不真實,似乎只存在於她身體裡另一個美好的理解世界裡,而牠們在閃爍的遠處發著亮光。有時候那些馬兒像是從地面升上來一樣,彷彿空氣形成一道強大而鼓漲起伏的銀色水流,將牠們拖動打轉,而不知怎地把牠們抹掉了,或者是抹去了部份,連瞬間的警告都沒有,然後那些沒腿或沒頭的馬匹就會在波狀的平靜空氣中四處徘徊。青草和整片天空中都是清晰的陽光。這情形像是一道潮濕的熱從一個藍色圓頂上突然傾瀉而下。
她還沒踩到草地外那小丘般的沼澤地上,腳下的每樣東西就開始彈跳起來。這裡不是堅實的土地,而是會略微移動的硬果凍。她的兩隻腳半埋進紅色泥巴裡,她也聞到泥巴有股生鏽的舊鐵味道。棕色的沼澤水啪啪濺到她鞋子上。她腳下的泥地發出哀鳴,泥巴從她鞋底粗魯地發出咆哮聲噴吐出來,泥沼似乎要吞噬她,但卻沒有;她的雙腳總是會在某個深度後就停住,不再下陷。於是她在這片奇特的空氣、泥濘和水的混合地面走得越遠,她的恐懼也就逐漸減弱了。不久後她還開始喜歡起這種滑稽事了:她的兩腳被一股不明的力量往下吸,她再用她自己的力量和意志力用力拔起來。當她克服了泥濘之時,土壤就會陷下,還發出咻咻的喘息聲。她每踩一步,沼澤都在說:「噗隆、噗隆、噗隆。」
她就像這樣在這片濕地上吃力的走著,很快就累了,因為她還不習慣這種柔軟的地面。
然後突然間她走到馬匹前面了,但是後來才看出來,那是馬匹隨著氣流的波浪緩緩地沖到她面前。牠們沒有停下吃草的動作,而是斜眼懷疑地看著她,露出眼白,又不屑地朝她和蒼蠅揮動尾巴。她感覺到牠們對她的嘲笑和不耐,因為她對馬匹一無所知,甚至連牠們的顏色都分不清。事實上,在她看來,牠們似乎全都很像,或者說牠們有彩虹中所有的顏色,只除了藍色。她只看過這種顏色的馬一次,是在一張圖上。
有一匹馬沒有避開。牠動也不動站著,顯然是在等候,而她也頗猶豫的走近牠。牠往上看她,豎起耳朵抬高頭,嘴唇因為吃了青草而濕濕的,牠注視她,就像是一個神聖的人物那樣,完全不動,由著她按照農夫教她的方法把馬勒套上去。之前他假裝把馬勒往她身上放,還用一個威脅的笑容說:「如果你是一匹馬,一個好農夫就是這樣給你上馬勒的。」
馬勒像是用了魔法般毫不費力地就套在馬的頭上,馬銜也毫無阻礙就滑進馬嘴。有一瞬間,她的兩隻手似乎長了翅膀似的,輕鬆就把馬勒滑進那滿是熱氣、冒著綠草色泡沫的馬嘴裡。這一切都很順利,這匹馬像是一個乖小孩,會幫忙自己穿上衣服。她就拉著繮繩把牠牽回家了。
到了農場,農夫正在等她,他問她為什麼沒有把牠騎回來。
「可是你不是說是要牽著馬的嗎?」她問。
農夫笑了起來,說最好讓她騎上這匹馬,看看她能不能騎,於是他立刻把她抱上馬背。
「我們馬上就知道了。」他露出一個很乾脆的表情。
突然,她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就結結實實的把兩隻腳往馬腹用力夾住,馬就急衝下坡,把她摔下馬背。她摔下的時候,有東西也成碎片般地旋了出去:岸邊的房屋、大海和她的玩伴。她眼前一片黑,滾落草地上,進到動物的世界。最後她停止了翻滾,在涼爽的草地上仰躺著,看著上方的天空,像是失神了一樣。她有種才剛死掉、此刻正第一次抬眼望著淡藍色的永恆,還有幾朵雲在上頭,但就在此時,農夫卻把她從這種平靜的感覺中抓起來。
「這可以讓你知道動物是很敏感的,」他說,「你必須去適應牠們。」
她沒有受到任何傷,可以站起來。就連她的脖子都沒有事,因為農夫說:「沒有,你的脖子沒有斷。從馬上摔下來不是每次都會摔斷脖子的。雖然有時候會,不過你太年輕了,你的骨頭軟。」
她的腦袋也沒飛出去!
農夫妻子對她很熱情的歡迎,彷彿她從馬上掉下來就掉進了這家人的生活中一樣,由於摔下馬這件事使她變得理直氣壯了。這天晚上她睡覺時,所有東西並沒有化為一團模糊在她身邊。
長途巴士出發的那一刻,女孩就開始思念起岩石和大海了,而當他們來到鳥鳴草長、河水流動、水塘和沼澤被陽光照得閃閃發亮的地方以後,她的失落感也變得更為加劇。當她坐在車窗旁,看著沿途飛逝而過的草原,讓她一直回想起那個夏天她獨自一人時候的大海。灰色的雲影掠過青草,瞬間就讓草色變成了墨綠,再恢復正常的顏色。之後有一絲絲的哀傷悄悄滲進陽光中,而這點哀傷又被雲影、平坦的原野和廣大無邊所擴大。這廣大不是大海的寬闊,而是大地的廣袤,愈來愈大而無邊無際,因為一片土地會接上另一片土地,而巴士似乎在這些高山、沼澤和河流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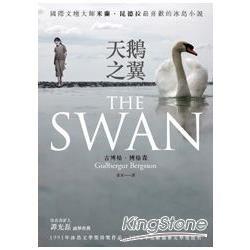

 共
共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