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Ian Hathaway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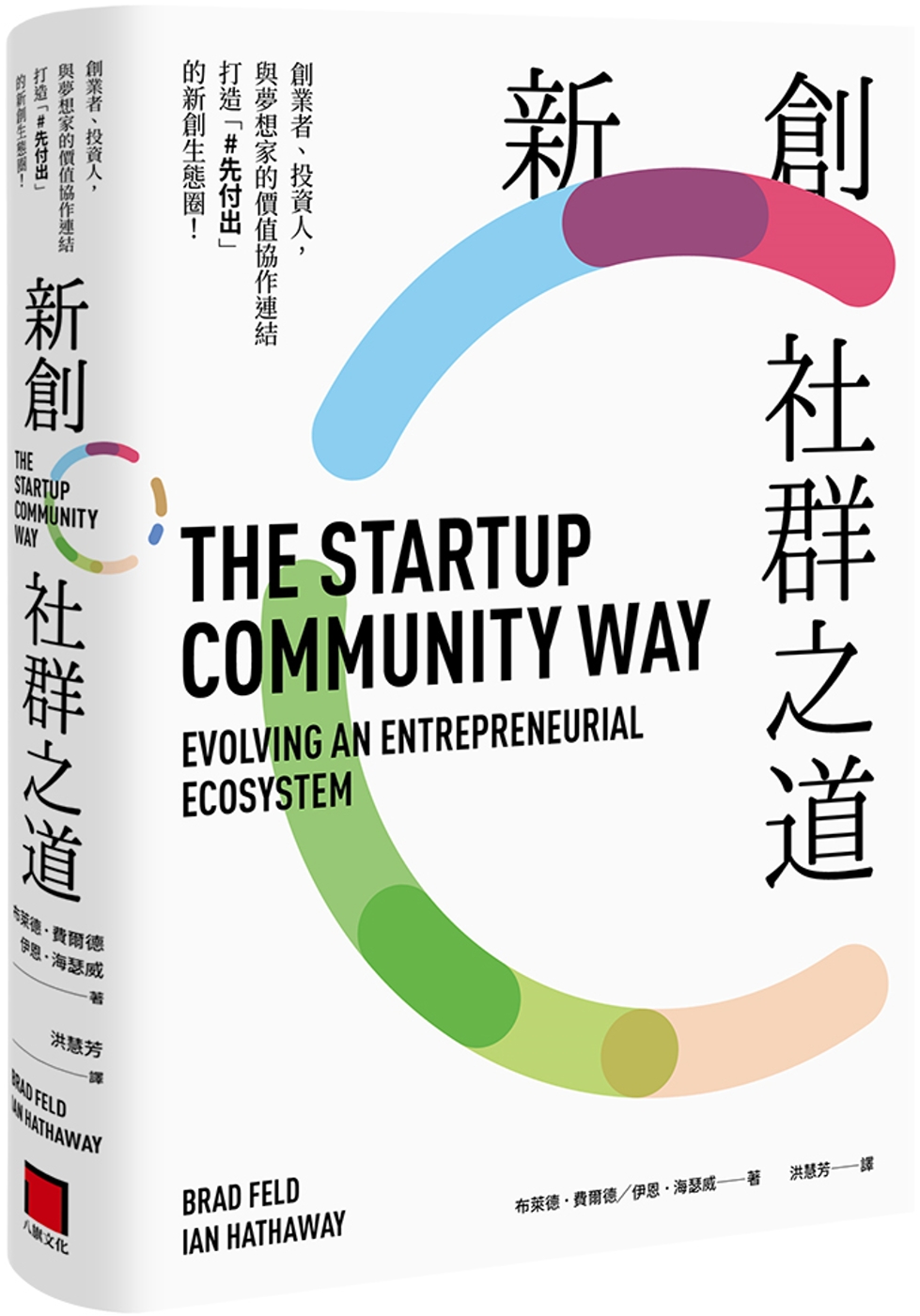 |
$ 300 ~ 540 | 新創社群之道:創業者、投資人,與夢想家的價值協作連結,打造「#先付出」的新創生態圈
作者:布萊德.費爾德(Brad Feld,Ian Hathaway) / 譯者:洪慧芳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1-12-28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00頁 / 14.8 x 21 x 2.7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686 電子書 | The Startup Community Way
作者:Brad Feld,Ian Hathaway 出版社:Wiley 出版日期:2020-08-03 語言:英文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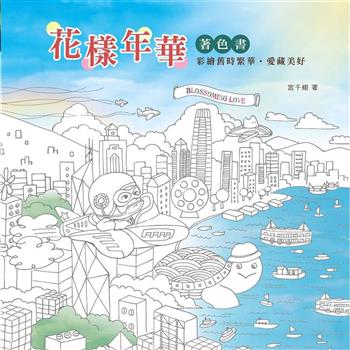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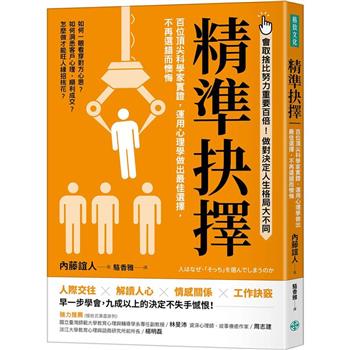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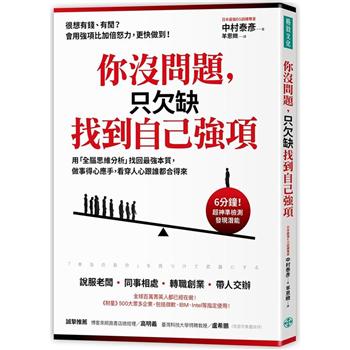





![圖解 適齡教養 ADHD、亞斯伯格、自閉症[暢銷修訂版] 圖解 適齡教養 ADHD、亞斯伯格、自閉症[暢銷修訂版]](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6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