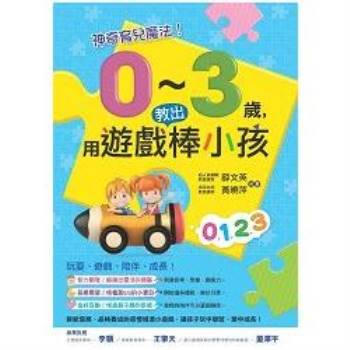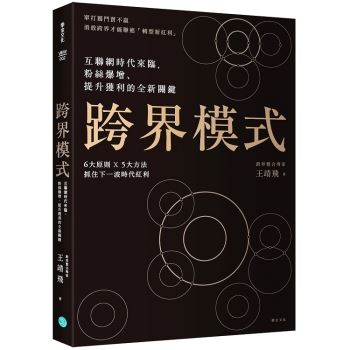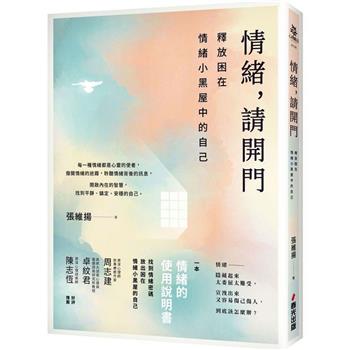第五章 尺度的問題
你怎樣才能把五○○,○○○磅的水浮懸在空中,而不用到看得見的支架?
(答案︰把它變成雲。)
——藝術家米勒(Bob Miller)
受邀去遊歷每一件事物都比我們世界中的要大許多或小很多的世界,似乎帶有一種迷人的魔力。去冥想海洋或天空的廣闊,或者在顯微鏡下觀看池溏中拿來的污水,或是去想像原子的內在生活,這些行為都把我們遠遠帶離到日常生活之外的領域,進入一個只能依靠想像力才得跨入、極有異域情調的景色中去。
能長成巨人的滋味是什麼?變成一隻小蟲的大小呢?愛麗絲吃了一枚蘑菇,就脹大到如美西感恩節遊行隊的大氣球,從她的屋中爆出去;她再多吃一點,就縮小成「不可思議的不斷縮小的女人」,她永遠的恐懼就是掉到洗手盆排水口裡[1]。從「小史都華」到「金剛」,從「親愛的,我把孩子變小了」到「姆指人」[2],這種能把大小變化的觀念,對我們的心靈顯然有一股極強的吸引力。
有很好的理由去想像,不同尺度的世界也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加一可能大於二;在量上面的改變,可以引起在質方面極大的不同。
當物體的大小有了基本的改變時,就有不同的自然律去管理它,時間的滴答聲也因不同的鐘而異,新的世界自無中生出來,而舊的世界則完全溶化不見。舉個例子,有一個奇怪的巨人——當然,毫無疑問的,他高大而強壯。可是高大的身材帶來了顯然的不便。按照霍登(J. B. S. Haldane, 1892-1964)在他的經典散文〈大小要正好〉中說的,一位六十英尺高的巨人,每走一步就會把他的大腿骨碎裂。
原因是很簡單的幾何原理。高度只按一維增大,而表面積則按二維增大,可是體積則按三維增大。如果你把一個人的身高加倍,支持他抗拒重力的肌肉的截面積會變大四倍(二乘二),而他的體積,因此也等於重量,會增大為八倍。如果你把他的身高加為十倍,他的體重要增加為一千倍,可是支撐他的肌肉及骨骼的截面積只增為一百倍。結果是︰骨骼碎裂了。
要支持這麼大的體重,需要結實而粗的腿。你可想一下大象或河馬吧。對牠們來說,跳躍完全是不可能的。超人一定只能是跳蚤的大小[3]。
長得愈大,跌得愈重
跳蚤當然經常表演超人的絕技,這就是現在幾乎已絕跡的跳蚤馬戲團的科學原理[4]。這些微不足道的小生物可以拉動比它們體重重了一六○,○○○倍的物件,可以跳到它們身高一百倍的高度。小生物的體重和它們的肌肉截面積相比起來,使得它們似乎無比強壯。雖然它們的肌肉比起我們的不知要微弱多少倍,可是它們要去拉動的質量更加小很多很多,因而使每一隻螞蟻都成為超生物,跳過高建築似乎也不成問題[5]。
巨人跌倒也不行。這古老的諺語也是真的︰「長得愈大,跌得愈重」。而愈小,跌在地上也愈輕。這原因還是幾何。如果一隻大象從高樓跌下,重力把它的極大質量重重拉下來,而牠那相對說來較小的表面積,對空氣的阻力則幾乎沒有。反過來說,一隻小老鼠的體積(及質量)小到重力沒有什麼可以去拉的,而相對表面積大到就像它有一頂長在身上的降落傘一樣。
霍登這麼寫道,一隻小老鼠可以從一千碼(約九百公尺)的懸崖跌下,毫髮無傷。大老鼠卻可能傷重致死。而人呢,必死無疑。而馬呢?霍登告訴我們:「血肉橫飛!」
同樣的相對關係,也可以應用在無生命的下墜物體,例如水滴。大氣中溼答答的充滿了水氣,即使水氣沒有我們能看見的雲的形象。可是,一旦一粒微小的水滴開始吸引其他水分子到它的邊上,事情就疾速發展了。當這成長中的水滴直徑增加一百倍之際,它的表面積增加的倍數為一萬,而它的體積增加的倍數則為一百萬倍。大的表面積能反射更多的光,因而使雲層變成可以看得見。這個增加了不知多少倍的體積,最後大到能被重力拉下,墜到地面成為雨點。
按照研究雲的專家的說法,空氣中的水滴同時被靜電的吸引力拉住(這電力把水滴拉聚成群成為雲)以及被重力往下拉。當這些水滴很小的時候,它們的表面積和體積相對來說極大,這時是電力在管事,因此水滴浮懸在空中。一旦水滴的大小大到某程度後,重力就一定贏。
針頭大小的物體幾乎察覺不到重力。重力是只有大尺度的物體才能感覺到的力。把分子聚集在一起的電力,比重力強了近乎一兆倍。這就是為什麼只要在空氣中有一絲一毫的靜電力,就能使你的頭髮豎立起來。
對跳蚤大小的超人來說,這些電力會造成很大的問題。首先,如果他想要飛得比子彈還快的話,會遭遇到極大的困難,因為對他而言,空氣就像濃極了的分子湯,從任一方向都可把他攔住。那就像在濃稠的糖漿中游泳一樣困難。
蒼蠅可以毫無困難的在天花板上倒著走,是因為把它們的腳黏在天花板上的分子膠的膠力,要比把它們微小的重量向下拉的重力強得多。可是,水的電力可像磁石一樣吸引住昆蟲。如霍登指出的,水分子的電力使得昆蟲想去喝水的動作,成為一種危險的絕技。一隻彎下身去小水坑喝水的昆蟲遭遇到的危險性,就如一個人在懸崖邊上彎下腰去採灌木上的漿果一樣。
水是最具黏性的物質之一。剛淋浴過的人身上帶了約有一磅重(○.五公斤)的水,可是這幾乎不能算是負荷。不過按照霍登的說法,一隻剛淋浴過的小老鼠身上帶的水,就幾乎相當於它的體重。對蒼蠅而言,水更具有捕蠅紙的威力;一旦蒼蠅身上沾濕了,就會被黏到死。按霍登的說法,這就是為什麼昆蟲有長的針狀吻(嘴)的原因。
事實上,如果你變成昆蟲的大小,生活中的每件事幾乎都不同了。一個螞蟻般大小的人永遠寫不出書來,因為一台螞蟻大小的打字機的鍵盤都會黏在一起,一本書的書頁亦然。螞蟻永遠不能生一團火,因為最小的火焰也要比它的身體大。
不同尺度,不同的力在管轄
把人或其他物體縮小到原子的大小時,就會把現實世界改變到不可辨認的地步,完全成了期望之外的新景色。原子大小的物體,和分子大小的物體或人的大小的物體,行為全然不同。管理原子大小的法則是量子力學的機率性定律。物理學家一定要極聰慧,才能把這些量子特性引誘出來,因為在人的大小的儀器中,這些特性根本不存在。我們看到的能量並不是可以很精確定量的一團,看到的繞著原子嗡嗡地轉的電子雲永遠都在機率狀態中。只有在很特異的情形下,才能在宏觀的範疇中看到這些特性。舉個例子,超導現象,這是一種超級有秩序的狀態,在這狀態中,材料裡的自由電子都自動排成隊,就如一排整齊跳著舞的「火箭女郎」[5]。由於所有的電子都鎖在齊步操舞中,在超導體中的電流可以毫無阻力的流動。
把尺度放大到分子大小時,電力就接管了。把尺度再放得更大,重力就接管了。如莫里森夫婦(Philip and Phillis Morrison)在合著的《十的威力》這本經典書中所指出的,如果你把手指放在糖罐中,拿出時,手指上沾滿了很小的糖粒,是電力把它們沾上的。可是,如果你把手指放在方塊糖的罐中,如果有方糖沾在手上,你必定會嚇一大跳;除非你存心抓一塊方糖出來。
我們知道,所有大尺度的物體都由重力管理,因為宇宙中任何比小行星大的物體都呈球形。原因是,重力把所有物體都拉向一個共同的中心。你我周遭的物體如房屋和山,外觀看起來都大不相同,可是山只能那麼高,再高的話就要被重力拉倒下來了。在火星上,山可以更高大,因為那裡的重力小些。大的物體在和重力掙扎時,就失去了凹凸不平的邊緣。「茶杯要像木星那般大小,可沒這回事,」莫里森夫婦這麼說。當一只茶杯成長到木星的大小時,它的柄和杯緣都會被自身的重力拉向中心去,直到變成一顆圓球為止。
再多加一些物質,重力的壓縮就會把核之火點燃,星球便在核火向外膨脹的壓力與重力塌縮的拉鋸戰中倖存。時間久了,核火燃盡,重力總是贏家。一枚巨星最後會塌縮成一個黑洞。這種現象與這星球周邊是否有行星繞著它轉,或者這星球最初是由什麼樣的塵雲組成的,毫無關聯。重力很民主,任何東西都可以成長為黑洞。
如果時間的腳步慢慢走……
在小事物的宇宙中,即使時間也滴答得快些。小動物動作快,吃下去的食物的新陳代謝也快些(吃得也多些);牠們的心跳快了些,生命的長度也短了些。大衛斯(Paul Davis)在他的書《關於時間》中提出這個問題︰是否老鼠覺得自己的生命很短暫,就像我們常覺得人生苦短?
生物學家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小動物滴答得快,生活步子也快,活得短;大的哺乳類活得長,生活步調慢。以體內各自的生理時鐘來衡量,不同大小的哺乳類,活的時間大致相同。」
我們都按自己的節拍器打出拍子,走我們人生的路程。可是大衛斯倡議說,所有的生命都分享同一種拍子,因為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依賴化學反應為生,而化學反應進行的時間窗口極窄。在物理學家佛華德(Robert Forward)的傳奇科幻小說《龍之卵》中,在中子星上生活的生物,能量是來自核反應;在它們的世界中,每件事物發生的時間都要快速百萬倍以上。地球上一分鐘的時間還沒有過去,那中子星上許多世代的生物都已經度過了從生到死的循環。
想像一下,如果我們能把新陳代謝慢下來,地球的形象會是什麼。如果時間的滴答夠慢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山的成長,大陸的板塊漂移、碰撞在一起。天空中爆滿了超新星,彗星會像隕石一樣規律墜落到崖岸邊上。每一日都像七月四日那樣[7]。
我的一位藝術家朋友喜歡作這樣的幻想:如果我們能站在離地球很遠的地方看地球,可是我們還能清楚看到人群,我們會看到每日有極大的人潮掃過地球;這些人從床上起身,而在夜晚當他們要上床去睡時,又有另一波巨大的人潮起身刷牙——這樣的人潮澎湃,從一時區移到另一時區去。刷牙波的起伏,追隨著太陽的影子掃過地面。
因為我們只能在我們的時間尺度中看到事物,因此失去了許多觀點。
顯微鏡下另有一片天地
探測我們皮膚表面的世界,可以成為一種令人恐懼的經歷。
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我試過。我用了舊金山探險館的一具裝了攝影機的可撓式顯微鏡來看過。膀子上的皮膚顯出了令人目眩的景色,有刻痕、皺痕、濕濕的看上去如巨紅木的汗毛——都藏在極大塊的穢物之中。鬚及眼睫毛看上去更令人生厭:順著睫毛泌出的油水,就如從狗尾巴流下污泥一樣。看到皮膚底下毛細管中流動的血球,的確令人驚服,就像看著不穿衣服的自己一樣。
更有威力的顯微鏡,還可顯露出所有住在你臉上的生物——掛懸在極細的絨毛上、或隱藏在你的睫毛中。更不必去提那億萬個在你床上和你共眠的,以及隱藏在你的浴巾、面巾裡的微生物了。有多少隻細菌可以站在一根大頭針的針尖上[8]?也許你不會想知道[9]。
我們都緊緊握住自己的生活尺度不放,因而錯失了生命中不少多采多姿的體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微生物學家培斯(Norman Pace)說:「海洋中還有哪些生物?人們只想到鯨魚和海豚。可是海洋中百分之九十的生物都小於二微米。」
在微生物學家馬古利斯與多立安.薩根所著的《演化之舞》[10]中,兩位作者指出了「大的生物總要優越些」這想法的謬誤。在細胞組成的生物(如我們)於地球上出現之前十億年中,簡單的細菌已把這行星的表面改了觀,它們發明了許多人類還在嘗試瞭解的高科技過程——包括以近乎百分之一百的效率去把太陽光轉變為能量(綠色植物經常在做)。真的,兩位作者指出我們體重(把水減掉後)的百分之十都是細菌,其中大多數細菌都是我們不能缺乏的,否則人類就無法生存。
再把鏡頭對準結實的桌子放大來看,桌子變成了有極大空域的空間,偶爾有一粒迷了路的原子核在那裡遊蕩,周邊圍滿了怒髮衝冠的電子雲。你再把鏡頭拉到極遠,然後快速拉近,這個新世界看起來先是簡單,後來變複雜,再變成簡單:從夠遠的地方看地球,只是蒼藍一小點而已;走近些,你看到了氣候的模式及海洋;再近些,人就出現在景象中;再近些,所有都消失了,你又回到物質內部的景色——大都是空空的空間。
因此,複雜性也因尺度而變。蛋是否很複雜?從外貌來看,只是一枚平凡的橢圓體,就如木星的巨紅斑。蛋的內部,有蛋白、蛋黃,及血管,及DNA(基因),及分子搭接起來的序列……
極小宇宙的奇異與豐富,已到了我們想去掌握都不可能的地步。沒有人可以說出比薛丁格[11]更好的話了︰
當我們的心靈之眼穿透入愈來愈短的時間、愈來愈小的距離的時候,我們發現自然界的行為表現,與我們周邊的、在可見光觀測到的、及可觸覺到的物體的行為表現,完全不同,因此沒有一個按照我們宏觀經驗所創出的模型,能說是「真確」的。一個完全能令人滿意的這類模型,非但在實際上是達不到的,而且可能根本是不可思議的。或者,更精確來說,我們當然可以去思考它,可是無論我們怎樣去思考,還是錯的;也許不會和「三角形的圓」一樣的無意義,可是也許要比「長了翅翼的獅子」更沒意義些。
正如我們在下一章會看到的,當我們從少轉移到多、或從大轉移到小之際,那出現的意想不到的魔景,真能使人膽怯;而這魔景的詮釋能力,卻又使我們感到敬畏。
【注釋】
[1]譯注:《愛麗絲漫遊奇境》的第一章。
[2]譯注:「小史都華」(Steurt Little)是卡斯(Williams Garth, 1912-1996)童話中的小人物,最近被拍成電影。「金剛」(King Kong)是一九三○年代的科幻電影,一隻大猩猩變成了四、五層樓高。「親愛的,我把孩子變小了」(Honey, I Shrunk the Kids)是一位化學家不慎把小孩變小的喜劇。「姆指人」(Thumbelina)為德國格林童話中的人物,描寫的是生下來只有姆指大的小孩的故事。
[3]譯注:超人(superman)為美國漫畫中的人物,來自外星,有超乎常人的威力,能飛,能把高速的火車停下。不做超人時則假裝為一位懦弱的記者。「超人」已拍成好幾集影片。
[4]譯注:十九世紀的歐洲,流行由訓練好的跳蚤來表演的馬戲團,觀眾要用放大鏡看跳蚤拉車等絕技。現已不流行,可能已失傳。
[5]原注:按照舊金山探險博物館(Explotorium)物理學家韓福雷(Tom Humphrey)的意見,粗枝大葉說來,所有生物能跳的高度都大致相同。跳蚤和人都能大致跳到一公尺左右的高度——很有趣的一個不變數。請看第十四章〈諾塞與愛因斯坦:真理的不變性〉中的「真和美」。
[6]譯注:火箭女郎(Rockettes)為紐約無線電城的跳舞女郎隊,以整齊及極準的節拍聞名。
[7]譯注:七月四日是美國國慶,傳統上於這一日大放焰火。
[8]譯注:這是引用一位中古世紀瑣碎學派的學者的研究工作,他花了不少時間去研究一枚針頭上可以站立多少位天使。現在用來作為不合實際的研究的諷語。這裡只是拿來做比喻,不是諷語。
[9]原注:要看大開眼界的景色,請去讀這本書《祕密屋》,博旦尼斯(David Bodanis)著。
[10]譯注:《演化之舞》(Microcosmos)的兩位作者: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 1938-),麻州大學講座教授,研究真核生物的演化大師,著名天文學家卡爾.薩根的前妻;多立安.薩根(Dorion Sagan),通俗科學作家,是馬古利斯與卡爾.薩根所生的兒子。《演化之舞》中文版由天下文化出版。
[11]譯注:薛丁格(Erwin Schrodinger, 1887-1961),奧地利理論物理學家,提出原子軌域模型及波動方程,一九三三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他所創的波動方程,即現在通用的量子力學方程,名為「薛丁格方程」。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Jerry E. Bishop的圖書 |
 |
$ 145 ~ 405 | 基因聖戰:擺脫遺傳的宿命 (新版)
作者:畢修普、瓦德霍玆(Jerry E. Bishop、Michael Waldholz) / 譯者:楊玉齡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0-04-23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534頁 / 20.5*14.8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基因聖戰 (新版)-擺脫遺傳的宿命
這場基因聖戰,沒有人能置身事外!
為什麼有些兒童彷彿被下了詛咒似的,還不曾學步,肌肉就開始萎縮,苦撐到二十歲上下終告不治?
為什麼許多人飲食有節,卻仍然躲不過癌症致命的侵襲?
有些人每日運動,還是逃不掉冠狀動脈心臟病要命的追擊?
又為什麼祖上有人精神失常,子孫裡總有人會步上後塵?
酒鬼的子女一出生便給好人家領養了去,為什麼長大後居然也嗜酒如命?
原來,答案就藏在基因裡!
人體中的十萬個基因,牢牢牽繫著每個人、每個家族的命與運。
我們能擺脫這遺傳的宿命 嗎?我們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嗎?
一項雄心足以媲美曼哈坦原子彈計畫、阿波羅登月計畫的「解讀人類基因地圖」大計畫,已經展開。科學家正發動一場追獵 致病基因的聖戰,矢志搜尋出三千種遺傳疾病的基因缺陷,並一一殲滅。這場戰役,關係著你我以及下一代的未來,沒有人能置身事外!
作者簡介:
畢修普(Jerry E. Bishop)
華爾街日報資深記者,資歷超過三十年,是該報醫學、科技議題的主筆,曾多次獲得新聞報導桂冠。近年最受人注目的,是於一九九0年初因報導冷核聚變 (cold fusion) 研究引發的爭議,而獲得美國物理科學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Science) 頒發之報導獎。
瓦德霍玆(Michael Waldholz)
華爾街日報記者,資歷逾十年,主跑醫學、公共衛生及製藥工業的路線。 瓦德霍茲因與畢修普聯手報導基因研究的現況,而獲得華爾街日報社內之頭版系列報導獎。這項肯定,促使兩人再度攜手,撰成本書。
章節試閱
第五章 尺度的問題
你怎樣才能把五○○,○○○磅的水浮懸在空中,而不用到看得見的支架?
(答案︰把它變成雲。)
——藝術家米勒(Bob Miller)
受邀去遊歷每一件事物都比我們世界中的要大許多或小很多的世界,似乎帶有一種迷人的魔力。去冥想海洋或天空的廣闊,或者在顯微鏡下觀看池溏中拿來的污水,或是去想像原子的內在生活,這些行為都把我們遠遠帶離到日常生活之外的領域,進入一個只能依靠想像力才得跨入、極有異域情調的景色中去。
能長成巨人的滋味是什麼?變成一隻小蟲的大小呢?愛麗絲吃了一枚蘑菇,就脹大到如美西感恩節遊...
你怎樣才能把五○○,○○○磅的水浮懸在空中,而不用到看得見的支架?
(答案︰把它變成雲。)
——藝術家米勒(Bob Miller)
受邀去遊歷每一件事物都比我們世界中的要大許多或小很多的世界,似乎帶有一種迷人的魔力。去冥想海洋或天空的廣闊,或者在顯微鏡下觀看池溏中拿來的污水,或是去想像原子的內在生活,這些行為都把我們遠遠帶離到日常生活之外的領域,進入一個只能依靠想像力才得跨入、極有異域情調的景色中去。
能長成巨人的滋味是什麼?變成一隻小蟲的大小呢?愛麗絲吃了一枚蘑菇,就脹大到如美西感恩節遊...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畢修普、瓦德霍玆 譯者: 陳芝儀
- 出版社: 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04-30 ISBN/ISSN:9789862165218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534頁
- 類別: 中文書> 醫學保健> 西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