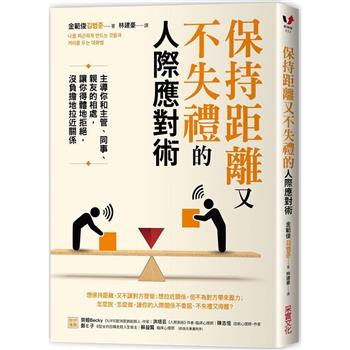推薦序
揭開亞當What’s in a Name/譚鴻鈞
不同於視覺藝術,表演藝術(performing arts)經常是種更為轉瞬即逝的存有。繪畫或雕塑在完成後通常就持久穩定地存在,而戲劇、舞蹈或音樂作品則藉由表演當下於一段特定時間在場。演出一旦結束,作品持續存在的地方,變成了觀眾和參與者的腦海。
然而,有點讓人出乎意料的是,隨著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攜手藝術家暨策展人林人中創辦的「亞當計畫──亞洲當代表演網絡集會」(ADAM,Asia Discovers Asia Meeting for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某些具持久性的東西似乎已然確立與扎根。亞當計畫作為年度活動,在廣大藝術社群中深具知名度。儘管它致力於轉瞬即逝的藝術,在歷經了連續五屆的舉辦,它已成功培養出一個由亞太區域及其他國際藝術家與節目策劃人組成的跨域網絡。這相當不簡單,因為此計畫在2017年創辦的時候,該領域已經有很多自1990年代以來起家的節慶活動、專業集會、文化產業市集和其他形式的聚會,皆鼓勵了亞洲各地表演藝術網絡的長成與發展,也促使世界各地的表演藝術場景有著更緊密的往來合作。
如果亞當計畫證明了自己具有持續性的能耐與實力,而不僅是眾多交流活動之一,部分原因在於它造就了獨一無二的機會,讓業界專業人士彼此交流連結,也讓藝術家們透過能持續相處的時間相互認識,並共同鑽研創意與正在進行中的作品。例如,在我親自體驗過的2018年那一屆,發生於亞當年會前的「藝術家實驗室」(Artist Lab),藝術家們透過數週的駐地活動相遇,一起創作、思考和生活。年會期間,駐地藝術家們會進行幾場成果發表,展示他們合作發展的作品,這些作品大多有著驚人的新鮮感和創造性,特別當它們都是在短時間條件內產出的。這種對藝術家發展的重視也是支撐亞當計畫的動力,讓它即便在面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無法旅行移動的處境下依然能堅持不懈。如今亞當計畫已超越最初幾屆以參訪聚會為主的功能,而煉鑄成一個裨益藝術發展的平台,像是2021年的「集會」便重新設計為三場獨立且貫串全年的實體和線上交流。
對過程性和思想的重視,突顯出亞當計畫的獨特優勢之一,即它所論及的「當代表演」。也就是說,除了將亞洲聚集在一起的地理野心外,該活動還跨越學科及領域,透過共用但卻具有不同意義的「表演」詞彙在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之間游移。「表演」(performance)在2000年代逐漸自成一格,與它的前身──行為藝術不同。行為藝術(performance art)自1960年代後期開始從視覺藝術中產生,部分是為偶發事件和其他類似行動的產物,並經常在非藝術的環境中呈現藝術家自己的身體;而「表演」則以經驗現場性為出發與基礎,展現劇場、舞蹈、音樂及其他藝術表演的共通性。然而,儘管編舞家在展覽配置中工作或視覺藝術家在舞台上表演已比比皆是,但能像亞當計畫那樣,讓來自不同領域的藝術家一起工作實則十分罕見。這個計畫反映了這些不同類型之間如何日益匯聚,將編舞家、表演者、導演、音樂家與視覺藝術家統合在一起──這並不令人感到驚訝,因為林人中本人在轉向視覺藝術空間的創作形式前就是從劇場起步的。透過這種方式,亞當計畫讓新的交流形式和論述生產變得可能,這是個令人興奮的見證。
此刻,在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設計的臺北表演藝術中心開幕之際,亞當計畫同步慶祝創辦五周年。我們當然希望,它會有更多的周年紀念。而且,正如「亞當」是第一個人類,且讓我們期盼亞當計畫在當代表演場域裡預示著全新一代的到來。
譚鴻鈞(John Tain)
亞洲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研究總監。曾任美國蓋蒂研究所現代和當代館藏的策展人。近期策展計畫包括第15屆卡塞爾文件展的展覽「翻越」(2022)、亞洲藝術學院(2021–22)、「社群築織」展覽(2020),以及與達卡藝術高峰會及康乃爾大學比較現代性研究所合作的「區域及跨區域現代藝術史︰非洲、南亞及東南亞」(2019–20)計畫。
引言
亞當計畫策展統籌 林人中
本書奠基在「亞當計畫」於2017至2021年間,呈現亞太及各地藝術家透過表演作為媒介、型態與方法所進行的交流、研究與實踐上,試圖在當代表演的全球在地語境裡提出或提問一種「仍處於過程中」的知識生產。它記錄了這個計畫平台的生成與運動軌跡,更並進一步延展與地緣政治、社群與社會參與、跨文化研究及跨域藝術等相關問題意識的交往。作為計畫主持人,我的工作是與藝術家一同持續地挖掘、攪動問題,並將他們舞動、雕塑、料理及循環諸類思辨的行動佈置成一場表演。
沿著點線面的途徑,《身體網絡:當代表演的文化與生態》將這些充滿表演性的操練過程放置在藝術家個體、合作及藝術生態系統三個面向,來描繪當代藝術的身體、社會與文化如何交織成一個盤根錯節的網絡(而本書所盡之境只是網絡中的局部)。
第一部「藝術家的身體與研究」呈現行為、舞蹈、劇場、新媒體及視覺藝術家們的現場展演與行動背後的創作研究與發展。他們的身體內部與所相連的特定歷史、社會過程及當代空間,啟發我們身體如何作為田調的語言與工具,而創作研究又如何充滿了以過程為目的的表演性。第二部「合作和跨文化實踐」採集了藝術家們合創與交互答辯的第一手經驗。藉由他們之間的各類撞擊與交流,展現跨文化實踐在理論框架外可能的實驗性論述。第三部「測量藝術生態」則書寫藝術家社群、當代社會及21世紀以降機構產業之間的對話與回應。進一步幫助我們檢視此時此刻身在何方,及各職類藝術工作者如何一同構築了生態,也包括這本書的所有作者:藝術家、策展人、學者、藝評人、製作人及文化機構成員等。
值得留意的是,這個身體網絡所概括的各種見解,並不存在單一、固定的對於「亞洲作為方法」的共識與理解。單篇文章需與同部或另一部裡的另一篇或幾篇文章對話,才可能產生立足點。因此,與其說這本書「構成了」一部論述,不如說,它其實「提問了」論述本身如何構成,更「邀請著」讀者及藝術從業者進入反身批判性的思考空間:關於「誰」、「在哪裡」、「為了誰」、「用什麼立場」,在觀看與排練「亞洲」、「亞際」及「當代」──而當中,又存在著什麼樣的文化與想像間的接合或背離。
亞當計畫的起心動念為要搭建一個開放且異質性的基礎設置,並藉由藝術家的研究與實踐,去尋找去中心且非二元對立式的當代表演文化論述。這本將工作現場的實況、幕後及反響轉化為意義生產的讀本,也回應了新冠疫情對社會及藝術生態系統造成的衝擊與改變。2022年,隨著臺北表演藝術中心開幕,亞當計畫以此書繼續提問,在亞洲與全球當代藝術裡擾動那不穩定的網絡與身體。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