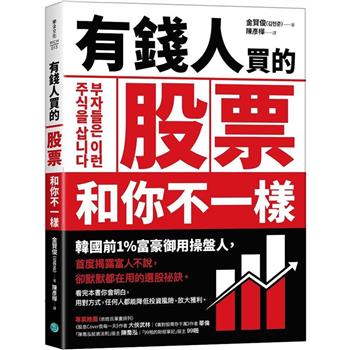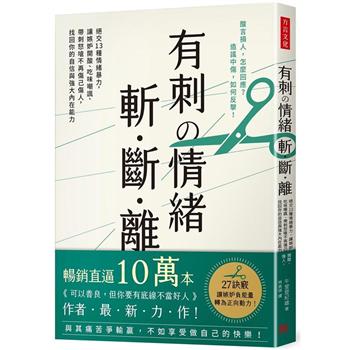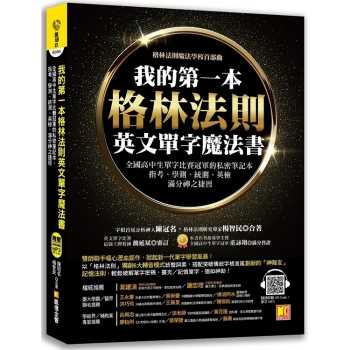一本設計師、藝術家都需要的色彩靈感泉源
原來顏色可以這樣看、這樣讀、這樣玩
一本超乎想像、最亮眼的色彩書
將打開你的雙眼,再次真正看見顏色
你知道……
認知心理學家對於「聯覺問題」的關心,就像紅地毯旁的狗仔隊一樣著急;
天文學家一本正經地慎重舉行研討會,就為了討論「宇宙的顏色」;
一件「帝王紫」的古羅馬長袍,需要鐵打的染工手指與一萬隻壯烈犧牲的骨螺;
毀了伊甸園的真的是艷紅的蘋果嗎?還是無花果、馬鈴薯,或是當時小亞細亞盛產的柳橙?
有的顏色迷人、開朗、活潑、幼稚;有的顏色令人反感、精力充沛,或散發誘惑。我們每天遊走於色彩的茫茫大海,卻似乎視而不見。作者朱蒂.史坦沃一手抓著妙筆,一手握著超乎想像的有趣透鏡,帶領讀者以截然不同的觀點看待世界。而這只透鏡就是──《紅橙黃綠藍靛紫》。
西元1856年,第一種人造染料──淺紫色誕生。不到兩百年後的今日,色彩的運用有了爆炸性的發展,現代人日常生活中能見到的色彩,不只繽紛絢麗且無處不在,甚至到人們開始不把顏色放在心上,色彩悄悄從在這世界隱形。
沉醉在色彩世界的設計師朱蒂‧史坦沃,用最詼諧幽默的方式,讓你不僅在不知不覺中熟知虛色、光譜與夸克的顏色(這種很深奧的理論),還能在知道為什麼鉛筆是黃色、火鶴的羽毛是粉紅色之後,意猶未盡地趕著看下一篇。
本書的目的在於,幫助讀者回歸真正看見顏色的時光,就像孩子第一次看到消防車的紅色。先帶領讀者了解基本概念,例如顏色是什麼、染料與顏料的歷史、色彩理論簡介,並從語言學家的(瘋狂)觀點探討色彩詞彙。隨後,進入彩虹世界「紅橙黃綠藍靛紫」,在每一種顏色的開端,會先鳥瞰此顏色的觸手會深入哪些主題。讀者也許會發現,這些故事似乎包含各個學門、跨越各種文化,目標很簡單,就是試著解讀色彩的意義。
作者簡介:
朱蒂‧史坦沃Jude Stewart
朱蒂‧史坦沃(Jude Stewart)為《石板雜誌》(Slate)、《信徒雜誌》(Believer)、《快公司》(Fast Company)等書刊撰寫設計與文化文章,也是《Print》雜誌特約編輯,每月在部落格上刊登兩次色彩、圖樣及其他與設計相關的文章。作者現居芝加哥,網站為:www.judestewart.com。
譯者簡介:
呂奕欣
師大翻譯所筆譯組畢業,曾任職於出版公司與金融業,現專事翻譯,譯作囊括建築設計、文學小說、語言學習、商業管理、旅遊知識、健康養生等領域。
推薦序
為何寫一本關於色彩的書?
我想起多年前讀到的一句話:「色彩並非塗出來的」(Color is not colored)。這句話出自哥雅(Goya,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望向窗外我看見種在屋子四周的橄欖樹。畫圖時,我偶爾會用到一種名為橄欖綠的顏料(PR101、PY42、PG7),但它其實和這些樹木的顏色不一樣。兩隻狗趴在地上望著屋外,據說牠們眼中的世界是黑白的,不知牠們看到的世界是否和我一樣。
──佩德羅‧卡布里塔‧瑞斯(Pedro Cabrita Reis)
我們天天沉浸於色彩的祕密中,日常生活宛如連環漫畫,輪廓裡原本的空白上了色,於是每一格滿是有顏色的東西,比方鉛筆、地鐵、雨傘、領帶、櫻桃、樹葉或煙。色彩無處不在,多到讓人視而不見,直到突然發生讓一切改觀的事。嬰兒其實看不見顏色,他們望向的是能吸引注意力的東西,比如一輛呼嘯而過的消防車(它會發出尖鳴、會發光,還會噴水!)孩子們把消防車視為一個閃亮亮的整體,唯有成人才能分別看待消防車吸引人的要素:它的顏色耀眼的紅色和銀亮的鉻合金。
對孩子而言,學習色彩的過程意味著把「魔法」換成「知識」。把物體貼上「紅色」標籤的過程,就是把範圍廣大的」,縮小為比較容易掌握的東西。色彩猶如許多桶子,我們不停往裡頭扔進許多東西。以紅色來說,先放進去的是蘋果、櫻桃、消防車、停止標誌,接著再放進龍蝦、小科爾維特跑車(Corvettes)、情人、長波短的光、火、這題答錯了、基督救贖、共產黨員、德州投票結果(譯註,美國選票以紅與藍代表共和黨及民主黨,身為共和黨鐵票倉的德州便是俗稱的紅州)、中國慶典、非洲葬禮、血、警告。
桶子裡越裝越多,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變得更困難:紅,究竟代表什麼意義?紅色代表共產主義的工人,還有上好的龍蝦。紅色表示憤怒(前提是當它不代表愛、勇氣、活力或死亡時)。全球一百九十四個國家中,僅二十六國的國旗不包含紅色,所以當兩個敵對國家在戰場上短兵相接時,竟是為了同一種顏色奮戰。那麼,紅色不代表什麼?我們腦中浮現的或許只有少少的這幾種可能:冷靜、寒冷、無聊、天真。如果紅色幾乎能包含所有意義,是否等於它不代表任何意義?這想法同樣叫人生氣。
1980 年代, 曾有一本很受歡迎的心靈勵志實用書《出色的妝扮與配色》(Color Me Beautiful)。書頁裡塞滿許多面露自信的女子,她們藉由穿上與膚色搭配出「正確」色彩的衣服改頭換面。書中「變身前」與「變身後」的對比照,很有說服力。書上的女子穿上粉紅色時,顯得嬌豔動人、容光煥發;穿上橘色則顯得憔悴縮小。色彩彷彿能吸走她的靈魂,也能把靈魂還給她,實在神奇。有一次,我在匆忙間將客廳漆成黃色,即使對廠商為這顏色取的蠢名字「小天使」嗤之以鼻。沒想到,客廳散發出的歡樂感迫人,就像不時發作的偏頭痛,教人動彈不得。《科學》(Science)期刊在2009 年發表的一份研究指出,紅色房間會讓在其中工作的人精準、謹慎,藍色則有助於發揮創意;類似的研究為數不少(認知心理學家似乎特別喜歡比較紅色與藍色分別能對心理產生什麼影響)。世上有超過半數人口,將藍色視為與神祇連結的管道,例如猶太人
披著藍色滾邊的禱告披肩,思考無窮無盡的時空;穆斯林在藍色清真寺禱告;佛教徒手持土耳其藍的念珠誦經。在宗教世界裡,大家心中除了藍,還是藍。
請你默想一下以下畫面,就像看彩通(Pantone)幻燈片那樣:焦黑的番茄;以藍筆寫的「黃色」;清新明亮的水彩組;愛爾蘭與伊斯蘭蓊鬱的綠色;可磨成顏料的青金石與印度黃石;一個紅色矩形——或是阿方斯‧ 阿萊(Alphonse Allais)畫的<中風紅衣主教在紅海旁採收番茄>(Apoplectic Cardinals Harvesting Tomatoes by the Red Sea);你支持的足球隊顏色;國家的顏色;敵人的顏色;療癒的顏色;以及所有能鼓勵你、令你不快或激發思考的顏色。當代畫家大衛‧ 貝奇勒(David Batchelor)曾以一本薄薄的《色彩恐懼症》(Chromophobia),解釋西方文化對顏色的微妙迷信,並指出人會出於恐懼,為「他人」賦予某種顏色。想想華爾街的商務人士,他們身穿的大概都是灰、黑與白。鮮豔色彩似乎代表俗氣、幼稚、反演化、怪異、性慾失控、反理性。總之,色彩必有意義。
無怪乎色彩會引起眾多爭端,且延續數千年。哲學家認為要說明感覺(sensation)的局限時,最好的媒介就是色彩,比如我們可問:我看到的紅色與你看到的一樣嗎?你如何知道是一樣的?藉由這些問題,我們可以探討人們的想法,以及語言與實際物體之間的落差,甚至世界的可知性(knowability)等諸多難題。哲學家路德維希‧ 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論色彩》(Remarks on Color)中問道:「對我而言,觀看,是否是件熟悉的真實?」色彩的複雜難解、不可能存在的色彩(如帶紅的綠色),以及不存在黑色的鏡子與棕色交通燈號等,他都感到十分驚奇。對政治運動人士而言,色彩是可用來推動革命的工具,而對畫家來說則是又愛又恨的對象。日常生活中,色彩也像惡性循環,在流行時尚中反覆潮近潮退,例如暗粉紅搭土耳其藍是1980 年代粉領族的代表配色,蘋果筆電MacBook 的白色搭配透明棒棒糖色彩,則代表我們這個時
代。同時,色譜上的所有色彩幾乎每天都會出現:瞧瞧孩子們為了一百二十八色的蠟筆正在爭吵;手指沾滿的復活節彩蛋顏料;還有一般人的臉部彩繪、染髮與指甲花彩繪。
我們每天早上都得打開衣櫃,思考該穿些什麼,做出什麼是完美配色的決定。當你想要寫一本關於色彩的書籍時,很快就會明白一件事:你可以想辦法用書頁或畫布將色彩與文字的距離拉近,兩者卻無法完全整合,它們之間也沒有什麼環狀解碼器(decoder ring)或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我們幾乎可以斷言,即使文字與色彩數量再多,兩者依然無法完美轉換。
所以,一本主題似乎無邊廣闊但內容有限的書,會是什麼模樣?如何能讓你在讀這本書時,加深日常生活色彩的了解?「習慣會吞噬工作、衣物、家具、妻子與對戰爭的恐懼」藝評維克托‧ 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在1917 年寫道「然而藝術的存在,讓我們得以重新發現生命的感覺。」色彩絕對無所不在,本書的目的在於,讓你回到真正看見顏色的時光,就像孩子第一次看到消防車是紅色的。《紅橙黃綠藍靛紫》的目標很簡單:把資訊放到你面前,讓你大開眼界,看出生活中色彩蘊含的豐富意義。
為何寫一本關於色彩的書?
我想起多年前讀到的一句話:「色彩並非塗出來的」(Color is not colored)。這句話出自哥雅(Goya,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望向窗外我看見種在屋子四周的橄欖樹。畫圖時,我偶爾會用到一種名為橄欖綠的顏料(PR101、PY42、PG7),但它其實和這些樹木的顏色不一樣。兩隻狗趴在地上望著屋外,據說牠們眼中的世界是黑白的,不知牠們看到的世界是否和我一樣。
──佩德羅‧卡布里塔‧瑞斯(Pedro Cabrita Reis)
我們天天沉浸於色彩的祕密中,日常生活宛如連環漫畫,輪廓裡原本的空白上了色,於是...
目錄
七 引言
十二 色彩: 分析史與使用指南
1 白
13 粉紅
25 紅
37 橙
49 棕
59 黃
71 綠
83 藍
95 靛與紫
105 灰
115 黑
125 彩虹之外
七 引言
十二 色彩: 分析史與使用指南
1 白
13 粉紅
25 紅
37 橙
49 棕
59 黃
71 綠
83 藍
95 靛與紫
105 灰
115 黑
125 彩虹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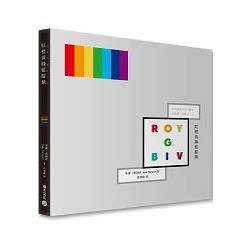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