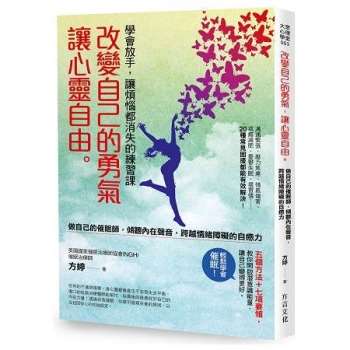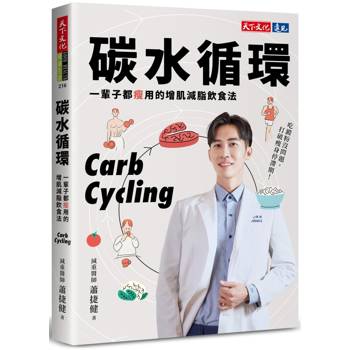推薦序1
在人權的兩端拔河
2010年3月的台灣,擔任法務部長的人權律師因為堅持不執行死刑,不惜「替死刑犯下地獄」,引發被害人家屬的怒吼,終至必須辭職以平息眾怒。人權,不是普世價值嗎?何以在台灣變成政治風暴的導火線?
法律人談的人權,經常是以被告、犯罪人、犯罪嫌疑人為中心,主要因為「無罪推定原則」乃「世界人權宣言」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共同揭櫫,以國家機器掌控的人力、資訊、權力、工具等無上的優勢,一旦由刑事司法系統發動對個人的偵查,若缺乏在程序上與正當性加以節制,很容易為了發現真實,卻犧牲了人權,甚至可能造成冤案錯判。因此,被害人在刑事司法體系中的地位相對的渺小,他們的人權沒有被法官、檢察官關照,完全無法同理犯罪被害人與家屬的感受,更何況有許多被害人的生命權早就被犯罪者剝奪!
1992年我在芝加哥進修,當時的芝加哥治安不寧,學校附近劫財劫色案件時有所聞。校方經常會提出警告,要求夜歸的女生要注意人身安全。一向鐵齒的我,絕沒想到我也會有犯罪被害的經驗。在某個月黑風高的冬夜,就在回家途中遇襲,被一個做勢持械的黑人逼到牆角,當時曾經擔任過警職、身懷「絕」技的我,強做鎮靜,與歹徒周旋,交出皮包換得全身而退。幾分鐘後我走回距離不到兩百公尺的住處,在室友開門後,我頹然跌坐痛哭,想起剛剛與歹徒的對峙,生死一線之懸,渾身顫抖不止。我第一次感受到被害的恐懼,當時的心慌,至今依然鮮活!
到底犯罪被害的痛能夠持續多久?被害人家屬的恨有長?我有限的經驗告訴我:即使有形的傷痕能被時間撫平,心頭的痛一輩子也忘不了。
我的大哥在他29歲的那年,被一個卡車司機越線逆向迎頭撞上而喪生。我還記得出事的那天上午,警察打電話到家裡告知噩耗,母親淒厲絕望的哭嚎,我永遠難忘,一直到三十年母親辭世前,對早逝的大哥思念日殷,對於奪命司機的恨未曾稍減。
除非得到犯罪人真正的懺悔,被害的痛不會消失。
1991年美國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市爆發聳人聽聞的連續殺人事件。這個被稱為密爾瓦基禽獸(Milwaukee Monster)的殺人魔Jeffrey Dahmer,被控略誘、姦殺17名少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Dahmer藉由姦屍、烹煮食用屍體得到性滿足與高潮,Dahmer被捕時,冰箱中尚存有待烹的屍塊與頭顱。即使他的罪刑令人髮指,但在沒有死刑的威斯康辛州, 32歲的Dahmer獲得957年徒刑宣判,終生不得假釋。當時的審判過程,被害人家屬帶著被害人遺照在法庭上對Dahmer的控訴,更是令人動容,只不過這些痛苦,在一個廢除死刑的法庭上無法得到救贖,引發深思:像他這樣罪無可逭的殺人魔,竟要人民納稅養他一輩子,正義何在?Dahmer入監服刑後,兩度被獄友攻擊,第二次更傷重不治,行兇的Christopher Scarver自稱「替天行道」,輿論甚至有正義終得伸張(Justice is served.)形容,雖然Scarver仍以殺人被判終生監禁。
在台灣,隨著國際間「廢除死刑」的理念蔚為潮流,許多法官對於許多惡性重大的罪犯,除非是「欲求其生而不可」的特殊案例,絕少做出死刑宣判。
兩年前新竹男子楊忠平被控強盜殺害鄰居女子後,搜刮其財物,且為滿足一己淫慾,污辱被害人之屍體2 次,進而燙煮、支解被害人之屍體,檢察官認為其犯罪手段極為兇殘、泯滅人性,對於被害人家屬之身心造成莫大創痛,實有永久與社會隔絕之必要而求處死刑,但法官認為楊在殺害女子後,仍起慾念對她姦屍,足證他對該女存有愛慕之意,認為未達須剝奪生命程度,因而改判無期徒刑。
三年前,一名特戰部隊退伍的計程車司機闕興華,因細故殺害懷孕的大陸籍女子,將她開膛破腹,曝屍八里山區,被捕後毫無悔意,甚至發出「還會再殺她一次」的狂言。這樣的兇手,法官也是判處無期徒刑。
死刑存廢的爭議,彷彿在犯罪人與被害人的人權兩端進行拔河,但是人民心中的那一把尺,正邪的果報、賞罰的度量衡早已決定。
1997年的4月14日白曉燕被陳進興等四個凶神惡煞擄走撕票;1999年的4月14日日本山口縣光市的本村家年輕的媽媽被姦殺,不到一歲的女兒被兇殘的猛摔勒斃。經歷喪女之痛的白冰冰女士化小愛為大愛,投入公益,成為維護犯罪被害人權益的主要倡議者;無獨有偶的,慟失妻女的本村洋,也成為日本司法改革的重要推手,他讓傲慢的司法終於可以垂下眼簾,瞥見被害人、被害人家屬的痛,終於能夠看見毫無悔意的兇手的「惡」。
白曉燕、本村彌生母女猶如劃過穹蒼的殞星,她們留下的幽光沒有因為她們的殞落而消逝,因為她們的家人靠著「與絕望奮鬥」的勇氣,讓法律能夠更貼近庶民心中的公理正義。就像星雲大師在談因果時所引用的「非、理、法、權、天」。意思是說,「非」不能勝過「理」,「理」不能勝過「法」,「法」不能勝過「權」,有權力的人可以改變法律,但是「權」卻無法勝過「天」。天,就是也能保障被害人人權的公理正義!
(葉毓蘭:中華警政研究學會理事)
推薦序2
你願意一起為捍衛司法而戰嗎?
「若是就這麼認定這次的判決,以後的審判都會以此案為基準。我絕不允許這種事情發生。就算上司反對我也要繼續上訴,即便失敗了一百次我也要嘗試第一百零一次。這件事非做不可。本村先生,你願意跟我一起為了改變司法而戰嗎?」
這是在本書《光市母女殺害事件》初審宣判之後,吉池主任檢察官對本村洋的承諾。
時間跳到2010年的三月,某日,我在家裡吃晚飯的時候,看到電視新聞報導台灣連續多年不執行死刑的內容。我把我參加研考會願景2020調查,和在部落格寫了多篇文章替受害者家屬打抱不平的文章的事情都告訴了我的家人。並且說了如果有可能的話,我想推動要求政府執行這四十四名已經定讞的死刑犯死刑的活動。
家母聽了之後眉頭深鎖,她委婉地告訴我,「你已經是有了小孩的爸爸,這樣會不會不太好啊?」
我當然知道母親的關心,我當然知道有些宗教覺得不管怎麼樣罪大惡極的人都不該死,否則會有報應。
但我也知道強凌弱是不對的。正因為不對,所以應該有人說些話,應該有人做些事。
被鐘德樹縱火活活燒死的受害者家屬曾經留言給我:「朱大,謝謝你替我們這種受害人家屬發聲。為什麼受害人家屬沒有聲音?因為一開口馬上就被"你要有寬大的心原諒他們"給堵死了,加上所謂人權團體都是所謂清高份子,誰會在乎你們受害人家屬的感受?就像我婆婆說過的:人家權力那麼大,我們沒辦法跟他們鬥...所以就只能選擇沉默。」
當面對人生平順,只能在網路上靠著打字憑空想像親人生命慘遭剝奪有多痛苦的網友時,她的回應是:「請想想:你的姊姊被鍾德樹潑了1身汽油,在她孩子面前點燃,臨死前最後一句話是叫孩子快逃!一個父母養育32年的人就這樣死在白髮人和孩子面前,情何以堪?」
本村洋在日本遭遇到的是法律過時、判例陳舊,不注重受害者家屬權益的高牆。
但在台灣,這些受害者家屬所面對的高牆更為奇特。他們是反對死刑的廢死團體。
這群在所有民意調查中從來無法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們,他們是擁有充足經費、國際奧援,甚至可以印刷出版書籍免費贈送的極少數人。他們是熟知法律、懂得如何非常上訴、懂得如何用盡手段遊說、關切的極少數人。因為他們打著「與國際接軌」、「生命無價」、「人權至上」、「尊重生命」的光環,他們所代表的這些少數民意,就和兩任違背國民之付託玩法弄權的法務部長施茂林、王清峰狼狽為奸,拿著這些受害者家屬所被承諾的處死四十四名死刑犯的正義來獻祭。
換取了什麼?換取了他們清高的形象,換取了他們拯救生命的自我滿足,換取了國際間組織的關懷金援。
那受害者家屬呢?那些摯愛之人生命遭到剝奪,從此再也不能相見的受害者家屬呢?有誰聽到他們來自靈魂深處的慟哭?有誰為他們本就被承諾的正義挺身而戰?
醒醒吧!各位!那些要求廢除死刑的團體發言人、投書報社、來回奔走的所謂廢死團體成員,哪一個人不是擁有專業的法律知識?哪一個人不是受過多年的法律訓練?哪一個跟你我這些升斗小民比起來不是人上之人?但這些人卻利用這些知識和能力去侵逼、壓迫那些經歷喪夫、喪妻、喪子之痛的家屬們,阻止、拖延已經經過重重審理,毫無冤獄可能之四十四名死刑犯的刑罰執行。
日本至今還有死刑。他們的司法官員表現是否比台灣的要好?看看職務等同我國拒簽死刑執行令的兩位法務部部長的日本法相鳩山邦夫吧。他在因為簽署了十三人的死刑執行令,而被朝日新聞稱呼為死神時,憤怒的回應:「實施極刑雖然會使心情難以平靜,但我認為不管多麼痛苦,為了社會正義也必須這麼做。(死刑犯)也有人權和人格。司法部門經過了慎重判斷,法律也有規定。我是在痛苦抉擇之後才決定執行死刑的。難道說他們是被死神帶走的嗎?」
為什麼在台灣卻正好相反?為了受害者家屬爭取法律承諾的正義卻必須承擔道德上的壓力?
而擁有法律知識,懂得操縱法律的人可以違背全台灣的主流民意,刑法明確的規範,自我感覺良好的犧牲受害者家屬所被承諾的正義?
答案很簡單。
因為你我沉默不語。
因為你我天真的以為法律會照章執行。
因為你我以為法有明文規定的正義不會被剝奪。
所以,我要問你一件聽起來很困難的事情。像你我這樣沒有受過司法訓練、沒有專業的法律知識、沒有國際組織奧援、不會因此而領到薪水、不是執業律師、永遠也不會成為法務部部長、當不上司法官、無法憑一己之力拖延刑罰的一般庶民老百姓;你我是否願意站出來,面對擁有這上述一切我們沒有的力量、資源、知識、背景、權勢和能力的人們,在這場強弱懸殊的對抗中,從他們的手中捍衛司法承諾給予被害人家屬的正義?
你願意一起為捍衛司法而戰嗎?
朱學恆
推薦序3
極限之外
在某個公開的場合,有人問我:「為什麼現在的法律好像都只保護壞人,好人的權利在哪裡?」
我想了一下,回答:「其實法律並不是保護壞人,也不是保護好人,法律保護的就是『人』,只是,有些人你覺得他壞到不值得保護。」
或許這就是人類社會無解的難題,我們拋棄了「上帝全能」的信仰,試著用世俗的方法解決世俗的糾紛;我們投入大量聰明的腦袋,反覆辯論,發展出一套又一套的理論,嘗試過一套又一套的制度,但搞到後來,這一套稱做是「法律」的東西,卻離我們理想的「正義世界」還有一大段距離。
或許我們要承認,人類的能力是有極限的。
法律就像是在抽象的社會行為上畫框框,框框以外的行為是黑,框框以內的行為是白(當然框框裡外還有框框,顏色也還有紅橙黃綠等);千百年來,我們透過戰爭、決鬥、選票、抗爭或霸佔主席台不斷地修正這些框框,讓它們能盡量配合這不斷變動的社會,但社會往往變得太快,或是有時人類的心理與行為太過複雜,無論框框們再如何申縮挪移,總還有一些黑色的行為落在白色的區域,或者是落在灰色的區域。而更麻煩的是,框框一旦畫下去,任何細微的調整,都要再透過戰爭、決鬥、選票、抗爭或霸佔主席台之類的程序。
這本<與絕望奮鬥>,便是記載本村洋先生那十年的歷經,一場人與法律在極限邊緣的掙扎。
西元1999年4月14日,日本山口縣光市,本村洋先生的妻子與11個月大的女兒,慘遭一名十八歲的少年沒有理由的殺害;而第一審與第二審的法官卻囿於長久的量刑基準,拒絕對被告宣佈死刑。整個案子於是進入漫長的司法之旅,直到2008年高等法院的更一審的死刑宣判,劃下句點。
刑罰的「去殘酷化」似乎是人類文明進步象徵,從古老的十字架與車裂,到斷頭台與絞首,到現在的槍決、注射與電椅,人們逐漸接受以較快速、較小痛苦的方式,永久隔離那些罪無可赦的罪犯。但是當刑罰的框框畫到了「殺」與「不殺」之間時,文明與正義,似乎開始了一些拉扯。
「我們」相信「我們」是「好人」,「我們」可以不將「壞人」挑斷手腳筋後再泡入糞坑裡,但「我們」還是要給他一槍,讓故事有個完美的結局(君不見電影中好人要是饒了壞人一命,壞人一定還會再耍些小手段)。死亡是個終極的句點,沒有什麼可以取代,也不該被取代。
<與絕望奮鬥>一書中,不可避免地大量觸及了死刑的問題,而由被害人家屬的角度出發,結論也是在意料之內,但作者門田隆將先生與本村洋先生卻不是以那麼直觀的方式達成這個結論,他們接觸不同的聲音,勇敢地觸碰自己理念中最脆弱的部分,尤其本書尾段的一場會談紀實,更讓讀者重新思考整個議題的各個層面。書中並沒有長篇大論的論理分析,而是簡潔卻深刻的親身經歷報導,或許在這樣脈絡上所粹煉出來的理由與結論,能提供我們另一個觀點,去看待這個始終難解的議題。
本書中另一個觸及的議題是刑事訴訟程序上被害人地位的問題。近代歐陸的刑法理念,將刑事訴訟定義為「國家」與「被告」之間的程序,國家透過刑罰所處罰的是被告對於法秩序(術語:「法益」)的破壞,而不是作為代替被害人向加害人索求正義的管道。在這種思考下,傳統的刑事訴訟制度中的確是沒有「被害人」的程序位置,被害人或其家屬最多也就是以證人的身份出庭就案件事實做出證言,但不具備任何程序主體的權利。
這樣的制度行之有年,或許大部分的法律人都已當成理所當然,但在這樣的設計下,被害人或其家屬究竟受了多少委屈與犧牲?而這樣的委屈是否又符合刑法上最基礎的法益保護概念?在本書中,本村洋先生同樣是以他親身的血淚經驗,給我們一個最佳的反思。
然而雖然主題是一個殘忍的犯罪,這本書卻並非如其書名所稱是絕望的;相反地,主人翁本村洋先生堅毅與沉著的態度,使得本書充滿了勵志的效果。如前面所說的,當法律的框框一旦畫好時,必須要再花費極大的力,才能修正分毫,因而只有極少數的人,願意將自己的理念貫徹到這些複雜的立法活動中。本村洋先生的執著與勇氣是令人感佩的,特別當他經歷了如此的人生變故,還曾一度在生死與崩潰邊緣徘徊之後。而我也相信,因為這世界上有著這麼多勇敢固執的人,在這不完美的制度中,面對人類無法取代上帝的事實,我們對於未來,仍是充滿了希望。
李柏青



 共
共  2010/05/24
2010/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