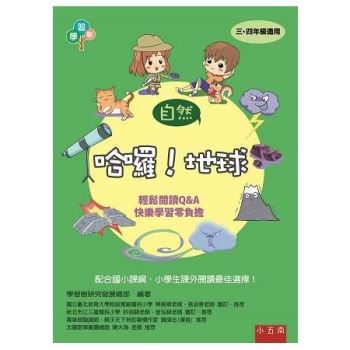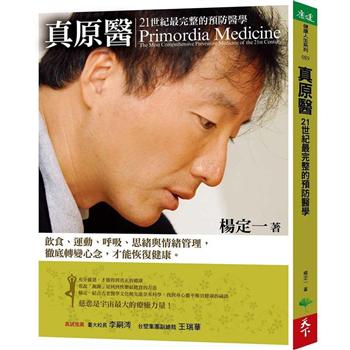銀行內部,到底隱藏了多少祕密?
銀行駭客──兩男一女的駭客團隊,踢爆銀行不法內幕!
年資已有二十年的資深銀行行員米山志乃、一心想挑戰市場的外商銀行交易員長峰卓、年輕的電腦高手後藤知哉。他們為什麼想要入侵銀行系統?他們目的是金錢?報復?或是……
這本小說結合了銀行的結算作業、衍生性金融商品、債券市場,兩男一女扮成駭客入侵銀行系統,盜取交易員的密碼在全球市場上進行交易,並成功「賺走」6億圓……
而且,他們從電腦系統裡發現了銀行的不法內幕!
高潮迭起的選擇權交易+網路犯罪,讓讀者彷彿親臨現場,令人心跳加速的金融犯罪小說!
日本知名經濟評論家佐高信解說。
閱讀重點:
※銀行的組織、系統的架構、入侵的方法
※駭客的道德、法律問題
※在銀行努力工作二十年的女主角的心境變化
※銀行,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作者簡介
幸田真音Kohda Main
1951年生於滋賀縣。曾在美商銀行和美商證券公司擔任外匯交易員、外國債券業務員等職務,熟悉國際金融市場。1995年以小說《避險》登上文壇,其他經濟小說作品還有《銀行駭客》、《傷─銀行崩壞》、《日本國債》、《理財專員有利子》、《偽造證券》、《藍色新興企業》、《凜冽的天空》、《代行返上》、《避稅天堂》、《周極星》(《欲望上海》)等,另有多本隨筆、對談式作品。她可說是繼高杉良之後,近十年來日本經濟小說的代表性作家。
2004年起擔任滋賀大學經濟學部風險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目前還擔任政府稅制調查會委員、財務省財政制度審議會委員、國土交通省交通政策審議會委員。她也擔任出版社鑽石社(Diamond Inc.)經濟小說大賞的選考委員。
★她的網站 www.kt.rim.or.jp/~maink/
譯者簡介
楊明綺
東吳大學日文系畢業,赴日本上智大學新聞學研究所進修。目前專事翻譯與文字編輯工作。譯作有《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五體不滿足的太郎》、《女性身心醫學百科》、《君空》等。
★個人部落格:blog.yam.com/mickey1036(東京兔跳格子)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