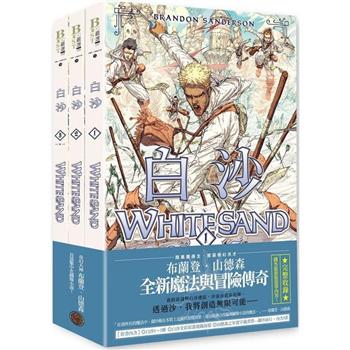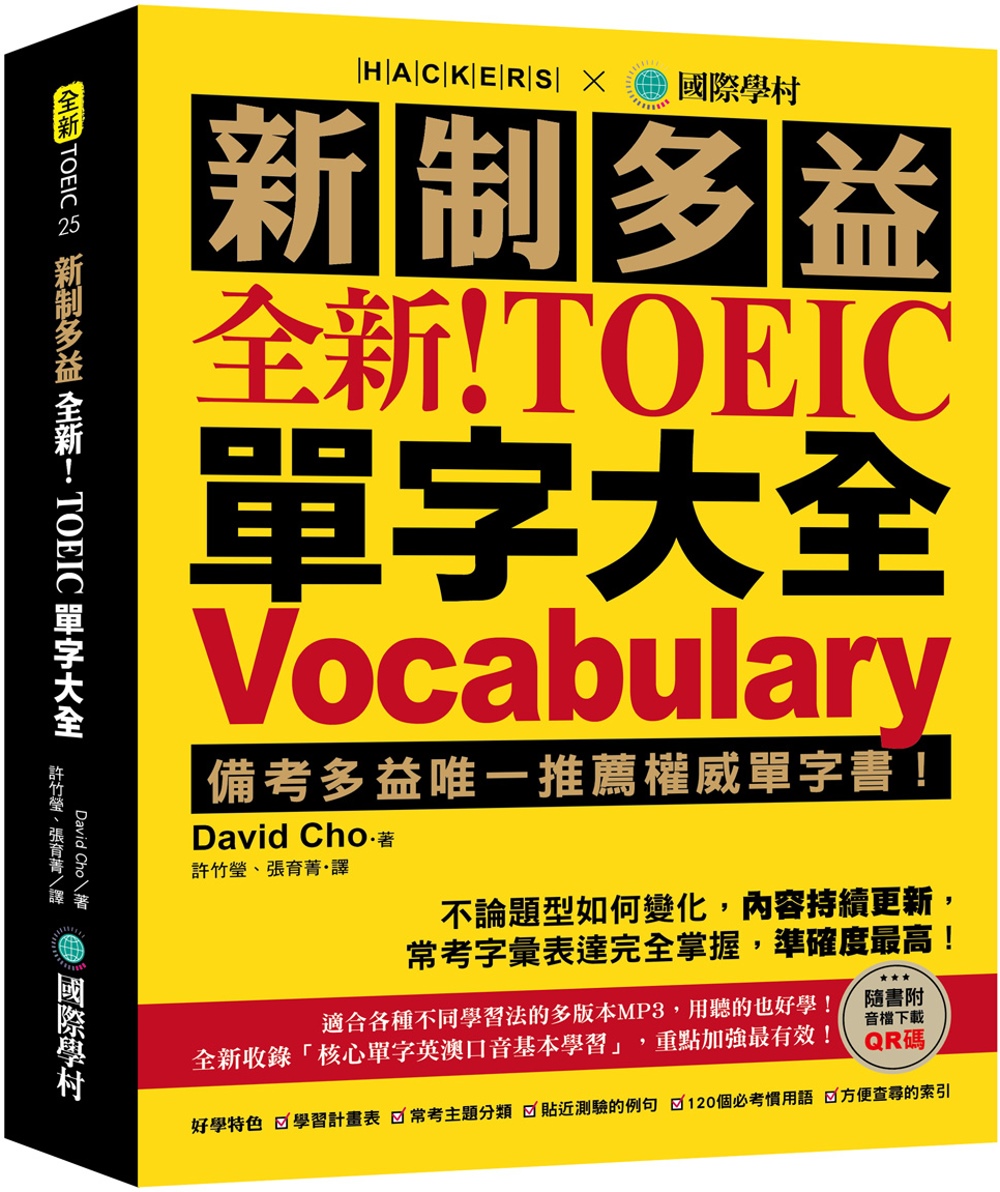原版序
2010年9月,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司法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舉辦為期兩天的錯誤定罪研討會上,本書的第一作者目睹了與會者對刑事案件審查委員會(下稱CCRC)慷慨激昂的批判,也因此埋下了撰寫本書的種子。該研討會僅有大約四十位參與者,而其中大多數是美國的學者、刑事司法實務工作者和司法部的員工。這是一場內部的研討會,安排了幾場報告和討論時間。有鑑於研討會主要是聚焦在美國,CCRC的主席以及其在蘇格蘭的姊妹CCRC的一名民間委員在研討會中的主要目的,是作為對全美各地無辜計畫的成效爭論的反方代表。但是,儘管大多數的報告都收到了禮貌性的提問和回應,CCRC主席的報告卻引起了在場另一位英國學術界人士的猛烈抨擊。
主席Richard Foster向與會者解釋了CCRC的工作內容:審查英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中可能的錯誤定罪,並將認為有「確實可能性」動搖原有罪判決的案件提交給上訴法院。雖然其報告資訊豐富,但卻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就是對CCRC目標的描述、以及對收到案件數量和提交案件的比例的摘要。批評者憤憤不平地說,對至少一部分的申請者來說,CCRC是個失敗且不負責任的機構,不應該成為其他地方改革的典範。他抨擊了CCRC的基本運作和職權範圍,並認為案件被提交回法院的比例低得令人無法接受。最有趣的是他為這一所謂的失敗所歸納的原因:他指控CCRC根本不在意冤案。接著,當來自紐西蘭和加拿大的專家談到,他們的國家有興趣將CCRC作為其定罪後的審查程序改革典範時,他更抓到機會,繼續貶低CCRC的明顯強項。
他爭論的激烈程度引起了第一作者的好奇。這個自十三年前成立以來她幾乎一無所知的組織,為何會激起如此大的憤怒?為什麼批評者如此肯定,一個從表面來看似乎比美國或其他同樣採用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提供了更多扭轉錯誤判決機會的機構,在成立之初就已經失敗了?同時,他的批評中,到底有多少是公平的?
七年後,當我們在撰寫本書時,恰逢CCRC成立二十週年。一份關心法律和正義的線上雜誌《正義鴻溝》(The Justice Gap)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來紀念這一項里程碑。大部分文章得出的結論是,雖然CCRC比起前身(內政部中的一個小型官方單位)確實有進步,但其紀錄就像「基層牧師的蛋」一般(like the curate’s egg),是「好壞參半」;同時,雖然有一些案件展現出了「教科書等級的」調查,但在其他的案件中,調查卻很糟糕(Robins,2017)。CCRC經歷了七年的批評,但卻沒有一個是建立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因為當時並沒有這樣的研究。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填補這一空白。
因此,本書呈現針對CCRC內部決策和裁量權運用的全面性的、為期四年的實證研究結果──這也是同類型研究中的第一份。它揭示了英格蘭和威爾斯地區中那些認為自己被錯判的人,向CCRC提出有罪確定後審查申請時,會發生什麼事。它探討了CCRC工作人員是如何行使裁量來找出並調查可能的冤錯案件,以供法院審查。我們的研究包括對案件資料和整體數據的質化和量化分析、與決策者的訪談、對員工的問卷調查,以及對在所有案件中為決策提供資訊的內部指引的仔細分析。這些內部指引是不公開的。本書試圖透過這些方式,從社會學的角度剖析CCRC的運作,並了解裁量如何在個人和機構層面上發揮作用。
裁量的行使是這項調查的核心,雖然法律創造了CCRC的決策架構,且CCRC為所有類型的案件、和每項調查的不同階段制定了詳細的「個案工作指引」來引導其工作人員,硬法和軟法(hard and soft laws)都為這些制度安排之間的運作實務,留下了相當大的裁量空間。因此,我們研究了影響CCRC在其關鍵工作上的裁量的結構性和文化因素。這些關鍵工作包含:從每年約一千四百份申請中選定一部分案件進行徹底的調查、在案件調查的過程中進行的決策;以及在CCRC被說服而對該有罪判決的穩固性有合理懷疑的情況下,作出認定是否有新爭點或新證據足以達到使法院撤銷該案的「確實可能性」門檻的選擇。
如上文和第二章所述,CCRC在履行這些職責時的職權範圍和效能受到了相當多的批評。這些批評尤其側重於它的提交比例、對於將有限的調查資源用於哪些案件的決定以及它與法院的關係。雖然我們對效能相關問題也很有興趣,但這份研究並不只是單純的想問「這有用嗎?」。我們不能只從CCRC提交給法院的案件數量或類型、或憑法院隨後推翻定罪的比例來了解它。我們也應該要檢驗它如何選擇要重視哪些案件、如何決定調查應該要包括哪些內容,以及如何決定這些調查何時進行以及如何進行。同樣重要的一件事是,將CCRC置於整個刑事司法程序來進行審視:它如何管理與其他刑事司法機構、客戶和利害關係人──申請人、他們的選任律師以及CCRC蒐集證據的對象──的關係。
在揭露這些問題時,我們仔細審查了CCRC的日常工作實務、工作規則和基本預設,以及這些是如何影響對「確實可能性準則」的理解並賦予意義──它認為哪些證據可能可以說服法院撤銷有罪判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不只是把CCRC描繪成一個法律機構,而是一個有文化的機構,並揭示其程序和技術的社會意義和重要性(Garland,2001)。然而,我們也沒有打算要建立一個展示CCRC如何運作的整體理論。相反地,我們試著從不同的角度探索它,以描繪出一個揭示其複雜性、多面性,有時甚至是明顯矛盾的本質樣貌。這主要會出現在第五到十三章中,而第一到四章則是說明研究背景、提供資訊,以幫助讀者理解我們的資料。
第一章會向讀者介紹CCRC,描述CCRC的起源和職權範圍,並透過比較的方式,提供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定罪後審查程序的資訊。第二章試著在描述本研究的目的和實現這些目的所採用的方法之前,先了解對CCRC的批判的性質。第三章介紹了形塑我們的實證研究,並幫助我們理解收集到的數據的理論架構。在第四章中,我們描述了CCRC收到申請時的處理情況,並提出了一個組織理論框架。我們在這個框架之下,討論CCRC是如何在整個調查過程中,作出關鍵的決定。
第五到十三章著重於我們的實證研究,帶領讀者了解CCRC對其收到的申請作出的決定。這些申請向CCRC呈現了一系列在警察和檢察官的調查中、在事實審中,和在定罪後的第一次上訴中的潛在問題。為了幫助讀者了解可能導致申請人被錯判、或認為自己被錯判的可能不當行為的範疇、以及法律、科學或人為的錯誤,第五章將CCRC收到的申請案類型依照有關於錯誤定罪來源的現有文獻進行分類。接著,第六章處理CCRC如何理解每年所收到的大約一千四百份的申請,以及它如何決定對其中哪些申請進行全面調查,同時也透過「檢傷分類(triage)」的過程及早篩選掉它們認為沒有明顯審查依據、不需要全面調查的申請案。
第七章回顧了我們樣本中最大的類別──依法醫和專家證據而翻盤的案件──其中所呈現的問題。它研究了CCRC如何調查此類申請並作出決定。第八章討論了CCRC處理那些所呈現的證據傾向與被害人之可信度有關的性犯罪案件的方法,而第九章則審視了那些與警察違反正當程序或瀆職行為有關的案件。第十章則集中在申請人主張其事實審中的辯護人辯護不力的問題。
CCRC建立的立法依據──1995年刑事上訴法(Criminal Appeal Act)──要求CCRC在部分的調查中與刑事司法系統的其他部門合作。1995年刑事上訴法第15條允許法院指示CCRC代表法院調查特定議題,這意味著CCRC可能會發現自己在第一次上訴期間或申請上訴許可期間調查案件。CCRC有權以其認為最合適的方式進行這項法院指示的調查,並有權調查相關事項,只要它隨時向法院通報其調查情況即可。第十一章討論了這類調查,還分析了CCRC根據1995年刑事上訴法第19條,使用其權力指派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並協助其履行職能的這類少數案件。
第十二章討論CCRC如何平衡其在每項調查中進行徹底調查的目標,以及為了回應等待案件審查申請人的漫長隊伍而對效率的要求。它對CCRC工作人員的調查方式中明顯的差異進行反思:例如,他們在甚麼時候會尋求專家證據、他們何時選擇與申請人約談、何時會認為研究案件卷宗和相關法律就足夠了而無需進行任何進一步調查。
在第十三章中,我們看見了當CCRC認定無提交理由,但申請人卻提供更多資訊,或是新的申請案試圖要說服CCRC它的決定有誤時,會發生什麼事。在考慮其對「進一步提交」或「重新申請」案件的回應時,我們也反思了其在調查過程中與申請人的關係,並考慮了對調查和申請結果的司法審查日益增加的威脅,可能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CCRC重新審視其早先決定的意願。
最後一章(第十四章)呈現了我們實證研究的主要發現,並描述了對決策的主要文化上和結構上的影響。它也提到了CCRC在整體國家機構中的地位,以及它與警察、皇家檢察署、選任律師、媒體和冤錯案倡議者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沒有忘記這些組織運作時,所處的更宏觀的政治格局。但它主要焦點還是在於CCRC與法院之間重要的關係,反映了對CCRC在決定哪些案件符合「確實可能性準則」時,對法院過於「尊重」的批判。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