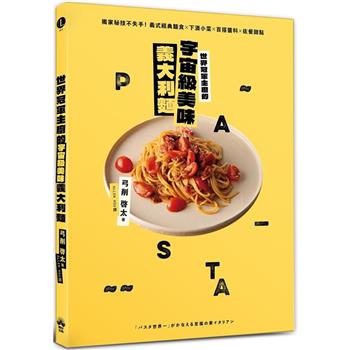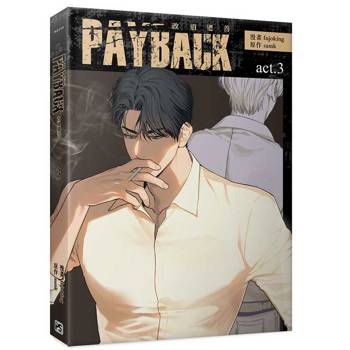譯者序
但願及早讀到……∕馬勵
二○○七年夏天,我有個機會回到二十年前工作過的紐約市,在一所私立中學裡擔任中文教師。這是我從事英語教學與文字工作多年後嚮往的生涯轉變,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就辭去台北的原職出國。卻沒想到就在半年間,年邁的雙親相繼離世。雖說他們均已年過九十,我們子女心中隱隱有數,但纏綿病榻一年多,情況時好時壞的父親,一旦感染,健康狀況迅速急轉直下,撒手人寰,還是令人有措手不及的感覺。而母親在睡夢中過世,雖說有福,卻也是突然。
去年五月跟橡樹林的編輯談到父母去世三年多,自己仍然極度哀傷,經常茫然失神,隨時激動莫名,淚水潸然而下。她介紹我閱讀這本由兩位哀傷治療師寫的專書,問我可有意願譯成中文。現在我想藉此向她表示誠摯的感謝,因為翻譯此書既讓我解開了對自己這三年「舉止怪異」的疑問,也學到了喪失摯愛後怎樣才能療傷止痛。不僅如此,從許多喪親者的誠懇分享中,我也得到了心靈的洗滌與安慰。本書雖然針對因摯愛遽逝而痛苦莫名的人所寫,但作者的觀察與建議,完全適用在那些至親久病而逝的人身上。不論往生是否在意料之中,天人永隔都是人生最大悲劇,除非親歷,無法了解其中痛苦。
就在一口氣讀完原文,正要開始翻譯時,傳來當年我在政大東亞所的老師關中、他的愛女在上海墜樓的消息,媒體鋪天蓋地地報導了好一陣子,老師與師母悲痛逾恆的畫面不斷出現在電視上,令人動容與不捨。死者已矣,生者如何自處?旁觀者又如何幫助關心的人走過哀慟,繼續生活下去?我在閱讀原文時,不斷產生但願早已讀過此書的感慨;看到老師與師母強忍哀慟應付媒體時,更是遺憾書中訊息尚未廣為人知,以至於實在太少人知道如何安慰與扶持哀慟中的人。
此書從兩位作者分享己身遭遇談起,首先表明之所以撰寫此書,實因自己在親歷生死大慟後遍尋無著療傷止痛的自助書刊。雖然西方文化對於死亡或許沒有東方文化那麼多忌諱,但在一個推崇成功與積極生活的社會中,死亡或悲傷這類負面事件依然令大多數人不自在。坊間固然充斥著規劃詳盡的勵志與自助書籍,卻鮮少實事求是、教人如何走出喪親哀慟的主題。兩人因此合作策劃此書,於一九九九年首次出版,問世後廣受好評。兩位作者也以心理輔導員和作家的身分繼續與讀者們溝通,並成立心靈工作坊,幫助許多人度過哀傷。二○○七年,她們增訂內容,推出新版,也分享了將近十年間自己的成長。中文版即根據原著二版譯成。
本書內容豐富,涵蓋了各種摯愛遽然離世的場景,小如毒蜂叮螫或車禍,大如海嘯或戰爭,也包含了自殺。悼亡的方式又因生者和死者的關係而有所不同。摯愛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子女;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戀人;還有可能是無法露面的第三者,或不為一般人接受的同性伴侶。作者們介紹了任何一種狀況下失去摯愛時可能出現的反應,也提出了自己如何面對,以及別人如何幫忙的方法。
由於此書的實用價值高,作者貼心地建議讀者不必重頭讀起,而是以閱讀參考書的方式,找當下對自己最有用的篇章先讀。以我的經驗,雖然因為翻譯的關係而從頭讀起,但書中提到第一年到第三年每年可能出現的症狀那一段,我就覺得自己當年應該先讀。尤其是書中描述喪親初期那惶惶不可終日的慘狀,更令我心有戚戚焉,得到莫大的安慰。
當年兩度匆匆返台奔喪,再迅速趕回數千里外的異鄉為人師表。在整理新居、應付迥異於台灣的家長與師生關係,以及緊湊的教學工作時程下,幾乎沒有為喪親而悲痛的時刻。當時只覺得自己精力大不如前,注意力好像也沒在台灣時好。雖然一方面認為這是自己中年轉行,自討苦吃;另一方面又恐怕自己是否有什麼毛病;隱隱地卻也懷疑或許與痛失雙親有關。讀了本書,印證了自己的懷疑,也確定了自己沒有毛病,正常得很。
作者指出,喪親第一年是非常特別的一年,幾乎可以用靈魂出竅來形容。這一年,雖然當事人未必自覺,但其實身心靈都因全力因應巨大的哀慟,以至於失去了往日的直覺。你可能經常恍神,也可能失去痛感。既然你連照料自己都有問題,那麼照顧幼兒與開車等需要專注的事就最好假手他人;也就是說,若要盡快身心復原,這一年的喪親者應該專心照顧自己的身體與內在,好好療傷。當事人的痛苦無可言喻,弔唁者簡單一句「節哀順變」沒有實質意義。朋友們能提供的最好的協助與安慰,就是了解當事人的力不從心,進而關心此人的日常作息,像是幫忙照顧孩子或購買日常用品,以及偶爾來幫忙做飯或帶他(她)出去吃一頓等等。當年的我不僅沒在療傷止痛上花時間,還要對付搬家、適應異域生活,以及改變工作場域的挑戰,難怪度過了可說一生中最慌亂的一年。
另外一個對我個人很有啟發性的論點是「情緒突襲」。以往只聽說有些人遭逢家變後迅速搬家,以免觸景傷情。但這本書說的,其實恰恰相反,因為哀慟不能逃避,所以一定要腳踏實地走過這段痛苦歷程,才能離開痛苦(但是痛苦不可能完全消失)。壓抑或推遲於事無補。
母親走後那年的一個夏日清晨,我忙裡偷閒想到去逛中央公園,盼望在暖陽中的綠樹繁花間,舒緩一週緊繃的神經。在觀光客熙來攘往的人行道上,淡金色的光線穿過樹葉撒在肩上,我頓時感到身心舒暢。但也幾乎同時,我發現自己竟然熱淚盈眶。擦著眼淚,腦中浮現的畫面是母親去世前一年,我在週末帶母親外出喝咖啡的畫面。好像在看電影,我看到自己推著輪椅,母親坐在上面,兩人有說有笑地經過松仁路樹蔭,轉到信義路上世貿對面的咖啡廳。我扶母親起來,收好輪椅,扶她進去找個位置坐下。一人一杯咖啡,再叫份她喜歡的加了泡沫奶油的鬆餅。接下來總是她微笑著聽我天南地北胡扯。然後母女再沐浴著陽光,慢慢回家去。紐約中央公園樹蔭下那聞起來一模一樣的暖日香氛,把我帶回了台北那些晴朗的週末早晨。然而天倫之樂惘然,換成我的串串淚珠。這樣超越空間的情緒突襲不是我所了解的觸景生情,卻在書中看到不少實例。正如作者所說,喪親之痛無可遁逃,如果你與逝者關係密切,那麼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到情緒突襲。作者指出,我們要正面迎接這種突襲,每一次經歷都讓你的心靈得到一次洗滌,使你在療傷止痛路程上繼續邁進。
《我還沒準備說再見》充滿了真人故事,作者筆端既有同理心,又有愛心,所有解釋與建議的目的,都是要幫助生者堅強走過哀慟。書中不乏打破習俗的說法。例如在安慰自殺者的親人時,她們提出了一個自殺者「完成」(而不是「採取」)自殺行動的概念。她們引用了自殺研究專家卡拉.范恩(Carla Fine)的話:「漸漸地,我了解到你有可能幫助一個怕死的人,卻未必幫得成一個懼怕生活的人。」表示自殺的原因往往是求死大於求生,在非自殺不足以解決痛苦的情形下,旁人不見得幫得了忙,因而不必以「要是我當時」的臆想折磨自己。
事實上,不只是自殺,任何原因致死,都可能讓悲痛莫名的生者發出「要是當時」「但願以前」等遺憾。這些後見之明不僅無濟於事,還徒生煩惱,不應該糾纏其中。正確而健康的做法是記住逝者的好,珍視曾經共同擁有的歲月,感激上天讓彼此進入對方的生命中,因而你要在美好的回憶中好好活下去。
前言
美國每年平均約有八百萬人失去一位至親。恐怖主義、戰爭、天災人禍,以及突發事件,都帶來了令人怵目驚心的死亡名單,而這種名單已愈來愈長。我們在媒體上看不到這些往生者的親朋好友。那些活下來的人在緊閉的門窗後、在我們的鄰里之間、在家裡和醫院的等候室裡傷心欲絕。他們或在加護病房外的走廊上來回踱步、或默默注視維生系統被摘除、或彷彿癱了似地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也有人焦躁地在旅館中等待遺體被尋獲。突如其來的電話把他們撕裂了,他們辛苦對付突然來到的死亡事件、突然的結束、突然的悲劇,其中沒有一人準備好了跟死者道別。
我們從呱呱墜地展開生命起,就相信生命的循環。嬰兒時期,我們相信父母會供應所需。孩童時期,我們相信周遭那些好人。我們受到的教導是,只要我們對別人好,別人就會對我們好。很快到了青春期,我們學到了事情有因有果。我們學到如果吃得營養,好好照顧身體,身體就會讓我們使用很長的時間。長大成人後,我們繼續相信這些循環。我們相信日出後必有日落,孩子一定會活得比我們久,我們有的是日子來珍惜所愛的人。
然而就在瞬間,一位摯愛遽逝的消息傳來,世界永遠變了,那個可以預期會不斷發生有秩序的世界結束了。我們被摔到荒原裡,手上能用的工具有限。我們沒有時間做心理準備,沒有時間收拾踏上旅途的必需品,更沒有時間處理未竟之業或道再見。生理上,我們或許可以說自己是由細胞、基因、皮膚和骨頭組成;但情緒上,我們卻是由思想、感覺、記憶,以及我們接觸過的許多人的片段組成。我們關愛的人的死亡創造了一個傷口,使我們多多少少因而改變。我們那根據正常生命循環的架構已永遠被打斷,只發現自己在昨日打下的地基上徘徊飄盪。
隨著悲痛而來的是,有時候你看著鏡子,竟然不再認識那注視著自己的眼睛。雖然太陽照舊升起與落下,但每件事看起來就是有那麼一點不同、一點扭曲。悲痛在我們四周投下了廣大的陰影。
我們兩人合作撰寫第一版《我還沒準備說再見》時,一般人用來描述哀慟的字彙很少。通常別人就是鼓勵我們「往前看,繼續走下去」、「恢復正常」,或者要我們抑制悲痛。一年以後,美國遭遇了始料未及的攻擊,數以千計的人命因而斷送。政治領袖昭告全國,鼓勵美國人設法「正常生活」。
但是,在遽逝出現以後,「正常」已經消失,我們需要表達悲情與重建生活。那些政治領袖那麼說固然是好意,但社會上大多數人並不了解什麼是突然失親,也不懂哀慟是怎麼回事。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以來,許多事情改變了,卻也有許多事依然故我。儘管我們現在比較懂、也比較會彼此扶持,但當我們或我們親近的人突然失去親人時,我們了解世上所有的教導與準備都不夠。除非我們身歷其境,否則無法了解「哀慟」的真實狀況。
根據寇爾(Michael C. Kearl)教授在《死亡社會學:死亡對於個人的影響》(Sociology of Death: Death’s Personal Impacts)導讀中所言,因喪親而來的哀慟,是人類最深沉、最具危險性的情緒之一。每年美國約有八百萬人喪失一位至親,生活模式因而中斷長達三年。國家科學院統計,大約八十萬喪失配偶的人之中,多達十六萬人經歷身心受創的哀慟。截至二○○七年四月,聯合國部隊已有四千名官兵喪生,戰爭慘況與傷亡真相因而進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每年美國有超過三萬兩千人自殺,超過十一萬條人命死於意外事故。死亡的因素愈來愈多。作為一種文化,我們辛苦地協助周遭那些悲痛的人。
當我們因生活基石崩潰而處於廢墟中時,社會總是期待我們迅速乾脆地重新站起來,恢復正常生活。可是,沒有任何人教我們怎麼做。我們看不到痛苦以外的東西,社會給我們療傷止痛的時間太少。舉例而言,有大約百分之八十五的妻子活得比丈夫久。在《時間戰爭》(Time Wars)一書中,傑洛米.瑞夫金(Jeremy Rifkin)提到,一九二七年時,愛蜜麗.普司特(Emily Post)提出,寡婦正式的哀慟期為三年。
二十三年後,瑞夫金發現這段時間已縮短至六個月。一九七二年,愛米.范德比(Amy Vanderbilt)建議悼亡者,「在葬禮後大約一週,設法找出一條尋常的社交路徑」。我們就這樣定下了一個人傷痛的期限,而且視為當然。雖然百分之九十的美國公司都讓員工請喪假,但大多數政策都只給失去家人者三天哀慟期限。
一個人無法向另一個不曾經歷過喪親之痛的人,解釋死亡悲劇的影響。除非你自己面對挑戰,否則便無法了解這種挑戰。你無法跟別人解釋失去至愛後的那種困惑、失焦與無助。
對於那些親人突然死亡的家人,不妨問問他們覺得自己能不能面對失去孩子、配偶、手足或好友的感覺。他們會告訴你沒辦法。許多人會說,若碰到這種狀況,他們一定會發瘋。大多數遽失摯愛者,從不認為自己能夠踏上並走過哀慟這段路。但就是同樣的這些人確實遭遇變故,之後仍然爬出了深淵,重拾信心,重建生命。
這本書包括我們兩人的故事,也包括過去十年我們認識的一些悼亡者。故事中的人以勇氣重建生命,分享感受。我們經由這些故事認識自己,走出孤獨,進入一個大家一起走過復健迷宮的社群。
在這本新版中,我們增加了新的故事與智慧,以及一些但願當初自己受苦時已經有的資訊。我們還加入了一些比你們早抵達人生黑暗迷宮者的現身說法。書中侃侃而談的人曾經痛苦捶牆,顛簸前行,摔得遍體鱗傷,最後在一個新天地中站起來。這本書固然與死亡有關,其實也是在談一種開始。我們在失去某個心愛的人以後,開始過另一種生活。我們像嬰兒一樣學習如何邁出第一步、如何走路和說話、如何做不一樣的夢、如何重新釋出信任,以及如何一方面緬懷過去、一方面創造新生活。我們永遠在改變。我們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待人生,也比任何人更知道每分鐘的價值,知道及時說該說的話有多麼重要。我們了解真正重要的事情。
我們那時還沒準備好說再見,在我們之前經歷喪親之痛的人,以及今後許多會讀到這本書的人,也都還沒準備好說再見。本書的目的是要成為一個身心健全的試金石,以便走過與遽逝相關的情緒高原。這座高原上高牆處處,濃霧將人密密裹住。我們與你分享哲學家卡爾.容格(Carl Jung)的話:「你面前若有一堵牆,就請像樹一樣把根埋下,直到清明智慧由最深沉之處出現,眼光遂能跨過高牆,繼續成長。」
布蕾克.諾爾&帕蜜拉.D.布萊爾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