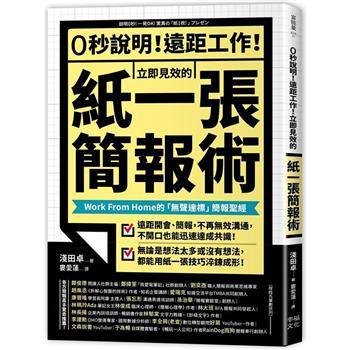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Peggy Shinner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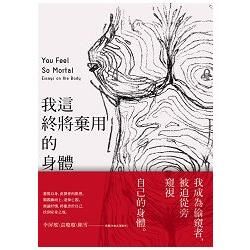 |
$ 140 ~ 350 | 我這終將棄用的身體:解剖自我、探索性別、追尋家族記憶的書寫
作者:(Peggy Shinner) / 譯者:柯清心 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16-03-3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28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我成為偷窺者,
被迫從旁窺視自己的身體。
佩姬.辛納,猶太人、女性、女兒、同志、兼職防身術教練——這些身份,對她有何意義?
面對自己的身體,她像個局外人,觀看自己的扁平足、蒜頭鼻與駝背,回溯長久以來的社會偏見如何建立可憐兮兮的猶太人形象,並犀利補上一刀,此種建構是「拙劣的模仿鬧劇」。她還把每次扭捏買內衣時,與試衣員來回直探雙方底線的窘況,寫成自嘲的喜劇,一路回憶發育期的彆扭氣惱,還順便上了一課內衣歷史。雖然她一向乖乖牌、連埋頭看書撞上路燈都會先說聲「對不起」,卻也想耍壞想離經叛道,但連偷竊都偷得不上道,只好順便回顧偷竊與慾望的關聯。
長出勇氣敘說自己,下一刻便是面對家人。她進一步以自己(承繼雙親而來)的身體為圓心,書寫父母。她在母親過世後整理遺留的書信時,才重新發現母親的另一面,也想起母親對她出櫃的無法諒解。父親過世時,她初始想驗屍釐清死因,但收到解剖結果後才發現,中年失怙的她事實上並不是想瞭解「死因」,而是父親為什麼就這樣死了——這是每個子女最深刻哀慟、卻注定沒有解答的疑問。
佩姬.辛納談論隱私一派輕鬆,說起逸聞趣事則信手拈來,並且優雅而犀利地來回切換,從各種身體討論生死、性別、認同,親情與愛情,並於其中展現她誤入困窘的自嘲,挑戰偏見的機智,以及勇於探索極限的勇氣。
審視自身,追憶家族,反覆詰問之間,終能忠於自己的身體,無論好壞,願來日能與它好好告別,面對終將棄用的身體,說聲:「好好照顧自己。」
作者簡介 |
佩姬.辛納(Peggy Shinner)
道地芝加哥人,在西北大學教授創意寫作。
譯者簡介 |
柯清心
台中人,美國堪薩斯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現任專職翻譯。著有童書《小蠟燭找光》;譯有《當我們撞上冰山——罹癌家屬的陪病手記》、《白虎之咒》系列、《擁有未來記憶的女孩》、《吸血鬼獵人林肯》、《一刀未剪狂想曲》等數十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