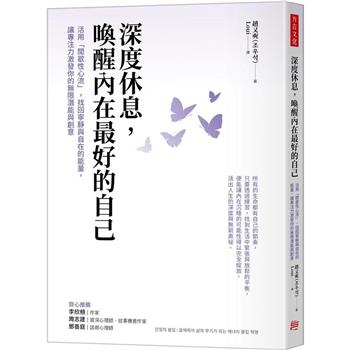作者序
想像你是陪審團的一員,你現在面臨的課題是,決定目前所擁有的證據是否足以確定瓊斯謀殺了他的妻子。你可能會認為有些證據非常重要,因為大部分這類型的犯罪中,這些證據會讓我們認定他殺了被害者。但是,同時你感到有點擔心,因為你只是根據這類犯罪的統計結果,得到瓊斯殺了被害人的結論。另一方面,你認為非常重要的證據同樣是統計的。假設瑪莉是檢方傳訊前來做證的目擊者,她聲稱看見瓊斯開著他的白色Toyota 在犯罪現場附近徘徊。但是近來的研究顯示,即使目擊者認為她非常忠實地描述當時的情況(相對於其他,例如現場的證據),這些證詞通常不太可靠。不管怎麼說,目擊者的證詞的確不是百分之百可靠,所以如果我們真的相信目擊者所說的,就是承認根據或然率計算的統計事實,這類型犯罪的目擊者所說的是對的。除此之外,在法庭上出現的證據,包括犯罪現場附近發現的血液的血型,以及DNA等,也都證明瓊斯似乎真的殺害了他的妻子,當然這個說法也是根據統計而來。所以,如果在這個情況下想要得到任何結論,最好承認我們透過統計事實得到結論的方式是合理的。想像一下,如果你經由某人的證詞得到一些結論,那麼你是否需要一些獨立於這些證詞之外的證成,才能相信這些證詞是可靠的?或者當你認為這些證詞是可靠的,並且根據這些證詞形成一些看起來像是為真的信念,是否就足夠了呢?
稍微調整一下上述的例子,想像你自己就是這個故事中的目擊者。你看到瓊斯坐在他的車上出現在犯罪現場附近。接著,辯方律師在開始質問之前提醒你,根據研究報告顯示,其實目擊者的證詞並不如他自己想像的那麼可靠。說完這些研究報告的證據之後,辯方律師再度問你是否仍然確定是瓊斯在開車?如果你是理性的,你應該會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沒錯?如果這些研究報告的結論會削弱你相信自己證詞的證成,那麼由於你沒有除了證詞以外的理由相信﹁你的感官證據﹂,這些證據會被削弱,甚至完全失效。在這個情況下,你仍會認定擁有任何證據嗎?一般來說,對於任何你得到結論的方式而言,我們應該設想只有在你擁有好的理由認定通過這個方式得到的結論是可靠的時候,這個結論才是理性的嗎?然而,如果我們對結論是否理性的要求這麼多,難道不會陷入嚴重的麻煩嗎?如果我們接受這個預設,即使某個方法能夠達到真理而且可靠,你也不能用這個方法證成你的信念「在沒有乞求爭點(begging the question)的情況下」,這個要求是否會使我們所有形成信念的方法無可避免地終歸失敗?畢竟,我們不可能不使用這些方法,而對我們所有形成信念的方式進行評價。
在這本書中,我們試圖更仔細地檢視上述提及的議題。知識論確實在哲學中占據著基礎的位置。如果一個人對哲學或者對真理有興趣,卻對知識論沒有任何興趣,是不太可能的。任何哲學上的主張,乃至任何脈絡中產生的爭論及有趣的主張,無可避免地都會產生知識論的問題。當你對一個在智性上充滿好奇的人提出具有爭議性的問題時,他會希望知道你如何確定你的主張為真,也希望知道你用來支持該主張的證據是什麼。評價關於知識和證據的主張,至少就理想的方式來看,有個還不錯的說法是,某人要知道或理性地相信斷言之前,應該預設某人要先能夠掌握什麼是知識和證據。
接下來,我會盡可能減少預設讀者需要具備的哲學知識,我希望這本書能夠被廣為接受,即使是未經過哲學訓練的人也能了解。同時,我也不希望因此犧牲這本書該有的清晰性、明確性以及哲學思辯性。總之,我希望這本書不只對新手,甚至是經驗豐富的哲學家來說,都會顯得生趣盎然。基於對可接受性的要求,會迫使我做出困難的決定,特別是必須省略一些重要且有趣的論證和觀點的討論。某些特定觀點的擁護者,偶爾會在自己的立場受到挑戰時顯得有點兒退縮。我會試著集中討論贊成或反對特定類型觀點的論證,而不依賴對這些觀點微妙的、有趣的或有用的區分。我也會試圖公平地看待對於知識論兩個進路之間的基本差異。現今在知識論中最有趣的爭議就是內在論者與外在論者的爭辯。然而我不想隱藏我自己的哲學觀點,我會非常努力地公平對待我所不贊同的觀點。對我來說,畢竟使讀者理解內在論者和外在論者如何辯護其觀點的理由這件事,遠比讓讀者最後贊同我的觀點來得重要多了。
我在本書最後,會針對每一章簡短列出建議閱讀的書或文章,有些是廣為人知且深具影響力的著作,有一些則不是甚為出名的著作,但是我認為這些書的某些篇章或文章寫得很清楚、容易閱讀,而且會有幫助。
我要謝謝麥可. 穆爾尼克斯(Mike Mulnix)幫忙整理這本書的原始草稿。同時也對杜貝拉. 海科斯(Deborah Heikes︶致意,謝謝她許多評論和批評。我非常感恩於麥可. 胡摩(Mike Huemer)以及提姆. 麥古魯(Tim McGrew)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對這本書的草稿加以擴充、註解,而使本書更具可看性。由於他們盡心而努力的協助,我希望這本書是成功的。這本書在他們無價的忠告下已經變得好多了。我也謝謝愛荷華大學提供的休假,這段期間對於這本書的寫作非常重要。
譯者序
理查.富莫頓(Richard Fumerton)教授是當代知識論的重量級學者,目前任教於美國愛荷華大學,曾於二○○二年造訪臺灣,也舉辦了數場的學術演講活動。當時富莫頓教授對知識論領域的各項議題,提出許多具有啟發性的觀點,在國內激起的熱烈討論和影響,許多學者至今仍津津樂道。這本書的出現,源自Blackwell 出版社構想出版一套系列叢書,並將該叢書命名為「哲學的第一本書」(The first book in philosophy),目標就是出版哲學各領域的入門書籍,這本「知識論」(Epistemology)是叢書中最快出版的作品,富莫頓教授對於知識論領域議題的熟稔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最令我深感困惑的問題,就是如何能夠一面準確地掌握並傳達文章內容,另一方面又能夠盡可能逐字逐句翻譯?面對這些困難,在翻譯過程中曾有一度不知如何取捨的困擾。然而,在請教過國內著名的知識論學者林正弘教授之後,我了解到翻譯這本書的目的,在於提供國內學子們了解知識論的議題與爭論要旨,故能夠讓讀者準確地掌握這些要點,才是翻譯這本書最重要的考量。因此,如果讀者對照原書閱讀,會發現我對某些段落有所補充或稍微改寫,目的在於盡量能夠增加讀者在閱讀上的樂趣。所以,我要對林教授提供的協助致上最大的謝意。除此之外,我要感謝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九十七學年度的大二同學們,你們在課堂上對於各種觀點的反應,提醒了我在翻譯時需要注意的要點。另外,也要特別感謝我的助理鄭依書同學,因為她不辭辛勞地擔任校對及完稿的工作。由於她的協助,使得翻譯這本書的工作進行得更加順利。當然,還要感謝五南出版社提供的機會,讓我藉由翻譯的過程,不斷地反思如何說明及討論知識論議題,這些反思對我的研究及教學都有極大的幫助。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