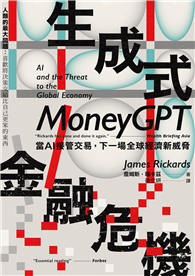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Sofia Stril-Reve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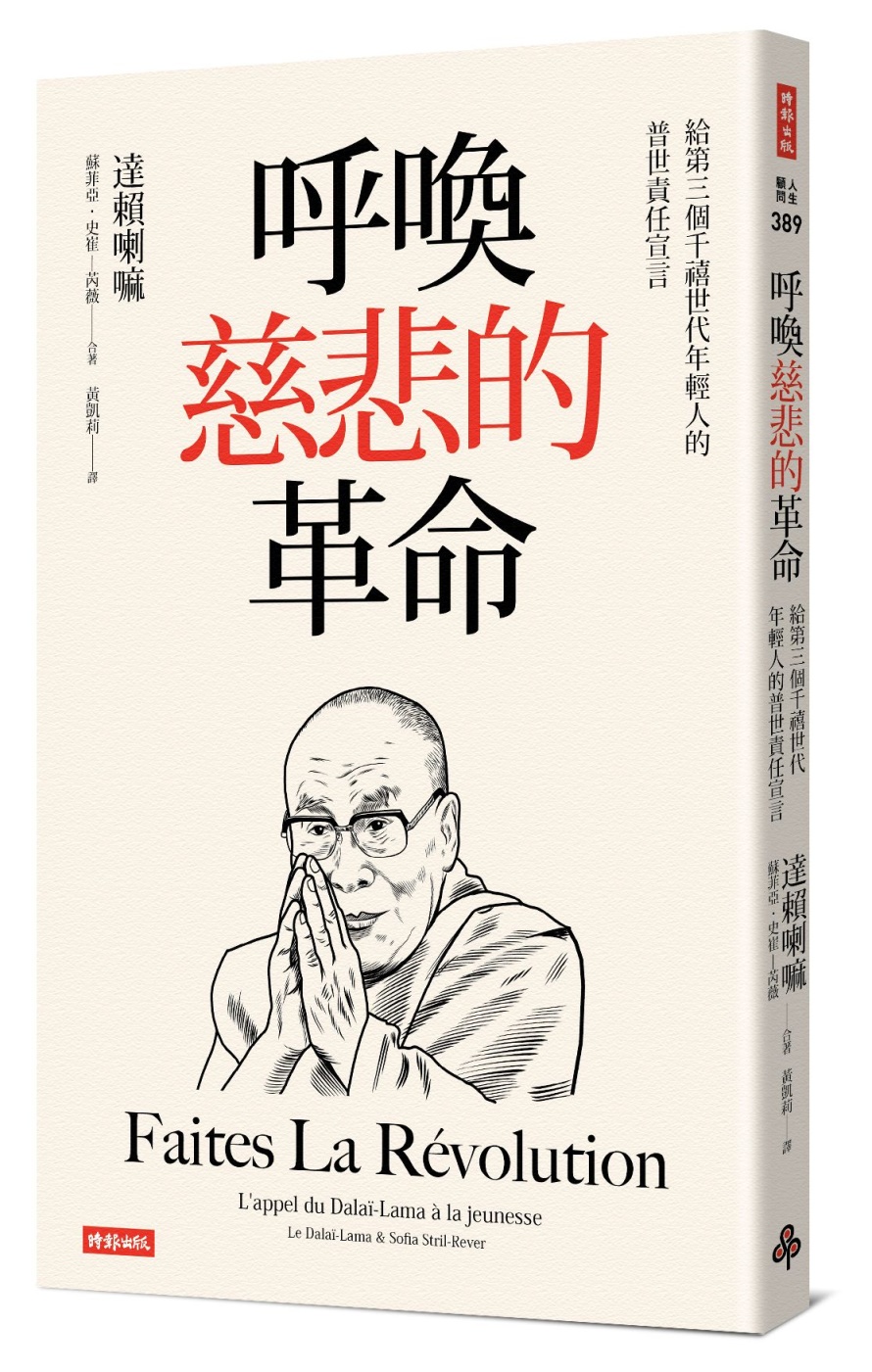 |
$ 130 ~ 252 | 呼喚慈悲的革命:給第三個千禧世代年輕人的普世責任宣言
作者:原文 Le Dalaï-Lama、Sofia Stril-Reve / 譯者:黃凱莉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0-03-24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60頁 / 13.5 x 21 x 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1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縱觀歷史,革命大多出於仇恨、憤怒和沮喪,而產生的利益衝突,直到無法控制,便觸發殘酷的浩劫。然而,即使是法國大革命、中國文化大革命都導致極端恐怖,但並未因此改變人類的心靈。
人類心靈追求的目標是擺脫無知,這是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的分裂,也是我們之所以痛苦的根源。平等是另一個精神追求,所有的有情眾生,不論是人類或他物,都具有證成佛果的潛力。
本書作者達賴喇嘛認為,二十世紀後半葉發生的革命與早期革命的動機不同,後期革命抱持的是和平主義,而年輕人是和平的革命者,他們挺身面對時代的挑戰,展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的革命。
這些挑戰包括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宗教衝突、極權主義興起、恐怖攻擊、氣候暖化、過度消耗自然資源等等,都是第三個千禧世代的年輕人必須挑起的普世責任。年輕人必須培養利他精神,承擔普世責任,因為人類的未來不再能依賴政治家、大企業或聯合國。人類的未來,是掌握在意識到自己是世界七十億人口一部分的年輕人手中。
不論是經濟、科技、教育、良知和心靈的革命,所有這些革命都渴望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但對達賴喇嘛而言,慈悲革命是心靈,是基石,是所有靈感的原始來源。
作者簡介
達賴喇嘛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尊者,是西藏精神領袖,自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以來,一直流亡與居住在北印度達蘭薩拉。尊者在1989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詳見達賴喇嘛官方網站:www.dalailama.com
蘇菲亞.史崔─芮薇(Sofia Stril-Rever)
與達賴喇嘛合作撰寫四本書,包括《達賴喇嘛的心靈之旅》(My Spiritual Autobiography),已翻譯二十種語言。她與巴黎律師協會共同發起「法律與意識」研究小組,根據普世責任概念來應對環境的挑戰,這是由達賴喇嘛倡導的二十一世紀人類生存關鍵的概念,詳見官方網站:www.lawandconsciousness.org
譯者簡介
黃凱莉
艋舺囝仔、石牌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志工、國際西藏郵報中文編譯與駐臺代表、妙法因陀羅網站及粉專版主、前書店流通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