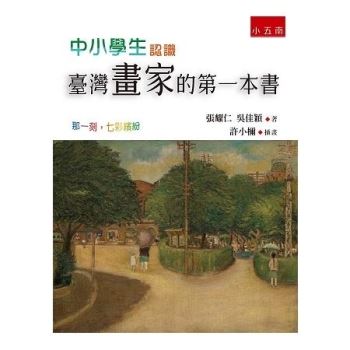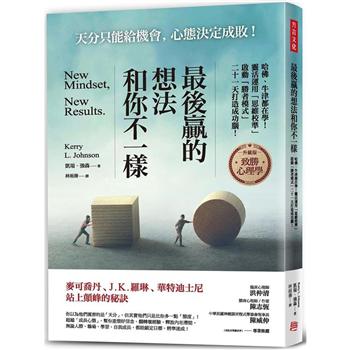序
二○一一年的暑假,超過五十萬的人到台北花博留下的「增豔館」,參觀「會『動』的清明上河圖」,這一幅《清明上河圖》選的是北宋畫家張擇端的作品,畫軸從右邊開始欣賞,郊野間小徑逐漸開闊,從容的步調逐漸快速,人物增多,樹逐漸減少,因為畫面左端就是城市生活的寫照:販夫走卒、演員、乞丐、化緣的、算命的、打鐵的、戲逐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賣酒的、賣榖物的、賣廚具、弓箭、燈籠、樂器、金飾、布疋的,各式各樣的交易買賣在進行。整幅畫軸的焦點集中在拱起的虹橋,虹橋上,小販聚集,人群往來;虹橋下,船隻忙碌,流水悠悠,由此延伸出去各式住宅、官邸、寺廟、旅店、農舍,由此延伸出去各種交通工具,馬、驢拉的車、駱駝形成的隊伍,乘轎子的、步行的,橋下還有漁船、遊艇,感覺上都向畫面集中,這就是城市,熱鬧、輻輳、繁華,行旅匆匆,商業行為頻繁而密集。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據統計,圖中出現的人物共有八百一十四人,未出現的人物那就更多了,到底多少人聚居的地方才叫城市,各國、各地區都沒有一定的標準。丹麥最低,二百五十人以上居民集中的所在就被視為城市,加拿大以一千人為下限,美國二千人,印度、馬來西亞則需抵達五千或一萬以上。這樣看來,所謂城市,類近於我們心目中的市鎮、街市,是生活概念下、商業概念裡,人口聚集、商業頻仍的地方,不是行政區域的「城」。台北建城竣工於一八八二年(清光緒八年)三月,至今不到一百三十年,彰化建城稍早,也只有二百八十八年,在這之前應該就有城市的雛形,那時的先民,如何在城市中過日子?建城之後又有什麼樣的更動?北宋汴京城有張本、仇本、清宮本等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圖》可據以考證,台灣的城市經驗又如何呢?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庶民生活圖本,是否有溫馨的生活小品可以留存?
《清明上河圖》描繪由鄉村進入城市的庶民生活,正呼應著人類的生活途徑即是由鄉入城,從村落到市鎮,台灣近三、四十年的發展,或者說近三、四十年成長的台灣青年人,也見證著城鄉疊合的新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總有一部分的時間在城,一部分的時間在鄉;不論喜歡或不喜歡,在城的時間逐漸多過在鄉的日子。這樣的生存經驗,我們的父祖或兄長,我們的藝文前輩留下了什麼樣的溫馨圖記?
今年三月到五月,我擔任香港大學駐校作家的工作,長達兩個月生活在無數座三、四十層高樓的窄街隘巷間,隨手可觸的高樓大廈近距離俯視著我,兩個月後回到台灣,看見的是具有一定建蔽率的高樓,沒有任何威脅,以那樣的香港經驗來看,台灣沒有城市,即使連台北信義區都不算是高樓密集的地方。多年前我到過荷蘭,連綿幾十公里都是麥田,一望無際,見不到任何農舍,心中疑惑:有農田卻不見農人,農人住哪裡?他們卻說這才是鄉村景象,以這樣的歐洲經驗來看,台灣沒有鄉村。到底台灣有沒有鄉村,有沒有城市?如此交叉比對,其實正說明了台灣自有自己的城鄉經驗,因為颱風和地震常常造訪的台灣,不會有蜂窩式的高樓群,受到儒家與道家的美學薰陶,台灣知道如何在天人之際取得和諧。台灣的城鄉經驗,另有一種溫馨的記憶。
《Taiwan.城市流轉》擔負起這樣的角色,記錄了這三、四十年台灣的城鄉轉換、生活記憶,首先由生活重心、人文觀察、文字書寫,以都市(特別是台北市)為主軸的隱地作為第一位嚮導,也邀請了長期來往於美國與台北之間,看多了國際級城市如紐約的簡宛女士,回頭看台北交通擁擠、人口眾多、空間侷促之外,還有什麼迷人之處?中生代作家鍾文音,來自雲林縣二崙鄉村,卻多書寫旅行世界各地的見聞,由家族書寫轉換為旅行書寫,她看見了什麼樣的城市特質?來自彰化濱海的和美的王盛弘,旅遊是他獲取新感動的重要媒介,出版《關鍵字:台北》,為台北樹立文學地標,出版《十三座城市》,分述上海、蘇州、香港、京都、東京、首爾、巴里島、愛丁堡、約克、倫敦、巴黎、巴塞隆納,而以台北收束,城市對他而言又有什麼樣的感動?
〈想像花蓮〉是陳黎所寫的一篇歷史與現實疊合的家鄉記憶,花蓮的文學地圖、文化觀光指南,讓讀者見識到花蓮的人文歷史、文化厚度;〈故鄉素描〉是三十年前林雙不所寫的雲林東勢,一個簡樸的聚落,三十年後的今天有了什麼樣的變貌可以對照?將來會成為繁華的都城嗎?再看看,詩人對城市高雄的感動又會如何?在地的李敏勇,走過世界各重要城市而後定居西子灣的余光中,來自馬來西亞的鍾順文,他們又會寫出高雄人哪些不變的生活場域、永恆的記憶?女性作家如陳幸蕙,會以什麼樣的驚豔心情寫城市邊緣的美?有如新鮮人的方秋停,翻尋東海大學的過去、生活、情義記憶,又會有什麼樣的晶瑩貝殼,或砂粒似的惆悵與喜悅?
城市之所以迷人,這些作家擔任著導覽員的角色,他們掌握住城市的脈動了嗎?呼應了我們的聲息,看到了我們的焦慮與喜樂嗎?讓我們隨著他們的筆,進入城市,感應他們的呼吸,感應時代的脈搏、城市的脈搏。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