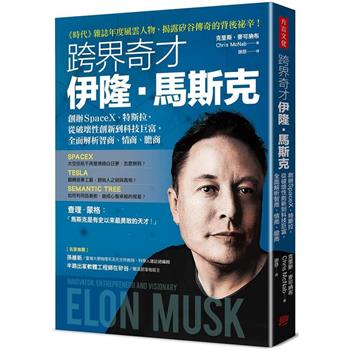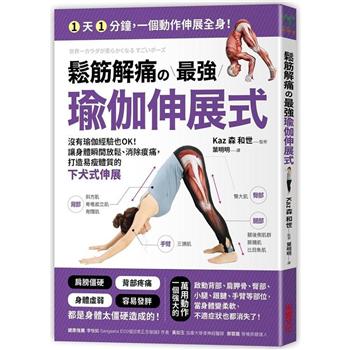名人推薦:
在《娃娃屋謀殺案》中,湯瑪斯.馬里奧這位刑事偵查學領域內的權威,發明了一種巧妙的方法,讓讀者瞭解犯罪現場調查是怎樣真正展開的。我向專業人員和偵探迷推薦這本書。這些故事和照片不只是具備解說的意義,它們還非常精緻寫實。
——吉拉德•林奇博士,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院長
做爲一名法庭作家,這些年我已經看過很多驚悚曲折的素材,但都沒有像湯瑪斯.馬里奧所製作的精緻微縮犯罪現場那樣令人著迷。如果我們不能全程參與湯瑪斯教授著名的實驗室演示,至少我們能好好鑽研一下這本《娃娃屋謀殺案》。
——傑西卡•斯奈德•紮克斯(Jessica Snyder Sachs),
《屍體:自然科學、法庭科學和死亡時間的確定》一書的作者
![娃娃屋謀殺案[2011年6月/2版/RL01]](https://img.findprice.com.tw/book/9789866098123.jpg)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