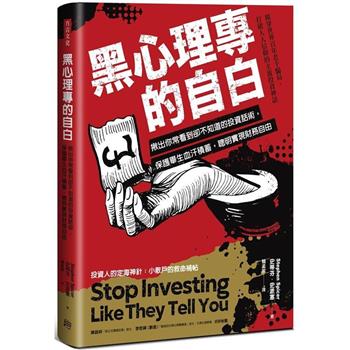〈漫談空間概念種種──世界、星球、網路〉(節錄)
洪丁福/文化大學政治系專任副教授
星球空間革命
「世界不在空間內,而是空間位於世界內!」
世界史與人的空間意識
如果說哲學的、邏輯的與自然科學的空間概念是抽象的,那麼較易為人們了解的具象空間要算是常識的空間,即吾人日常所經驗到的,這主要是基於實際的理由,像是個人心理空間、公共的地理空間,前者涉及個體的生活與生存課題,後者則是有關我們所生存的地球與周遭環境的科學領域,諸如地球物理、製圖學(cartography)、地形學(topography)、地勢學(風土研究)(topology)等,除此,地理空間與人類歷史發展,文化類型亦有密切關係。一部世界史其實就是人類爭奪地理上的陸地空間、海洋空間與天空、外太空的過程;而從文化面來看,例如西方歐美主張個人的隱私空間,而東方文明(儒家、伊斯蘭)則強調群體的空間,但澳洲原住民卻認為土地並不屬於人,而是人隸屬於土地空間,至於國家領土主權的普遍性實乃是政治空間意識的產物,若從此一角度來看待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治糾葛,其實也可將此理解為空間認知上的分歧,因為雙方皆認定憲法上的國家人格(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領土空間義涵,是生存的根基,但如何界定其適當的界限卻無共識,也是兩岸關係目前看來仍是「無解」的原因之一。
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在其「陸地與海洋」一書中指出,任何人類的大地律法規範了國土疆域與司法管轄的範圍,一旦跨越了一國疆土以外,涉及地表共同空間秩序問題,其核心必指向空間的攫取、分配與擴張,他就借用希臘字Nemein/Nomos對比德文字Nehmen/Nahme,說明在人類歷史過程中不變的法則順序就是土地空間、海洋空間與天空空間的爭奪與演進。直到十五與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之前,地球上主要文明地區的國家首先鬥爭的空間對象是陸地,希臘、羅馬、中國、印度、埃及與波斯等城邦或帝國皆然,中世紀的歐洲則是以陸戰為主,十六世紀之後歐洲各國紛紛走向海洋,葡、西、荷、法、英都是要角,其中英國則在十八與十九世紀期間出類拔萃的征服了世界大洋,跨出陸地空間走向汪洋大海,成了「日不落」的世界帝國,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才被美國取代。美國崛起於十九世紀末,地緣上屬濱臨兩大洋的「大島」,一如不列顛列島,天然上屬於海權國家,憑藉著科技優勢發展成名符其實的「全球」霸權,這一切乃由於電子、運輸、航空、通訊等技術的革新,使美國得以同時支配陸地、海上與空中的三維空間,如今延伸至外太空與深海甚至無垠的遙遠星球。但更驚人的科技突破則是今天世人正在經歷的資訊科技(IT)產業、電子通訊、數位、生物化學等領域的大躍進,對人類生存空間與生活方式產生了古人無法想像的變遷。
歷史學者長久以來的疑惑是,為何是西方國家而不是中國對世界主要地區進行殖民與帝國主義的統治,因為明朝的鄭和早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1492)七十餘年之前就已達非洲,為何中國人到達了非洲未留下拓殖,答案似乎就如一般學者所認為的,應歸咎於中國朝廷官員的鎖國心態。從民族與文明所處的地理位置來看,大陸型國家相對於海洋型國家可能較傾向有限的空間意識,也往往被視為較「落後」或是保守,而島嶼國家由於生存依靠海洋,如同一艘船或一條魚必須悠悠於大洋,較不像大型的陸地國家易於固定於土地上,島嶼、半島與海洋國家的空間意識則傾向無涯的大洋,前者的範例是中國、俄羅斯與印度,後者則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與英國。不過,為何同為島嶼國家,日本卻未能辦到,獨獨英國成為「海洋之子」(children of the sea)呢?
事實上,早在英國崛起於海上,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就已征服了美洲大陸,相對晚起步的英國以海盜船聞名,從十六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初,也就是新教國家對抗天主教的西班牙,海盜、海盜船實際是與本國政府當局聯手展開海上霸權的爭奪戰,期間英國在一五八八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Armada),之後取得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特權,一六五五年克倫威爾(Cromwell)佔領雅買加;英國已奠定其世界海洋的政治基位。但讓英國徹底從一島國成為「日不落國」,是無法僅僅從過去數場戰役或地理位置予以解釋的,因為英國的獨特性是無法類比的,或許借用西方神話中的海怪利維坦(Leviathan)與陸地巨獸(Behemoth)的轉變得以隱喻英國的獨特性,它連結著英國人的政治哲學傳統,霍布斯製造的利維坦(或巨靈)原是巨怪上了陸地後,以武力與契約創造了秩序與安全,霍布斯的國家學說不僅奠定近代主權、法治與國際關係基礎。隨著往後科技與工業革命的突破,焦煤爐(1735)、鑄鋼(1740)、蒸汽機(1768)、紡織機(1770)、梭織機(1786)等系列的發明,英國自十八世紀以降已遠遠超越其他歐洲海上強權。利維坦這隻海怪變成了機器巨獸,英倫小島在地理上、心理上已不屬於歐陸,尤其在十九世紀初擊敗拿破崙後,至中葉的克里米戰爭、中英鴉片戰爭與美國南北戰爭,英國的海上霸業已無出其右者,一場星球空間革命真正的從陸地走向海洋,而下一場星球空間界定與意識變遷,則要到二十世紀科技對空中的征服,人類全面掌握了了立體三維度的空間概念後,舊的陸地與海洋空間攫取、瓜分已到盡頭,也讓位給了新的空間元素-虛擬網路空間(Cyberspace),科技與人類的權力關係在今天似乎已進入另一個維度。
省思:人與空間的權力─從前廳到冷氣房
人乃狼人(Homo homini lupus)
人乃神人(Homo homini Deus)
人乃凡人(Homo homini homo) 拉丁諺語
這幾年在台灣社會家戶喻曉的政治事件之一就是前總統陳水扁的入獄,估不論前因後果,有一事實是路人皆知的:總統夫人的角色。此一關係揭露了權力本質不變的邏輯,一種內在的辯證法則,也就是名義上的在位者與親近者之間的關係,到底誰才是權力的真正主人,誰又是此一權力的奴僕,或者說,誰直接行使權力,誰間接左右權力。權力的投射似乎必然是從某一空間開始,因為抽象的權力必定是由某一人(某一群人)在某一時空中所行使,例如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克里姆林宮、唐寧街七號或是台灣總統府內某一樓層某一房間,也可能是廚房、臥室、或車廂內。遽聞羅斯福總統、菲特列大帝性喜與僕人談心,其他的大權在握者可能好與司機或情婦談國事,在此,權力的人性面是與心理與物理空間因素密不可分。當權力愈集中於一人或少數人,通往權力的管道就愈密集與窄化,權力者所落腳的空間(Raum; room)所相連的前廳(Vorraum; lobby)、走道(corridor)必充斥各種耳目、窺視、聽聞就會在權力核心外圍聚集形成,世界史所提供的文獻揭露了多采多姿的前廳、後門、暗室、廂房、候客室(antichambre)的軼事,直接或間接與權力者有關人士,部長、大使、將軍、神父、御醫、秘書、僕人或情婦總是處心積慮、想方設法接近權力核心,這一來不論是智者、愚夫或騙子都有機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權力者,誰得以進駐、佔領前廳後院,誰就可以暗地的發揮無名分的左右力,詭異的是,當權力愈集中,權力週遭的勢力也就愈凝聚,權力空間(Macht-Raum)也就提供了前廊或通道以便分享權力,尤其是當廂房內的掌權者愈專權或是病弱,房內覬覦者就愈渴望瓜分權力,某種權勢者與無權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往往會上演角色互換的人間戲碼,由於前廳或後門切斷了專權者與外界的聯繫,此時,身邊的非權力載體-無名小卒-也就順理成章地成支配了權力者,昏君與小人、皇帝與宦官、宰相與情婦、總統與總統夫人,就成了一對一的諮詢與談心的對象了,從古至今或明或暗的案例可說不勝枚舉。
人─權力的載體─,不論是賢人、暴君、帝相或總統,實難逃權力之間內在邏輯法則的支配,直接或間接的權力施受總是無所不在,人際間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就是一種自我標榜與自我疏離的辯證過程,然而,若說人與人之間的權力心理是體視於社會空間內,則人類對世界的支配欲就是透過科學理性與科技投射於大自然,並以此形塑了整個人與星球空間的權力辯證關係,人創造科技、駕馭科技,但到底是科技役於人類?還是人役於科技?近數十年來,世人讚頌「新」科技、「高」科技,似乎已改寫了傳統的政治意義,所謂民主、極權或獨裁的內涵在科技與權力控制術結合下已分不清誰是主誰是奴了。
在記憶猶存的年代,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其著名小說《一九八四》描繪了極權世界的駭人景象,一位「大哥一直在監視著你!」(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執行著全面性監控,廢除所有個人隱私、思想改造、洗腦,祕密警察(格別烏KGB,盡世太保Gestapo,史塔西Stasi)或警總令人聞風喪膽,中國的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也成為歷史了,甚至也改頭換面加入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陣營。雖說如此,新的微電子科技、數位革命與所謂全球化卻大張旗鼓聯手,似乎正在進行一場靜悄悄與無暴力的空間革命,一場無須獨裁者也可以辦到的全面性對市民的監控,且正是在自由民主的空間內發生,更令人驚訝的是,人們雖偶爾抱怨,卻不加反抗,「自願」接受監控,其施加的折磨也甘之如飴。
眼前的現況是:資訊科技的幾位「大哥們」谷歌(Google)、微軟(Microsoft)、蘋果(Apple)、亞馬遜(Amazon)與臉書(Facebook)配合政府聯手掌控市民的各個生活領域,包括了無所不在的監視錄影器,電話與電子郵件的自動化監聽與檢查,高解析度的衛星空照掃描地表上每一寸土地,以及每個人分分秒秒的行蹤,此外生物測定臉孔辨識機遍佈機場、公司行號,身體健康與疾病資料中央化儲存,從個人銀行到資金往來、各種信貸、提供電子卡片,從書籍文字、圖片、影片到影音的數位資料檔案皆可濃縮在一丁點的裝置內,其儲存空間以兆元或千兆元計算,巨大的實體物料空間化為肉眼不見的微世界,而各種資訊工程師、電腦與計算機專家、數學家、駭客、軟體研發家、密碼專家則坐在冷氣房按著鍵盤,就能辦到對市民生活方式的絕對操縱,這些「大哥們」其實都喜愛隱姓埋名,從幕後全面監控自由公民的生活空間,從交友、線上交易、廣告、網際網路、銀行轉匯,各行各業的運轉,無一能逃脫網路空間的滲透與支配並留下紀錄,而人人還心甘情願的在鍵盤上按下「我喜歡!」,而這正是歷史上任何獨裁體制都望塵莫及的。
然而,網際網路所創造的虛擬空間真是法力無邊、無盡無涯的嗎?就像已有人宣稱一個地球是不夠的論調,一如數千年來人類已先攫取與瓜分了地表上的土地空間,接著又走向海洋,再接著是空中以及投向似乎是無垠的宇宙太空。顯而易見的是,人類是不會僅滿足於星球的空間,舊的空間因素(土、水、氣)如今迅速被新的空間元素(數位、奈米)取代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被鉗入實體與虛擬的混合世界,對新型態空間的無盡需求,意味著誘惑與渴望,但卻又擔心成為網路受害者,就像古人畏懼無岸的大洋,今人則淹沒在浩瀚的資訊大海。不論是征服深海抑是無涯的外太空,人類的空間意識其實是人的能量、活力的場域,人類生存方式的變遷,以及該如何看待它,端視我們的衡量標準,即使今天世人大力頌揚、歡呼甚至著迷於網路空間,彷彿那是有著無限的可能性,但又意識到陷入無法自拔的癮頭,以及那對它的依賴與虛空的恐懼,但人終究還是要找到適合人的尺度與合乎比例的活動空間啊。
內文選摘(二)
〈卡繆作品中的空間書寫〉(摘錄)
吳錫德/淡江大學法文系教授
空間與神話
做為一位「現代派作家」,卡繆不僅在文字表達上力主「極簡」原則,也大量使用現實生活中的新聞事件或廣告文案作為文本的一部份。以「嵌空」的方式置入文本,如此不僅提高文本的張力和可讀性,也開創了另一個新「空間」。這個空間既屬真實(naturelle)又似虛幻(invraisemblable)因而開創了文本的另一個側面,使它具有某種詩意的隱喻。譬如:他在牢房的床墊下找到一張發黃的報紙碎片,上頭是「克魯申制鹽公司」的廣告。它是真實的,但卻傳達更多的好奇、疑問以及想像。
又如,回憶母親轉述其早歿的父親,某日特早出發趕去觀看某個死囚的斷頭刑,回家後昏睡及嘔吐的情景。這事也是真實,卡繆還又更詳實地寫進他的自傳《第一人》裡。終其一生,這事件一直纏縈在他的思緒,最終讓他徹底反對死刑制裁,因為那是另一種暴力的展現,令更多的無辜者成為受害者。在此他透過文學提領出他的人道主義觀點。此外,最膾炙人口的新聞事件便是,捷克一對母女謀財害命,「誤殺」出外打拼喬裝成旅客衣錦還鄉探親的兒子。卡繆還將這則真實新聞改編成舞台劇《誤會》。他在小說中提到:「這段故事,我不知讀了幾千遍。一方面,這事不像真的;另一方面,卻又很自然。無論如何,我覺得那個旅客有點自作自受,永遠也不該演戲。」總之,社會新聞事件本就誇張且不尋常,但畢竟是真實。卡繆藉此強調了人生的「似非而是」,以及「虛實不分」。
卡繆擅於將日常生活場景、稀鬆平常的事物,或耳熟能詳的觀點,以現代隱喻的手法,使之「傳奇化」,並假以主觀及想像的敘述,進而粹煉出某種帶有詩意的神話內容,開創了新的書寫,而深入讀者印象。他是這樣描寫「靈車」的:「長方形,漆得發亮,像個鉛筆盒」。他對即將判決他生或死的「陪審團」的印象則是:「彷佛電車上一整排互不相識的旅客,盯著新上來的乘客,想發現他有什麼可笑之處」。最經典的莫過於卡繆對「牢房」的書寫,他把囚室媲美住在枯樹幹裡:
如果讓我住在一棵枯樹幹裡,除了抬頭看看天上的流雲之外無事可幹,久而久之,我也會習慣的。我會等待著鳥兒飛過或白雲相會,就像在這裡等著我的律師的奇特的領帶,或者就像我在另一個世界裡耐心等到星期六擁抱瑪麗的肉體一樣。何況,認真想想,我並不在一棵枯樹幹裡,還有比我更不幸的人。
接著,卡繆又將「牢房」裡的空間加以「傳奇化」:「這樣,睡覺、回憶、讀我的新聞,晝夜交替,時間也就過去了。我在書裡讀過,說在監獄裡,人最後就失去了時間的概念。但是,對我來說,這並沒有多大意義。我始終不理解,到什麼程度人會感到日子是既長又短的。日子過起來長,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居然長到一天接一天。」卡繆還辯證道:「時間沒有重複,所以就沒有所謂的時間。」他還說:「我學會了回憶的那個時刻起,我就一點兒也不感到煩悶了。〔…〕於是我明白了,一個人哪怕只生活過一天,也可以毫無困難的在監獄裡過上一百年。」在此,卡繆拿「回憶」來對抗「時間」,以及「空間」。「監獄」這個空間成了卡繆辯證其不受時空限制的深廣意識。他還更上層樓,淋漓盡致地發揮了巴舍拉所言的「內在空間」,使自己跳脫被禁錮了的空間,自由地品味他的想像力:
審訊結束。走出法院登上車子的時候,一剎那間,我又聞到了夏日傍晚的氣息,看到了夏日傍晚的色彩。在這走動著的,昏暗的囚車裡,我彷佛從疲憊的深淵裡聽到了這座我所熱愛的城市,某個我有時感到滿意的時刻的種種熟悉的聲音。在已經輕鬆的空氣中飄散著賣報人的吆喝聲,滯留在街頭公園裡的鳥雀的叫聲,賣夾心麵包的小販的喊叫聲,電車在城裡高處轉彎時的呻吟聲,港口上方黑夜降臨前空中的嘈雜聲,這一切又在我心中劃出了一條我在入獄前非常熟悉,在城市隨意亂跑的路線。
莫索在等後最後的判決,卡繆是這樣寫道:
我聽見大廳中一個低沉的聲音在讀著什麼。鈴又響了,門開了,大廳裡一片寂靜,靜極了,我注意到那個年輕的記者(即卡繆安排自己入書)把眼睛轉向別處,一種奇異的感覺油然而生。我沒有朝瑪麗那邊看。我沒有時間,因為庭長用一種奇怪的方式對我說,要以法蘭西人民的名義在一個廣場上將我斬首示眾。我這時才覺得認清了我在所有這些人臉上所看到的感情。我確信那是尊敬。法警對我也溫和了。律師把手放在我的腕上。我什麼也不想了。庭長問我還有什麼話要說。我說:「沒有。」他們這才把我帶走。
在這裡,法庭大廳是以第一人稱當事人的視角予以描述,但作者捨棄了物理空間的書寫,改以「意識空間」的方式敘述。其結果反而凸顯了一種「客觀書寫」。宣判的結果幾乎是由「他者」的眼神宣佈的,換言之,當事人是透過「觀看」他者的眼神提早獲知了判決的結果。沙特說過:「他者即地獄」。在此,「他者」既是空間裡的配角,也是主角,更是關懷的,溫馨的,是人道主義的……。只是結局都是一樣的殘酷!卡繆正是通過這樣的書寫,提出他最為沉痛的「反抗」。
空間性與現代性
根據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理論,存在有一種「三元組合概念」,即可將空間區分為:「感知空間」(espace perç)、「構思空間」(espace conçu)以及「生活空間」(espace vécu)。當中感知空間就是人從如萬花筒般的物理空間所感受的一切。構思空間則指被各類專家所「支配」的空間,或者由藝術創作者所「想像」出來的空間。至於生活空間(即經歷過的空間)才是人類最適存的空間,它既包含前兩種空間,更是人類應極力爭取自由和解放的空間。當中既包含統治與服從(即權力關係),也包含了人類的「反抗」。而卡繆藝術創作的核心價值及終極目標正是「反抗」。他說過:「我反抗,故我們存在。」質言之,卡繆有關空間的思索正是聚合了這三種空間,並予以凸顯,當中既有他的所見所思,亦有他的所慮所言,更有他的創作和使命。這便是他的詩意與策略。
卡繆可說是刻意地將「空間」大量書寫進他的作品裡,並且還予以無限的擴衍。這個「空間」恒早就已存在,對它的描述也不乏其人。只是卡繆的特色在於,將現代生活中早已碎片化的空間加以組合,又很高超地加以黏合。透過現代人對「時間」的新感知,添加了對「空間」的新認知及感受,並且利用「極簡敘述」手法,將這些「構思空間」串連在一起,使書寫更具意象化,更具臨場感,更具張力,也更見荒謬,更為現代感。
羅蘭•巴特在論述《異鄉人》時,是透過卡繆不尋常的「時間書寫」,發現了「白色書寫」(極「零度書寫」)。並從書中「時間」的氛圍瞧見卡繆作品中的「現代性」。這個「現代性」當然是有別于文學裡的古典主義修辭法,以及寫實主義裡的刻板敘述。至於「空間」的「現代性」,英國文化地理學者克朗(M. Crang)認為是:「產生於工業化的一種情感結構(A Structure of Feeling)。」卡繆正是透過這種「情感結構」,用了最簡潔有力的「極簡敘述」去彰顯現代社會中種種看似「自然」,又「虛幻」(難以置信)的二元辯證關係,並從中凸顯「荒謬」的存在。不過,最關鍵的還是,他是透過藝術家的想像與敏銳,將這些稀鬆平常的「空間」予以「傳奇化」,如此才拉近並感動讀者。
結語
卡繆的書寫簡約、客觀,而張力十足,早有定論。他不僅在時間的敘述上力創新猶,呈現一種現代性的美學風格;透過其對空間的感知,將空間書寫的諸多可能靈活運用,並連番上場,而精彩繽紛。尤其配合他所身體力行的「極簡敘述」,而臻於一種既批判,又帶有詩意,及人道主義精神與傳奇效應的敘述風格,使作品的氛圍既飽和,又充滿想像,而為世人所驚豔。
「空間性」的介入顯然更有助於凸顯,體驗,並領悟卡繆的詩意和敘述手法;也同樣更有助於掌握卡繆作品的核心論述,不論是荒謬性或人類的反抗,及其作品的氛圍,如疏離感和現代性。若能聚合這些考慮和因素,也就更能多面向,更具體的體驗卡繆作品的美學。
總之,強調「空間書寫」可讓文本的呈現更立體化,更具體可徵,同時還能更清楚凸顯主題論述,譬如,讓疏離感更具體,讓荒謬感更像神話,讓「他者」更鬚眉畢現等等。而最珍貴的莫過於提升「想像」的作用,讓它更寬廣、更深厚的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建立起一道共鳴。這應當就是我們現代人所探尋千百回的「現代性」吧!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WPRLD LITERATURE的圖書 |
 |
$ 205 ~ 351 | 空間與身體
作者:WPRLD LITERATURE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公司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空間與身體
國內唯一跨越文化與國家界線的世界文學季刊
這是一份廣納視角,沒有藩籬的刊物,大語種小語種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分身或天地。編輯委員會以音樂中最接近人聲的樂器——「拉長號」的態度面對這份刊物,希望長號的人性、伸縮彈性,以及拉出高、中、低音的能量,可以跟大多數的讀者產生共鳴,結合一體。
《世界文學》內容兼顧學術與通俗,既追求廣度也要求深度,試圖向台灣讀者宣告「文學全球化」的時代已經來到了!
《世界文學》第二期在熱情的夏季出刊,本期的主題研究特區為「空間與身體」。
「空間與身體」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氛圍與環境。吳爾芙在《自己的房間》裡標榜女性創作,要有足夠的收入,還要有「自己的房間」,沒有獨立自主的空間,就無法揮灑心靈之筆;波赫士的〈兩個國王和兩個迷宮〉揭示大自然的奧祕勝過人工的取巧:無形廣袤的沙漠空間遠比巧奪天工、繁複多奇的迷宮更令人震懾恐懼、迷惘不知所措。達文西的《維特魯威人》,完美的比例呈現「十」字型和「火」字型人體,同時鑲嵌在一個矩形和圓形當中;而蠶繭中的蛹、娘胎裡的嬰兒蜷伏在窄小的薄膜中,卻孕育出亮麗的新生命;卡繆的《異鄉人》(1942)、塞拉的《杜瓦特家族》(1942)、薩巴多的《隧道》(1948)立基於存在主義的思維,一致勾勒受刑人身陷囹圄的孤寂與桎梏;其他如物理、數學、網路空間,都與我們的身體與動力息息相關,我們若用更廣闊的心和視窗凝望,會處處感受到學術的雋永與況味,這也是《世界文學》的願景。
本期的主題是「空間與身體」,主要收入的文章如下:
卡繆作品中的空間書寫
村上春樹《1Q84》的身體書寫
蹺家、毒品、暴力──蘇萊瑪‧鑫的《街頭小孩》
話文學、說故事──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台灣論壇
TOP
章節試閱
〈漫談空間概念種種──世界、星球、網路〉(節錄)
洪丁福/文化大學政治系專任副教授
星球空間革命
「世界不在空間內,而是空間位於世界內!」
世界史與人的空間意識
如果說哲學的、邏輯的與自然科學的空間概念是抽象的,那麼較易為人們了解的具象空間要算是常識的空間,即吾人日常所經驗到的,這主要是基於實際的理由,像是個人心理空間、公共的地理空間,前者涉及個體的生活與生存課題,後者則是有關我們所生存的地球與周遭環境的科學領域,諸如地球物理、製圖學(cartography)、地形學(topography)、地勢學(風土研究)(top...
洪丁福/文化大學政治系專任副教授
星球空間革命
「世界不在空間內,而是空間位於世界內!」
世界史與人的空間意識
如果說哲學的、邏輯的與自然科學的空間概念是抽象的,那麼較易為人們了解的具象空間要算是常識的空間,即吾人日常所經驗到的,這主要是基於實際的理由,像是個人心理空間、公共的地理空間,前者涉及個體的生活與生存課題,後者則是有關我們所生存的地球與周遭環境的科學領域,諸如地球物理、製圖學(cartography)、地形學(topography)、地勢學(風土研究)(top...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編輯室報告
張淑英
《世界文學》第一期在各界的支持與各個領域的學者戮力合作下,順利在春意盎然的三月出版。這幾個月來,編輯委員會聆聽各方建言,結集讀者、作者、編輯、出版等等不同角色的觀點與意見,在必要的堅持與理想之間,嘗試可能的微幅改變和調整,不敢夸夸而談學術與大眾無縫接軌,但也不希望拘限於「曲高和寡」的小眾知音。《世界文學》歷經十年的空窗期得而再生,識者共同的抱負是潛心耕耘,引導它成長茁壯並能安身立命,一份由學術的養分醞釀出來的日日春期刊。尤其重要的是,這是一份廣納視角,沒有藩籬的刊物,大語種小...
張淑英
《世界文學》第一期在各界的支持與各個領域的學者戮力合作下,順利在春意盎然的三月出版。這幾個月來,編輯委員會聆聽各方建言,結集讀者、作者、編輯、出版等等不同角色的觀點與意見,在必要的堅持與理想之間,嘗試可能的微幅改變和調整,不敢夸夸而談學術與大眾無縫接軌,但也不希望拘限於「曲高和寡」的小眾知音。《世界文學》歷經十年的空窗期得而再生,識者共同的抱負是潛心耕耘,引導它成長茁壯並能安身立命,一份由學術的養分醞釀出來的日日春期刊。尤其重要的是,這是一份廣納視角,沒有藩籬的刊物,大語種小...
»看全部
TOP
目錄
編輯室報告/張淑英
研究特區
王美玲 蹺家、毒品、暴力――蘇萊瑪‧鑫的《街頭小孩》
吳錫德 卡繆作品中的空間書寫
洪丁福 漫談空間概念種種――世界、星球、網路
曾秋桂 村上春樹《1Q84》的身體書寫
吳寬 朝聖與節慶:西班牙中世紀詩歌內之聖與俗
書評書藝
張雪媃 為流亡人潮寫歷史見證: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周智民 翻譯的射程:評芥川龍之介的《竹林內》
高翊峰 性、愛與政治的假面人生:評《激情三部曲》
鄭欣怡 囚室少女歷劫餘生:評《3096天》
學海省思
莫渝 迷戀或者被蠱惑...
研究特區
王美玲 蹺家、毒品、暴力――蘇萊瑪‧鑫的《街頭小孩》
吳錫德 卡繆作品中的空間書寫
洪丁福 漫談空間概念種種――世界、星球、網路
曾秋桂 村上春樹《1Q84》的身體書寫
吳寬 朝聖與節慶:西班牙中世紀詩歌內之聖與俗
書評書藝
張雪媃 為流亡人潮寫歷史見證: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周智民 翻譯的射程:評芥川龍之介的《竹林內》
高翊峰 性、愛與政治的假面人生:評《激情三部曲》
鄭欣怡 囚室少女歷劫餘生:評《3096天》
學海省思
莫渝 迷戀或者被蠱惑...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世界文學編輯委員會
-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8-1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96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世界文學總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