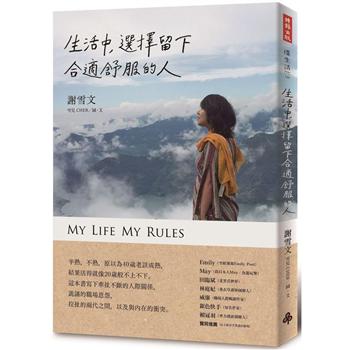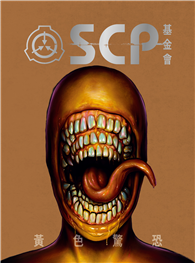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Wen-Yin的圖書 |
 |
$ 149 ~ 342 | 短歌行
作者:鍾文音(Wen-Yin(nina),Chung) 出版社:大田 出版日期:2010-03-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88頁 / 14.8*21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百年物語2:短歌行
【台灣百年物語二部曲】
這不是我的家族故事,
這只是一些人的故事,
與際遇碎片……
土地散發著陳年老書的那股霉味,
紙頁彼此相偎的一種腐朽又甜美的氣息,
是鍾小娜喜歡的氣味。
這種腐朽又有點像奇異的老書皮味道,
於她一點也不難聞。
只是聞到的她,突然在那一刻就老了。
這是一去不復返的味道。 島嶼的大雨就像歷史的複製,不斷地去而復返。
下了太久的大雨,讓土地有著一張老臉。
許多片斷,歷史幽魂,
常在雨夜飄來她的夢裡……
作者簡介
鍾文音Wen-Yin(nina),Chung
淡江大學大傳系畢,曾赴紐約視覺藝術聯盟習油畫創作兩年。
現專職創作,以小說和散文為主,兼擅攝影,並以繪畫修身。
長年關注家族寫作、愛情等題材,並熱愛旅行、喜愛遊蕩,十多年來足跡遍及世界五大洲。近年持續寫作不輟,已出版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及散文集多部,質量兼具、創作勃發。
被譽為九○年代後期崛起之優秀小說家,曾獲中國時報、聯合報等十多項全國重要文學獎(1997-2000),2002年台北文學創作年金,
2003年雲林文化獎,2005年吳三連獎、第一屆林榮三短篇小說獎暨散文獎。
2006年出版的長篇鉅作《豔歌行》,一出版即獲2006年中時開卷版中文創作十大好書!2008年,再入圍台北國際書展小說大獎!
鍾文音成立美學網 www.bestlife.tw
鍾文音之驚世花園 www.wenin.tw
鍾文音的中時部落格 blog.chinatimes.com/wen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