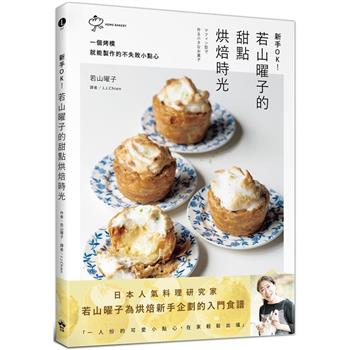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alastair santhouse的圖書 |
 |
$ 199 ~ 342 | 其實,問題出在心理受傷了:心理如何治癒身體,英國皇家醫學會精神科醫師的身心安頓之道 (電子書)
作者:艾勒斯特‧桑豪斯(Alastair Santhouse) / 譯者:呂玉嬋 出版社:奇光出版 出版日期:2021-09-15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初版  共 1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擲地有聲,動人心弦,掌握時代脈動,讀來饒富興味!
──《衛報》書評
不要問這人得了什麼病,要問病著的是什麼人。
一位精神科醫師對身心平衡的醫療照護,最真摯懇切的省思和提醒──
我們的心理左右我們對疾病的理解,對症狀的反應,
主宰我們所接受的治療,甚至決定治療是否能夠見效。
希望大家用新的方式,來思考你的心理、你的身體以及你的健康。
◆英國皇家醫學會精神醫學分會主席暨精神科醫師桑豪斯陪伴過數千名個案,在這本發人深省的臨床故事集中,分享親身經驗,闡明我們的情感心境與身體健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什麼是健康?是我們身體裡的什麼東西嗎?還是某種主觀的東西——屬於心靈層面的東西?本書精闢闡釋身心之間存在著難以阻擋的連結,反對將疾病的生理和心理原因分割開來,對身體有症狀的人,對正在治療症狀的人,甚至對所有人,都是一本重要的書。
◆本書探討近20個重要議題,從輕生的悲劇、憂鬱症的治療、疼痛的意義,到圍繞肥胖和精神疾病的汙名、自我誘發疾病的奧祕,以及世紀之疫COVID-19帶給世人的衝擊,提供審視人類病痛的新穎視角,揭露現代醫學經常失靈的原因,也揭示現代醫學最終能夠取得成果的關鍵在於──以人為本,講求身心平衡的醫療照護。
「健康是複雜的,要提供有用的照護,就需要了解人性,也需要了解人體。醫師要做出艱難的判斷,也要承認判斷帶有不確定性。我們必須靈活變通,必須能夠容忍不確定性。人體健康狀態衰退的方式有限,但人的生活、歷練、個性和心理健康與健康的互動方式是無窮的,呈現給醫師的樣貌也是數不清的。這就是我一直以來深受吸引的範疇。心理對身體具有如此深刻的影響力,這似乎難以相信,卻是千真萬確的——它決定了我們現在的一切和日後的一切。」──本書作者艾勒斯特‧桑豪斯
今日的醫療模式辜負了我們,它提倡專業化,
輕忽了我們健康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的心理狀態。
一個人的心理健康和性格,不只決定了他承受的疾病症狀,
也決定了他一輩子身體健康問題的後果。
無論在身體健康方面還是一般生活中,我們都是自己的個性和心智的囚徒和產物,
不過未必只能如此。我的經驗是,在幫助人們突破這些牢籠,理解身心相互作用方式的過程中,
醫學藝術可以結合醫學科學,變得比單獨任何一方都更有用也更有效。
一晚,菜鳥醫師桑豪斯值班,獲知要送來急診室的婦人在救護車上身亡──他的第一個反應是,太好了,可以回去補眠了!但是,他怎樣也睡不著了,因為他那雀躍的反應錯得太過離譜。就在那一晚,桑豪斯醫師決心啟程,步上從急診室通往精神醫學的漫長之旅。
在這本書中,桑豪斯醫師記錄下多年來治療個案的經驗,探討心理對健康造成的深刻但被低估的影響。心理決定了我們對症狀的反應,支配我們所接受的治療,也左右了治療的效果。心理甚至是影響我們會否產生症狀的關鍵。
透過嚴酷的誠實、深切的同情和詼諧的幽默感,本書回顧一些疑難病例,揭露最令人困惑也最具爭議的醫療問題——從輕生的悲劇、憂鬱症的治療、疼痛的意義,到圍繞肥胖和精神疾病的汙名,到自我誘發疾病的奧祕,以及世紀之疫COVID-19帶給世人的衝擊。最終,桑豪斯醫師發現,今日的醫療模式辜負了我們,它提倡專業化,輕忽了我們健康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的心理狀態。
作者簡介
艾勒斯特‧桑豪斯(Alastair Santhouse)
英國曼徹斯特出生長大,畢業於劍橋大學,目前是倫敦蓋氏醫院及莫茲利醫院的精神科顧問醫師。2013年至17年期間,擔任英國皇家精神科醫學院照會精神科副主任,2016年擔任英國皇家醫學會精神醫學分會主席。臨床工作側重於身體和心理健康的交集。目前與妻子及四個孩子住在倫敦。
譯者簡介
呂玉嬋
專事筆譯,樂在文字,譯有書籍數十餘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