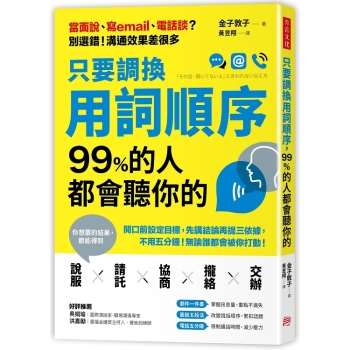價值牽涉的不僅只限於金錢,但是價值型投資
或許可以給你更多時間,讓你享受生命其中其他重要的事情。
讓自己的思維遠離華爾街1,269哩,這樣的經驗值得探討,
你的視野也會變得更清晰……
●如果投資界的傳奇巴菲特邀請你共進午餐,你會想跟他討論什麼?
結構型財務專家珍娜‧塔瓦科莉將自己針對信用衍生商品所發表的著作寄給這位奧馬哈先知,而巴菲特回覆以一次午餐邀約。在《巴菲特親自幫我上的一堂課》中,塔瓦科莉讓讀者親臨這場午餐邀約的現場,聆聽大師針對財務界近期某些最混亂的時刻所發表的睿智談話。
本書說明了巴菲特的智慧如何照亮現今的財務世界,包括巴菲特如何以審慎且透明化的態度面對衍生性商品,並避開華爾街慣有的羊群心態。作者透過她與巴菲特之間的廣泛對談,針對房貸危機、避險基金、草率的會計手法以及整體市場的衰敗,闡述她自己與巴菲特兩人的精闢見解。
作者在書中娓娓道出巴菲特一生成就中的某個特殊層面,許多人士由於專注於他的穩定投資報酬率與特殊的價值型投資原則,因此忽略了這一點。除了因眼光獨到而能獲取穩健的長期收益之外,巴菲特也成功避開了許多財務災難與崩塌,似乎早已預見這些事件會發生。深刻理解巴菲特與作者預見財務危機的方法後,相信你的人生投資學將會有嶄新的收穫。
作者簡介:
珍娜‧塔瓦科莉(Janet Tavakoli)
塔瓦科莉結構財務公司(Tavakoli Structured Finance)總裁。這家位於芝加哥的顧問公司,服務對象包括財務機構、法人投資機構與其避險基金公司。作者早同業針對許多重大金融機構倒閉事件提出警告,包括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第一聯合房貸公司(First Alliance Mortgage)、儲蓄銀行產業以及當前的信用泡沫。《商業週刊雜誌》(BusinessWeek)稱作者為「信用衍生商品的卡珊卓」。作者曾經擔任芝加哥大學商學院財務系助理教授,講述課程為衍生性商品,並著有多本財務專書,其發表的談話經常受到財經媒體的引述,包括《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商業週刊》以及《紐約時報》等。並經常受邀出席電台節目、包括CNN、CNBC、CBS Evening News、Bloomberg TV、First Business Morning News、Fox News、Fox Business News、ABC以及BBC等。
譯者簡介:
張淑芳
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畢業,美國麻州大學企管碩士,譯作包括《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你擁有多少錢才夠?》、《瞄準未來投資》、《信念與財富》、《一個計量金融大師在華爾街》、《要獲利不要市占率》、《新世代資本家》、《Top Sales百日魔鬼訓練營》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珍娜‧塔瓦科莉很早便提出警告,史上最嚴重的信用泡沫即將出現。她在本書中詳細說明了世人當初原本能夠避開這場災難,未來又該如何避免重蹈覆轍。」
——投資大師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著有《中國很牛》、《熱門商品》、《資本家的冒險》與《投資騎士》等書
「珍娜‧塔瓦科莉以清晰且活潑的筆觸,探討導致美國財務市場崩塌的奇異且深奧難解的財務工具。作者博學多聞而且能夠清楚闡述其所要表達的理念。她將近幾年出現的不法作為與巴菲特的卓越分析與常理判斷兩相比較,這種做法既恰當,又有助於說明不理性行為的瘋狂程度。」
——投資家 亞當‧史密斯(George J.W. Goodman),著有《金錢遊戲》與《超級貨幣》等書
「如果你是一位投資人,不管是直接投資或透過共同基金或管理帳戶進行投資,一定要閱讀這本引人入勝的著作。各位需要了解,像美林、花旗集團、Wachovia銀行以及瑞銀集團(UBS)等知名金融機構,如何因為自己發明的不良財務商品損失數百億美元,而購買這些商品的投資人的損失更加慘重。作者早已預見這種結果,並在本書中以條理分明且具說服力的方式,清楚解說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並且在書中穿插說明巴菲特的投資理念,以強烈對比那些必須對當今的財務災難負責的主要金融機構。了解這場財務浩劫如何演變,你將會更進一步明白如何評估自己的投資,以及幫你進行投資的中介機構。」
——Gleacher Partners LLC公司董事長艾瑞克‧葛利澤(Eric Gleacher)
「珍娜‧塔瓦科莉擁有一種特殊的天賦,能夠透過個人軼事與簡單的語言,解釋複雜的結構型財務商品。《巴菲特親自幫我上的一堂課》透過一般大眾都能了解的淺顯文字,深入解析當今的全球信用危機。對所有負責配置另類投資商品的信託受託人來說,這是一本必讀的佳作。」
—Calamos Investments公司董事長、執行長兼共同投資長約翰‧卡拉莫斯(John P. Calamos Sr.)
名人推薦:「珍娜‧塔瓦科莉很早便提出警告,史上最嚴重的信用泡沫即將出現。她在本書中詳細說明了世人當初原本能夠避開這場災難,未來又該如何避免重蹈覆轍。」
——投資大師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著有《中國很牛》、《熱門商品》、《資本家的冒險》與《投資騎士》等書
「珍娜‧塔瓦科莉以清晰且活潑的筆觸,探討導致美國財務市場崩塌的奇異且深奧難解的財務工具。作者博學多聞而且能夠清楚闡述其所要表達的理念。她將近幾年出現的不法作為與巴菲特的卓越分析與常理判斷兩相比較,這種做法既恰當,又有助於說明不理性行為的瘋狂程度...
章節試閱
第一章 一封未回覆的邀請函
「如果你來到奧馬哈,又想聊聊信用衍生性商品,請務必來找我…」
―巴菲特於二○○五年六月六日致塔瓦科莉的信
二○○五年八月一日,我將當年六月六日的通訊檔案夾裡的一封信重新看了一遍。這封信來自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也就是企業巨擘波克夏集團(Berkshire Hathaway)的執行長。我尚未回信,除了感到有點敬畏以外,我沒有理由可以解釋自己何以遲遲未回信。在此之前幾年,巴菲特一直是《財富雜誌》(Fortune)全球最富有或第二富有人士。他跟比爾•蓋茲(Bill Gates)每年都在爭奪全球富豪的寶座,最後的結果要視波克夏與微軟公司(Microsoft)的相對股價而定。
我曾經在幾年前寄給巴菲特一本我寫的書《信用衍生性商品與結構型商品》(Credit Derivatives & Synthetic Structures)。巴菲特在給我的信中表示,他在重新閱讀這本書的時候發現裡面塞了一封信。「請接受我的道歉,」他在信中寫道,「因為我在一收到書的時候沒有立刻回信。」他邀請我在有機會造訪奧馬哈時一定要去找他。經過這幾年的時間,我已經不記得我在這封古老的信上寫了些什麼。我知道的是,我當初的確沒期望巴菲特的回音。但現在輪到我需要回信,一份遲來的回音。「親愛的巴菲特先生,」我開始寫道。
我是波克夏公司A股股票的投資人,但是巴菲特先生不會了解這一點,因為我是透過經紀人的帳戶持有股票。巴菲特先生或許覺得有必要挑選我,因為我曾經針對信用衍生性商品以及這類商品隱含的財務槓桿提出警告。由於我不斷在揭發財務體系的弊端,《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稱呼我為「信用衍生性商品的卡珊卓」(Cassandra,譯註:希臘神話中善於預言災禍的女性)。但是大多數記者忽略了巴菲特在二○○二年致波克夏股東的信當中一些更重要的相關談話。波克夏投資許多業務內容繁雜的跨國企業,這意味著這些投資必須進行避險,或是透過各種操作以創造租稅或會計利益。巴菲特先生也曾寫道:「我有時會進行大規模的衍生性商品交易。」然而,我猶豫再三,並未回覆這封信。
一九九八年,波克夏收購了通用再保險公司(General Reinsurance)。剛開始時,巴菲特說該公司是他的「問題兒童」,跟旗下的通用再保險證券公司(General Reinsurance Securities)是一對難兄難弟。早在這筆收購案之前,巴菲特跟波克夏的副董事長查理•曼格(Charlie Munger)便已了解,通用再保險證券的衍生性商品交易的價值受到高估,並曾試圖拋售這些投資。有些契約的到期日長達二十年,這些業務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才能脫手。此外,這類商品的評價模型,也無法合理計算出通用再保險證券某些深奧的衍生性商品契約真正的依市價結算(mark-to-market)價值—也就是可以在市場中買賣這些商品的價格。這些衍生性商品根本沒有真正的市場存在。這些契約的訂價或計價方式,都是根據所謂的依模型計價(mark to model)。巴菲特寫道,有些極端的個案根本是在「依神話計價」。
巴菲特在他於二○○二年致波克夏股東的信中寫道,有些時候,這些新的衍生性商品契約,似乎是由「瘋子」想像出來的。巴菲特的不平之鳴,是他因投資衍生性商品失利所造成的多年後遺症,主要是通用再保險證券的信用衍生性商品。資料顯示,這筆投資的損失高達一億七千三百萬美元,部分原因在於重新編列多年前與衍生性商品有關的錯誤但例行的財務報表。這筆損失促使巴菲特將衍生性商品形容為「大規模毀滅性的財務武器」。這句警語在全世界引起迴響。在看到財經報導引述巴菲特這段談話之後,有位投資銀行家開玩笑說,我針對信用衍生性商品所寫的書就是「如何炸毀地球的手冊」。
巴菲特給我的信於二○○五年六月送到我手上,這對我來說是個忙碌的月份。我有一位法律事務所客戶,在一樁證券詐欺訴訟案中代表一家大型貨幣中心銀行控告另一家大型貨幣中心銀行。對方的律師團請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的前主席擔任專家證人。我之前已經完成我的專家意見書,並寫了一份報告反駁該前主席的看法。我準備要出席歷時兩天的庭訊,說明我對這件牽涉數百萬美元損失的訴訟案的看法。被告已經看過我的資料,他們了解自己這下麻煩大了,隨之改變策略。事實上,他們派了最有經驗的律師要來反駁我。
@
我將巴菲特這封信放在皮包裡以提醒自己要記得回信。庭訊第一天的早上,我看到這封信,一股自信心油然而生。我不是個迷信的人,但實在是忍不住要將這封信當成一個好兆頭。我將信放在我的通訊檔案夾當中,結果又忘了回信。
庭訊開始又結束,原告的律師團非常滿意。「在戰場上的每個人都會受傷,但你簡直是在大開殺戒。」面對事實,被告的論述完全站不住腳,這件案子後來根本沒有經過審訊。不久之後,被告接受原告的條件,雙方達成和解。
到了六月底,我再度檢視我的通訊檔案夾,將這封信又讀了一遍。我不需要到奧馬哈洽公,而且相當確定巴菲特不會需要我的協助。
二○○五年七月又是一個忙碌的月份:我太專注於上述的證券詐欺案,以致工作堆積如山,因此放了自已一星期的休假以舒緩壓力。七月底時,我再度檢視尚未回信的通訊檔案夾,裡面只剩下一樣東西:巴菲特的信。
在八月一日再看了這封信之後,我寫了一封回信,提出三個日期,最早的一天是八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巴菲特七十五歲生日的前五天:
這次輪到我因為這麼晚才向您回信而致歉…我在短期間的未來不會需要前往您所在地的方向洽公,但是我很願意在某一天搭機前往奧馬哈—因為我樂於這麼做…」
八月三日,我收到巴菲特透過助理寄來的電子郵件,表示八月二十五日沒問題:
如果你可以趕上午餐的時間,我很樂意帶你到一間沒有裝潢但食物可口的餐廳。
全球財務界的每個人都聽聞過巴菲特的名聲,他的名字不斷出現在財經報導當中,不過,我從事的是業界的小眾市場,在我的世界裡,巴菲特只是背景的一部分而已。我還沒有看過任何一本探討巴菲特的書,也沒有讀過太多與他個人有關的文章。但是我讀過波克夏的許多股東年報,包括巴菲特致該公司股東的信,我非常喜歡這些文章。
巴菲特在六十歲時便已經是身價數十億美元的富豪,這項事實本身就是一項成就,世上唯有極少數的人可以做到如此,但是他之後的成就更加驚人。由於他的財富基礎雄厚,加上持續以複利成長的效應,在巴菲特累積大部分財富的時候,跟他同齡的人多數早已退休去享用自己的積蓄了。
在我的事業生涯當中,我合作的一些對象,最後都見過巴菲特或是跟他交易過。這就好像我們都唸同一所大學,巴菲特是受歡迎的學長,我則是新鮮人。身為白手起家的女性,我在自己的領域中備受尊敬;但巴菲特是財務界的傳奇,對替自己跟公司股東創造財富的功力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
一九八七年,巴菲特跟曼格出手營救索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執行長約翰•葛特馮德(John Gutfreund)。他們兩人出資七億美元購買索羅門兄弟的可轉換優先股,這項「白騎士」(white knight,譯註:將企業從不利的併購行動中挽救出來的個人或機構)投資,讓葛特馮德得以抵擋羅納德•派洛曼(Ronald Perelman)的惡意併購。熱愛雪茄且生活風格多采多姿的派洛曼是有名的企業掠奪者(corporate raider,譯註:以惡意手法併購企業的人),素以冷酷無情聞名,在一九八○年代拿下了露華濃(Revlon)、Sunbeam、Panasonic等許多企業。相形之下,巴菲特跟曼格並不知名,不同於受到媒體瘋狂包圍的企業掠奪者,從他們兩人的生活中找不到腥羶色的題材。
剛開始時,索羅門兄弟的優先股對波克夏來說是一筆理想的投資。巴菲特從來不提供經營團隊;他找尋的是優秀且誠實的經理人,他覺得葛特馮德就是這樣的人才。情況到一九九一年出現改變。在爆發公債交易醜聞之後,索羅門兄弟的套利部門的交易員保羅•莫澤(Paul Mozer)對多項重大罪嫌伏首認罪。該部門的交易主管約翰•梅利魏勒(John Meriwether)告訴葛特馮德,莫澤已經向他坦承犯案。由於他們二人並未立即將案情交代清楚,致使醜聞越演越烈,最後兩人皆未能脫身。巴菲特不得不出面保護波克夏的投資。一九九一年夏天,他心不甘情不願地擔任索羅門兄弟執行長一職,時間長達十個月。巴菲特的領導能力與正直的名聲挽救了索羅門兄弟,業績很快便有所起色。該筆可轉債的績效勝過波克夏代替索羅門兄弟出售的固定收益債券的表現,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時,這些可轉債的換股憑證變得一文不值。一九九七年時,巴菲特將所有持股出脫給山帝•魏爾(Sandy Weil,譯註:美國知名的投資銀行家,後來出任花旗銀行的執行長與董事長),索羅門最後成為花旗集團的一員。
我於一九八五年夏季成為索羅門兄弟的儲備幹部,這也是我的同學麥可•路易斯(Michael Lewis)所寫的《老千騙局》(Liar’s Poker)一書嘲諷的對象。不同於路易斯在書中的描繪,我是真正用心學習的儲備幹部,但是在巴菲特短期出任索羅門兄弟執行長職位時,我已經不在該公司工作了。
在紐約華爾街與倫敦工作將近二十年之後,我目前在芝加哥經營一家顧問公司。我的客戶仰賴我提供的專業知識。我出書探討信用衍生性商品與複雜的結構型財務產品,金融機構、避險基金與精明的投資人會尋求我的意見以解決他們的潛在問題。
雖然我是經驗豐富的財務專家,我的研究重點並不是價值型投資。芝加哥大學對效率市場的神話深信不疑,偏重知名經濟學者所提出的理論。巴菲特從哥倫比亞取得企業管理碩士學位。他後來成為班哲明•葛拉罕(Benjamin Graham)的學生及友人,並任職於葛拉罕的避險基金。我讀過葛拉罕和大衛•陶德(David Todd)於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證券分析》(Securities Analysis),但是並未將該書的原則積極運用到自己的投資組合當中。我讀過約翰•波爾•威廉斯(John Burr Williams)所著的《投資價值理論》(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Value)以及第四版的《智慧型投資人》(The Intelligent Investor)。這個版本包含了巴菲特為了向已故的葛拉罕致敬所寫的一篇導論,還有巴菲特於一九八四年對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的演講,題目是「來自葛拉罕—陶德維爾市的超級投資人」(The Superinvestors of Graham-and-Doddsville)。我還記得該篇導讀以及演講的內容,為了跟巴菲特見面,我又重新研讀了一遍。我的焦點主要放在衍生性商品與複雜的證券。雖然我在分析複雜的財務商品時會運用到許多價值投資的原則,我尚未將這些原則運用到自己的投資當中,或是根據價值型投資的角度檢視全球市場。
衍生性商品就是針對某個事件會不會發生所下的賭注。所有財務投資都是一種賭注,但衍生性商品是以小搏大的賭注。只要付出很少的頭期款―有時候甚至不用頭期款―你可以大撈一筆(或是損失慘重)。大多數投資人會試著不去思考,自己的損失有可能損失慘重。有些時候,販售這類商品的投資銀行可以幫助客戶達到這項目標,方法是用極其微小的字體說明相關資訊,並將之隱藏在厚達數百頁的文件當中。
由於以小搏大的賭注非常受到歡迎,衍生性商品所牽涉的金額因此高過股票或債券。金融界這種融資浮濫的問題在於,大家往往會同時拋售資產,因此會將市場價格壓低。財務槓桿有時候會牽動全球市場,如果不加以約束的話,這類操作在理論上有可能在全球市場引發有如車諾比(Chernobyl)核能外洩般的浩劫。
效率市場理論認為,價格會反映所有已知的資訊,但巴菲特對此不表認同。他在致股東的信(皆刊登在波克夏企業的網站上)中提供了投資人所有必要的資訊,讓他們能夠了解貸款詐欺、訂價錯誤的信用衍生性商品與訂價過高的證券,而這些資料全都公開在網站之上。
我知道財務市場正面臨嚴重的風險—就像有個小孩在的乾燥的森林裡把玩火柴一樣—但是在二○○五年那個炎熱的夏天早晨,當我登上飛往奧馬哈的班機時,這些想法完全不在我的腦海當中。我即將跟財務界的傳奇人物見面,他也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投資人。
與巴菲特共進午餐
「謝謝你寄來的…網路連結,我還沒有看過內容。或許會有人將他的公司取名為巴菲特、柏南克與塔瓦科莉公司。」
―巴菲特於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致塔瓦科莉的信
當天晴空萬里,從芝加哥出發的航程只歷時一個多小時。我心中不禁納悶,像巴菲特這樣的富豪的行為舉止會如何。已故的霍華•休斯(Howard Hughes,譯註:1905-1976,美國知名的富豪、實業家與電影導演)因為自行駕駛飛機墜機導致腦部受創,因而造成歇斯底里的精神分裂。根據眾所周知的傳說,他曾經大聲嘶吼:「我不是百萬富翁。該死的…我是億萬富翁。」如果一個人有錢到了瘋狂的地步,一點點幽默感是不可或缺的。
在我跟巴菲特預定見面的兩個小時之前,我的航班便已飛抵奧馬哈。我希望能趕得上午餐的時間。當我告訴計程車司機地址時,他一臉茫然。我還以為奧馬哈的每個計程車司機都知道巴菲特先生辦公室的地點,但是我錯了。這位司機向另一位司機問清楚方向,我們就上路了。這趟車程不遠。
司機在一棟毫不起眼的淡黃色辦公大樓前讓我下車。我打開大門後進入一個看似走道而不是大廳的地方。一名警衛獨自坐在一個小書桌後面。他似乎在期待我的來臨,告訴我直接上到十四樓。電梯早已在一樓等候,大廳裡空無一人。我獨自搭乘電梯上樓。
電梯門打開之後,在我面前的是一條無人的走廊。當我步出電梯之後,我聽到一個友善的女性聲音說道:「珍娜,請向右轉之後再右轉,接著請向前直走,」著實嚇了一大跳。我很快地環顧四周。我身邊空無一人,也沒有發現攝影機或是喇叭。我在心裡回想自己從進入大樓之後的舉動,想到自己並沒有在電梯裡調整自己的裙子,心中感到如釋重負。那位女性的聲音重複了之前的指示,這一次,我聽從指示行動。
巴菲特的一位助理坐在小接待區的右側,除此之外,現場並沒有其他人員。我告訴她我早到了,打算閱讀保羅•厄德曼(Paul Erdman)針對一九九○年代中期的全球貨幣危機所寫的《匯率拔河賽》(Tug of War)一書。她問我需不需要飲料,我要了一杯開水。我只啜飲了一小口水,巴菲特便出現了。他很快打量了我一眼,然後精神奕奕地說道:「噢,珍娜來了。請她現在進來。」
巴菲特比我想像得要高而且苗條。他後來告訴我說,他每週有三天的時間會跟著教練健身。他著名的眉毛已經經過修剪—跟網路上那張舊照片不同—皮膚好似剛刷洗過般地散發光輝。他穿著淺灰色的西裝,看起來像是為了講求舒適合宜,而不是要讓人印象深刻。
他請我在沙發上就座,他則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水珠沿著我的水杯滴了下來,我驚慌地望著他的咖啡桌,想要找尋杯墊或煙灰缸。我不想在平滑的桌面上留下一攤水。噢,那個水漬嗎?那是珍娜•塔瓦科莉來訪時留下的印記。巴菲特注意到我的遲疑,從他的書桌裡拿出《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他將報紙放在桌上,告訴我可以將杯子放在報紙上。我低頭望著報紙,知道自己會把報紙弄糊掉。那份報紙看起來多麼平整。巴菲特年少時曾擔任過《水牛城新聞報》(Buffalo News)送報生,他曾經說過,《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是波克夏股東在二十世紀裡最划算的投資之一。巴菲特對報業的熱愛眾所週知,他也是《華爾街日報》的忠實讀者,時間超過半世紀之久。想到我要將巴菲特的報紙弄亂,我的心情為之一沉。他看完報紙了嗎?我抬起頭來,看到巴菲特似乎有點緊張,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除非我接受他的好意,不然他就無法感到自在。除非我放鬆,否則他也無法放放鬆。我放下杯子並坐了下來,在心裡暗自微笑。
接著我就出糗了。我笨拙地想化解尷尬的氣氛,於是說道:「有一天,《華爾街日報》就會只剩下這個用途。」
他突然轉過頭來,用銳利的眼神看著我。幾秒鐘過去。「我同意,」他終於說道。
但是我知道他說的不是真心話,我說的也不是真心話。而且,他知道我說的不是真心話,我懷疑他也了解,我知道他說的不是真心話。《華盛頓郵報》的禮儀專欄作家茱蒂絲•馬汀(Judith Martin)主張,禮貌這個字詞已經遭到污名化,因為有些陌生人會藉此跟我們攀交情以佔用我們的時間、隱私與資源。真心誠意的客套話是一項有效的社交工具,目的是要在不犧牲自己的權利之下讓對方感到自在。幾個月之後,巴菲特寫信告訴我,他不認為自己已經「參透她的這項建議,」但是我認為他已經深得其中的精髓。
《華爾街日報》引發各界對新聞媒體變革的探討。媒體可以提供近乎即時的股市報價。當今的財經新聞比以往更加豐富,而且來源更加廣泛,包括網際網路在內。
巴菲特熱愛報紙,他也了解,報社的所有權帶有與經濟利益不成比例的地位與影響力,如果經營有道,報社也可以創造可觀的經濟利益。巴菲特在談話中提到凱伊(Kay)。凱伊?我在心中思索。凱伊是誰?還好,我很快就了解他指的是已故的凱薩琳•葛蘭姆(Katherine Graham),《華盛頓郵報》的前任總經理兼發行人。巴菲特說她是一位「偉大的女性」,一位「了不起的女士」,並建議我閱讀《個人歷史》(Personal History)—她獲得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的個人自傳。
在葛蘭姆的支持下,握有重要股權的巴菲特成為具代表性的《華盛頓郵報》的董事之一。巴菲特說,葛蘭姆是他所見過的最缺乏自信的人。基於葛蘭姆尊崇的生活、社會地位與成就,這一點著實令人好奇。葛蘭姆在自傳中表達了她對巴菲特的推崇,並感激他在財務事宜方面對她的指導。葛蘭姆倚重巴菲特對她在事業與個人層面的支持,巴菲特與她亦師亦友的關係,是葛蘭姆力量的來源,能夠帶給她信心。除了葛蘭姆之外,《華盛頓郵報》的董事會成員全為男性,他們剛開始時對兩人的關係曾有所疑慮,葛蘭姆也察覺到一絲性別歧視的存在:「湯姆•莫菲(Tom Murphy,該報的一位董事)可以徵詢巴菲特的意見,沒有人會質疑他。可是如果我徵詢巴菲特的意見,這件事就會顯得帶有威脅性且居心不良。」如果男性與女性保持密切的事業關係,這段關係往往會被形容為一樁魔鬼交易,但是如果男性之間彼此建立一段緊密的商業關係,這就會只是一種事業關係。葛蘭姆還寫道:「當巴菲特跟我相聚的時間越來越久,大家的眉毛就會挑起。我當時年紀還不算太老,足以讓我們兩人的關係成為一項話題。」即使是像葛蘭姆這樣具有地位的年長女性―她比巴菲特年長十三歲―也逃不過眾人的流言蜚語;但是她並未讓這些流言阻止她借助巴菲特的專業知識,或是她對兩人情誼的重視。
我很能了解葛蘭姆倚賴巴菲特的友誼,當他回想葛蘭姆的時候,整個人便容光煥發。看起來,巴菲特喜歡與女性為友,但也知道有所節制。這其中的差異就像是跟藝術鑑賞家或飛賊共聚。前者會讓你覺得自己是一國之寶,後者會讓你覺得自已即將被塞在某個包包裡面,從此不見蹤跡。巴菲特說他欣賞葛蘭姆的勇氣與毅力。
巴菲特了解,新聞事業已經有所改變。他說《華爾街日報》痛失了一次可以主導網路商業新聞的黃金機會。網路上的財經新聞具時效性但可信度較低。報紙與雜誌―即使是知名平面媒體的網路版―時效往往不如部落格與某些專業新聞服務業者。有少數幾位網路財經記者跟平面媒體的頂尖記者一樣出色,但是他們散落在網際網路的各個角落。
麥修•科利爾•波頓(Matthew Currier Burden)曾經針對這個現象寫過一本書:《戰爭的部落格》(The Blog of War)。由於士兵在部落格上傾訴自己的故事,軍隊因此難以掌控敏感的資訊。在我們共進午餐的隔一天,我寄給巴菲特一篇由約翰•哈肯柏利(John Hockenberry)所寫的文章In Iraq for 365,該篇文章刊登在Wired.com網站上。巴菲特在回信中寫道,他覺得有關伊朗的部落格非常有趣,而且「有可能改寫新聞學」。
駐防伊拉克的士兵在這些部落格中提供的訊息,比任何官方的新聞媒體都要豐富,包括電視、廣播、報紙、雜誌與網路新聞來源。巴菲特對這一點特別有興趣。傳統的資訊管道遭到來自前線的第一手資訊的取代與超越,這種現象在網際網路年代之前從未發生過。士兵的描述比主流媒體的所謂「專業」報導來得更加生動且有內容。
第一章 一封未回覆的邀請函「如果你來到奧馬哈,又想聊聊信用衍生性商品,請務必來找我…」―巴菲特於二○○五年六月六日致塔瓦科莉的信二○○五年八月一日,我將當年六月六日的通訊檔案夾裡的一封信重新看了一遍。這封信來自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也就是企業巨擘波克夏集團(Berkshire Hathaway)的執行長。我尚未回信,除了感到有點敬畏以外,我沒有理由可以解釋自己何以遲遲未回信。在此之前幾年,巴菲特一直是《財富雜誌》(Fortune)全球最富有或第二富有人士。他跟比爾•蓋茲(Bill Gates)每年都在爭奪全球富豪的...
目錄
第1章 一封未回覆的邀請函
第2章 與巴菲特共進午餐
第3章 草原王子與黑暗王子:認股權證
第4章 難以滿足的好奇心:避險基金
第5章 保證互相毀滅的房貸:強權對弱勢
第6章 當心帶著禮物的怪客:抵壓債務型債券
第7章 財務占星術:信評AAA墜落之星
第8章 我想檢視標單:財務槓桿
第9章 避險英雄開上奪命彎道
第10章 美國財政部長與慘痛的代價
第11章 債券保險重創華爾街
第12章 錢、錢、錢:巴菲特與華府
第13章 戰爭、宗教與政治的迷霧
第14章 尋找價值
第1章 一封未回覆的邀請函
第2章 與巴菲特共進午餐
第3章 草原王子與黑暗王子:認股權證
第4章 難以滿足的好奇心:避險基金
第5章 保證互相毀滅的房貸:強權對弱勢
第6章 當心帶著禮物的怪客:抵壓債務型債券
第7章 財務占星術:信評AAA墜落之星
第8章 我想檢視標單:財務槓桿
第9章 避險英雄開上奪命彎道
第10章 美國財政部長與慘痛的代價
第11章 債券保險重創華爾街
第12章 錢、錢、錢:巴菲特與華府
第13章 戰爭、宗教與政治的迷霧
第14章 尋找價值



 共
共  2012/01/16
201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