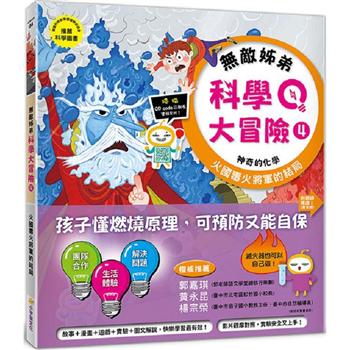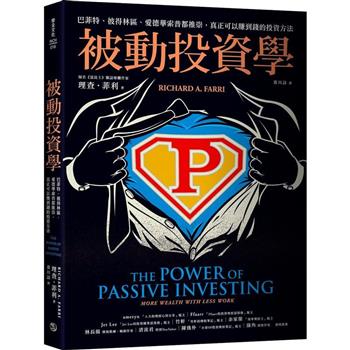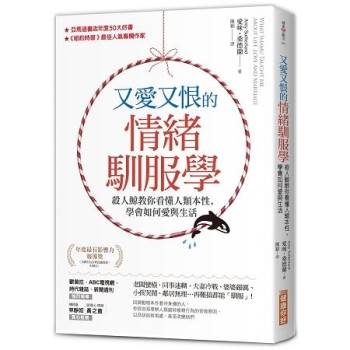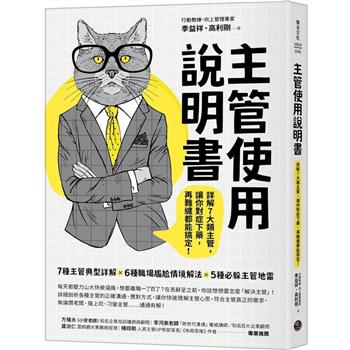在大學教書十五年之後,
她發現自己越來越不了解學生們都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
同事們和她一樣都有個相同的問題:
「為什麼今天的學生越來越難教?…」
於是,她讓時光倒流,重返新鮮人生活……
本書作者匿名的麗貝嘉‧納珊(Rebekah Nathan),是美國一所型的州立大學人類學教授,教了15年書之後,她發現自已無法瞭解當前大學生的行為舉止。她和同事商談,發現大家都很困惑:為什麼今日大學生變得那麼難教?現在的大學生比以前愛作弊,更無禮,更無精打彩嗎?他們到底關不關心成績和教育?納珊決定利用休假一年的時間,以高中畢業的良好成績,獲准註冊入學,混跡在大一新生之間,「刺探」現代大學生是怎麼回事?
為了體驗學生生活,她搬進學生宿舍,登記了全讀課程。她在學生餐廳吃喝,加入學生俱樂部,並且以五十來歲的年紀堅持參加體育活動,定期玩翻翻滾滾的排球和拉拉扯扯的美式足球。納珊成功地處理她的身份問題,發現班上同學難得問她私人生活,或是她為什麼以這種年紀上大學。
納珊的這項舉動,危險性不下於情報員,因為一旦被人識破,後果可能破壞一生學術。此外還有個更大問題,學術倫理和一般道統如何看待資深學者偽裝做學術研究?一九四○年代的「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與後來的電影「變蠅人」也有類似將自身置入研究的情境中。匿名麗貝嘉‧納珊在這本書中,是個真實的化身博士,冒著變蠅人的危險,從事人類學研究。
她也自問人類學界和學生能允許學者這樣做「化裝刺探」嗎?她算不算欺騙?學校贊同嗎?然而更重要的是,她發現了什麼?對美國大學和全球教育界,有什麼啟示和警惕?本書「後記」也花了不少篇幅來討論訪問者與被訪者之間的互相尊重關係。可以說是對讀者上了一堂人際、法律和人權的課程。
《當教授變成學生》是納珊與學生、教授和其他大學教職員的訪問、交談、互動,以逐日細心觀察為基礎,所撰寫的真實大學生活。是學生、家長、教授、大學行政人員、以及今日任何關懷高等教育的人都應該讀的書。
相關推薦
「麗貝嘉‧納珊運用她的人類學家素養,以及教授當學生的技巧,呈現給我們大學一年級新生體驗的特殊面貌。她還展現今日大學生面對學生文化,社會規範和大眾期望時,未經過濾的純潔看法。對當前所有從事大學教育者,這是本有深度的書。」
- 蘇珊 H. 莫菲 (康乃爾大學,學生與學術部,副校長)
「這是本讓人從頭到尾一口氣看完的書。主題牽涉廣泛,橫跨友誼和群體生活,地點涉及大學教室和宿舍生活,經驗涉及少數民族,以及人數日益增加的國際學生。麗貝嘉‧納珊遂以其熟練的人類學技巧來研究這個‘大學村’。當我們親近的這些大學生,參與這個社會的大團體時,老師、學生、父母會發現本書的光芒。」
- 露依絲葳絲 (作家,《同學會》作者)
「首先要說明,坊間極少這類書。作者住進學生宿舍,在教室上課,而她原本卻在此擔任多年教授,多麼神妙。從她註冊為新生開始,透過她的人類學者眼光,我們始得知學生世界有多不同,不是教授能想像的。我想,每個對大學生生活感興趣的人,不管是否為了學術,都會想看這本書,都會欣賞這本書。」
-瑪格麗特愛森哈特 (科羅拉多大學包德分校教授)
「這是本傑出的書,也是我在本世紀閱讀過最重要的書。我深知它會改變我的教課,激發我的寫作。麗貝嘉‧納珊隱藏自己,當個學生,住進校舍,可謂膽大心細,特別是她已是個五十來歲的人類學女教授。她那些同學的故事非常迷人,而這些學生是多麼疲憊,卻又聰明地適應著當前的制度………大學系所人員多半渾然不覺的世界。她的記載揭露,也解決了不少神秘的事,像為什麼有那麼多大學生不讀指定的書?為什麼星期五的課如同大難?什麼原因學生不願意參加課堂討論?為什麼多半大學生不願意在課外討論觀念問題?為什麼國際學生見到美國大學生的舉止那麼吃驚,甚至驚嚇?本書值得我們重視,在於它對於私人事物的道德療方,例如醉酒和欺騙。納珊擅於說故事,她描述人們努力在大學營造共同體之際學生方面的發展,讀來既有趣又傷感。《當教授變成學生》就是一本既有趣又傷感,令人眼前一亮,心智掙扎的好書。如果我知道作者是誰,我會熱切而誠懇地向她祝賀。」
-愛蜜麗托絲 (路易斯安納大學,作家)
「《當教授變成學生》觀察敏銳,充滿睿智,但是毫不做作。它可當成小說,參考書來讀。,尤可喜的,它說出許多我們關心的事。麗貝嘉‧納珊細心的實地調查訪問,以及精明地慎選主題研究,為美國大學生活帶來動人而重要的收益。」
-約翰范馬能 (麻省理工學院)
作者簡介:
麗貝嘉‧納珊(Rebekah Nathan),人類學博士,曾在美國海外廣泛進行實地研究工作。目前是“某大”人類學教授,教大學部及研究所課程,兼任大學畢業生輔導協調人。
章節試閱
1歡迎來到「某大」 Welcome to "AnyU"
十年前,我絕不會想到要寫一本書來談有關我在「某大」的大學生涯。我是個文化人類學者,畢生大部份的教書生涯是在美國之外的一個偏遠鄉村裡(不說明地點是為了尊重所有本書中的匿名者及更改姓名者)。我是個傳統的文化人類學者,花了好幾年時間,學習當地語言,瞭解另種文化習俗。我參與村裡的活動,觀察人們的生活。我加入村裡的組織,訪問當地人,還跟他們建立起長期的友誼。我記載下人類社會演進史,或是以描述的方式寫出一群人的逐日生活情況,希望能捕捉到造成這個社會生命及文化改變的個人動力。從美國的學校宿舍換到國外村莊生活,真是個大改變,然而也許如此反倒使我找到撰寫本書的一些理由。
我記載下人類社會演進史,或是以描述的方式寫出一群人的逐日生活情況,希望能捕捉到造成這個社會生命及文化改變的個人動力。從美國的學校宿舍換到國外村莊生活,真是個大改變,然而也許如此反倒使我找到撰寫本書的一些理由。在大學教了十五年書後,我發現我對學生越來越不解。為什麼那些大學生除了有必要解決的課業問題外,不再到我辦公室來聊聊?為什麼他們對我真誠邀請,在我指導下做些課外研究,沒有反應?為什麼在我進行大班級講課時,有些學生不做筆記?怎麼會有學生帶了整套午餐進教室,居然在上課時吃喝起來?這時班上有些學生還把頭或腳擱在書桌上,小睡起來,絲毫不覺得難為情?
我開始記下自己和同事的教課情形,努力找出是什麼原因造成現在學生的古怪行徑。只是我們自己不喜歡?還是今日的學生大不同了?他們的行為難道不是……在欺騙嗎?不講理嗎?不用功嗎?他們不是在自我擴張權利嗎?為什麼我們要去教室引導學生討論時,有種進診所拔牙的感受?為什麼學生不事先讀讀指定的課業,使得討論時大家能暢所欲言?可是儘管我們找出許多學生懶於讀書的原因,其中有些予人「啊,原來如此!」之悟,也儘管學業結束兩年後,我收到了學生的感激信,然而那段期間我記下的例子卻越積越多。
在當前瀰漫以學生為中心的大學校園裡,我對學生接受教育的態度,越發感到憂心。全國各地大學教授越來越常聽到,大學管理當局的口吻好像是企業經理,他們認為自己身處教育商場,在做商業競爭,學生都是顧客。大學的主持行政者,除了照顧學生住校、註冊入學,以及如何使學生感到親切舒適之外,他們改變了教書本質,背離了教育法則、課程安排,以及學位頒授的原則,代之以迎合學生口味,滿足他們的慾望,為的是吸引更多學生入學。在這種氣氛中,學生的需求是什麼,他們所瞭解的教育是怎樣的,反倒成為當前大學的重心了。
最後激勵我來做這項研究的是,我參加了期待已久的同事間非正式的旁聽課程。得到指導教師的允許後,我參加了電腦設計班及佛教班。這兩班的課程內容顯然大異其趣,吸引的也是不同興趣的學生。我按時間上課,做筆記,讀書。不過我跳過交作業,不參加測驗和評定學位的考試。我在以螺旋串繞的筆記本上寫筆記,舉手發問,坐在位子上靜候老師進入教室。我覺得這樣已足夠讓我看來像個大學生,即使是個老學生。讓我興奮的是,我開始聽到一些學生間的談話,有時他們把我也扯了進去:「噓 ……噓 ……,對不起,妳星期五來上課嗎?我不能來,要去滑雪。回來後能不能借一下妳的筆記?」「嗨,妳知道他說要在這次考試時怎麼做嗎?我聽了嚇呆了。」「在一個星期裡,又交報告又考試,妳覺得公平嗎?」
很快地,像穿過一層玻璃,能看到聽到一樣,我在掩護下被拉進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我以前的學生從不跟我分享。我聽到了週末聚會的種種事,哪個人在清晨三點到四點半,在醉醺醺之中寫完作業。我還聽到她們對班上的不平之鳴,為什麼我們該上那麼多自由研究的課?我做了學生,自然而然聽到那麼多的事,內容、形式、說話語調都不一樣。我不只發掘出來,也令我吃驚。我在大家談話之際,在筆記本上記下一句句片段,以免事後忘記。「我是說,妳在派對的歡樂場合,還會想到尼采嗎?」這是在我記載之中,首度有人認為哲學不合乎現代。
我明白,我又開始研究人類族群了,以我人類學者的經驗和眼光,利用學期之間放假的時候,以實際當學生的方式進行研究。美國大學校園裡的美國文化演變,是我此番研究的主題。大學生是我研究的對象,研究的方式是在自己所教的大學,回到大一,重當新生。我綜合性地列出研究大綱:以我所教的「某大」(姑隱其名)作為美國公立大學的例子,找出當前大學校園文化是什麼?現代美國大學生對教育的瞭解如何?他們希望從其中得到什麼?他們如何適應大學生活?大學真正教了他們什麼?
參與觀察
為了達成這項任務,我特別重視「親身參與」的觀察方式研究,而不僅是早先人類行為研究者,以自定的教授身份的方式訪問學生,或從旁觀察得到資料。因此我決定每天都融入其中,與他們一起上課,住在學生宿舍,像個老學生般和他們相處。莫法特的研究工作與我相近,但是並不真正上課。莫法特以學生身份參加一個星期的新生訓練後,就以教授的身份每週在學生宿舍住一晚,為期兩個學年。他的大量資料是基於教授與學生的關係。換言之,其真實性要倚賴學生的觀察,以及與學生的訪問對話內容。
二○○二年春季,我以高中畢業學歷證件,申請進入我現在所教的大學一年級生,我沒有特別選修主科。我很快被接受了,接到「歡迎加入某大」信函和一套資料,包括學雜費及財務支助途徑,膳食和住校計劃。所有大一新生必須參加暑期新生入學訓練,另外可以自由參加開學之前的激流泛舟,以及徒步登山旅行這類活動。
我在參考若干意見後,決定一旦得到大一學生證就參加所有項目。我像多半大一新生一樣,選擇住校,而且在校內包伙。我在選住校園中心的女生宿舍表上簽字,並且向校方請求住單間,結果我獲准單獨住一間,其他房間多半是十九歲到二十歲的女學生合住。我的宿舍不是給一年級新生住的,因為我和新生同住,太顯得格格不入,學校也不把年紀大的新入學者和一般新生混住。因此我住的是高年級生宿舍。這個區域住的多半是二年級,或更高年級生。
我交出參加為期兩天的新生訓練表格。新生訓練通常由父母陪伴,接受校方在開學前對大學課業和生活的介紹。我計劃好,開學前一週先搬進學校住,以便參加對新生和舊生返校所舉辦的「歡迎週」。我猶疑再三,最後還是撕下了我原有的教授停車證,收藏好我的教授證。我已準備妥當,回到大一,當個新生了。
我怎樣表現自己
我的大學生活計劃,自始就在我的真實身份以及杜撰身份間有著微妙的平衡。我依規定向學校列出所有我要讀的學科,以及想得到的學位。我在主要申請表上填寫了高中學歷,最後以引號註明「請見附加說明」。在另一張紙上我寫道,「為了順利申請入學,我希望僅使用我的高中學歷證件。我曾念過三所大學,但是我不希望引用這些學歷證件。如果您需要得到更多個人資料,請與我聯繫。」顯然,如果我以宣佈我是個大學教授的方式,走入大學生的世界,必定在執行我的計劃上有所偏失,達不到某些目標。
我要看到的是,大學生在大學裡的生活實況,即使是從「返校」的老學生眼裡。我要以大學生身份體驗大學生之間如何相處,以及他們和系科教職人員之間的關係,而不是以教授或研究人員的身份去進行。可是與此同時,我的人類學者的專業,卻能使我在扭曲自己進入我所研究的族群中時,有所擇取和提煉。在這兒說明一下「返校」這個詞,指的是原先想讀較高年級的班級,但是因故休學,現在重新回到學校繼續課業。「返校生」是「老學生」的委婉語,原本不是指重返大學讀書的大學生。
朋友和同事在這項計劃中,協助我對我的身份屬性問題解惑,他們問我:「如果有人問妳,靠什麼維生,妳怎麼回答?」「我能不能說,我沒工作,因為,我是學生?」我回答他們。我想,這是事實,雖然並非完全真實。「沒錯,」有個同事同意我,「但是如果他們問妳,以前是做什麼的?」「我就告訴他們,我做過很多事,事實上也真如此。我可以說,我現在還是個作家,因為我仍然在領最新一本書的版稅。」「但是,如果他們說,妳還做過什麼?」一名同事逼問。 「好吧,我希望他們不問我。不過我想,這時我必須告訴他們,我教書,也做研究。」
友繼續以學生的口吻問我:那麼妳的主科是什麼?「我沒選主科。」妳的家鄉在哪兒?「我在紐約出生長大。」那妳為什麼選擇進「某大」?「我要體驗大學生活,因為我是個作家,也是個學生,同時這所學校離我家近。此外,我喜歡這個鎮,附近的山,附近的環境。」我回答他們。這些全都不假。對我的身份就這樣演練下去,但是也引起眾說紛紜。每天的這類談話中沒有人直接問我,有關我今後的生活如何。只有一人例外,她比別人有見地。有兩個學生朋友向我吐露,想到像我年紀這樣大的女人住在學生宿舍,令她們感到難過。她們不想再問我問題,深怕會出現脫節曝光的情節。
我進行正式訪談時,永遠嚴守學術研究的規矩。我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執行大學生生活研究計劃的研究員。她將把研究結果出版,公諸於世。我把研究的目的和計劃的書面資料交給接受研究的對象,要求他們簽字,同意進行訪談。我的許多研究對象知道我是個研究員學生,不過我懷疑他們也許覺得,我的研究目標以及將研究結果出版的動機,只不過是個理想願景和學術上的誇大做法而已。在我日後撰寫的〈後記:道德倫理與人類學〉中,探討了我對這些項目研究的身份與公開的不同意見。
墜入深淵
我首次回去體驗大學生生活是在二○○二年六月。當時我去參加暑期新生入學訓練,每個新生都必須經過這段訓練。兩天密集的事務,包括在一棟新生宿舍住一晚。我們接到通知,每人都要帶睡袋、毛巾和枕頭進入學生宿舍。兩個人一間寢室,家長住的房間在大樓另一邊,與學生分開,不過他們有床。
當天我在早上八點鐘到達這棟巨大的學生宿舍大廳外,等候登記。我仔細想過該怎麼穿著,於是穿了身「舒適便裝」,粗布短褲,有領子的高爾夫衫和棒球帽(學校告訴我們要準備帽子),運動襪,以及一雙不太新的慢跑鞋。我揹著睡袋、枕頭和過夜的物品,尷尬地夾雜在新生行列中,等候登記和分派同寢室的新生。「對不起,女士。」服務台後一名紮著金黃馬尾巴的高年級女生,手指著遠處對我說,「家長請到那一邊。」「不是。」我笑著回答她:「我不是家長,我是新生。」我順著她的手指望去,一群家長在大廳的另一旁等候著。那些人裡面一半以上也穿著粗布短褲,或運動短裝,以及高爾夫領的便裝,還穿著運動襪和慢跑鞋。而我這邊的學生穿的卻是鬆垮的短褲或牛仔褲,無領的汗衫。態勢很明顯,我對文化的觸覺早已過時。
「哦,好抱歉唷!」那個辦事的女孩說,「妳原來是個新生,好酷!那妳和珍妮佛一間。」她指著站在我前面,也是紮著金黃馬尾巴的女生說。珍妮佛看來像是休士頓讀醫學健康類的大學生。我看見她的臉上很快掠過一絲不安,但是忍住那份不安,她很快對我微笑了下,打個招呼。我內心一陣歉疚,這個可憐的新生入學第一天同寢室友,就被抽中是個老女人。不過我覺得我們倆可以談談各自的學科,為什麼要選擇讀「某大」,以及這兩天的訓練項目。
接著兩天裡,我發現了不少過去對我自己的大學所不知道的事。我參加了伙食安排班,登記上學分課,知道如何取得助教指導、資訊服務,選修不同學費的指導課,以及如何安排作息時間。走廊裡有長排的桌椅,為新生提供校園裡的各種服務。作為新生,這一切讓我眼花撩亂;作為教授,我對眼前的三件事甚為驚奇──學生聯誼會和女生交誼會,不同的宗教組織團體,以及各種商業性質的服務,其中包括信用卡和電話服務等。這些事或團體主宰了新生校園,吸引了學生的注意。我是人類學家,又是個教授,但是對我學生的校園生活世界,竟然所知有限。
歡迎週:另一種文化的生活
八月間的一個星期六,學生獲准住進自己房間的第一天,我搬進了學校宿舍。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被稱為「歡迎週」。這個星期裡,學生可以選擇性地參加各種社交、運動項目,以及開學前的指導班。宿舍大廳的牆緣懸掛著活動日期表、宣傳圖,以及大型海報。宿舍門口貼了許多小紙條,歡迎同學參加大學各類競賽活動。
歡迎週的日程表上詳列著,兩點鐘起在校園某處舉辦足球班,三點半在校園北端商討活動教室的時間分配事宜,下午七點鐘在宿舍大廳舉行霜淇淋社交會,會中住宿助理(Resident Assistants,書中簡稱RA)會提醒住校生,下一波的活動有些什麼,並且鼓勵大家參加。RA已提早一個星期住進宿舍,為新生準備宿舍房間門上的名牌,設計活動,張貼海報圖表,以及到處佈置。RA是些高年級學生,他們得到免費宿舍和伙食,以及若干津貼。他們的工作是在分配的某些宿舍或某一層樓,為新生擔任資訊服務,他們也負責維持宿舍大樓裡的秩序和規定。在第一週介紹期間,RA像啦啦隊長一樣,指導並鼓勵新生「參與」。他們是唯一能叫出所有新生名字的人,「嗨,麗貝嘉,千萬別忘了今晚的電影,有免費爆米花哪!」
這樣設計是為了讓新生能選擇參加各種活動,結交新朋友,熟悉和習慣校園生活。我儘量多參加活動。歡迎週一開始,我就知道我的調查工作已經開始了。不過我絕沒有預期,這次大學生活的實地調查,會和我過去在海外偏遠鄉村裡進行的類似。我擔任了十四年大學系所的全職人員,又是系所委員會委員,也是幾所大學組織的委員,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大學院系瞭如指掌。我認為自己知道校園通往各處的捷徑,不論是地理還是行政方面,我都能應付裕如。可是令我吃驚的是,現在,搬進了學生宿舍,我居然發現自己失去了方向,就像我以前初次到海外的鄉村研究一樣。
第一週為新生安排參加的活動,遍及校園各角落。此時呈現在我面前的校園,外貌上完全是嶄新的場景。我當教授時,習慣把各班級都安排在校園南端我教的人類學大樓裡,或是我研究工作的附近。當我需要穿越到校園另一端時,我習慣把車子從這個院系的停車場,開到另一個院系的停車場。我總是由大樓最接近停車位置的門進去,而且以「逛街」式的眼光瀏覽一下校園風光。
學校多半的大樓都有「向街面」或「走廊面」。走廊面看出去的是綠地和樹,休息椅和野餐桌,其間有散步道和腳踏車道。我現在是學生,有學生停車證,但是只限於停在自己的宿舍附近停車場。如果要去校園另一端,必須靠步行或是搭校園裡的某路線巴士。對我來說,視野現在換新了,那些大樓和地理景觀全變了,不是我熟悉的,以致我常常無法辨明自己身在校園何處。那些大樓不是以前我熟悉的面貌,進入的門也不對了。我找不到書店在哪兒,也找不到診所,找不到國際學生中心,這些建築我以前開車去是很容易的事。尤有甚者,我常被通知去一些以前沒去過的地方;領取個人租用冰箱的倉庫,新生諮詢辦事處,旅館及餐廳營運系的研討室。這些地方絕非位於我家草坪上,垂手可得。
我變成了新生之一,那些高年級生總是耐心回答我,「坐三號巴士,在學生會站下。」或是,「沿著小徑走到底,大樓就在左邊。」我震驚於自己變得如此脆弱,和我原來的本質大相逕庭。我常常往不對的方向亂走,迷了路,只好叫住一名看起來熟悉方向的學生來指點迷津。我真真正正覺得自己是個大一新生,或者至少是個外來訪客。
我重回大一生活持續了一學年。本書的主幹就是述說這一年裡,我所參與和觀察到的大學生生活,包括我自己的經歷和別人的。然而我必須在此說明一件事。我以中年婦女回到大一的個人體驗,無法直接說明「大學生經驗談」。我不是十八歲,不屬於那種推推拉拉打鬧的族群,也不是那種私密性的社交活動一員。我從海外得到的人類學經驗是,人絕不可能真正歸屬於「當地人」,也無法期望個人在當地經驗就能夠代表土生土長的文化。然而同時,也就是這種在村子裡生活的經驗,提供了相當的優勢和內涵,使研究者能問出深入的問題,而且深刻瞭解對方的回答。就是基於這種體認,我希望能完成「重返新鮮人」的研究工作。
此後的篇章,內容來自不同類型的資料。除了基於全國教育的研究,以及對於我的大學本身的調查外,我還對美國大學生和國際學生進行了四十個正式訪談,兩組研究(一組對大一新生,一組對非新生),以及若干「小型研究」,包括學生對時間分配方面的活動日記記載,以及在學生用餐區誰和誰一起吃飯(以性別和可以察覺出的族群為對象)的五個月觀察研究,以及住校和通學的研究,學生宿舍裡所有正式活動,詳加說明內容的每週佈告,以及非正式的日常談話題材。
我雖然全心全意做個親自參與的觀察者,然而就像一般大一新生開始大學第一個學期一樣,我牢記各種規定,和同學聚會,適應住校生活,參與學生社團,發掘什麼事物有助於我的學術研究。一週裡每天每晚我都在宿舍和校園裡,上滿這個系的五門選課。我像別的學生一樣,只偶爾在週末晚上或是假日「返家」。我很細心地從很廣的範圍來挑選課程,從現代語言到商業和機械。我選我不認識的教授,上他們的課。因為我認為,我不認識他們,他們也不會知道我是誰。我的名字列在那些還沒有決定未來主修科目的新生名單中。
就像多半實地考察的研究學者一樣,我先研究我住的宿舍地理環境,「普查」各區域住戶的性質。我列下牆上或佈告欄上的所有通知、廣告,以及正式貼在浴室的消息和宣傳單內容。我也記下個別寢室門上外側張貼的留言、小物品,以及一些裝飾。我記載下宿舍開會、商量或發生的事情,我也逐日隨手記下,這些瑣事中我與別人對話的內容、觀察所得,以及個人的看法和感觸。
第二學期,我增加了對學生的正式訪談次數,以及小型觀察研究。因此我默默地把我上的課減少到只有兩科,以容納我的實際研究課題。這段期間,我每星期總有幾個晚上回到自己家,坐在電腦前工作。早上上完了課,回到宿舍,打開電腦,檢視昨晚在家裡做的研究,並加以增添和修正。在學期前兩季裡,我自願擔任這層樓回答「女生浴廁文章」的工作。女生浴室和廁所「文章」,是大學女生傳統的「塗鴉式」行為。她們在廁所牆上黏貼小紙條,列出黏貼者的問題,並且附上一些小張的白紙和鉛筆。上浴廁的人以無記名的方式,寫出自己的看法,或提出辯駁,也有的再提出新問題。這樣做,成為學生對事物或關心話題評論和互動的不絕來源。
本書還有個大目標,就是記錄「大學生生活經驗」。這件事如果想要以嚴格要求美國大學的統計數字方式來得到,是不可能的。因為任何學校的情況都不能適用於其他學校,即使在同一個學校內,一組調查或訪問的內容,也不能完全代表別的人。舉最近一次教育調查為例,統計了美國四千一百所合格院校進修學士學位的高年級生,大家的大學生經驗各式各樣,不盡相同。這樣的不同,研究一所學校,一個學生的經驗,如何能代表大學生生活?
「某大」一直享有大學教育的美譽,不論是課堂上的教授(不是指剛加入教職的大學畢業生),還是校園和住宿,以及與一般「大型大學」比起來略小的班級。「某大」每年吸引了大量新生,他們入學前的成績在各自中學裡都是前百分之二十五的學生。「某大」可以說在美國大學系統裡,屬非常結實的中等大學,在美國大學生中該是很知名的大學,雖然大學生的生活未盡相同。我謹慎選擇,不參加那些進一步教育選修的主科,也就是通訊教育,或是全職工作者選修的通勤半讀課程。
在採用「某大」案例時,我要向讀者說幾句人類學者該說的話。人類學者認為,任何文化最自然的本質,就是互相學習,以及共同分享。我住在海外村落時,每個人都能告訴你,什麼是播種的時節,就如同每個美國人都會告訴你,聽到國歌請起立一樣。雖然某些層面的文化互有爭議,例如墮胎應否合法化?英語是否應該定為美國官方語言?同性戀可否結婚?等等,這些問題爭議的本身往往是文化背景的認同問題。因此,我能寫出一本完全以文化變化中的村落一個家庭為故事背景的書,卻發現這個國家的人能從書中體會他們自己的故事(他們之中有些人寫信告訴我)。
美國公立大學院校的情形完全一樣。儘管大學科系和學生本質極為相異,但是幾乎所有美國大學生都能證實以下幾點:很多學生慣於睡到中午甚至更晚才起床;同學總是避免星期五去上課;大教室的第一排座位總是到最後才坐滿;不滿十八歲的學生私下喝酒。當然也有學生起得早,少數人願意選第一排坐,未成年的學生也有的絕不喝酒。但是他們可能明白,他們是在輕視,或對抗一般大學生的習俗。然而,他們自己也在扮演著大學生文化的一部份角色。
由於我在大學裡,參與、觀察、訪談,每天朝夕相處得來的體驗,使我得以把目標定位於研究大學文化。我把所見種種融會貫通,從幾個制高點加以評論,包括以教授的觀點、外國學生的看法,以及對全國大學生活調查結果的分析。然而對我的分析研究的最後驗收,是大學生。他們才能決定,對本書描述有關他們的大學生活和他們的世界,是否該加以認同。
1歡迎來到「某大」 Welcome to "AnyU" 十年前,我絕不會想到要寫一本書來談有關我在「某大」的大學生涯。我是個文化人類學者,畢生大部份的教書生涯是在美國之外的一個偏遠鄉村裡(不說明地點是為了尊重所有本書中的匿名者及更改姓名者)。我是個傳統的文化人類學者,花了好幾年時間,學習當地語言,瞭解另種文化習俗。我參與村裡的活動,觀察人們的生活。我加入村裡的組織,訪問當地人,還跟他們建立起長期的友誼。我記載下人類社會演進史,或是以描述的方式寫出一群人的逐日生活情況,希望能捕捉到造成這個社會生命及文化改變的個人動力...

 2 則評論
2 則評論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