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能有幾次重新來過的機會?
狄妮被綁架後展開了她的第二段人生,
而這場綁架事件卻開啟了無限機會,希望花兒將永遠綻放……
Liberoooooo!這個世界實在是太美好了!Viva!Viva!
十三歲的狄妮(全名是:多門妮卡.珊多利亞.頓恩)從小就跟著擁有流浪性格的爸爸到處尋找「機會」。當老爸在鎮上找不到工作時,便往其他地方找差事去,這時老媽便開始打包,全家人等著老爸打電話來說:「我找到一個很棒的地方了!你們看了就會知道有多棒!」
就這樣,狄妮一家人待過的地方連十根手指都不夠數。東遷西搬的結果是,狄妮的哥哥到處惹事:戳破路邊的汽車輪胎、吸大麻、燒毀穀倉、偷車……各種壞事都插一腳);姊姊在全家人毫不知情的狀況下結婚懷孕生子,而狄妮自己連乘法和除法都不會,在各地的學校裡永遠是「那個新來的」。一家人陷入亂七八糟的生活之中,狄妮找不到生活重心和目標,認為自己是個毫無長處的小不點。
但是狄妮作夢也沒想到,自己第二段嶄新的人生竟然是在被兩個陌生人綁架後展開,而這場綁架事件卻為她開啟了無限機會……
從沒搭機出過國的狄妮突然間來到了全新的環境——瑞士的盧加諾——被不同的語言、迥異的文化、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所包圍——總是精神奕奕,喊著liberoooooo,做出瘋狂舉動的古瑞斯、不停抱怨現況的萊拉、英文不流利卻能創造出最貼切字眼的啟介……。正當狄妮一方面懷疑自己會不會被囚禁在此,另一方面又夾在新舊生活之間奮力掙扎時,她發現自己漸漸有了改變……
一向封閉在泡泡世界裡的狄妮該如何擁抱這個美好的「花開機會」呢?
(本書節錄部分英文原文)
作者簡介:
莎朗.克里奇(Sharon Creech)
美國童書作家,一九四五年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南歐幾里德,在一個兄弟姊妹眾多的熱鬧家庭裡長大。莎朗.克里奇多次獲文學大獎:Walk Two Moons(《印地安人的麂皮靴》,維京出版社)獲一九九五年紐伯瑞金牌獎、The Wanderer(《少女蘇菲的航海故事》,維京出版社)獲二○○一年紐伯瑞銀牌獎、Ruby Holler獲2002年卡內基文學獎,其他尚有Heartbeat、Absolutely Normal Chaos等作品。
莎朗.克里奇的創作和自身環境及經歷密不可分,多以尋找自我價值的青少年為主角,並從第一人稱的敘述手法來說故事,讓故事本身更能貼近青少年讀者。其小說往往在探討人生中嚴肅的課題,但卻以幽默筆調來緩和現實的殘酷;其寫作特色是使用大量的擬聲詞、誇大的用語和口語字眼。
《花兒都開了》的創作構想源自莎朗.克里奇曾在瑞士的一所美國學校任教兩年的所見所聞。當時莎朗.克里奇在該校教英文,先生擔任學校的校長,兩個孩子就在此校就讀。莎朗全家人都深深愛上瑞士,因此在任教的最後一年,她寫下《花兒都開了》,永遠將瑞士的景色與人們烙印在心中。
莎朗.克里奇網站:www.sharoncreech.com
譯者簡介:
趙曉南
文字工作者,現任出版社編輯,另譯有數本童書。認為閱讀同旅行,能到達世界的彼端、超越想像的極限。希望讀者翻開《花兒都開了》之後,除了跟著主角狄妮登上瑞士高山之外,更能掌握住生命當中處處的「花開機會」。
章節試閱
當我被兩個完全陌生的人綁架之後,我就展開了我的第二段人生。我媽不但協助這次的綁架計畫,還直說我太誇張了。這兩個陌生人不能說是完全的陌生,因為我以前見過他們兩次,他們是我媽的妹妹和妹夫:珊蒂阿姨和麥克斯姨丈。當時他們突然衝到我們居住的新墨西哥州裡的小山城,跟我媽談了一整晚。第二天早上,阿姨和姨丈強行要我上他們的車子。(好啦,他們其實並不是「強行」要我跟他們走,可是從頭到尾沒半個人問過我對這次綁架計畫的意見。)他們帶著我和我的一只箱子,一路開車到阿布奎基(Albuquerque)的機場……
***
我的第一段人生是跟我的媽媽、哥哥克里哥、姊姊史黛拉,加上如果沒開車上路就會待在家裡的老爸住在一起。我爸是個卡車司機,有時候又是修理技工或摘果工人或是油漆工。他叫自己是「什麼都會的傑克」(不要懷疑,傑克是他的真名),但有時候我們住的鎮上並沒有雜工可以做,他只好去別的地方找差事。這時我媽便會開始打包,全家人等著老爸打電話來通知我們跟他會合的時間。
他總是說:「我找到一個很棒的地方了!你們看了就會知道有多棒!」
每次只要我們一搬家,剩下的箱子不是越來越多,反而是越來越少。我媽會說:「狄妮,妳真的需要那些東西嗎?它們不過是東西罷了,別帶了啦!」
一直到我十二歲的時候,我們已經跟著老爸從肯塔基州到維吉尼亞州,再到北卡羅萊納州、田納西州、俄亥俄州、印第安那州、威斯康辛州、奧克拉荷馬州、奧勒岡州、德克薩斯州、加利福尼亞州,最後落腳新墨西哥州。我的個人物品僅剛好塞進一只箱子。有時候我們會住在嘈雜的市中心裡,但大多時候老爸會為大夥兒找個歪斜的屋子,而這棟房屋會坐落在一個荒涼小鎮旁的荒涼道路上。
我媽以前在城市裡長大,而我爸則是個鄉下男孩;就我有記憶以來,我媽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試著忘記自己曾經是個城市女孩。有那麼幾次,我們剛好住在市中心,她似乎顯露出回家的感覺,而且是她真正的家、永遠的家。她可以在辦公室或是設計室裡工作,而不再只是鎮上的小餐廳。她知道怎麼搭乘公車、如何在人潮當中穿梭來去,而且她似乎聽不到喇叭、警報器和鑽洞機發出的惱人噪音。
但這些事卻讓我老爸抓狂。「我知道這裡有工作,」他說,「但這裡到處都是人跟車輛,只要跨進街道一步,就好像會被宰掉。這不是養孩子的好地方。」
老爸只要說了類似這樣的話,我媽就會變得超級安靜;而很快地,老爸就會出發尋找更適合居住的地方,然後我媽就會再度開始打包。我姊史黛拉發展出一套理論,那就是老爸不停地帶著我們搬家,這樣我媽的家人就找不到我們——他不信任她任何一個兄弟姊妹,當然他也不信任自己的。他認為他們總是擺出一副高姿態,想要說服老媽搬回自己的出生地紐約。他說他們瞧不起我們。
有一次,大概是我七、八歲的時候吧,當時我們全家住在威斯康辛州——嗯,不對,也許應該是在奧克拉荷馬州——或是有可能在阿肯薩斯州(我剛剛忘了把阿肯薩斯州算在內;我確信我們在那住了六個月),有天我放學回來看到一個纖細、將滿頭白髮向後梳攏成髻的女士坐在我們家的客廳裡。我還來不及脫掉外套,她渾身充滿香水味把我抱個滿懷,不斷地叫我carissima(義:達令)或是「甜心小貓咪」。
「我才不是什麼小貓咪。」我邊說邊從側門溜出去。克里哥在外頭對著想像出來的籃框投著籃球。
「裡面有個女士。」我說。
克里哥瞄準目標,以漂亮的弧線射出一記球,然後看著球彈出車庫的界線滾到隔壁去。「妳白痴啊,」他說,「她才不是什麼女士,她是妳的費歐蕾麗外婆。」
那天晚上在我上床後,隔著廚房和側邊小房間的中間布簾聽到她們爭執不休。老爸出去了——他只看了一眼我們的外婆女士就閃人了,甚至連招呼都沒打。所以在廚房裡爭執的人是我媽和外婆。
我媽告訴外婆老爸多有辦法,什麼事都可以做,而我們過的生活有多富裕。睡在我隔壁床的史黛拉傳來聲音:「媽真是愛作夢。」
廚房裡的外婆說:「富裕?這叫做富裕的人生?」
我媽更激動了,她說:「媽,錢不代表一切。」
「那妳又為什麼放任他替兒子取『克里哥』這樣的名字?這算是哪門子的名字啊?聽起來像是在穀倉裡被養大似的。」
我爸媽以前達成一項協議——男孩由老爸命名,女孩就由老媽命名。老爸告訴我,「克里哥」是以他們曾經住過的地方旁邊有條小溪來命名的(克里哥唸起來就和英文的「creek(小溪)」發音一樣)。有一次,當我寫學校作業時用了克里哥這個字,老師不但打了個叉,還在上面更正為「小溪」(creek),她說沒有克里哥這個字。我沒把這件事告訴老爸,當然更沒告訴克里哥。
我媽為第一個女孩(就是我姊)命名為史黛拉.瑪麗亞。後來我出生時,我猜她一定是想了很久,因為她把我的名字取為「多門妮卡.珊多利亞.頓恩」(Domenica Santolina Doone),意思是「星期天—南方—木頭—河流」。我出生在星期天(我媽說這是種恩賜),那時候我們住在南方,依傍著樹林和河流。我的名字若以義大利語發音會是:多—門—依—庫。多門妮卡.珊多利亞.頓恩——唸起來很不順,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叫我狄妮。
廚房裡費歐蕾麗外婆的火氣逐漸升高。「妳應該替自己想想,」她說,「應該替孩子想想,他們可以去讀一間像妳妹工作的學校。妳的丈夫需要一份像樣的工作——」
「他有一份像樣的工作——」
「每六個月就換一次?Basta!(義:夠了!)」外婆說,「他為什麼一份工作做不到六個月?好啦,他到底在做什麼?他為什麼不去上大學,這樣他就可以得到一份像樣的工作啊?妳怎麼能在這堆亂七八糟的事情當中過生活?」
「他在找一個恰當的機會,」我媽說,「他什麼事都可以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他只是需要休息——」
外婆只要一開口,就會再度提高音量;這次她像公牛一樣大聲怒吼:「休息?É ridicolo!(義:荒謬!)如果他不去弄個大學文憑,他又怎麼能夠休息啊?妳回答我!」
「又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大學文憑。」我媽說。
「當我們來到這個國家時,我和妳爸連一個英文字都不懂,但是你們各個都有上大學——」
史黛拉朝我丟了個枕頭過來。「狄妮,不要聽了!」她說,「把頭蒙在枕頭下,睡覺吧!」
不過這個枕頭阻絕不了費歐蕾麗外婆的聲音,她繼續喋喋不休。「那妳自己呢?」外婆對我媽說,「看看妳,妳是個受過良好訓練的藝術家,我打賭妳甚至沒有一枝屬於自己的畫筆。」
「我有畫畫。」我媽說。
「像是什麼?畫牆壁?油漆剝落的牆壁?Basta!妳應該跟妳妹妹好好談——」
隔天早上費歐蕾麗外婆離開了,老爸也是,他去找新的地方,因為他聽說有個好機會。
就這樣我們跟著老爸四處遷移,從一個機會換到下一個機會,而克里哥同時也惹上越來越多的麻煩。克里哥說這不是他的錯,而是他在我們所到之處,都會認識教他做壞事的朋友。根據克里哥的說法,有幾個奧克拉荷馬州的男孩要他對學校的窗戶投擲石頭;幾個奧勒岡州的男孩要他戳破輪胎;幾個德克薩斯州的男孩要他抽大麻;幾個加利福尼亞州的男孩要他燒毀一座穀倉;幾個新墨西哥州的男孩要他偷一輛車。
每一次我們搬家,老爸就會告訴他:「你可以重新來過了。」
而每一次我們搬家,史黛拉就會變得越來越沉默。每次我們才搬到一個鎮上不到一星期的時間,整天有不同的男孩來敲我家的門說想要見她。什麼樣的男孩都有:粗獷強壯的、安靜內向的、書呆子型的、酷帥的型男等。
在加利福尼亞州,那時她十六歲,在和一個姊妹淘度過一個星期之後(她是這樣說的啦),有天晚上她回家說她結婚了。
「不,妳不可以這樣做。」老爸說。
「好,那我不結婚。」她說完後去睡覺。
她告訴我她已經嫁給一個海軍陸戰隊的士兵,還給我看一紙結婚證書。這個海軍陸戰隊的士兵現在出海執行任務去了。之後她開始一直吃個不停,整個人變得越來越圓、越來越腫。在我們到達新墨西哥州的小山城後,有天晚上她把我叫醒說:「去叫媽,快點叫她過來。」
史黛拉有了娃娃。老爸出門在外,克里哥進了監獄,而現在史黛拉卻有了娃娃。
那是我第一段人生度過的最後一個星期。
當我被兩個完全陌生的人綁架之後,我就展開了我的第二段人生。我媽不但協助這次的綁架計畫,還直說我太誇張了。這兩個陌生人不能說是完全的陌生,因為我以前見過他們兩次,他們是我媽的妹妹和妹夫:珊蒂阿姨和麥克斯姨丈。當時他們突然衝到我們居住的新墨西哥州裡的小山城,跟我媽談了一整晚。第二天早上,阿姨和姨丈強行要我上他們的車子。(好啦,他們其實並不是「強行」要我跟他們走,可是從頭到尾沒半個人問過我對這次綁架計畫的意見。)他們帶著我和我的一只箱子,一路開車到阿布奎基(Albuquerque)的機場……
***
我的第一段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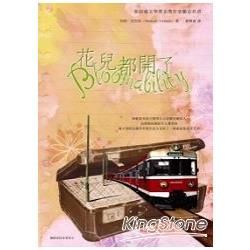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