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國家
也是一個逼人即使會死也要去愛的國家
陳雪羅毓嘉感動推薦
愛上同性是罪,喪失記憶是罰,
反抗這個荒唐暴虐的國家,是她的戰鬥──
但願這本書能夠陪伴所有對愛迷惘、因為孤獨而顫抖的人──中山可穗
由於經濟低迷、少子化,日本被「愛國黨」獨大把持,政府為獎勵生育,提供生育大量嬰兒的夫婦優渥的稅制補助,而未生育的夫婦、墮胎、單身者及同性戀,則遭到恐怖的歧視。瘋狂的國民更把景氣惡劣的憤怒,歸咎於同性戀亡國的論點,出現大量反同志遊行、新納粹組織大規模掃蕩同志,政府也設立了同性戀收容所,以各種殘酷不人道的方式來強行「矯正」男女同志。
同性戀矯正中心是建在海邊懸崖上一座名副其實的監獄,男女同志被湊對關在牢房中,兩人若發展出感情、生下小孩才能「治癒」出獄。收容所的生存條件比監獄還要惡劣,所謂「治療」,則是以粗暴的電擊來虐待囚犯,不堪而死的人會被摘下器官運至黑市販賣,試圖逃獄的犯人不是墜落懸崖,就是被當成獵物擊斃。
她被人救醒的時候在京都一間偏僻的墓園,緊緊抱著墓碑,失去了記憶。
曾是專門飾演美少年的天才演員,歷經生離死別、失憶衝擊、素人參選、性向矯正、朝聖巡禮、絕食抗議等磨難,那段痛苦又純真的愛情到底為何落得如此下場?她該如何找回記憶中的戀人?而這個無藥可救的政權,有辦法顛覆嗎?
作者簡介:
中山可穗
一九六〇年生。一九九三年以《駝背的王子》出道。一九九五年以《天使之骨》獲得朝日新人文學獎,二〇〇一年以《直到白玫瑰的深淵》獲得山本周五郎獎,二〇〇二年以《花伽藍》入圍直木獎。著有《情感教育》、《馬拉喀什殉情記》、《弱法師》、《科赫爾》、《西貢探戈咖啡館》、《悲歌》等。她以敏銳的文筆、濃厚的抒情性、天馬行空的獨特夢幻風格,令讀者總是熱切期待她推出新作。
譯者簡介:
張智淵
台北人,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課程修畢,從事翻譯十餘年,譯有《艾比斯之夢》、《利休之死》、《千兩花嫁》、《何者》等五十餘本小說,以及《這樣學習改變了我》、《活化大腦生活術》、《差一點分手,更幸福》,現為專職譯者。
E-mail:akiracat@seed.net.tw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日本讀者淚崩好評:
──生來第一次,我邊哭邊看完一本書。
──書中的一字一句都刺痛我的心,明明痛苦不已,又渴望繼續看下去。讀的時候,我甚至錯覺自己變成王寺滿或久美子,深深愛上了對方。這本書描寫同志被迫害的架空未來,我想,對少數族群來說,恐怕常常是內心深處,最害怕成真的陰影吧!如果不喜歡同志,更該看看這本書,因為它寫出了最純粹的愛。
──這本書融合了所有的元素,關於愛、宗教、政治、旅程與世界,精緻而龐大的鉅作。書中沒有任何多餘的字句,滿滿都是直擊胸口的美麗台詞,才讀完前一百頁,我就在電車裡哭了。
──這本書,從書名就以非比尋常的魔力深深吸引我,讀的時候,彷彿場景一一呈現在面前,愛、苦澀、憤怒、糾纏、迷惘、絕望、孤獨、瘋狂、微小的希望、純粹、熱情……這些感情化為荊棘,藤蔓一樣纏上來,遇到殘酷的場景,甚至動用了五感。隨著人物登場,內心深處被這些不明所以的感情輪番襲擊,甚至好幾次不禁鼻酸。
──小心翼翼地讀著作者不斷琢磨的精緻文字,唯恐錯過一字一句。就如同作者描繪主角王寺滿的成長,這次的作品也增加了深度和豐富驚豔的表現,令我目眩神迷。厚實的表達貫串頭尾,正如作者所說:「這本書成為遺作我也無悔」,《愛之國》絕對是中山可穗的代表作。
──這本書絕對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對我來說,是獨一無二的讀書體驗。
──好久沒看到這種重量級小說了,讀完非常滿足。書中描寫了四國巡禮、同性戀收容所、朝聖之路等相當殘酷的場景,但是一旦開始閱讀,就深深陷入作者的世界無法抽身。我認為這本書已經超越了愛情小說的領域,和恐同與偏見奮戰不息。看完之後,我也為書中阿靜的愛情哭了。
名人推薦:日本讀者淚崩好評:
──生來第一次,我邊哭邊看完一本書。
──書中的一字一句都刺痛我的心,明明痛苦不已,又渴望繼續看下去。讀的時候,我甚至錯覺自己變成王寺滿或久美子,深深愛上了對方。這本書描寫同志被迫害的架空未來,我想,對少數族群來說,恐怕常常是內心深處,最害怕成真的陰影吧!如果不喜歡同志,更該看看這本書,因為它寫出了最純粹的愛。
──這本書融合了所有的元素,關於愛、宗教、政治、旅程與世界,精緻而龐大的鉅作。書中沒有任何多餘的字句,滿滿都是直擊胸口的美麗台詞,才讀完前一百頁,我就在電車...
章節試閱
第二章、探戈課
2
在收容所的生活,區分成治療時間、勞動時間和反省時間。
治療時間會被帶到治療室,和醫師一對一,先進行諮詢。患者在那裡被測量自己的同性戀程度,從輕度分類至重度。被視為輕度至中度的患者,會接受比較柔性的心理療法,而對於重度患者,則會採用厭惡療法這種有點粗暴的心理療法。這是從前實際在美國進行的治療法之一,讓患者看同性的裸體照片之後,給予電擊或催吐劑。王寺滿在諮詢中,每次都被判定為重度,只得反覆徹底進行這種療法。
每當電極安裝在束縛器,電流流經腦中,王寺滿就會一點一點地確實感覺到,自己的人性在逐漸流失。腦中的老鼠似乎逐漸變肥,一點點將自己吃光,自己變成老鼠,接受著活體實驗。一旦電流流過,麻痺般的悶痛就會在腦內繼續一整天,受到強烈的倦怠感、無力感和嘔吐感折磨。她心想:假如這種事情一直持續,也難怪會被逼到只能自殺或發瘋的地步。即使回到房裡,被電擊之後,也吃不下任何東西,更無法好好睡覺。哲太郎焦急地注視著只能神情恍惚地蹲著的她。
「妳真令人焦急。只要表現得更機靈一點,妥善應付不就得了。詢諮的時候,妳說話太老實了。掩飾的方法很多吧?唯獨電擊,不巧妙地避免不行啦。」
「我不知道怎麼掩飾。不管怎麼回答,那個院長都看穿了我是本性難移的女同志。」
「起碼得吃東西才行。如果不補充體力,沒辦法在這裡存活的。」
「這裡的餐點不合我的胃口。我想,連羅馬時代的奴隸都吃不完吧。」
「別說是奴隸了,我也覺得難吃到連快餓死的馬都會吃剩,但是現在不是挑剔口感的時候吧?要是營養失調,妳馬上就會死掉喔。」
「我不認為這裡的餐點有營養可言。」
「我說妳啊,妳如果不吃,胃就會不斷縮小,日子久了,連大便都出不來。那樣的話,妳就真的慘了。不管有沒有營養,也得硬逼自己吃。」
在這裡,只會供應像是從某個團膳中心運過來的剩飯般的餐點。肉片只有油脂多的薄邊料,魚只有魚骨的部分,米摻了莫名其妙的雜穀,麵包像是紙拉門或黏土一樣。份量只有成人勉強不會餓死的程度,調味是只使用化學調味料的噁心味道。而且所有食物都是不新鮮、接近腐壞的狀態。甚至令人覺得供餐的單位故意只挑選快要過期的食材,狠狠地殺價購買。天氣如此炎熱,這些食物在沒有冷氣的地方烹調,又放在衛生狀態極差的地方,吃了一定會腹瀉。房內籠罩在臭味之中,令她感到非常難堪。
「妳不用在意。我拉的屎也很臭。」哲太郎如此說道,但她沒有神經粗到滿不在意的地步。如果不是腹瀉,就是連續便祕,無論是進食或排泄,她都變得非常厭惡。
「習慣餐點和廁所是這裡的第一道難關。久而久之,妳連這種事也不會在意了。人真是堅強。」
勞動時間會被放到建築物外面,在隔壁的用地被迫從事另一棟設施的興建工程。院方從未說明,但是哲太郎說,那裡是監禁政治犯、重度精神病患和沒有治癒希望的遺傳性疾病患者的設施。是被視為所謂「不值得生存的生命」的最終目的地,也是用來緩慢地肅清他們的地方,據說一旦進入那裡,就再也出不來了。
「比起被關進那裡的人們,我們或許還算好的了。」
「這有什麼差別呢?都一樣。沒有治癒的同性戀者遲早會被關進那裡。」
除了沐浴日在走廊上擦肩而過之外,就只有在勞動時間,能看到哲太郎之外的其他囚犯。男女囚犯合計三十人至五十人左右,工作人數會依日子而有所不同。雖然總是被獄卒監視,囚犯之間禁止交談,但是也有人趁獄卒不注意向王寺滿搭話,或者露骨地對她賣弄美色。假如遭到男性獄卒盤問,避免不了被毒打一頓,所以王寺滿會謹慎地避免。雖然是體力活,但是她覺得在看得見大海的戶外,一面感受流動的風,一面活動身體,起碼比那種令人鬱悶的治療好太多了。但是,一旦知道眾人現在正在興建的工程用途,她就不禁心生罪惡感。儘管不是自願,但還是被迫參與了國家的惡行。
反省時間則是被帶去另一個房間,被迫針對至今所有的性衝動懺悔,寫反省文。只有這個時候,能夠被當成一個真正的人看待。負責這個活動的是副院長,他比院長好說話許多,是個四十多歲的長臉男人。他跟其他醫師們一樣,幾乎不會展現情緒,面無表情,但是完全不會威嚇總是交出白紙的王寺滿,光是努力平靜地說話,試圖展現耐心的態度,就可說是較有良心了。她心想:如果院長是鞭子,這個副院長應該是扮演著胡蘿蔔的角色。
「又是白紙啊?妳也真頑強。」
「因為我沒有義務向別人坦誠自己內心的性衝動,更沒有什麼好反省的。」
「我們只是想幫助妳而已。聽說妳今天也接受了厭惡療法,不是嗎?如果接受太多電擊,恐怕會對大腦留下嚴重的損傷。妳如果稍微展現反省的態度,我就能替妳勸告院長,不要對妳進行電擊療法。」
「反正我的大腦是塊到處都是洞的起司。」
「關於妳的記憶障礙,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也想助妳一臂之力。」
「既然如此,讓我看我的表演影片。」
「院長還沒同意。那個影片相當刺激。除了兩個女人的親吻戲之外,還有猥褻的舞蹈和背面的裸露。就某種層面來說,Chiropractic前期的戲劇遠比A片更危險。不過,激烈程度在後期稍微減輕,增加了藝術性。也就是說,妳慢慢成熟了。」
「這麼說來,你們也有後期的影片囉?」
「如果是Chiropractic的戲劇,前後期所有作品的影片都保管在這裡。因為作為不好的同志文化範本、頹廢藝術的樣本,那些是最適合放進潘朵拉盒子的素材。」
「所以將那種素材全部集中在這裡,連同創作者一併關進潘朵拉的盒子,蓋上蓋子嗎?」
「沒錯。但是,其中摻雜了可能成為人類遺產的東西,所以這正是令人煩惱的根源。不得不承認,同性戀者經常擁有優異的天分,我覺得真是可惜。比方說,妳也是其中之一。為何明明是女人,但是非扮演少年不可呢?明明劇團裡有其他男演員。根據目前為止的鑑定結果,妳不是性別認同障礙,但是搞不懂妳為何只扮演少年的角色。」
「就算你問我,我也不知道。」
「妳的戲劇沒有那麼煽情,假如妳以女演員的身分站在舞台上,和男演員演出親熱戲的話,就一點問題也沒有了。假如妳反省、懺悔,保證妳今後會以女演員的身分站在舞台上的話,或許我可以幫助妳。」
假如聽到院長說一樣的話,王寺滿應該會朝他吐口水,但是從這個副院長的嗓音中,能夠感覺到幾分誠懇的溫暖。但是,她覺得那說不定是因為連日的電擊,麻痺了判斷力的緣故。只要不必接受那種電擊,或許什麼謊言都說得出來,自己變得懦弱,她感到害怕。
「我覺得你在這裡的工作人員當中,是感覺比較正常的人,所以我問你,你真的相信同性戀能夠治癒嗎?你真的認為同性戀是精神障礙?」
副院長慎重地保留回答,沒說「是」,也沒說「不是」。取而代之地,他抱起雙臂,以深思熟慮的表情注視著她。
「如果是你這種知識分子,應該動動腦就會知道。同性戀在日本,自古以來就是一種文化。在武士社會中,男色是男人的嗜好,而僧侶、武士、朝臣也無一例外地擁有心愛的侍童。完全否定這種日本人特有的豐富精神性,豈不野蠻?」
「我知道妳想說什麼。除了日本之外,同性戀在歐洲也是一種傳統文化,延續至今。據說達文西《蒙娜麗莎》的模特兒不是女人,而是他心愛的少年,而基督教禁止同性戀,但是梵蒂岡的戀童之愛絕對不會消失。假如不是這個國家的少子化變得如此嚴重,同性戀應該也會是一種被人接納的文化。妳覺得為何日本女性不生小孩?因為生了也沒有能夠好好養育小孩的經濟基礎。日本人不像亞洲和非洲一樣,即使國家貧窮,人民也能一個接一個,堅韌地生小孩。相較於亞洲和非洲各國,日本花費太多錢在住宅和教育上。一旦擁有世界第一的經濟力,食髓知味,就再也不能降低等級了。」
「不要轉移話題。同性戀和少子化無關。」
「不,有關。日本從前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擁有這麼多憂慮、自暴自棄的年輕人。找不到好工作、無法成家的年輕人,變成了遠超出政府想像的暴徒。如果不增加人民的數量,這個國家不久就會破產。同性戀的煽動活動替少子化雪上加霜,已經和對國家的破壞活動產生了直接關連。」
「這種邏輯太蠻橫了吧?明明大多數同性戀者沒有從事煽動活動,只是默默活著。」
「要讓國家團結一心,度過危機,需要簡單明瞭的標的。」
「像是納粹將猶太人作為標的一樣?」
「但是,我們不會屠殺。」
「國家不弄髒手,讓同性戀者自行滅絕?」
淚水從王寺滿的眼中撲簌簌地落下,副院長靜靜地遞出手帕。
「我想幫助像妳這種具有豐富感受性和天分的人。如果妳主動悔改,向世人表明妳轉性了,那應該會對全國的同性戀者造成莫大的影響。如果妳這種人和男人結婚、生小孩,應該會對全國不生小孩的女性造成莫大的影響。」
「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生小孩啊。假如和心愛的女性之間能有小孩的話……假如做得到的話……假如神明賜予那種魔法的話……」王寺滿肩膀顫抖,抽抽噎噎地哭泣。她一面哭,曾幾何時在某個地方越說越激動地說著類似的話的閃回,在一瞬間掠過腦海,但那或許是電擊導致大腦疲勞的緣故。電擊好像也具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一點一點地引出她被埋沒的記憶,因為來到這裡之後,閃回比之前更頻繁地出現了。
「我知道。你們遲早一定會展開屠殺。為了販售器官,隨手讓同性戀者腦死,或者活生生地偷走新鮮的器官。」
「今天到此為止吧。抱歉,把妳弄哭。我請妳好喝的紅茶和糕點致歉。我收到等了四個月的年輪蛋糕。妳很愛甜食吧?」
王寺滿靜靜地停止哭泣時,院長端來了倒進高級茶具、香氣四溢的伯爵茶和年輪蛋糕。她覺得這種作法很下流,但是聞到香味,無法抗拒。
「別告訴其他患者唷。這是妳才有的特別招待。」
副院長如此說道,眨了眨眼。
回到房內,哲太郎一如往常地正在做仰臥起坐和伏地挺身。
他每天要做仰臥起坐和伏地挺身各兩百下,即使勸他「這樣會讓肚子更餓」,他也不肯停。彷彿這種習慣是忍受在這裡的痛苦的唯一方法似地,按照固定的步驟,做仰臥起坐和伏地挺身各五十下,反覆四組。
「給你,禮物。」
王寺滿遞出偷偷藏在口袋裡帶回來給哲太郎的年輪蛋糕。
「副院長給妳的吧?給妳之前,說他等了四個月。」
「搞什麼,不只是我有嘛。」
「這是那傢伙的慣用伎倆。免了,妳自己吃。」
「但我是想留給你吃,才偷偷帶回來的。你討厭甜食嗎?」
「超愛。可是,我現在正在減肥。」
哲太郎的身體也瘦得皮包骨,根本沒有必要減肥。這裡的囚犯無一例外地都瘦得不成人形。並非因為他們是注重外表、在意體型的男同志和女同志,大概是因為這裡的惡劣餐點和壓力所致。哲太郎想讓王寺滿多吃一點,婉拒了她。
「我剛跟副院長交談才知道,這裡好像有我的劇團的所有影片。如果能夠看那些影片,說不定我被帶來這裡也有了一點意義。」
「妳那麼想知道從前的事嗎?我倒是有一堆不堪回首的過去,恨不得喪失記憶算了。」
「我想知道自己的事。像是創作了哪些戲劇、和稻葉久美子之間發生了什麼事、那是殉情,還是意外?如果不知道真相,我不知道今後該怎麼活下去才好。」
「可是,妳再也不能演戲了。」
「就算如此,我還是想知道自己是誰。你如果也真的喪失記憶的話,就會懂了。」
「是喔……既然這樣,對妳而言,那些影片是唯一的希望囉?」
「嗯。即使是最終令人絕望的希望,只要其中有希望,人就能只仰賴那絲希望活下去。」
「我第一次聽妳在這裡訴說希望耶。讓我也想說一說希望了。要是被獄卒聽到就糟了,妳靠過來一點。」
哲太郎對她招了招手,王寺滿一坐在他身旁,他便悄聲說了起來。
「我的希望是,從這裡逃跑。」
「咦?怎麼可能,逃得掉嗎?」
「噓!那些傢伙的耳朵很靈,用氣聲說話。勞動時間外出時,是唯一的機會。」
「可是,有獄卒在監視。再說,要逃去哪裡呢?」
用地四周蓋了矮圍牆,和右邊的山中間隔著一條國道,左邊是大海。隔著矮圍牆也能環顧右邊永無止境的山,以及左邊大海連綿的一片單調景色。
「能夠趁獄卒不注意,跨越圍牆。問題在於那之後。一旦逃跑被發現,警報就會響起。逃進山裡的話,當地的獵人會拿著獵槍展開搜索,一被發現就會被射殺,以被獵人誤會是熊或山豬擊斃結案。逃向海邊會更悲慘。斷崖大約有八十公尺高,所以一躍而下的話,不是頭蓋骨破裂,全身骨折地摔成爛泥,就是浮上海面,被拍打上岸,卡在岩石之間,日漸腐爛……大概八九不離十。」
「那豈不是不管逃到哪,都不可能獲救嗎?」
「往山逃的話,不要被獵人發現就行了。往海逃的話,不要一躍而下,沿著崖壁往下爬到海岸線就行了。如果運氣非常好,就能存活。」
「你打算往哪邊逃呢?」
「大海吧。妳別看我這樣,攀岩是我的興趣,我有一點自信。」
「沒有攀岩繩、岩釘,也沒有岩錘,你要徒手攀岩嗎?太亂來了。」
「我國中、高中都是游泳社,還曾是跳水選手。緊急時,我就跳入海面。儘量往遠方跳,避免強烈撞擊岩石區,就有可能獲救。」
「目前為止,有人成功逃走嗎?」
「就我所知,有三人嘗試逃跑,但好像還沒有人成功。一人逃進山裡,被獵人擊中心臟而死。這一帶的獵人盡是百中選一的精銳好手,一槍就命中了心臟。另一人跳進海裡,頭裂了一個大洞而死。據說腦漿四濺於一片血海之中。最後一人為了前往山那一邊,試圖穿越國道,被卡車輾死。因為警報馬上響起,獄卒們
追了過來,令他慌張了。這裡的傢伙還有些下流嗜好,為了殺雞儆猴,喜歡把他們的屍體照片張貼在浴室。」
「別逃,千萬別逃跑。我不想每次在沐浴日,都要看到你的屍體照片。」
「可是,那是我唯一的希望。即使是最終令人絕望的希望,只要其中有希望,人就能只仰賴那絲希望活下去。這是妳剛才說的話。」
「那不是希望,只是假裝希望的絕望。」
「與其在這種地方自殺或發瘋,被掠奪自己的器官,我寧可反抗死去。即使是人妖,人家好歹也是男生。」
王寺滿這才知道至今總是鼓勵自己,乍看之下堅強的哲太郎處於多麼窮途末路的狀態,這也是頭一次接觸到他危險的一面。而一想到他克己的訓練,就知道他是認真在考慮逃跑,也能感受到他的堅定意志。
「哲子,你聽我說。愛國黨政權不會永遠持續。遲早一定會發生政權輪替,我們會從這裡被釋放。只要忍耐到那時候就行了。即使不冒著生命危險逃跑,也一定有能夠抬頭挺胸從這裡回到自由世界的一天。」
「什麼時候?妳說啊!一點指望也沒有。能夠打倒愛國黨的勢力,究竟在哪裡?待在這裡,或許對外頭的情況一無所知,但是我知道一件事:被送進來的人正在慢慢增加。法西斯的力量非但沒有減弱,反而越來越強了。」
「可是,在這面圍牆外、整個四國、整個日本,都有反抗軍的鬥士。我來這裡之前就見過幾個。有一群人打造穩固的組織、擁有高遠的志向,正在和法西斯主義奮戰。現在這一瞬間,他們也持續著反政府運動,持續向國際社會控訴愛國黨的非法行為。」
「那妳可以相信他們,在這裡等待。但我差不多到極限了。進來這裡之後,反抗軍鞭長莫及。除非靠自己逃脫,否則誰也不會救妳。」
「就算萬幸不死,從那種懸崖跳下去,也免不了身受重傷。說不定腳會骨折。你是舞者吧?不在乎再也不能跳舞嗎?」
「反正待在這裡也沒辦法跳舞。不能跳舞,活著也沒有意義。」
「只要活著,就能跳舞。在這裡也可以跳舞。跟我跳舞吧,教我探戈。」
霎時,哲太郎像是看見耀眼的光芒似地,瞇起眼睛注視王寺滿。彷彿看見若有似無的微小希望的形貌、宛如聞到在地獄深淵綻放的一朵花的香味、像是緊抓著那一道曙光,順著光的方向走,就能活下去似地。哲太郎試圖微笑,但是馬上變回毒舌的人妖,一如往常地咒罵:「哼,妳是白痴嗎?又沒有音樂,怎麼跳探戈呢?」
「在腦海中哼起音樂不就得了?」
「怎麼可能兩人同時在腦海中哼起一模一樣的旋律。只要節拍稍微偏差,動作就合不起來了。真是的,外行人就是令人傷腦筋。」
「那麼,一起邊哼歌邊跳不就好了?」
「妳有多瞭解探戈,哼得出歌嗎?」
「人妖的嘴真的很壞耶。廢話少說,先試試〈化妝舞會〉(La Cumparsita)吧。」
「〈化妝舞會〉也有各種不同節奏的版本喔!」
「先試最標準的、稍快的節奏,就試試兩分半左右結束的版本吧。」
「舞步怎麼辦?」
「我會基本舞步的莎利達(salida),你再教我接下來的舞步。」
「哇,妳會莎利達?那就先用莎利達跳〈化妝舞會〉看看。」
「這樣才像話。開始囉。」
兩人站了起來,各自將右手和左手放在對方的手和肩上,一面哼著〈化妝舞會〉的旋律,一面緩緩地開始舞動。那是一首小心翼翼地互相觸碰對方,彷彿彼此的孤獨刻骨銘心的探戈。
「太慢了!」
「等一下,節奏太快。不再慢一點的話,我跟不上。」
「那以慢一倍的速度。啦、噠、噠、噠,噠啦啦啦~啦,啦、噠、噠、噠,噠啦啦啦~啦……這樣如何?」
「好像勉強跟得上。」
「沒錯,就是這樣!」
「啊,會撞上馬桶!轉身!」
「哎唷,挺厲害的嘛。不愧是王子殿下。」
「可是,這裡好窄。」
「一直跳莎利達,好無聊。」
「有什麼辦法,我只會這個嘛。」
「這次再稍微加快節奏唷。」
「OK,老師。」
「啦、噠、噠、噠,噠啦啦啦~啦,啦、噠、噠、噠,噠啦啦啦~啦……左腳打結囉!」
「就跟你說,還是有點太快嘛!」
「如果更慢的話,舞步會慵懶得讓人想睡唷。」
「我有點喘了。」
「阿滿,妳駝背了!挺直背脊,丹田使力!探戈的關鍵在於姿勢唷。」
「是,老師。」
王寺滿一面和哲太郎跳舞,一面覺得自己體內的什麼慢慢放鬆了。她玩味著內心湧現的一陣熾熱感動,一面出現和某個人跳探戈的閃回,那個人肯定是久美子。她能夠清楚地感覺到,從前將久美子抱在懷裡,隨著音樂搖擺身體,沉浸於彷彿永恆的無限舞步的喜悅之中。像是逃離危險的外界,躲在兩人的世界中,以只有兩人能夠明白的語言互相傾訴似地跳著探戈。然而,那是一種除了幸福之外,還伴隨著些許悲傷的感覺。彷彿明明緊密貼合,卻無法感到對方的體溫、似乎轉身的瞬間,她就會滑溜地從自己懷裡逃走;又像是每次踏步,腳底下的大地就會被削掉一塊似的擔憂,總是揮之不去、如影隨形。
這時,隨著獄卒宣告熄燈的聲音,燈光熄滅。兩人像是從夢中醒來似地,佇立在黑暗中。
「意外的有趣耶。」
「明天再跳吧,接下來每天教我探戈吧!」
「妳別得意忘形。別看我這樣,我可是專家,上課要收錢的。妳該不會打算免費上我朱雀哲太郎的課吧?」
「我沒錢耶,該怎麼辦才好?」
「交換。妳上我的課,相對地,妳要教我什麼呢?」
「抱歉。我沒有什麼能夠教你。演員一點用也沒有,就是所謂的酒囊飯袋。」
「可是,妳也是劇作家吧?既然這樣,說給我聽、演妳寫的戲劇給我看。」
「就跟你說,我都不記得了。」
「也對。那麼,妳現在重新創作吧。」
「戲劇嗎?」
「是啊。就算妳喪失記憶,天分應該沒有喪失。接下來也能再創作新的戲劇吧。」
王寺滿彷彿在聆聽天籟般傾聽著哲太郎的話。彷彿在沙漠的盡頭聆聽風的低語、彷彿在視網膜烙下一瞬而逝的流星燒灼的軌跡、彷彿迫切地一片片重新拾回所有被粉碎的希望碎片。然而對於失去一切的王寺滿而言,這席話實在美得太不切實際了。
「我辦不到。沒有演員的話,我寫不出來。」
「妳的意思是,妳一定要先決定扮演該角色的演員,才寫得出來?」
「畢竟,劇本就像是寫給演員的情書。迷戀上眼前的演員,一心思考、思考、不斷地思考該怎麼做才能讓那個人綻放最耀眼的光芒,才能醞釀成一部戲劇。無論是莎士比亞或契訶夫,一定也都是這樣的。」
「真是的,無趣的女人。明明是創作者,卻連半樣能夠打發獄中閒暇的技藝都沒有,這怎麼行?妳得在這裡找到有效打發時間的方法才行,妳要是想太多無謂的事,會發瘋的。」
「抱歉,我無能。」
「別把人妖的毒舌當真啦!對了,不如這樣吧?妳把我當作演員,替我寫一部劇本看看?寫一齣探戈舞者的故事。這樣的話,妳寫得出來吧?」
「原來如此。嗯,這樣的話,或許寫得出來。」
「真的嗎?」
「光是人妖舞者,就引起我的創作慾,而且你很有趣。可是,說不定要花一點時間哦。」
「時間多的是。就這麼決定了!我教妳探戈,妳寫探戈舞者的劇本。說定囉。」
兩人打勾勾之後,哲太郎道聲「晚安」,隨即就寢了。王寺滿心想,這下有了用來讓他打消逃跑念頭的藉口。如果為了避免看到唯一的朋友頭破血流的照片,她什麼事都肯做。她願意去寫一齣永遠不可能上演的戲劇、每晚撐著疲憊的身軀跳探戈直到筋疲力竭。探戈、探戈,如果能夠全心投入應該曾和久美子一起跳過的探戈,說不定對死亡的恐懼、瀕臨發瘋的畏懼、塞滿空洞腦海的虛無和絕望、像靜靜落下的積雪般的孤獨,都可以拋諸腦後吧。說不定將來有一天會想起和久美子有關的真相、和久美子一起體驗的愛的景象,以及兩人一路摸索直至地獄的路途。至真的美只存在音樂和舞蹈之中。如此一來,她彷彿潛入深深的洞窟般沉浸在音樂和舞蹈之中,凝眸注視所有光景,真摯地側耳傾聽一切樂響。
那一晚,王寺滿夢見的是和哲太郎跳舞時所緩和下來的情緒翻轉,化為過去的部分記憶出現的情景。久美子壓根沒有出現在夢境中,令她感到駭人的失落。久美子已不在人世的事實狠狠地重擊身心,她被喪失言語和情感的絕望擊潰,沉入波濤洶湧、陰暗的深灰色海中。漫天風雪在海上飛舞,海水寒冷刺骨,王寺滿抱著即使溺不死,也可能凍死的一縷希望,趕往久美子的身邊。海水淹至頸部,心臟彷彿被急速冷凍的痛楚蔓延全身,傾盆而下的雪塊像針一般扎進臉頰,還鑽進眼睛和鼻子中,好礙事啊!王寺滿像是在洗臉似地,把頭也沉入海裡。
「喂,振作一點。妳還好吧?」
她被人拉扯頭髮,在背部銳利的疼痛中醒來,看見哲太郎搖醒自己,對她說:「妳做噩夢了,叫得好大聲。我被妳吵醒一看,妳邊睡邊哭,哭得好慘,我實在看不下去了。」
「抱歉,吵醒你了。」
「我知道妳有時候會邊睡邊哭,但是今天特別嚴重。」
「因為跳舞的時候出現閃回,我看見了久美子,好像因此做了奇怪的夢。那不知是夢,還是記憶的一部分。」
「真的是從前記憶的一部分嗎?」
「我想,大概是。」
「如果妳那麼痛苦的話,我們就不要再跳舞了?」
「我不想停止。無論再痛苦的記憶,我都要想起來。就算是在閃回裡,我也想見到久美子……」
王寺滿在哲太郎的懷裡抽抽噎噎地哭泣。哲太郎一直撫摸她的頭髮,直到她哭著入睡為止。
第二章、探戈課
2
在收容所的生活,區分成治療時間、勞動時間和反省時間。
治療時間會被帶到治療室,和醫師一對一,先進行諮詢。患者在那裡被測量自己的同性戀程度,從輕度分類至重度。被視為輕度至中度的患者,會接受比較柔性的心理療法,而對於重度患者,則會採用厭惡療法這種有點粗暴的心理療法。這是從前實際在美國進行的治療法之一,讓患者看同性的裸體照片之後,給予電擊或催吐劑。王寺滿在諮詢中,每次都被判定為重度,只得反覆徹底進行這種療法。
每當電極安裝在束縛器,電流流經腦中,王寺滿就會一點一點地確實感覺到,自己的...
目錄
致親愛的台灣讀者/中山可穗
愛之國
第一章、京都翠鳥聯盟
第二章、探戈課
第三章、朝聖之路
後記
致親愛的台灣讀者/中山可穗
愛之國
第一章、京都翠鳥聯盟
第二章、探戈課
第三章、朝聖之路
後記



 共
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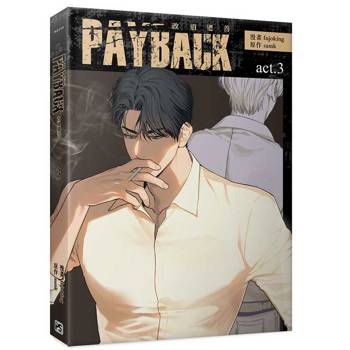




日本作家中山可穗的「愛之國」說的是主角王寺滿追求愛情與自由的故事。是同性的愛情故事,鋪陳在一個獨裁國家中,以及這些不被認可的愛情所面對的暴力虐罰。 說的是一個虛構的社會。有秘密警察,有隔離禁閉,有虐死酷刑等等一切都因為同性愛是病態的,需要被矯正,甚或剷除。然而,不自由,毋寧死。為了愛,犧牲生命都是值得的。 為什麼這樣讀來似乎是虛構小說的情節,卻帶給讀者異樣的熟悉感?為什麼讀來似乎荒唐的情節,卻讓人覺得一點都不陌生? 從什麼時候開始,愛被規定有對象的限制?為什麼教人愛人的宗教會禁止愛人?為什麼高喊人權的政府會剷除與他理念不合的平民百姓?為什麼人們可以干涉他人的生活,只因為他人和自己不同?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停滯,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只剩下莫名的恐懼與仇恨? 中山可穗說:「這本小說中,包含了我至今書寫的所有主題。關於愛、孤獨、旅行與創作,特別是少數族群的悲哀。」 人類的科技結晶已經探勘到火星上了,但是我們連什麼叫做「愛」都不懂。我們狹隘無知到以為眾神跟我們一樣無知(如果有眾神),只愛跟自己一樣的人,仇恨跟自己不一樣的人;只能愛某些人,不能愛某些人。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讀得到一部數萬字書寫同性血淚的小說,毋寧也是一種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