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獸的關係】
這事最初著實嚇我一跳。幾個年輕人,看樣子都不到二十歲,圍住一個老頭兒,拳打腳踢,乒乒乓乓。打人的,挨打的,全是蓬頭垢面,怪嚇人的。老頭兒本來癱在濕磚地上,像攤爛泥,被人提溜起來,遭著拳腳,不停地仰臥起坐,磕牆撞地,跌歪滾爬,一味吭哧,連聲救命、饒命的話也不喊,也看不到一點反抗的慾望。我想,起碼是實力懸殊,老頭兒不敢呼喊激怒打手,更不敢過招。街上早已打得一鍋粥,真刀真槍,血肉模糊,類似小踢打,本不在話下,但年輕人成夥打一個弱不經風的老頭兒,還沒見過。若在平時,我會上前勸阻,有話慢慢說。可現在不行,這是監獄,犯人打犯人,我也是犯人,說話誰聽呀!有意思的是,伴著帶髒字的國罵,媽媽、奶奶、妹妹、姥姥,罵得全面出色,年輕人像極憤怒,可不時擠眉弄眼,又不像真的多麼憤怒。一片貓戲鼠情景。別是下馬威吧?又不像。下馬威是對新犯人用的,讓你守規矩,新犯人是我,剛來幾天,老頭兒那種骯髒癱子模樣,不知在角落裏蝸伏多少天了。下馬威怎麼對他呢?很奇怪。獄室空間太小,最多十平米,幾手拳腳功夫,即顯得聲勢浩大,雷霆萬鈞。更奇怪的是,這樣明顯的恃強凌弱,同監二十幾個「同學」,沒有一個勸解或制止。可能同我的心理一樣,同是犯人,誰管誰啊!但也不對,有犯人組長,平日管事不少,令行禁止,今天卻也一聲不吭。我又想了,這也許同外面一樣,甚至同國際關係一樣,弱肉強食,司空見慣,各種各樣的主義、理論,早已揭露了這個人類和獸類的基本事實,都裝模作樣地斥責,煞有介事地提出形形色色的解決方案,但是,有文字記載的就有幾千年了,解決什麼啦?什麼也沒解決,反而有點變本加厲。最早是木棒石頭,後來是大刀長矛,再後來就是洋槍洋炮導彈核彈了。小小獄室裏,幸虧沒有導彈,些許拳腳也是本性使然吧!還有奇怪的,獄室外就有看守的辦公桌,不會聽不見室內的雷霆動靜。竟也沒有像往日那樣,掀開監望孔的鐵蓋看看。清脆的鐵蓋開關聲對犯人有威懾力量呀!或許裝聾作啞也算一種管理方式吧?最後還是犯人組長說了聲:「行啦!」才算完。年輕犯人一個個擦汗,罵罵咧咧退回原位,挨打的老頭兒呲牙咧嘴又癱坐在濕磚地上。是一個十七歲的初中學生使我的幾個奇怪得到破解。他是因開車撞傷了人被送到這裏來的,挨我睡,很文的,愛和我悄悄說話。這次大概看到我的惶惑樣子,悄悄告訴我:那是個老王八蛋!因為他糟蹋了好幾個十來歲的女孩子。這樣揍他,已有幾回了。初中生大概還不習慣帶髒字的國罵,嘴裏出現這一罵,充分表現了他內心的憤怒。王八也是獸,把老頭兒罵為禽獸,很貼題。這使我想起曾琢磨過的一些事,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就是人和獸的區別。狗在大街上交媾,貓在房頂上叫春,蒼蠅在玻璃窗上交和……小時候思想單純,認為禽獸才這樣不懂羞恥。長大了,知道人也差不多,區別只在明暗之間。學習社會發展史,古人類雜交,大概和禽獸差不多吧!演化到逐漸文明起來,有了衣冠遮羞,貞節牌坊之類。在一夫一妻已成為制度的情況下,還有通姦、強姦、亂倫之類,禽獸痕跡從來沒有根除過。往大處說,世界大戰,篡權奪位,漫天血腥,同禽獸相殘有什麼區別?細菌戰、毒氣戰、法西斯集中營、南京大屠殺,人們稱獸行。古書上記載的「人食人」,同虎豹火拼,狗狼廝咬,太相像。還有一種什麼動物,雌雄作愛,多麼親暱歡快,一當事畢,雄的便成為雌的腹中之物,稍加思索,觸目驚心。人類中如此可驚心者,不也多如牛毛!國際間,政權更迭間,統治與被統治間,不管呼喊多麼美麗的口號,刀光劍影,一概翻臉不認人。
幾個世紀前,最初提出「人性」的人,大概是看到古來那麼多獸性不像話,不符合人是高級動物的身份,喊「人性」喊了起碼幾百年。到了現在,又認為那是資產階級騙人的玩藝兒,所以要批判「人性論」。這時外面正大張旗鼓批判「人性論」,我借這裏出現老獸的機會,同獄中才子陳仲龍探討人性和獸性的關係。(陳才子很值得懷念,後面會談到。)來言去語,時斷時續,把我原有的一些想法引伸了,多少又明晰了一點,今天回想著記下來,有多少價值,且不管它。一切動物,無論多麼高級,都有獸性,是共性;人性,人類才有,是個性。根據共性寓於個性之中的原理,獸性寓於人性之中。這是我說的。才子說,同意。自封高級動物,也還是動物,「動物」與「獸」可視作等同語。高級獸的提法新鮮,確否待考。都有獸性可能是真理。
還可以這麼看,人類文明的發展與人性不斷克服獸性的過程同步,但永遠滅絕不了獸性。對,假如獸性滅絕了,人也就不再是高級動物,變成別的什麼東西了。若果如此,咱們的討論就沒有什麼意義了。這假設大概不存在,人身上的獸性永難滅絕,應該是本性使然。我也這麼想。一不小心壓抑人性,獸性必然大發作,造成災難。看看到處流淌的血沫就明白。才子壓低聲音,樣子有點神秘:批「人性論」,連「母愛」「童心」也批了,沒有了這些,人性還要不要?現在是用階級性批駁人性。這有點自搧嘴巴。階級性只有人類才有,是人性的一部分。你能給虎狼犬豕定階級成分麼?想用人性的一部分批倒整個人性,是人性的悲衷。「母愛」「童心」大概算作人性的另一部分。哪個階級的母親不愛子女?哪個階級的兒童不是童心?不是童心,是什麼心?「母愛」不要了,把黨和祖國比作母親的歌詞都得修改。自搧嘴巴的事有的是。 咱想的似還淺點。人性問題實際涉及「性善論」「性惡論」的哲學問題。 也涉及人類學,也許還涉及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等等諸多領域。叫人越想越糊塗。 我何嘗不是?許多事越想越不明白。咱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吧!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任希儒的圖書 |
 |
$ 316 ~ 360 | 獄裡獄外事:走過文革的人生實錄
作者:任希儒 出版社:新銳文創(秀威代理) 出版日期:2012-02-1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38頁 / 14.8*21 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獄裡獄外事:走過文革的人生實錄
本書以「我」這個小人物串起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入獄以及出獄的一個個故事,描述在那特殊年代及其前後形形色色普通人的生活狀態。透過本書呈現了一段歷史的見證,展示誠實、氣節、鄉愿、出賣、奴才性等等諸多色彩;讚頌忠貞耿介,鞭撻醜惡殘酷,並揭露權勢者的謊言及其背後的恐懼。
作者簡介:
任希儒男,一九二六年一月生於天津,編審,中共黨員。一九四六年十月參加地下書店工作,一九四九年始介入編輯工作。先後供職於讀者書店、知識書店、天津通俗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二月離休。主編《書店風雲》,著有《另類的夢》、《天津出版史略》、《墨子的政治和經濟思想》等作。
章節試閱
【人和獸的關係】
這事最初著實嚇我一跳。幾個年輕人,看樣子都不到二十歲,圍住一個老頭兒,拳打腳踢,乒乒乓乓。打人的,挨打的,全是蓬頭垢面,怪嚇人的。老頭兒本來癱在濕磚地上,像攤爛泥,被人提溜起來,遭著拳腳,不停地仰臥起坐,磕牆撞地,跌歪滾爬,一味吭哧,連聲救命、饒命的話也不喊,也看不到一點反抗的慾望。我想,起碼是實力懸殊,老頭兒不敢呼喊激怒打手,更不敢過招。街上早已打得一鍋粥,真刀真槍,血肉模糊,類似小踢打,本不在話下,但年輕人成夥打一個弱不經風的老頭兒,還沒見過。若在平時,我會上前勸阻,有...
這事最初著實嚇我一跳。幾個年輕人,看樣子都不到二十歲,圍住一個老頭兒,拳打腳踢,乒乒乓乓。打人的,挨打的,全是蓬頭垢面,怪嚇人的。老頭兒本來癱在濕磚地上,像攤爛泥,被人提溜起來,遭著拳腳,不停地仰臥起坐,磕牆撞地,跌歪滾爬,一味吭哧,連聲救命、饒命的話也不喊,也看不到一點反抗的慾望。我想,起碼是實力懸殊,老頭兒不敢呼喊激怒打手,更不敢過招。街上早已打得一鍋粥,真刀真槍,血肉模糊,類似小踢打,本不在話下,但年輕人成夥打一個弱不經風的老頭兒,還沒見過。若在平時,我會上前勸阻,有...
»看全部
作者序
【序 怎麼寫起這本小書】
這是本故事書,說的是指那特殊的十年,又不限於那十年,歷史總是一步步走,前後有聯繫。那十年,中老年人多有記憶,形勢好了,回憶它,可以溫故知新,使工作、日月更好。年輕人不知道,應當告訴他們,中華民族曾有過那樣一段實實在在的歷史,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故事裏有事有人,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從中獲得一點生活參考。
有些事不能捂著蓋著,不能瞞,瞞和騙緊相連,過去我們吃這種虧不少,說開了,可以前覆後戒,才走得更穩,少花修車錢。心放正了,實無必要怕。
寫此小書還包含著一個動機,即有些事...
這是本故事書,說的是指那特殊的十年,又不限於那十年,歷史總是一步步走,前後有聯繫。那十年,中老年人多有記憶,形勢好了,回憶它,可以溫故知新,使工作、日月更好。年輕人不知道,應當告訴他們,中華民族曾有過那樣一段實實在在的歷史,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故事裏有事有人,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從中獲得一點生活參考。
有些事不能捂著蓋著,不能瞞,瞞和騙緊相連,過去我們吃這種虧不少,說開了,可以前覆後戒,才走得更穩,少花修車錢。心放正了,實無必要怕。
寫此小書還包含著一個動機,即有些事...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任希儒
- 出版社: 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12-01-10 ISBN/ISSN:978986609446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8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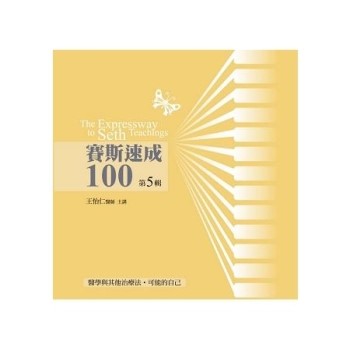








 2025【精選作文範例】國文(作文)[速成+歷年試題](不動產經紀人)](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5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