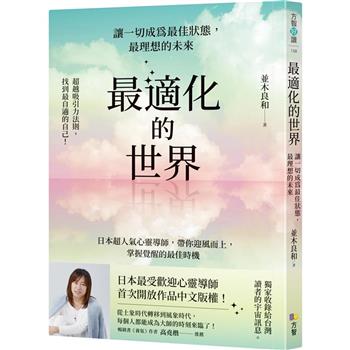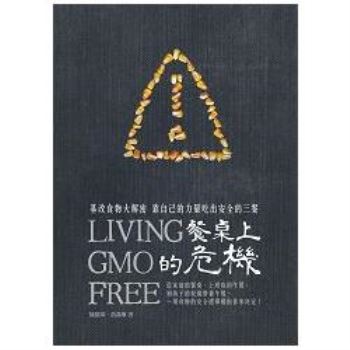她在我最脆弱時來到我身邊,
她讓想傷害我的人消失不見,
她是我的守護者、愛人、抑或敵人?
一座神祕危險的城市,兩顆親密相契又猜疑不安的心靈,燦爛的北非陽光下,記憶與真相眩目得看不清……
★電影版將由史嘉蕾‧喬韓森主演、喬治‧克隆尼擔任製片
★榮登博客來網路書店外文館選書、英國水石書店每月選書、美國獨立書店聯合選書
★提子墨、黑咖啡聊美劇、黃羅、簡嫚書 好評推薦
┤故事簡介├
一九五六年的摩洛哥大城坦吉爾,明媚風光中暗湧著獨立前夕的騷亂。柔弱內向的英國女子愛麗絲隨新婚丈夫約翰移居這個繁華炎熱的城市,原本對異鄉生活滿懷期待,但難以適應的新環境、迅速冷卻的夫妻感情,使她成了被自己軟禁在家中的憂鬱囚犯。
所幸,愛麗絲大學時代的密友──活潑獨立、聰慧率性的露西──遠渡重洋來訪,在露西的幫助之下,她重振精神,這才看清了約翰接連不斷的外遇、以及謀奪她娘家遺產的企圖。露西計劃帶著好友逃離摩洛哥、告別這段充滿陰謀算計的婚姻,但愛麗絲猶豫了,因為這個情境似曾相識:在大學的最後一年,露西也希望她離開當時論及婚嫁的男友,她嚴辭拒絕之後,那個男生旋即在校園附近發生車禍,當場身亡。
無獨有偶地,在愛麗絲舉棋不定的現時,約翰的情婦墜樓受傷,他不久後也離家失蹤。愛麗絲沒有因此如釋重負,反而更加懷疑,露西究竟是來救她重獲自由,還是故技重施地除掉敵手以獨佔她的關注?
儘管坦吉爾的情勢逐漸動盪,她仍決心在此查明真相。但當警方懷疑她因妒殺夫、找來證人與她對質,她卻發現她一提及露西的嫌疑,記憶和說辭便全都變得零碎而矛盾,愈想澄清實情,愈讓自己顯得罪嫌重大,甚至因為旁人眼中歇斯底里的表現而受困於精神療養院。在藥物與禁閉造成的空茫昏眩中,她隱約又看到一位神祕訪客來到她的病房……
究竟是誰在陷害她?又有誰真心想拯救她?
她要如何證明自己不但無辜、更是神智清醒?
還是說,她真如旁人指控的一樣偏執瘋狂、手染鮮血……?
┤推薦佳評├
克麗絲汀.曼根以上個世紀的摩洛哥王國為背景,細火慢燉出節節升溫的懸疑驚悚,銳利的筆鋒也如刀刃般精準地切入人性。在女主角們雙重視角的敘事鋪陳下,我們方認清眼見為憑的人事物,不見得是事實;更意識到任何表象上的言行舉止,真正的底裡或許與我們所理解的大相逕庭!
── 提子墨(作家、英國與加拿大犯罪作家協會PA會員)
女人永遠是個難解的謎,這句話霍金深表認同。讀完這本小說之後,你不必聰明如霍金,也會明白居心叵測的閨密更是如夢魘般的謎。
──黃羅(推理評論家)
在北非熱浪般充滿壓迫感的氛圍中,《愛麗絲的訪客》將一個關於執迷與控制的故事融合了海史密斯和杜穆里埃的風格,以一九五○年代坦吉爾的舊城區與暗街為舞臺上演。曼根的首部小說逐步成為現代經典,充滿濃厚的懸疑感與心理層次的權力競爭。
──英國水石書店
猶如唐娜・塔特、吉莉安・弗琳與派翠西亞・海史密斯聯手合寫電影劇本,而導演是希區考克。氣氛到位,吊足胃口。
──喬伊絲‧卡洛‧歐茨(普立茲獎小說家)
詭譎驚悚且充滿趣味。
──珍妮佛‧伊根(《霧中的曼哈頓灘》作者)
兩名女主角之間的複雜糾結詭譎而刺激,令人停不下瘋狂翻頁的速度。黑暗的背景故事和心理性的懸疑,讓我感覺彷彿親自遊歷了坦吉爾,而且是由達芙妮‧杜穆里埃的文學傳人擔任嚮導。
──蘇珊‧林道爾(《神祕打字員》作者)
保證名列年度最佳新人小說。情節緊湊、充滿異國風情。
─—《娛樂週刊》
曼根先是操弄筆下兩個敘事者的不可信特質,接著又將她們兩人的歷史一併重寫……這部小說召喚出的並不是坦吉爾這座城市,而是人們對它的欲望,一場浪漫與冒險的朦朧綺夢。
──《紐約客》
愛麗絲與露西一來一往,如同網球賽一般,交替說出各自版本的故事,而且賽況逐漸緊繃。露西宛若變色龍,她重新創造身分的能力,令海史密斯筆下的湯姆‧雷普利相形見絀。
──《華盛頓郵報》
曼根以古典好萊塢的色彩學勾勒出兩個敘事者的樣貌。
──《紐約時報》
《愛麗絲的訪客》優秀之處是不斷推進的刺激情節,接近結局處尤甚,以及經典不墜的驚悚小說主題元素。
──《村聲》"
作者簡介:
克麗絲汀.曼根 Christine Mangan
都柏林大學學院英國文學博士,南緬因州大學小說創作碩士,專攻的研究領域是十八世紀哥特文學,這個文類對場景氛圍與象徵性的重視、描繪女性角色的壓抑與瘋狂的手法,也深深影響了她個人的小說作品。《愛麗絲的訪客》是她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甫完成初稿、尚未正式出版時即售出九國外語版權,電影改編權利更由喬治.克隆尼的製片公司拿下,找來《性愛成癮的男人》及《鐵娘子》金獎編劇操刀劇本,預計由史嘉蕾.喬韓森主演。
譯者簡介:
力耘
台北人,兼職譯者多年。
譯有《妳帶走的秘密》、《黑殼》、《變態療法》、《社交動物》等。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愛麗絲
禮拜二是上市場的日子。
不只我,整座城市皆如此。里夫地區的婦女浩浩蕩蕩走下山,吹響序曲;她們的籃子、推車堆滿蔬果,巍顫顫地左右掛在驢背上。而坦吉爾則以熱情喧鬧作為回應:人群傾巢而出,街上擠滿男人女人、外國人和本地人。這堆指一指、那堆買兩斤,你討價我還價,最後掏出銅板換來一點點這個和一些些那個。這幾天,太陽似乎更形熾熱、更加燦亮,導致我的頸背曬得有如燒傷。
此刻,我站在窗前俯視下方爆滿的人群,暗自希望今天仍是禮拜一。然而我也知道,禮拜一永遠只是虛假的盼望、空幻的慰藉,因為禮拜二終究會來,我也得被迫站在底下這片洶湧翻騰的混亂中,被迫站在一個個教人印象深刻的里夫婦女面前:她們以各種鮮豔色彩妝點自己,攫取眾人目光,兩隻眼睛則毫不客氣地打量我單調乏味、完全無法與她們匹敵的服裝,神色亦略帶擔憂——擔心我多付了錢卻渾然不知,擔心我給錯銅板,擔心我措辭有誤,擔心我當眾出糗、使她們不得不哈哈大笑,而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證據——證明我大錯特錯,竟然決定來到這裡。
摩洛哥。這個名字猶如魔法,變出一片巨大、荒漠般的空無景象,以及高懸空中、光芒萬丈的赤紅太陽。我頭一次聽約翰說起這地方時,正勉強小啜一口他塞給我的雞尾酒,還因此嗆咳一陣。我們在倫敦皮卡迪里區的麗池飯店見面,而且還是因為茉德姑姑堅持要我去,我才去的。自從幾個星期前、我從班寧頓學院歸國以來,我經常感覺到這份敦促與堅持,猶如一樁永遠擺脫不了的頭疼事。我回到英國也才幾個月,認識約翰的時間更短,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很確定我感覺到了什麼——他的興奮、他的旺盛精力充滿我倆周圍的空間,穿透溫暖的夏日空氣,陣陣傳送過來。我傾身靠向它,渴望抓住它、握緊它,宣示所有權;於是我任自己應允這個屬於我倆的安排與決定。非洲。摩洛哥。若是幾個禮拜前,我會猶豫;說不定幾週之後,我只能大笑——但是在那個特別的日子、那特別的一刻,我聆聽約翰的話語、他的承諾和他的夢想,它們一個個都變得好真實,彷彿全部都能付諸實現。我發現,這是我離開佛蒙特以來頭一回萌生想要的念頭——我並不明確理解自己想要什麼,而且我也懷疑,這個念頭並非此刻坐在我面前的男子使然,但我仍深切渴望某種東西。我輕啜他點給我的飲料。香檳已然變溫,氣泡也沒了;我嚐到舌尖的酸味,感覺肚腹翻攪。我伸出手——趁我還未改變心意——手指覆著他的手。
儘管約翰・麥克埃利斯特肯定不是我一直以來夢想的典型——他太聒噪又熱愛交際,性情急躁且偶爾有些魯莽——可是我發現自己深深陶醉在他獻上的機遇與無限可能之中:讓我遺忘,將過去拋諸腦後。
讓我不再想起佛蒙特州綠山那個冰冷冬日的每一分、每一秒。
現在,事發一年之後,我依舊困在重重迷霧中,一次又一次在記憶迷宮中跌倒,找不到出口。或許這樣也好——後來當我告訴茉德姑姑,我的記憶宛如罩著一層朦朧光澤,使我再也想不起來那個恐怖夜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甚至連之後幾天的事情也記不得了——她如此對我說。過去的事就放下吧,她極力勸服我,好似我的記憶是某種能牢靠地裝箱打包、保證永遠不會洩露箇中秘密的東西。
而我某種程度也算是對過去閉上眼睛,只看著約翰、看著坦吉爾、看著摩洛哥的熾烈驕陽,睜大眼睛迎向他許諾的冒險——當然少不了求婚和一只恰當的戒指,但沒有實際儀式,只有簽署雙方姓名的一張紙。
「可是這樣行不通吧?」起初我並不同意,「我們幾乎不認識彼此呀。」
「誰說我們不認識?」他再三安撫。「妳的家人和我們家其實是親戚,如此說來,妳我可說是再熟悉不過了。」他戲謔地大笑。
我決定不冠夫姓——這點我相當堅持。就某種程度而言,在經歷這麼多風風雨雨之後,能保有部分的自我、我的家庭和家人,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不過還有一些別的理由,一些很難清楚說明、就連對我自己也解釋不清的理由。因為,理論上來說,雖然姑姑對我的監護權將因為我立下婚約而解除,但是在我滿二十一歲以前,她對我的財產信託仍舊握有實際宰制權;換言之,在我二十一歲生日後,爸媽的遺產才會真正轉入我名下。這種雙重監護的作法實在非常嚴謹也令人沮喪,也因為如此,每當我遞出護照,上頭總還是寫著「愛麗絲・希普萊」。
剛開始,我告訴自己坦吉爾沒有那麼糟。我想像自己成天在摩洛哥豔陽下打網球殺時間,想像成隊的僕人卑躬屈膝聽候我們差遣,想像我們以會員身份周旋於全城各種私人俱樂部之間——世上還有比這更糟糕的生活方式,我心裡明白。但後來,約翰一心想體驗真實的摩洛哥,真實的坦吉爾,因此當他的朋友或生意夥伴紛紛雇用廉價摩洛哥幫傭、而他們的妻子亦日日流連游泳池畔或籌劃派對,約翰則是對這一切避之唯恐不及。他和摯友查理在城裡到處閒晃遛達,不是往澡堂或市集裡鑽、就是躲進咖啡館深處抽麻菸,無時無刻不費盡心思博取本地人的喜愛,對自己的同事同鄉則不屑一顧。當初力勸約翰遷居坦吉爾的人就是查理。他不厭其煩地向約翰描述這個國家的傳說故事——美麗風光,無法無天的自在逍遙——直到約翰幾乎愛上這個未曾謀面的國度。而我在一開始也竭盡所能,陪他逛跳蚤市場挑傢俱、至露天市場採買食材。我也曾與他同坐咖啡館,啜飲牛奶咖啡,試著在這個塵土飛揚、炎熱不堪、教他一見鐘情卻始終令我自覺格格不入的城市裡,重新撰寫我的未來。
後來出了跳蚤市場那場意外。
當時,攤商與小販推擠叫賣,古董及垃圾無序地隨興堆疊,一層蓋過一層;我才轉身,約翰就不見了。我愣在原地,陌生人從四面八方穿越、推撞過來。熟悉的焦慮感逐漸升起,我的掌心越來越濕黏,視野邊緣亦有黑影舞動——那些條狀、扭曲的幽靈。醫生表示那只是某種症狀,但對我而言卻無比真實,有血有肉,伸手可及。幽靈越來越多,灰暗的身影徹底佔據我的視線,在那一刻,我驚愕地體認到自己離家有多遠,和我原本為自己設想的人生已然離得好遠好遠。
事後,約翰笑著堅持他不過只離開了一分鐘,然而下回他再邀我一起出門時,我搖頭拒絕了;之後的再下一次,我又搪塞別的藉口。既然不出門,我便投入大把的時間——漫長、孤單且日復一日的個把鐘頭——從我們舒適的公寓逐步探索坦吉爾。第一週的歷程結束時,我已掌握從公寓這一端到另一頭要走幾步路:四十五步,但時有增減,端看我的步距而定。
到後來,我覺得約翰的懊悔逐漸壟罩我倆心頭,態勢越來越明顯:我們的談話內容僅限於實際事務與財務狀況(我的定期津貼成為我們的主要經濟來源)。約翰不擅理財——有一次,他咧嘴笑著向我承認;當時我也微笑回應,以為他是指他不在乎錢,也不擔心沒錢。但我很快了解到,原來他言下之意是他的家產幾已散盡,餘下的僅足以維持體面穿著,好讓他能繼續作戲,宣稱自己依然擁有繼承得來卻已不復存在、深信自己理當擁有的財富。一切全是假象。於是,我只好每週按時交出津貼;至於這些錢最後花到哪兒去,我不在意也不真的感興趣。
每一個月,約翰仍持續他偶爾神隱的習慣,懷抱我無法理解的狂熱與喜愛,一頭鑽進這座謎樣的城市,獨自探索她的秘密;而我則依然裹足不前——我是我自己的俘虜。
我瞥瞥時鐘,蹙了蹙眉。前一次抬頭看時鐘,時間才剛過八點半,但此刻時針分針正穩定邁向正午。我輕聲責備自己,快步走向稍早——我渾然不覺已過了好幾個鐘頭——攤在床上的外出服。今天我已經答應約翰,我會去市集。今天。我允諾自己再試一次。我低頭打量:衣如其人,活脫脫就是一副尋常婦女準備出門採買必需品的尋常打扮:褲襪,皮鞋,以及我遷居坦吉爾前、在英國購置的連衣裙。
我把連衣裙套過頭,聽見前襟發出微微的撕裂聲——約莫是領口和蕾絲縫合之處。我皺起眉頭,抓近細瞧,一看見破損的布料便竭力止住顫抖,告訴自己這並非徵兆,亦不代表厄運,完全不具任何意義。
房間頓時變得太過溫暖。我踏出陽台,當下彷彿極需逃出高聳的屋牆。我閉上眼睛,絕望地想感受微風拂面;我等待,但一絲微風也無,只有坦吉爾始終不變、乾枯炙人的酷熱,無情進逼。
一分鐘過去。又一分鐘。我靜靜聆聽自己的呼吸,突然意識到有種遭人窺視的古怪感覺。我睜開眼睛,朝下方的街道迅速一瞥。沒人。只見幾名本地人步履匆忙朝市集走去。收攤的時刻緩緩到來。「好好振作!」我低聲叮囑自己,同時掉頭返回安全的室內。儘管方才才為自己打氣,我仍緊緊關上身後的窗門,心臟怦怦跳。瞄瞄時鐘,竟然已經一點半了。市集之約可以再等等,我告訴自己。
這個約定必須延後,我心裡明白。我用顫抖的手拉緊窗帘,就連最微弱的陽光也不讓它透進來。
第二章 露西
我抵著欄杆,艷陽狠狠照在身上。腳下搖晃的程度益發強烈,我的胃也隨之翻攪;渡輪走走停停,笨拙地緩緩邁向終點:摩洛哥。我趕緊抓起行李袋。過去幾個月,我不時夢見那些一字排開的雄偉建築,活力充沛卻又錯綜複雜宛如迷宮的露天市場,以及豐富多彩的馬賽克磚和漆牆鮮豔的胡同窄巷。渡輪準備靠港,我伸長脖子,迫不及待想一賭初次見面的真實非洲。在這之前,我已嗅到她的味道——非洲的氣味從岸上飄送過來,引誘我們,允諾某種比我在冰冷的紐約街道所體驗過更深刻、更豐富無限的未知與期盼。
還有愛麗絲,她也在這裡。隱身在這座生氣勃勃的城市某處。
走下渡輪,我掃視人群、搜尋她的臉龐。乘船渡海的這幾個鐘頭,我努力說服自己相信,儘管發生過那些事,她說不定仍會在港口迎接我。但她不在這裡。人群中沒有半張熟悉的面孔,只有十數名年輕男孩或上了年紀的男子卯足全力勸誘、說服我以及其他剛下船的旅客,購買他們提供的各種服務。「我不是導遊,就是個本地人,而且大家都認得我。我會帶您走訪其他導遊都不知道的秘境。」眼見此番說詞收不到效果,這些本地人轉而亮出商品:「女士要買皮包嗎?」或者向我身後的男士問道:「先生買條皮帶吧?」他們敞開長衫,取出各式商品,連番掃過每一位謹慎低頭、初來乍到的旅客眼前:珠寶、小木雕、充滿異國風情且造型奇特的樂器。而我就跟其他人一樣,不耐煩地揮手、撥開這些廉價小物。
介紹坦吉爾的旅遊指南不多,但我把能找到的文獻資料全部讀過,一句一句理解這座我即將稱之為家的城市(不論時間有多麼短暫)。我讀了伊迪絲.華頓和馬克.吐溫的文章,甚至一度迫於無奈而拿了安徒生的幾頁故事來讀;結果令我訝異的是,眼前反倒是安徒生的故事幫助最大,讓我做好準備、面對當地導遊急切猛烈的攻勢——他們有如蝗蟲過境,無數張臉孔猶如海嘯襲來、撲向剛靠岸的船隻,胸有成竹地向毫無經驗的天真旅人兜售服務。我或許沒什麼經驗,但「天真」一詞肯定無法套用在我身上。於是我打起精神、做好心理建設,以事先鑽研的知識和單字武裝並保護自己,對抗眼前這幅渾沌景象:我確切知曉在離開安全且相對安靜的渡輪之後,我將踏入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但說到底,華頓、吐溫或甚至是安徒生的文字終究無法化為利劍和盾牌,無一能助我做好萬全準備。
吸引力(affinity)。進入班寧頓學院的第一年——那一小群或說坐落、或說隱身於佛蒙特州綠山心臟地帶的奇妙建築——我拿起字典認真翻查這個詞的意思。對事物自發或自然萌生的喜好。因擁有相類的特質而形成的關係。我亦著手尋找同義詞,譬如相似(similitude)、傾向(inclination)。我把它們全抄在筆記本上,不論去圖書館或教室皆隨身攜帶。我把這本藍色封皮略微磨損的筆記本緊扣在胸前,悉心保護亦掛記在心,一次也沒遺落過:它是我珍藏金玉良言、名言錦句的寶庫。我不時展頁細讀,在早上第一堂課之前讀它,晚上入睡前也讀。我低聲唸誦,彷彿我必須銘記這些話語好應付日後的測驗,彷彿這些話語已和我的課程、和我能否在班寧頓生存融為一體。
初見愛麗絲之後數週,我偶然讀到吸引力這個特別的詞。那一刻的心情既酸楚又深刻——它表達了某種我還不知道自己正尋尋覓覓、找尋其描述方式的一個詞。這個詞描述我和愛麗絲在初見面後短短幾週內所形成的、某種我倆都在彼此身上感覺到的特殊感,而這種感覺遠遠超出任何理性描述範圍。於是我決定,「吸引力」可以算是個不錯的開始。
我倆是在入學第一天見面的。愛麗絲站在我們分配到的宿舍走廊上——這種木板屋每棟有兩層樓,每層樓大概有十數間房,一樓還有一間附壁爐的共用起居間。她在找我們的房間,手裡捧著一大疊書,彷彿「隱身消失」是她當下最衷心的期盼。其實她也差不多快「消失」了——她的臉和上半身幾乎消失在那疊顯然太過沉重的書堆後面。當時我已經曉得她是我室友。到校前,我們先透過安排互相認識,並多次魚雁往返、亦附上照片,好讓彼此一眼就能認出對方。儘管如此,我仍禁不住等待、拖延,盡可能延後相見的那一刻——我不想就這麼上前幫她、貿然自我介紹。時機未到。
於是我等待。我觀察。
我不曾見過如此纖細的手腕和腳踝。夏季未了,她那有如芭蕾舞伶的裙擺輕飄飄地抵著小腿肚,纖薄上衣清晰可見內裡的短袖背帶式內衣。她擁有一頭金色長髮,那種捲度比較像是做出來的、而非天生。待她終於走近,我看見她光亮的指甲呈現淡淡的粉紅色,若有似無,難以察覺——她的妝容也同樣適用這套描述。有那麼一瞬間,我納悶她到底有沒有上妝;但下一刻我認為她畫了妝,只是幾乎看不出來,雖不易察覺仍依稀可見。這妝上得極好,旁人恐難體會其用心程度。她這麼做非為了博取注意、或乞求關注,然而她所做的一切卻牢牢吸引眾人目光。
於是我才知道,她已然習慣他人注視,習慣在眾人面前展現自己。而她也同樣坦然告訴我,她從來不曾攢錢存房租,從不擔心沒錢填飽肚子,也無需斤斤計較手上的現金能再撐一個星期或是一兩天。即便如此,我並未疏遠她(不像我對待其他女同學的方式)。這個女孩身上不見絲毫驕縱之氣,亦不曾流露半點優越感。學院裡的其他女孩汲汲營營想證明自己比他人優秀,成天炫耀度假細節、不時說幾個她們心知能令他人恐懼敬畏的大人物名號;但我很快發現,愛麗絲和她們完全不同。其他女孩費盡心思打探誰是乞丐(即她們口中「拿獎學金的窮學生」),但愛麗絲對待我這個「來自隔壁小鎮的乞丐」的方式,與對待其他人並無不同。那天,在我們還沒互相問候之前,我看著她,打心裡覺得她看起來十分仁慈且和藹,甚至有點孤單。
後來我回到房間,表面上假裝盯著空蕩蕩的白牆壁,實則屏息以待,等待她慢慢走近,卻又在那個瞬間深怕我若蹉跎太久、若再多等一分鐘,說不定就會錯過她,將她拱手讓人。最後,她終於出現在房門口。我微笑招呼:「我是露西.梅森。」我伸出手、同時走向她,彷彿我想說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皆扭曲纏結成這一個不起眼的手勢,好似現在與未來的一切端賴這一刻如何決定。我彷彿等待了無盡這麼久——雖然不過是須臾片刻——思忖她會不會握住我的手,思索這個動作將引領我倆走向何方、以及我倆相偕共度的旅程將如何開展。
她將手裡的書本換至另一手,臉上綻開微笑。「我還擔心妳會忘了呢。」這句話使她臉頰飛上兩朵紅雲,而她的英國口音字正腔圓;「我是愛麗絲。愛麗絲.希普萊。」
她的手好溫暖。「很高興見到妳,愛麗絲.希普萊。」
隔天早上,我細心著裝打扮。
我動手整理散落在摩洛哥傳統客棧裡的隨身物品。昨晚我租了間房,想在長途跋涉後讓自己好好換件衣服、重振精神,不想頂著一頭亂髮、踩著扯裂的褲襪現身愛麗絲家門口。我巡視屋內,一回,再一回,直到我滿意地確認自己沒落下任何東西,這才關門離去。
來到舊城區,我站在某個小攤販前排隊買早餐——某種我沒見過、外形像辮子的麵包,表面撒了芝麻,餡料嚐起來像過期的麵糊。我倚牆立食,感覺麵糰奇異的紋理緊貼我的舌頭和口腔,不時停下來小啜一口和麵包一起買來的牛奶咖啡。我放眼街頭,任視線漫遊。
我看著咖啡館裡的觀光客啜飲薄荷茶,看著一群本地人卸貨,從驢背交到搬運工手上再送進店裡;後來,我的視線終於對上他。
他坐在幾公尺外,廣場上櫛比鱗次的某間咖啡館裡。個兒高、黝黑,稱不上英俊。我猜他是本地人,但也無法百分之百確定。他戴著一頂軟呢紳士帽,帽緣低垂遮住半張臉,帽冠則鑲了一圈鮮豔的紫色緞帶。我又多站了幾分鐘,感覺他的視線停在我身上,好奇他到底在看什麼、又或者何事引他如此注意。今天早上,我確實費了番心思仔細打扮,穿上我在這趟跨海之旅前購入的體面洋裝(吊牌上的數字足足耗去我一小筆積蓄)。我用左手順順衣裙,喝完咖啡,上路遠離鬧區,走出男人好奇探詢的注視。
經過近一個鐘頭的瞎走亂逛與多次原途折返,無視侍應生的輕蔑訕笑(因為我在這種炙人的大熱天竟然副武裝:一身正裝還繫上小領巾),我一次、兩次、三次經過同一間餐館門口,甚至一度瘋狂地以為每一條路最終都會通往「小廣場」;最後,我終於找到了。穿過舊城區和卡斯巴區往西走,愛麗絲的宅邸安坐在昨日我首次踏入的渾沌外緣。旅遊指南標示此處為「瑪商區」,早在我還未意識到任何實質改變之前,我就已經感受到某種奇妙變化了:此處的街道兩旁有路樹(惟其模樣在我看來相當罕見且不熟悉),綠意較濃,此外還有一種說不上來的輕盈感,彷彿隨著我越走越近,壓在我肩上——不對,正確說來是肩胛骨之間——的緊張壓力亦逐漸消散。說不定這只是因為我離她越來越近,我心想。於是我停步,放下行李袋,深深吸一口氣。
這棟建築本身並不起眼,輕易隱身在其他樓房之間:建物本體以白石塊建成,另以鍛鐵陽台和寬敞大窗點綴;我想,這款建築就算在巴黎亦不顯突兀。當然,這種視覺上的熟悉感是可預期的,但我仍無法排開微微的失落感——我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才來到這裡,歷經數月的規劃和攢存,數不清幾個鐘頭的輪船、火車再遠渡重洋,一路風塵僕僕,故我的心緒也因為探索這塊新天地而疲累受折磨。因為如此,我對這趟旅程的終點自然期待甚高——我想像閃閃發光的大門,富麗堂皇的宮殿,總之是某種戲劇化、最隆重亦最極致的象徵:這是妳的獎賞——妳終於找到屬於妳的道路了。我伸出手指,按下電鈴。
我等了好一會兒,但無人回應。我感覺心臟越跳越快——難不成她回歐陸去了?還是我抄錯地址?我緊盯手中的紙條,紙上的墨水因反覆攤折而有些模糊。我想像自己掉頭回到港邊,看見自己又買了一張船票,無視渡船工人嘲笑奚落的眼神(因為他們才剛載我渡海靠岸),笑著看我登上渡輪,再一次、而且是挫敗地跨海折返。門兒都沒有。我用力甩甩頭。一想到紐約,就想起另一段烏雲罩頂的茫茫冬日,想起我在那座城市各處落腳過的、狹小拮据的分租雅房,想起數不清的女人足蹬高跟鞋在走廊來回小跑步的聲響。然後還有氣味——儘管午後陽光炙熱,我仍禁不住打了一記寒顫。那股詭異、沉重的香水味彷彿牢牢緊跟她們每一個人,甚至濃烈瀰漫在大夥兒共用的浴廁牆壁之間。這種刺鼻的味道總是帶著一股膩死人不償命的甜味,猶如某種即將腐敗的果物。我用力撇撇嘴。不要。我才不要回去。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不回去。
「請問哪位?」
我先聽見聲音,然後才看見她。我把頭稍稍往後仰,炫目的陽光令我什麼也看不見。我舉手遮陽,設法擋掉部分陽光,這時,她的身形才終於呈現在我眼前,卻也被燦亮的白光分割成好幾片。
「愛麗絲?」我並未拔高音量,短暫陶醉在喊出她名字的喜悅中;「是我。」
第一章 愛麗絲
禮拜二是上市場的日子。
不只我,整座城市皆如此。里夫地區的婦女浩浩蕩蕩走下山,吹響序曲;她們的籃子、推車堆滿蔬果,巍顫顫地左右掛在驢背上。而坦吉爾則以熱情喧鬧作為回應:人群傾巢而出,街上擠滿男人女人、外國人和本地人。這堆指一指、那堆買兩斤,你討價我還價,最後掏出銅板換來一點點這個和一些些那個。這幾天,太陽似乎更形熾熱、更加燦亮,導致我的頸背曬得有如燒傷。
此刻,我站在窗前俯視下方爆滿的人群,暗自希望今天仍是禮拜一。然而我也知道,禮拜一永遠只是虛假的盼望、空幻的慰藉,因為禮拜二終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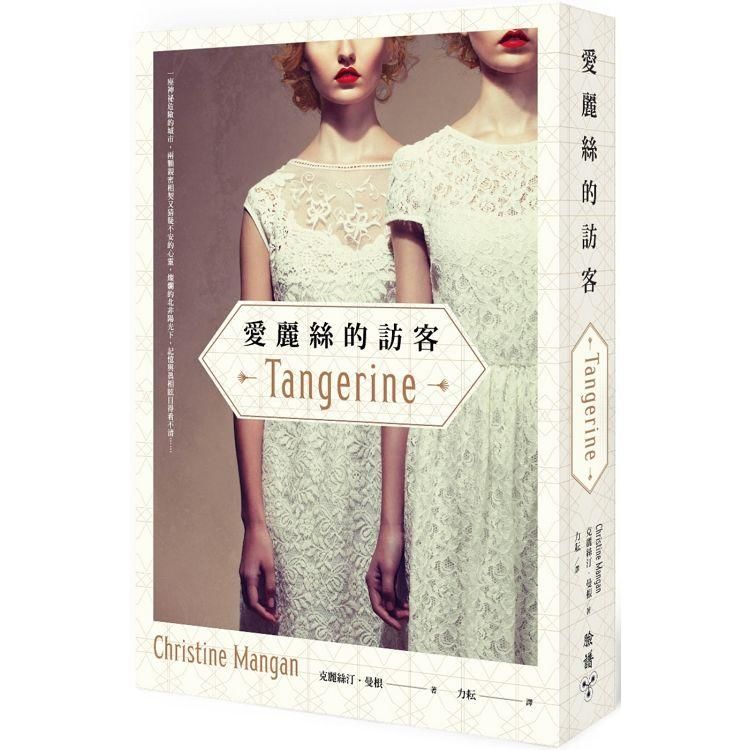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