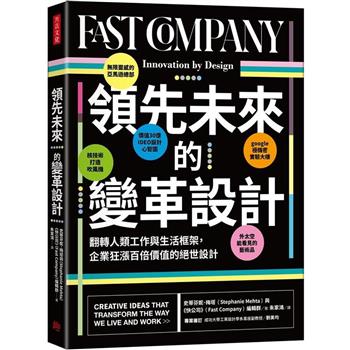作者序
拙作顧爾德傳能夠譯成中文,並由台灣商周出版社發行,我感到非常光榮,據我所知,台灣方面一向對西方音樂及西方音樂家非常熱情。我相信如果顧爾德還在世的話,他一定也很高興看到這本書的繁體中文版問世。他一生都對東方文化相當景仰(特別是華人文化與日本文化),因為他發現,對照到西方社會中一些不甚美妙的發展趨勢,東方文化提出了許多美學、道德、哲學上的另類見解,很值得西方採納。舉例而言,在華人藝術裡頭,他就感受到某種莊嚴、安頓、內省的品質,這些品質他認為都是藝術最高境界的象徵之一。事實上,他最寶貝的收藏之一,就是華人藝術家趙無極的一幅油畫,這幅畫掛在他牆上超過二十年之久。
我的這本書不過就是顧爾德「死後暢銷」的最新佐證,而「死後暢銷」這個現象也已經證明是顧爾德故事中最精彩的環節之一。他已經死了超過二十年了,而如今他卻在世界各國吸引到比過去更多的樂迷和聽眾。(目前為止,繁體中文版是我這本書的第七個語言版本,此前已有法文版、義大利文版、德文版、西班牙文版、俄文版與日文版發行問世。)對我而言,顧爾德「死後暢銷」的現象可以說是一大激勵與鼓舞,不僅因為我也是他的樂迷,更因為他在我生涯發展中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我第一次認識顧爾德是在一九八二年他過世那時候,那時正值我敏感、容易受影響的十九歲那一年,而他帶給了我一個強烈而直接的影響。顧爾德在事業與思想上所激發出來的種種觀點,首度向我顯示,原來音樂不僅是娛樂而已、還可以是這麼地饒富智性,我對這個深感興趣。於是我一頭栽入顧爾德的思想中,而這引發我日後想要念音樂、想把音樂當成未來正業的念頭,所以一九八三年秋天,我真的到大學裡面念音樂了。整個大學期間,我持續追逐我對顧爾德的興趣,最後一九九六年,我學生生涯的最後計畫、也就是我的博士論文,也決定以顧爾德的美學思想、鋼琴風格、和音樂詮釋為內容去完成。(這本論文於一九九七年在英國出版成書:《葛蘭?顧爾德:作品的演繹者》〔Glenn Gould: The Performer in the Work〕)。
拙作這兩本書,不僅是我對顧爾德的興趣臻於高點的象徵;同時也代表了我對這位決定我一生志業的藝術家的感激。源於這個理由,這兩本書所獲得的成功,特別是這本傳記書能夠在國際上流通、流通到台灣這麼遠的地方,對我來說真是相當令人歡欣。能夠看到這本書的繁體中文版、以及能夠看到這本書由一個顧爾德生前所景仰的文化地區來出版,則是更加令人心花怒放。
—凱文.巴札那
布蘭特伍德灣,英屬哥倫比亞,加拿大
二00七年十二月七日
導讀
可辨但不可解——顧爾德的永恆之謎 焦元溥
俄國鋼琴家,茱麗亞音樂院教授雅布隆絲卡雅(Oxana Yablonskaya〉,曾告訴我她親眼見到的一則趣事。
有一年她帶學生至牛津大學朝聖,接受當代巴哈祭酒杜蕾克(Rosalyn Tureck〉指導。「那是個讓人昏昏欲睡的下午,杜蕾克年事已高,學生彈琴時她其實多在閉目養神,我們也不知道她究竟聽進去多少。」突然間,在樂曲某一關鍵處,學生彈出一個極為特別,但一聽就知道是顧爾德的句法和裝飾音——
「No!No!」嚇了大家一跳,沉睡中的杜蕾克竟立刻站了起來。「老太太搖搖頭,直接走向鋼琴,親自把那段『糾正』成她要的樣子。」
先不提這二十世紀兩大巴哈名家彼此間的瑜亮情結,讓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雅布隆絲卡雅的感嘆——「唉,顧爾德就是顧爾德!那怕是一個句子、一個裝飾音,他就是讓你認得出來,而那也永遠屬於顧爾德,怎麼學都不可能變成你的!」
是的,這就是顧爾德。
直到今日,顧爾德當年的音樂魔力仍是不朽傳奇。1957年五月七日,年方二十四,在蘇聯沒沒無聞的顧爾德於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大廳登台,開演時座位不過半滿。怎知中場休息一到,全廳聽眾竟瘋狂衝出:樓上拉樓下,學長招學弟,音樂院全宿舍的學生蜂擁而至,電話亭外排滿了人,寒風中爭相走告快來見證天才!隔天不只莫斯科剩下三場賣光,之後到列寧格勒也一樣轟動,音樂廳在舞台上擺滿座位仍不能滿足需求,最後只得把人硬塞進站票區。坐票賣了一千三,站票竟也賣了一千一,還得出動警力控管秩序!在他從未去過的法國,1974年導演蒙賽瓊(Bruno Monsaingeon〉為他拍攝的《音樂之道》(Chemins de la musique)播出後竟也反應熱烈,不僅為他帶來持久聲望,錄音銷售數字更火紅到連唱片公司都難以置信。
但更令人驚訝的,是顧爾德過世後名聲非但不墜,還能水漲船高,連唱片銷量也節節高升,賣得比他生前還好。去年為紀念顧爾德逝世二十五週年,新力唱片整理出顧爾德大全集,一上市就造成熱賣。不管你喜不喜歡,從加拿大到日本,全世界都知道顧爾德,也都在討論顧爾德。甚至「顧爾德」本身已成為一抽象象徵,自小說到電影,由音樂至舞蹈,每每成為其他創作的靈感來源與文本材料。二十世紀音樂家中,大概只有女高音卡拉絲(Maria Callas〉能和「顧爾德現象」相提並論;但卡拉絲畢竟是公眾人物,情史緋聞無一不是新聞,顧爾德卻在死前就退出舞台近二十年,生前更以避世聞名。至今,顧爾德仍是熱門話題,甚至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死後暢銷熱潮也已引發研究探討,成為二十世紀至今最獨特的音樂現象之一。
究竟顧爾德的魅力從何而來?為何關於他的討論歷久不衰,甚至愈來愈熱?撇開所有偶像崇拜與行銷策略,最簡單地說,顧爾德滿足了成為長久話題人物的兩大條件。
三位一體:音樂家、作家、廣播大師
首先,顧爾德夠豐富,甚至太過豐富。
對一般愛樂者而言,顧爾德是技藝高超,名滿天下的鋼琴名家。雖然他曲目出奇,在巴哈和當代音樂之外幾乎放棄所有浪漫派作品——如顧爾德所言,巴哈《賦格的藝術》和華格納《崔斯坦與伊索德》之間的百年空白:他覺得貝多芬好戰,舒伯特囉唆,更不能忍受舒曼、孟德爾頌、蕭邦、李斯特等一脈炫技傳統。在德奧典範之外,其他國家作品都遭到他的質疑,更不用說他不喜歡芭蕾和義大利歌劇——但他錄音等身,即使對其不甚喜愛的作品(如莫札特鋼琴奏鳴曲〉也可見演奏,獨奏、協奏、室內樂皆不擋,甚至還跨足大鍵琴、管風琴和指揮。透過大量錄音,愛樂者得以見識顧爾德極其偏食卻又至為飽足的音樂菜單,並藉由其演奏認識他孤奇獨絕的藝術天地。就一位音樂演奏家而言,光是錄音作品,顧爾德就足以形成一門學問讓後人鑽研。
但顧爾德自己卻更希望是一位作曲家。早在十五、六歲時,他就已決定自己的終極志願是成為作曲家,在全心作曲後能把舞台演奏拋諸腦後。雖然顧爾德的確具有作曲天分和想法,也留下些許作品,但這個願望在他缺乏專業訓練的音樂寫作下終未能實現。但即使他的想法和概念未能由作品落實,或理想與實踐之間落差太大,光是想法本身仍然值得探索,而所留下來的《弦樂四重奏》等曲雖有明顯缺點,卻也因構想出奇而令人側目,讓人持續討論。
不過寫不出的作品要如何被知曉與討論呢?這就得歸功於顧爾德的作家身份。顧爾德愛寫能寫,自小就以一種炫學筆法鋪陳滔滔雄辯,也發展出獨門顧式艱澀用字和冷笑話風格。迄今已有超過一千五百頁的顧爾德著述問世,而這還不包括他的公開演講以及廣播節目稿。他熱愛為自己的唱片寫作曲解,更在1964年算起的十年間在不同報刊上發表數十篇文章。顧爾德也寫日記,甚至自己的病史報告研究,而在1984年《顧爾德文摘》(Glenn Gould Reader)創刊後,他生前文章、腳本、信件、訪談等各式寫作也都被一一整理,各種版本的顧爾德文選也不斷發行,譯成多國語言在世界各地造成熱烈迴響。無論是早期冗長不順的語句、浮誇不實的耍寶、矯飾造作的文字遊戲,或是四十歲後在長期寫作中修練出的自如揮灑和幽默魅力,顧爾德的文章可以偏頗惱人,也可極盡搞笑,但總是言之有物,引人一看再看。大量文字也讓顧爾德的存在感更加真實,和眾多錄音一同呈現他的想法,逼人無法忽略他的見解。
顧爾德的寫作雖然風格獨具,但他影響力更大,也更專業的一門工夫,則是他所製作的廣播和電視節目。顧爾德做節目完全樂在其中,不計成本,更把他的完美主義和創造狂想發揮至極,其中又以廣播為最。他自寫腳本,親自剪接,甚至在多年研習下把自己訓練成當時全世界最高竿的超技剪接師。他的廣播節目一如音樂,主題、形式和風格三者之間都有緊密聯繫,更發展出如賦格曲般的「對位式廣播」,所謂「音樂作曲法」的全新廣播模式。在顧爾德自創的廣播風格中,他將素材構合出有意義的全新混成品,以絕妙想像、組織能力、音韻接合和剪接技巧,造就獨一無二的廣播節目,成品甚至根本可以被視為音樂創作。顧爾德的廣播不但在加拿大造成轟動,也在國際間廣受矚目,是自成一家的經典。
本地讀者若知道廣播在歐美的重要性,就不難想像對聽眾而言,顧爾德絕對不只是一位音樂家,更是動見觀瞻的廣播節目家。而一人身兼音樂家、作家與廣播大師,顧爾德的人生雖短,卻豐富無比,一旦為其魅力所迷,他所留下的世界真能讓人以一生探索。同樣是鋼琴家,霍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和李希特(Sviatoslav Richter〉的演奏魅力雖也歷久不衰,但他們都沒有顧爾德的多方觸角與大量論述;羅森(Charles Rosen〉和布倫德爾(Alfred Brendel〉雖然著作豐富,但他們的演奏又缺乏顧爾德的獨特魅力。平心而論,顧爾德能有如此深遠巨大的影響力,唱片公司行銷手法和媒體渲染不過是推波助瀾,真正的原因還是在於顧爾德的豐富與獨特。
不覺得自己是怪人的怪人
沒錯,除了「豐富」之外,顧爾德還必須「獨特」,而他的獨特還不只是「獨特」,簡直是「怪異」。眾多錄音、文字、廣播、影像為天下「顧迷」提供源源不絕的討論食糧,但能成為如此熱門話題,其讓世界各地愛樂者決定大塊朵頤的誘因,卻往往是顧爾德的「怪異」。雖然他自己一點兒也不覺得自己怪,但顧爾德還真是怪,根本是矛盾的化身:他二十出頭就天下聞名,晉身全球最受尊崇的音樂家,卻在三十一歲退出舞台,和音樂會與掌聲徹底告別。年輕時的顧爾德面貌俊美脫俗,但他的彆扭姿勢、怪異坐姿、手舞足蹈加哼唱的演奏,怎麼說都讓人難以覺得「正常」。
說起顧爾德的怪事異行,那真是一本書也寫不完(也早已成為諸多文章與書籍的內容〉,但即使回到他的事業,那也是一則罕見的弔詭大全。可不是嗎?經過有心人士數十年努力,眼看大鍵琴將要再度站回早期音樂舞台而成為主流時,顧爾德竟以一曲《郭德堡變奏曲》就讓世人徹底傾倒於鋼琴演奏的巴哈魅力,一張唱片就改變音樂演奏史的走向——而顧爾德那時對加拿大以外的世界而言,甚至只是一個不知名的多倫多少年!此外,他的音樂追求理性,表達卻充滿浪漫情感,精心佈局下盡是深情款款,但情感之外卻又往往是諷刺與反叛。無論名氣多高,顧爾德從不妥協,排出曲目依然故我,但也唯有他能照樣以乖逆曲目吸引大眾,只是他的選曲也沒一般人想像中的前衛:雖然對新音樂發展保持關心,顧爾德的音樂口味卻在青少年時定型,對新潮流幾乎漠然以對。簡言之,顧爾德只要做自己,讓世界來遷就他而非他去適應世界。他將不必要的意外和干擾降到最低,並以縝密的規範條件追求絕對控制。
但這樣一個幾乎過著隱居生活的人,卻留下大量錄音、文字和廣播,以他想要的方式努力讓世界知道自己的想法,造成極其深遠的影響。當顧爾德的豐富和怪異撞在一起,所點燃的就是永不熄滅的討論熱火。他的演奏可以傳統也可以創新,而其創新說好聽是不墨守成規,措詞強烈些就是離經叛道,只是顧爾德的叛逆背後卻有深厚學養。他讓聽眾反其道推敲琢磨,在極端表現中上下求索,逼出作品的抽象形貌。多數顧爾德的「創新」演奏,乍聽之下令人錯愕疑惑,有時還會被激怒,但聆賞者若能回到作品,仔細研究顧爾德和樂譜指示故意相反的表現,卻往往能發現他清楚一貫的詮釋邏輯,甚能因此更加了解作品。像顧爾德的莫札特鋼琴奏鳴曲錄音,根本是不懷好意的嘲諷之作。但若細聽他在這些作品中所展現的速度運用與結構設計,再對比他在其真心讚美的海頓奏鳴曲中的曲式處理,聽者就能看出顧爾德所欲嘲弄為何。
然而始終不變的,是顧爾德對「對位法」的熱愛與執迷。無論是演奏、作曲或廣播,顧爾德都以對位法技巧與美學表現一切。晚期顧爾德演奏愈來愈理性,也往往將早期的清冷抒情轉化為更嚴密的抽象思維。但即使是我個人並不喜愛,甚至感到失望的顧爾德巴哈《英國組曲》錄音,若能以對位法的眼光審視,就能察覺在那幾乎全然拉平的線條中,其實蘊藏著純粹的邏輯與秩序之美,樂句思索與表現更無一絲茍且。在大部份情況下,顧爾德的怪其實「有所本」,並非單純譁眾取寵。就像顧爾德自己所言:
好,假設說這個全新版本完全建立在一個「怪」字上面,你一心只想「撼動人心」,希望樂評家對你這「撼動人心」的版本寫出可怕的評論,那麼我還是會說:算了吧。因為很明顯,「作怪」這個目的並不足以支持你去做任何事情。「怪」的背後一定要有某個強烈、具說服力的理由來支撐。一旦你有能耐同時搞定這兩件事,也就是既把貝多芬彈得很怪,而且這「怪」又怪得很有道理,大家都不得不服你,那麼,我會拜託你,無論如何一定要把它出成唱片。我確信這就是做唱片的理由。
但有沒有實在解釋不通,根本是顧爾德全然作怪的時候呢?當然有,而且還為數不少!這時「顧迷」就能從豐富文本中搜尋他的看法,找出惡搞的理由,甚至自行整理出一套「顧式詮釋學」。像是他完全破壞結構、徹底消滅樂曲衝突性格的貝多芬《熱情》奏鳴曲錄音,其實詮釋上和他與伯恩斯坦大幅放慢的布拉姆斯《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就意義而言堪稱異曲同工。若進一步比對他以「和諧」為判準,認為懷森伯格(Alexis Weissenberg〉與卡拉揚合作的拉赫曼尼諾夫《第二號鋼琴協奏曲》是最佳協奏曲演奏的觀點,更可見其反英雄主義的一貫立場與音樂美學。但至於這能否再延伸解釋到顧爾德其他特殊演奏,「顧迷」永遠可以自顧爾德的文字與思想中找答案,在解謎過程中樂此不疲——事實上,顧爾德正是猜謎狂,他的音樂創作正像設計精巧的謎題,只是往往先把自己困住。但在音樂詮釋的領域裡,在別人的文本上,顧爾德的再創造讓他永遠成為出謎贏家,甚至顧爾德自己就是一個讓人好奇且著迷的大謎題,而他也永遠不吝惜給予解題線索。
驚豔巴札納
只是顧爾德這個謎可不比其演奏好解,至少他的話不見得完全可信。無論是文章或訪談,他常選擇性誇大其詞,或刻意在媒體面前裝腔作勢、自我標榜,甚至開玩笑地鬼扯亂講。讀者若見樹不見林地照單全收,對顧爾德的形象只會愈來愈模糊,最後只能歸納出他是個無法理解的怪人或瘋子,偏偏他的諸多奇異事蹟也加深世人如此印象。在這一點上,凱文.巴札納(Kevin Bazzana)所寫的《驚豔顧爾德》(Wondrous Strange: The Life and Art of Glenn Gould),堪稱關於顧爾德汗牛充棟的著作、研究與論述中,最全面周詳的解謎示範。巴札納自1995年起即擔任《葛蘭?顧爾德》國際雜誌編輯,前一本著作《葛蘭?顧爾德:作品的演繹者》(Glenn Gould: The Performer in the Work)探索顧爾德其樂,研究他的鋼琴演奏與詮釋,而《驚豔顧爾德》則討論爾德其人,從音樂家、作家、廣播電視人三個面向多所探討,自大量文件與調查考證中整理出顧爾德的真實面貌。在美學思考與藝術表現上,巴札納細心對比出荀白克思想對顧爾德的深刻影響,更用心追溯顧爾德的生長環境與師承,解釋顧爾德和「北方風格」的關係,並點出他並非如自己宣稱般幾乎自學而成;顧爾德對早期音樂的興趣和學養,甚至演奏風格,其實都受老師加雷洛(Alberto Guerrero〉影響甚深。
在顧爾德的人格特質和生活記錄上,一如老練而學養豐富的樂曲版本校訂者,巴札納能不被表象所惑,在許多衝突相悖的描述與記錄中看出那其實是銅板的兩面,自幽微交集中提綱挈領出顧爾德的思考與性格。巴札納眼中的顧爾德「特別」但非「怪異」,他不神格化或誇張顧爾德的成就,卻也絕不貶低任何顧爾德應得的讚美,讓主角同時閃耀天才與常人的光芒——而這正是多數顧爾德論述所不及之處。在寫作取材方面,巴札納行文頗見格調與品味,既能澄清諸多揣測傳聞,引例也不流於八卦雜事,甚至可說具體而微地表現出顧爾德的幽默諧趣。而全書章節設計和筆法則向顧爾德一生與《郭德堡變奏曲》致敬:《郭德堡變奏曲》主題在三十段變奏後悄悄重返,結尾即是開頭。而顧爾德以《郭德堡變奏曲》建立國際名聲,卻也在五十歲錄完此曲二次錄音後不久中風辭世,《郭德堡變奏曲》也等於是顧爾德的起點與終點。此書首篇「終曲(以序曲格式)」雖是引言,但若看至第六章結尾,卻會發現這其實也正是結論。本書開頭正是結尾的筆法,如《郭德堡變奏曲》般循環從頭,確實是非常「顧爾德風」的「音樂寫作」,也是難得的巧思。
當然,我們不見得要全盤接受作者對顧爾德行為的所有解釋。對於顧爾德的思想和人際關係,巴札納的整理分析確實令人信服,也提出清晰合理的文本溯源和綜觀各方意見後的審慎心得,但這並不代表他對顧爾德青少年時期起的個性解釋一樣詳盡。一方面是資料不夠,二方面是並非所有行為都有環境、文化或個人經驗上的解釋。巴札納試圖為顧爾德所有行為提出解釋,有些論點自顯得一廂情願。
此外巴札納雖是用心細心的顧爾德專家,但在討論顧爾德以外的人或事時,仍有資料或論述上的錯誤。他對范?克萊本(Van Cliburn)和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天才事蹟的稱讚,就誇大而未盡查證之責。有時他的解釋也稍嫌過度或缺乏重點;像是他支持顧爾德的論點,認為「對於他愛彈的那種音樂,他堅稱音樂廳剛好就是錯誤的發表場所:他愛彈結構上複雜,但在規模和語言上偏精巧親暱的作品,因為就音樂史實而言,這些作品的確幾乎沒有一首是作曲家當初設想要在大音樂廳為集體觀眾演出。」他的陳述雖然正確,但若進一步看音樂史,則絕大部份的鋼琴與大鍵琴作品(遠不只顧爾德喜歡演奏的〉,當時都不是為大音樂廳和集體觀眾演出,甚至連完整演出的機會都不大。顧爾德所愛之巴哈如此,所厭之舒伯特亦然,並不能以此為由來合理化顧爾德的見解。
又如巴札納花了一番工夫整理顧爾德心中的理想鋼琴,將顧爾德所要求的「打擊系統調快、琴鍵重量調輕、按鍵深度調淺、琴槌與鋼弦距離調近」等等指示以其演奏技法(手指導向〉和音樂美學(顧爾德曾表示他偏好大鍵琴而非鋼琴,而他喜愛的鋼琴音調則類似被刨潤的大鍵琴〉來解釋。但如果作者對鋼琴機械原理有更深刻的了解,並知悉其他鋼琴家對鋼琴構造的見解與要求,就會知道顧爾德對史坦威原廠標準的更動,其實和許多同樣調整設定的鋼琴家所見相似,包括霍洛維茲、普雷特涅夫(Mikhail Pletnev〉和齊瑪曼(Krystian Zimerman〉——換言之,顧爾德的調整雖然有其個人風格,但其實並不「特別」。這些鋼琴家所做的,其實是在保留現代史坦威音色與音量表現能力下,再融入十九世紀鋼琴之物理特性。顧爾德的巴哈演奏聽起來有大鍵琴風,那是他透過調整過後的樂器性能所塑造出的音樂效果,並不是那架鋼琴本身聽起來就是如此。這也是為何顧爾德的巴哈和早期音樂雖有「古風」,但同一架鋼琴仍能讓他表現荀白克等當代作品,聽眾卻不會認為他的亨德密特鋼琴奏鳴曲聽起來像是以大鍵琴演奏。不過就此點而言,幾乎所有討論顧爾德鋼琴者,其論述都犯了這倒果為因的錯誤,不能為此特別苛責巴札納。
謎樣的魅力 永遠的顧爾德
就音樂而認識顧爾德的愛樂者,透過《驚豔顧爾德》一書的整理分析,不但能充份了解並掌握顧爾德的音樂思考與演奏美學,更能窺見那音樂之外,顧爾德在文章與廣播中的斐然成就。但巴札納不曾忘記,鋼琴演奏是顧爾德吸引世界的開端,也是一切榮耀的來源與總結。無論世人如何評價,我永遠不會忘記,顧爾德在巴哈《三聲部創意曲》錄音中,那鋼琴色調的微妙變化,聲部線條的絕對控制,以及對位美學的燦然大觀,皆是舉世難再的音樂奇觀。而這也是在「豐富」與「特殊」之外,顧爾德永恆魅力的來源——他的怪異從來沒有比他的音樂表現更重要。在解釋一切之後,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顧爾德就是魅力的化身,而那是這位佈局大師所留下諸多詭題中,最迷人,也是唯一不可解的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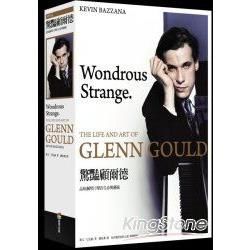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