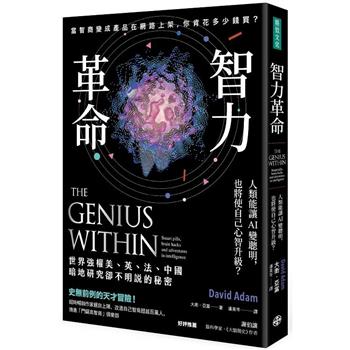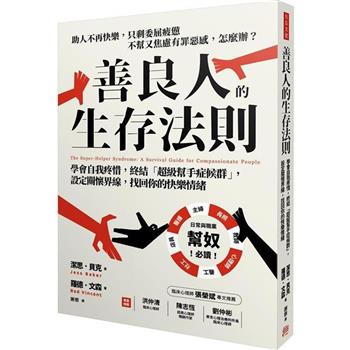「社團法人高雄市小鄉社造志業聯盟」由參與過莫拉克風災重建的工作者組成,扎根於高雄旗美九個行政區的社區。他們深知偏鄉社區資源極為有限,因此致力孕育在地人才與能量,讓彼此協力共創,互為資源,讓在地永續得以實踐。
秉持「以社區為本」的理念,小鄉藉由長期關懷及陪伴社區,逐步建立起在地網絡。他們也舉辦如「伴我一聲」社區廣播、「120公分的角度」影像發聲行動,以及木梓社區的「火把節」等培力活動,從社區的視角與需求出發,揉合在地元素,打造出社區與小鄉皆有感的行動方案。
本書介紹社區工作的概念與方法,藉由實務經驗呼應學說論述,深入爬梳小鄉如何以「融入社區」、「建構夥伴關係」與「舉辦在地活動」等策略,凝聚社區居民,讓地方長出自己的力量。
只要社區願意一起努力,他們就傾盡全力,這是──屬於小鄉的地方志業!
★一本社會工作與地方創生實務工作者不可錯過的珍貴參考!
本書特色
◆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黃肇新(臺灣全球社會力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蕭淑媛(前高雄縣政府社會處約聘社工督導)──專業推薦!
◆高雄旗美區,一群「另類社區工作者」秉持著「以社區為本」的理念,走出制度邊界,走入人群與土地深處,以從土地而生的實務智慧和在地知識,建構出主流方法以外的多元路徑!
◆一本社會工作與地方創生實務工作者不可錯過的珍貴參考!
各界推薦
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黃肇新(臺灣全球社會力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
蕭淑媛(前高雄縣政府社會處約聘社工督導)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劉美辰合著的圖書 |
 |
$ 410 ~ 411 | 小鄉的志業:在地深耕的實踐智慧
作者:黃彥宜、陳昭宏、張淑菁、賴梅屏、陳薇伊、葉晏慈、劉美辰合著 出版社: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25-06-24 語言:繁體書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小鄉的志業:在地深耕的實踐智慧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黃彥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退休教授。畢業於英國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社會工作研究學系博士班、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應用社會學組碩士班。研究和教學領域為社區工作、社會工作理論、綠社工和戲劇與社會工作。
長期致力於研究和整理臺灣社區組織的在地經驗與實踐智慧,並將其和學院知識連結與對話。希冀透過這樣的方式能和實務工作者一起共創知識,也協助尋求話語權的一線工作者發聲。
社團法人高雄市小鄉社造志業聯盟
成立於2014年,是一個從莫拉克風災重建累積經驗,深耕高雄旗美地區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推動多元的社區照顧與文化傳承工作。
透過持續在地陪伴與專業協作,小鄉專注於了解山村居民的真實需求,促進資源整合與跨領域合作,強化社區內部的支持網絡,在社會福利與地方發展間扮演重要的橋梁角色,致力於營造包容共好的生活環境,期望讓山村居民的生活更具尊嚴與韌性。
黃彥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退休教授。畢業於英國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社會工作研究學系博士班、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應用社會學組碩士班。研究和教學領域為社區工作、社會工作理論、綠社工和戲劇與社會工作。
長期致力於研究和整理臺灣社區組織的在地經驗與實踐智慧,並將其和學院知識連結與對話。希冀透過這樣的方式能和實務工作者一起共創知識,也協助尋求話語權的一線工作者發聲。
社團法人高雄市小鄉社造志業聯盟
成立於2014年,是一個從莫拉克風災重建累積經驗,深耕高雄旗美地區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推動多元的社區照顧與文化傳承工作。
透過持續在地陪伴與專業協作,小鄉專注於了解山村居民的真實需求,促進資源整合與跨領域合作,強化社區內部的支持網絡,在社會福利與地方發展間扮演重要的橋梁角色,致力於營造包容共好的生活環境,期望讓山村居民的生活更具尊嚴與韌性。
目錄
推薦序 基進社工學者的「鄉愁」書寫/王增勇
推薦序 像一粒芥菜種子/黃肇新
推薦序 同齊行,走出作伙ㄟ路/蕭淑媛
自 序 經驗可以不斷累積與延續/黃彥宜
前言
第一篇 從小鄉的經驗談社區工作的概念
第一章 什麼是社區
第二章 什麼是社區工作
第三章 社區工作的策略
第二篇 小鄉的志業:一百二十公分的角度、伴我一聲和婦女培力
第一章 充權和影像發聲
第二章 伴我一聲:小地方大鄉民社區電台
第三章 社區婦女的能動性
第三篇 災變中的韌性:小鄉和協力夥伴的努力
第一章 莫拉克風災的省思:綠社工的觀點
第二章 疫情下的社會復原力
第四篇 小鄉的模式:小鄉理監事和小鄉們的觀點
第一章 小鄉模式:社區為本的協作模式
第五篇 小鄉們的反思
地方重新來過的契機和經驗累積/陳昭宏
莫拉克翻轉了我的人生/張淑菁
跟著姊妹遇見小鄉/賴梅屏
我在小鄉的學習/陳薇伊
工作在社區,生活在地方/葉晏慈
小鄉幫助我成為更加成熟的大人/劉美辰
謝辭
參考書目
附件一 高雄縣/市莫拉克災後社區重建人力培育計畫
推薦序 像一粒芥菜種子/黃肇新
推薦序 同齊行,走出作伙ㄟ路/蕭淑媛
自 序 經驗可以不斷累積與延續/黃彥宜
前言
第一篇 從小鄉的經驗談社區工作的概念
第一章 什麼是社區
第二章 什麼是社區工作
第三章 社區工作的策略
第二篇 小鄉的志業:一百二十公分的角度、伴我一聲和婦女培力
第一章 充權和影像發聲
第二章 伴我一聲:小地方大鄉民社區電台
第三章 社區婦女的能動性
第三篇 災變中的韌性:小鄉和協力夥伴的努力
第一章 莫拉克風災的省思:綠社工的觀點
第二章 疫情下的社會復原力
第四篇 小鄉的模式:小鄉理監事和小鄉們的觀點
第一章 小鄉模式:社區為本的協作模式
第五篇 小鄉們的反思
地方重新來過的契機和經驗累積/陳昭宏
莫拉克翻轉了我的人生/張淑菁
跟著姊妹遇見小鄉/賴梅屏
我在小鄉的學習/陳薇伊
工作在社區,生活在地方/葉晏慈
小鄉幫助我成為更加成熟的大人/劉美辰
謝辭
參考書目
附件一 高雄縣/市莫拉克災後社區重建人力培育計畫
序
自序
經驗可以不斷累積與延續
黃彥宜
當被問及身為一位「資深學者」,我書寫小鄉一書時是帶有很多情感和情緒,還是客觀地站在一個學術研究的立場去思考和評述?因為該書完全沒看到小鄉的限制與缺點,好似在呈現一個完美的實施模式?我當下陷入很深的焦慮和不安,一路走來歷經三個國科會計畫案,我為什麼會寫成這樣?我是否該將其束之高閣?質性研究難免帶有主觀和情緒,我努力回想整個歷程,透過這篇自序誠實面對我當下的狀況,也讓讀者瞭解書寫這本書的初衷,當有人有興趣繼續瞭解小鄉時,可以跨越這本書的限制,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
當我在埔里的暨南國際大學任教時,拜訪了一些自九二一地震後一直留在當地的基金會和協會。其中聽到一句話讓我感受很深,一位在地震後看到很多無助和無依的老人,因而放棄自己的事業挺身投入照顧長者,從地震後堅持迄今的「村長」,她跟我說剛剛設立時,有一位社工系老師來訪評,跟她說:「妳不是社工,妳會不會以為妳在幫助他們,但卻反而害了他們?」後來我在埔里深入走訪時,發現一些基金會和協會雖然不是社工單位或由社工背景者來提供服務,卻充滿社工的理念和價值。我授課時經常安排學生參訪這些單位,也曾被部分學生質疑我是在教社工嗎?即使我很努力地在課堂將那些單位或主事者的作為和社工論述、價值與概念作連結,但不是社工做的,也不是社工當前的主流方法與實施領域,總讓部分學生充滿懷疑。也有研究生助理很貼心地提醒我:「老師你開的課社工師考試不會考,可能會倒課喔!」還真被她一語命中。這些讓我陷入很深地反省,我一路從大學至博士班唸的都是社工,我自認是「社工出品」,怎麼會變成離「社工路」愈來愈遙遠?
我曾邀請我在英國修習博士學位的恩師Professor Lena Dominelli到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紙教堂參訪,她跟我說:「Yenyi,紙教堂是綠社工很好的實踐基地,你要帶學生來這裡學習!」我當下有點豁然開朗。在臺灣經常聽到你不是社工!這是社工!那不是社工!的區分,加上曾被學生質疑我教的不是社工,一直讓我處於忐忑的狀態。而國際大師Lena她根本不在乎做出成果者的學科背景,而是看是否符合社工價值與精神,然後社工可以與之合作,注入社工學門的理念,繼而拓展新的實施領域和共創新知識。這些經驗讓我覺得釋然也重新激起一些熱情。我持續在課程中加入一些單元,讓學生認識埔里「非社工但又很社工」的單位,也組織他們參與在地社區行動,這都需要用到很多課外時間,過程辛苦又耗時,也難免引起一些學生的情緒反彈,我做了選擇,凡事都會有代價。曾有同學幾年後跟我說,她很懷念我以前的課,因為開展了她的視野!我自知個性急躁,不是一位諄諄善誘的老師,想必學生當時應該吃足苦頭,很開心她願意和我分享。
後來,我和當時在長榮大學任教的黃肇新老師參與了加拿大一個災後長期重建的研究案,團隊中有來自英國、澳洲、美國和印度的學者,我在其中深受啟發。每年的國際社工研討會議召開前,參與研究案的學者會提前二至三天抵達,召開兩天會議,大家很認真地分享各國的研究發現,然後很詳細地檢視目前社會工作的概念與論述有哪些是需要修正的,如「復原力」(resilience)原本都從心理學角度出發,關注個人特質和能力,但對社會工作而言,「社會復原力」(social resilience)是否更重要?在災難過程中經常面對不均和資源分配的不正義,權力是重要議題,在討論「充權」(empower)時不能忽略其核心的權力概念;大家也關注到婦女在災變過程中所展現的能量和在體制與社區脈絡下所受到的限制;也有討論是否創發新範型,如「綠社工」(green social work)或其他,但也有學者認為傳統「生態觀點」(ecological perspective)即提供很好的論述,只要加以修正即可。過程中大家都很仔細地分析、討論和做整理,並將討論結果彙整後交由當時任研討會keynote speaker的一位成員納入她的講稿中,目的不是在呈顯研究團隊的研究績效,而是社工就要把握任何一個發聲的機會做倡議和激發新議題的討論,這些經歷都讓我燃起滿滿的社工魂!
爾後,我參加了莫拉克風災重建期結束後的一個研討會,一群參與莫發克風災重建的在地工作人員認為重建尚未結束,災難不曾遠離,在會中他們宣布將成立「社團法人高雄市小鄉社造志業聯盟」持續重建工作,這是我認識小鄉的開始。後來因緣際會,小鄉社造志業聯盟工作人員想藉由參加一個研討會來發聲,因為時間有點趕,希望我能參與合作書寫。此後我也透過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案開始和位於旗山的小鄉工作團隊有較長期的合作。期間旗山的小鄉工作人員有所更迭,人數最高有五位,是跨學門的團隊,有社工、文學、護理和會展設計。當這本書的書寫告一段落,我重新回顧審視,我自覺書寫過程中我將情感與情緒重重地投入其中,以致這本書「長成」現在這個樣子。
原因之一是我的職涯一直在轉換工作,研究所畢業後我在高雄的國際商專擔任輔導老師,後高考及格,分別在屏東仁愛之家(現在改稱「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任職,然後轉至高雄醫學院(現在改稱高雄醫學大學)的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任教。唸完博士學位回來,曾任教於長榮大學、亞洲大學和暨南國際大學社工系。中間工作轉換有因為高考實習、出國唸書,或單純地想換一個地方居住、認識一個新社區以帶來新的教學刺激。外子當時任教嘉義縣的大學,我們定居在民雄鄉,我將民雄方圓百里內的社工系都教過了。這樣職涯的游移經驗,讓我對十多年一直「種」在當地,生活和工作幾乎沒有清楚劃分的小鄉充滿好奇。
其次是我長期教授社會工作理論,就讀碩士班時很感謝徐震教授在社區工作上的啟發,修讀博士班時繼續跟著Lena學習社區工作,我對理論充滿興趣,加上參與加拿大研究團隊的經驗,更讓我熱衷將在地經驗與社會工作和社區工作理論做結合。小鄉的工作人員敘事能力很強,他們的述說常讓我有滿滿的畫面,這些豐富素材讓我覺得可以穿梭串聯概念、方法和理論。書寫時我試圖在理論中融入本土在地素材,也因為太專注和熱衷這樣的連結,而造成在書寫上的盲點。我深知小鄉的運作有一些限制,從他們人員的流動,經費申請的不易,每位工作人員內心深處隱隱的徬徨與不確定,但書中並未談論或挖掘這些問題,討論到政府機關或其他單位時也常將他們當成「對照」經驗。但書寫的用意不在呈現小鄉的經驗都是對的,其他單位都不好,小鄉十多年來雖然受到很多肯定,尤其團隊多數非社工背景(今年有一位小鄉工作人員入社工學分班就讀),在經費申請上常遇到一些困難,也受到一些質疑。本書想突顯的是處於偏鄉「非主流」團隊的一些視角和觀察,而非在批評其他組織的作為。
小鄉的經費有六成來自政府,他們很多的理監事也因為原高雄縣政府社會處在風災前即長期投入社區培力和人才培育而有豐富的社區組織或參與經驗,這些都是小鄉發展的重要基礎,政府經費的配置對社區韌性的建立影響甚鉅。
在書寫小鄉一書期間,因為體檢而發現罹患肺腺癌第四期,當初幫我檢查的醫師說我若沒有好好治療只有六個月存活期。中間也因為種種治療和檢查而辦理提前退休,書寫也中斷。後轉至柳營奇美醫院接受曹朝榮榮譽院長的診治,他行醫四十多年,每次看診高達兩百人,從早上看到深夜,仍然不急不徐,仔細親切問診,而他也曾罹患舌癌,這樣的仁醫精神讓我深深地感佩。他說癌症治療都是不完美的,因為每種藥都會產生抗藥性,只能在不完美中求完美,這不只是醫學也是哲學議題。治療近三年,期間受到醫護人員細心照料,健保也幫我給付「貴森森」的癌症治療費用,還有親友們不斷地鼓勵與支持,那麼多人幫助我延長「存活期」,總覺得要做一些社會回饋,或許能用出版和版稅對偏鄉的在地組織有些支持,於是又開始著手修改小鄉一書的文稿,本書的收益將全數捐給「社團法人高雄市小鄉社造志業聯盟」。
我瞭解這本書有很多不足之處,需要大幅翻修,但一邊化療一邊修改,體力實有所不足,只能微幅調整,盡量在不完美中求完美。生命有其盡頭,知識和經驗可以不斷傳承、延續和累積。臺灣有很多優秀的在地團隊,小鄉只是其中之一,許多豐富的寶貴經驗,值得好好記錄和書寫,也希望後續對在地團體有興趣的夥伴,能跨越這本書的障礙與限制,繼續往上堆疊。
二○二五年一月六日
經驗可以不斷累積與延續
黃彥宜
當被問及身為一位「資深學者」,我書寫小鄉一書時是帶有很多情感和情緒,還是客觀地站在一個學術研究的立場去思考和評述?因為該書完全沒看到小鄉的限制與缺點,好似在呈現一個完美的實施模式?我當下陷入很深的焦慮和不安,一路走來歷經三個國科會計畫案,我為什麼會寫成這樣?我是否該將其束之高閣?質性研究難免帶有主觀和情緒,我努力回想整個歷程,透過這篇自序誠實面對我當下的狀況,也讓讀者瞭解書寫這本書的初衷,當有人有興趣繼續瞭解小鄉時,可以跨越這本書的限制,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
當我在埔里的暨南國際大學任教時,拜訪了一些自九二一地震後一直留在當地的基金會和協會。其中聽到一句話讓我感受很深,一位在地震後看到很多無助和無依的老人,因而放棄自己的事業挺身投入照顧長者,從地震後堅持迄今的「村長」,她跟我說剛剛設立時,有一位社工系老師來訪評,跟她說:「妳不是社工,妳會不會以為妳在幫助他們,但卻反而害了他們?」後來我在埔里深入走訪時,發現一些基金會和協會雖然不是社工單位或由社工背景者來提供服務,卻充滿社工的理念和價值。我授課時經常安排學生參訪這些單位,也曾被部分學生質疑我是在教社工嗎?即使我很努力地在課堂將那些單位或主事者的作為和社工論述、價值與概念作連結,但不是社工做的,也不是社工當前的主流方法與實施領域,總讓部分學生充滿懷疑。也有研究生助理很貼心地提醒我:「老師你開的課社工師考試不會考,可能會倒課喔!」還真被她一語命中。這些讓我陷入很深地反省,我一路從大學至博士班唸的都是社工,我自認是「社工出品」,怎麼會變成離「社工路」愈來愈遙遠?
我曾邀請我在英國修習博士學位的恩師Professor Lena Dominelli到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紙教堂參訪,她跟我說:「Yenyi,紙教堂是綠社工很好的實踐基地,你要帶學生來這裡學習!」我當下有點豁然開朗。在臺灣經常聽到你不是社工!這是社工!那不是社工!的區分,加上曾被學生質疑我教的不是社工,一直讓我處於忐忑的狀態。而國際大師Lena她根本不在乎做出成果者的學科背景,而是看是否符合社工價值與精神,然後社工可以與之合作,注入社工學門的理念,繼而拓展新的實施領域和共創新知識。這些經驗讓我覺得釋然也重新激起一些熱情。我持續在課程中加入一些單元,讓學生認識埔里「非社工但又很社工」的單位,也組織他們參與在地社區行動,這都需要用到很多課外時間,過程辛苦又耗時,也難免引起一些學生的情緒反彈,我做了選擇,凡事都會有代價。曾有同學幾年後跟我說,她很懷念我以前的課,因為開展了她的視野!我自知個性急躁,不是一位諄諄善誘的老師,想必學生當時應該吃足苦頭,很開心她願意和我分享。
後來,我和當時在長榮大學任教的黃肇新老師參與了加拿大一個災後長期重建的研究案,團隊中有來自英國、澳洲、美國和印度的學者,我在其中深受啟發。每年的國際社工研討會議召開前,參與研究案的學者會提前二至三天抵達,召開兩天會議,大家很認真地分享各國的研究發現,然後很詳細地檢視目前社會工作的概念與論述有哪些是需要修正的,如「復原力」(resilience)原本都從心理學角度出發,關注個人特質和能力,但對社會工作而言,「社會復原力」(social resilience)是否更重要?在災難過程中經常面對不均和資源分配的不正義,權力是重要議題,在討論「充權」(empower)時不能忽略其核心的權力概念;大家也關注到婦女在災變過程中所展現的能量和在體制與社區脈絡下所受到的限制;也有討論是否創發新範型,如「綠社工」(green social work)或其他,但也有學者認為傳統「生態觀點」(ecological perspective)即提供很好的論述,只要加以修正即可。過程中大家都很仔細地分析、討論和做整理,並將討論結果彙整後交由當時任研討會keynote speaker的一位成員納入她的講稿中,目的不是在呈顯研究團隊的研究績效,而是社工就要把握任何一個發聲的機會做倡議和激發新議題的討論,這些經歷都讓我燃起滿滿的社工魂!
爾後,我參加了莫拉克風災重建期結束後的一個研討會,一群參與莫發克風災重建的在地工作人員認為重建尚未結束,災難不曾遠離,在會中他們宣布將成立「社團法人高雄市小鄉社造志業聯盟」持續重建工作,這是我認識小鄉的開始。後來因緣際會,小鄉社造志業聯盟工作人員想藉由參加一個研討會來發聲,因為時間有點趕,希望我能參與合作書寫。此後我也透過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案開始和位於旗山的小鄉工作團隊有較長期的合作。期間旗山的小鄉工作人員有所更迭,人數最高有五位,是跨學門的團隊,有社工、文學、護理和會展設計。當這本書的書寫告一段落,我重新回顧審視,我自覺書寫過程中我將情感與情緒重重地投入其中,以致這本書「長成」現在這個樣子。
原因之一是我的職涯一直在轉換工作,研究所畢業後我在高雄的國際商專擔任輔導老師,後高考及格,分別在屏東仁愛之家(現在改稱「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任職,然後轉至高雄醫學院(現在改稱高雄醫學大學)的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任教。唸完博士學位回來,曾任教於長榮大學、亞洲大學和暨南國際大學社工系。中間工作轉換有因為高考實習、出國唸書,或單純地想換一個地方居住、認識一個新社區以帶來新的教學刺激。外子當時任教嘉義縣的大學,我們定居在民雄鄉,我將民雄方圓百里內的社工系都教過了。這樣職涯的游移經驗,讓我對十多年一直「種」在當地,生活和工作幾乎沒有清楚劃分的小鄉充滿好奇。
其次是我長期教授社會工作理論,就讀碩士班時很感謝徐震教授在社區工作上的啟發,修讀博士班時繼續跟著Lena學習社區工作,我對理論充滿興趣,加上參與加拿大研究團隊的經驗,更讓我熱衷將在地經驗與社會工作和社區工作理論做結合。小鄉的工作人員敘事能力很強,他們的述說常讓我有滿滿的畫面,這些豐富素材讓我覺得可以穿梭串聯概念、方法和理論。書寫時我試圖在理論中融入本土在地素材,也因為太專注和熱衷這樣的連結,而造成在書寫上的盲點。我深知小鄉的運作有一些限制,從他們人員的流動,經費申請的不易,每位工作人員內心深處隱隱的徬徨與不確定,但書中並未談論或挖掘這些問題,討論到政府機關或其他單位時也常將他們當成「對照」經驗。但書寫的用意不在呈現小鄉的經驗都是對的,其他單位都不好,小鄉十多年來雖然受到很多肯定,尤其團隊多數非社工背景(今年有一位小鄉工作人員入社工學分班就讀),在經費申請上常遇到一些困難,也受到一些質疑。本書想突顯的是處於偏鄉「非主流」團隊的一些視角和觀察,而非在批評其他組織的作為。
小鄉的經費有六成來自政府,他們很多的理監事也因為原高雄縣政府社會處在風災前即長期投入社區培力和人才培育而有豐富的社區組織或參與經驗,這些都是小鄉發展的重要基礎,政府經費的配置對社區韌性的建立影響甚鉅。
在書寫小鄉一書期間,因為體檢而發現罹患肺腺癌第四期,當初幫我檢查的醫師說我若沒有好好治療只有六個月存活期。中間也因為種種治療和檢查而辦理提前退休,書寫也中斷。後轉至柳營奇美醫院接受曹朝榮榮譽院長的診治,他行醫四十多年,每次看診高達兩百人,從早上看到深夜,仍然不急不徐,仔細親切問診,而他也曾罹患舌癌,這樣的仁醫精神讓我深深地感佩。他說癌症治療都是不完美的,因為每種藥都會產生抗藥性,只能在不完美中求完美,這不只是醫學也是哲學議題。治療近三年,期間受到醫護人員細心照料,健保也幫我給付「貴森森」的癌症治療費用,還有親友們不斷地鼓勵與支持,那麼多人幫助我延長「存活期」,總覺得要做一些社會回饋,或許能用出版和版稅對偏鄉的在地組織有些支持,於是又開始著手修改小鄉一書的文稿,本書的收益將全數捐給「社團法人高雄市小鄉社造志業聯盟」。
我瞭解這本書有很多不足之處,需要大幅翻修,但一邊化療一邊修改,體力實有所不足,只能微幅調整,盡量在不完美中求完美。生命有其盡頭,知識和經驗可以不斷傳承、延續和累積。臺灣有很多優秀的在地團隊,小鄉只是其中之一,許多豐富的寶貴經驗,值得好好記錄和書寫,也希望後續對在地團體有興趣的夥伴,能跨越這本書的障礙與限制,繼續往上堆疊。
二○二五年一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