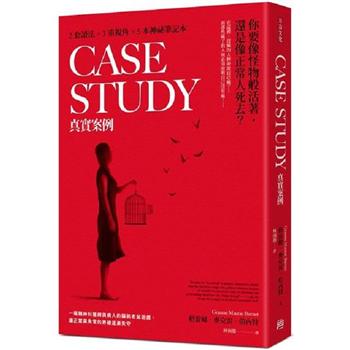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原文 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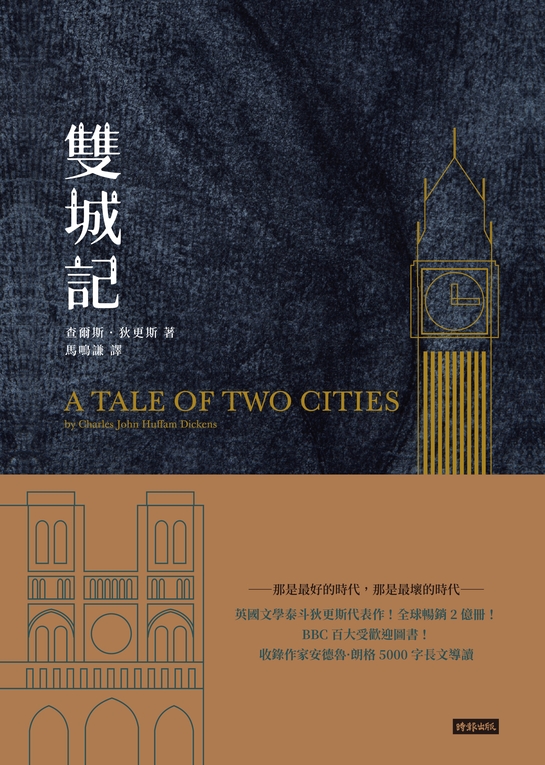 |
$ 336 ~ 432 | 雙城記 (電子書)
作者:原文 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 / 譯者:馬鳴謙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0-03-2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 初版  2 則評論 2 則評論  共 1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1757年12月,巴黎的年輕醫生曼內特,被帶往侯爵家出診,不料卻目睹了殺人事件。他決心為受害者伸張正義,結果卻遭了算計,被祕密關進巴士底獄。他的妻子大受打擊,不久便去世了,去世前託付友人將女兒露西帶到倫敦撫養。十八年後,長大成人的露西,突然得到父親的消息,她從倫敦趕往巴黎,父女終得團聚。
父女兩人返回倫敦的途中,邂逅了達尼,露西和達尼情愫漸生,並論及婚嫁,然而,曼內特見到達尼時總是心神不寧,原來這位法國來的年輕人正是當年陷害醫生的侯爵的侄子。不過,法國大革命爆發時,達尼為了營救家中老僕,自願回到法國,反而遭到逮捕入獄,眼看命在旦夕,幸虧和達尼身材、外貌皆相似的英國律師卡爾頓出手搭救……
「我現在所做的事,遠比我做過的一切都更加美好;
我將獲得的休憩,遠比我知道的一切都更加安逸。」
狄更斯在書中運用了很多對稱、排比,比如英國之於法國、卡爾頓之於達尼,在敘述場景時更是充滿畫面與音樂感,如手拉手繞圈旋轉的卡瑪奧勒舞、面對面搖動磨刀石的男人,狄更斯運用種種文學手法,構築出一部高潮迭起、結構完整的鉅作。
作者簡介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1870)
征服世界的文學大師,極受歡迎的英國文豪。
全名查爾斯•約翰•赫法姆•狄更斯,出生於英國南部樸茲茅斯,其父是海軍職員。童年時家道中落,一度被迫輟學,但天賦出眾,聰明好學。
十歲前,讀盡父親藏在閣樓裡的全部古典小說。十二歲時,為補貼家用,去皮鞋作坊當童工,在磨難中成長。
二十一歲時,心驚膽戰將沒有署名的處女作投稿給雜誌,發表後受到巨大鼓舞。二十四歲時,長篇處女作《匹克威克外傳》出版,頗受好評;同年結婚、劇作上演。狄更斯總共創作了十四部長篇小說、數百篇短篇小說和散文。
為了紀念狄更斯,很多地方每年都會舉辦狄更斯節。
經典代表作:《匹克威克外傳》、《孤雛淚》、《小氣財神》、《塊肉餘生記》、《雙城記》、《遠大前程》。
譯者簡介
馬鳴謙
作家,歷史及佛學研究者,一九七○年出生於蘇州。
著有長篇小說《隱僧》、《無門訣》、《合歡樹下》、《降魔變》。
譯有奧登文集數種,其中《奧登詩選:1927-1947》入選多家媒體年度十大好書榜單。二○一八年簽約作家榜,傾心翻譯《雙城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