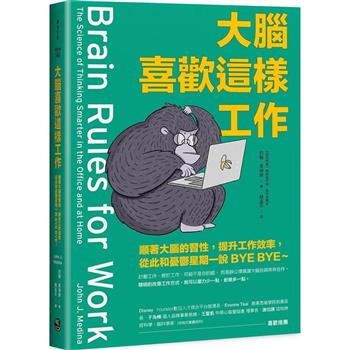2010年改編拍成同名電影,2011年榮登台北電影節開幕片!
我沒料想到它是會有療效的,只是單純的寫下自己幼年的故事,而當它已成為完整的初稿時,我再回頭讀它,我才發現自己今天的某些行為,是因當時發生的某些事件所造成,像是疑惑有了解答,一些生命中的傷口似乎有了出口……
─ 史奈傑
味覺記憶著我們的人生,
當味蕾在某一刻碰觸到熟悉的味道,
過去便一幕幕重現……
童年是作家的存摺,而味覺記憶便是留存童年的防腐劑。
這是一個飢餓男孩的記憶。
那記憶從吐司開始,史雷特的文字接連烹煮出一段段故事……
亨氏海綿蛋糕,是每個星期日的午餐歡笑。
和母親一起做的肉餡餅,是母親預先對他訴說的告別。
像吻一樣柔軟甜蜜的棉花糖,是父親對他的呵護。
蛋白酥檸檬派,是他心裡對後母的違抗。
手工黑李子果醬,是14歲的他那極度緊張的第一次烹飪課。
澄汁鴨胸,是他的初戀……
《吐司》不只是一位偉大廚師的傳記,不僅僅是能觸動你味覺體驗的發酵粉,它是每個人對生命的成長體悟,以及追求夢想時都有的挫折與掙扎。
得獎紀錄
榮獲2003年英國書卷獎之「年度最佳傳記獎」!
作者簡介
史奈傑(Nigel Slater)
英國國寶,1958年生,是英國知名廚師與作家,被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譽為「英國國寶」!
他已出版過多本膾炙人口的暢銷書,包括經典的《Real Fast Food》、《Real Cooking》,以及獲獎無數的《Appetite》。他為《美麗佳人》雜誌與英國《觀察家報》撰寫叫好又叫座的專欄長達十多年,英國國家廣播公司著名的紀錄片影集「Arena」也拍攝他的專輯。
《吐司:敬!美味人生》於2003年榮獲英國書卷獎之「年度最佳傳記獎」;「WH史密斯讀者票選獎」選為「最佳傳記獎」;「安德魯西蒙獎」;「觀察家報年度當月美食書獎」、「格蘭菲迪年度書卷獎」,並入選為「星期日泰晤士報暢銷書」。
譯者簡介
林靜華
曾獲得民國69年行政院「兒童圖書著作金鼎獎」,歷任聯合報系歐洲日報編譯組副主任。譯作有:納尼亞傳奇《黎明行者號》、《最後的戰役》;《深夜小狗神秘習題》;《名廚吃四方》;《上帝不眨眼》;《媽媽這一行》;《漂泊紳士》等書。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