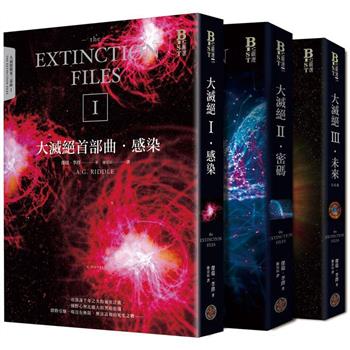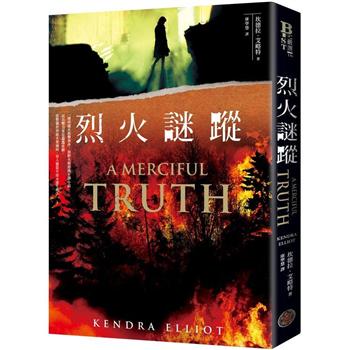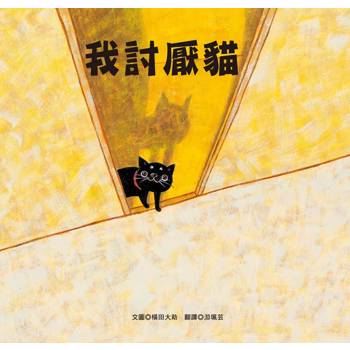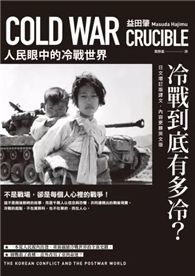誰叫你不聽話,闖進了我的秘密……
地下室中囚禁著可割可棄的蒐藏品,
絲質內衣褲散落一地、鎖鏈叮噹作響,
還瀰漫著滿足的味道……
紐約市的人口很多,在這人山人海中,想成名很難,要隱姓埋名卻很簡單。這裡是連續謀殺案發生的完美之地,平均每日都有六百人死亡。若殺了人想棄屍,只要藏回人潮裡就行。馬文是名不得志的編劇,時常自這個都市的犯罪獲得大量靈感,甚至曾隨機跟蹤陌生女子返家。儘管如此,他揚言自己可不是什麼殺手,只是為了寫作劇本而蒐集素材。馬文熱衷於帶著劇本到各大知名電影人的豪宅前站崗,以便能堵到電影人本尊、親手奉上自己的作品,就算時常被警衛驅趕也在所不惜。
馬文怪異的行徑吸引了兩名紐約警探的注意:凶悍的黑人探員透納,以及美麗的白人女探員瑪辛柯。兩人正在調查一起連續殺人案,他們發現馬文的生活背景和生活習性都意外符合凶手的特徵。但狡猾的馬文也不是省油的燈,除了對瑪辛珂有諸多遐想之外,他還打算設計陷害老是對他惡言相向的透納。
依然逍遙法外的神祕凶手在地下室中囚禁著一位性感女子莎拉,凶手在地下室裝設了偷窺孔,一方面滿足窺視的癖好,另一方面也監視莎拉的行動,凶手訓練著莎拉滿足自己各式各樣的慾望,若有不從便會毒打和電擊她。
狡猾的馬文在身為劇作家的同時也會是一名連續殺手嗎?性感美麗的人質和慾望橫流的地下室到底在哪裡?是真有其事、還是只存於馬文的狂想中?當真相被藏匿在不見天日之處,偶然闖入的人又必須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作者簡介:
史蒂芬.萊瑟 ﹝Stephen Leather﹞
新一代驚悚大師 ※ 2011年英國出版界百大影響人物
萊瑟出生於1956年,他當過生化學家、採石工人、加油站服務員、麵包師傅、酒保與稅務局員工,並在數家重要報紙(如泰晤士報、每日鏡報)擔任記者10年,直至36歲才開始全職寫作小說,著作不斷。
2010年的聖誕前夕,亞馬遜網路書店甫於英國推出電子書商場,萊瑟以高明的商業頭腦,成功將書推至暢銷書榜第三名,銷量直逼《龍紋身的女孩》。次年的亞馬遜電子書世界排行榜中,他的作品銷售量已在英國作家中位列第二,甚至被雜誌票選為英國出版界該年最具影響力的100名人物之一,《衛報》更將萊瑟譽為「英國獨立作家之首」。在2012年初,《地下室》亦在亞馬遜電子書的英美排行榜中名列前茅。
除了小說寫作外,萊瑟也編寫電視影集。他的作品類型多為犯罪、監禁、軍事、恐怖分子及反恐行動,地點多位於倫敦及遠東地區,並廣泛帶入自己旅行蒐羅的經歷。目前他的作品已被翻譯成十種以上的語言,被譽為英國驚悚小說大師。
譯者簡介:
傅凱羚
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肄業。曾入圍臺灣文學獎,獲優良電影劇本獎、林語堂文學創作獎及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目前從事翻譯、編劇、寫作。譯有《淚流域》、《夢境闇影》及《末日發動機》。
章節試閱
這些人睡著時,看來永遠脆弱無比。如此毫無防禦。你可以很輕易殺掉這些人,割開喉嚨,或把刀插進胸膛再轉動,而且這些人或許永遠都不會曉得。你有時會好奇這件事,你想知道睡著時死掉會怎麼樣。你會繼續作夢嗎?死亡的那一刻會延展去填補空隙,讓夢永遠持續下去嗎?還是逐漸消逝成一片黑暗?如果夢永遠持續下去,是快樂的夢,亦或夢魘,有不同嗎?一個是天堂,另一個是地獄?
她在床上挪動著身體,嘴巴張開,舌頭舔舔上唇,嘴唇就濕潤且發亮起來。一縷金髮落在左邊臉頰,她抬起左臂要拂去,但鏈子阻止了她,限制了她的動作。她在睡夢中輕輕呻吟,緩緩搖頭。頭髮滑過她的臉龐,她再度舔舔嘴唇。床很大,雙人加大尺寸。你就希望是張大床,因為你計畫要跟她做那些事。你就是需要這麼大的空間。
她試著翻身側睡,但鏈子繫住她的雙腳腳踝,讓她被固定仰躺的姿勢。她先挪動左腿,然後又挪動右腿,鏈子隨之叮鈴作響。鏈子不粗,不需要是粗的鏈子。約束一個女人的行動不需多費力,你從經驗知道這一點。女性是弱者。
她的衣服看來昂貴。剪裁良好。或許是設計師品牌。她的穿衣風格是吸引你找上她的原因之一。此外還有頭髮。及肩的金髮悄悄說被輕柔撫觸的想望,說著想感覺你的手指溜過它們之間。你在床上坐下,伸手摸她的頭髮。絲滑。感覺柔軟而絲滑。她的皮膚摸起來也很柔軟。柔軟得像小女孩的皮膚。她幾歲?也許二十七吧。頂多二十八歲。絕對不會再多了。她生過兩個小孩,都是女生,都有一樣的蜂蜜色金髮。是別的東西吸引她找上你。女兒們。
你撫摸她的左邊臉頰,手滑至她的下巴。她在睡夢中喃喃說了話,但你聽不懂她在說什麼。她的聲音很美麗,是想望總是會被滿足的聲音。堅定的聲音。堅定但柔軟。你坐在貨車上,在她家外面等候時,聽過她呼喚女兒們進屋。你聽到她的聲音時興奮起來,想著她若乞求跟懇求,聲音聽來不知如何。
你看看自己的錶。藥效應該再幾分鐘就會退了。你用過太多次這種藥,知道它多有效。你在自己身上用過一次,所以你知道那是什麼感覺,也知道就算在醒來後,至少還有十分鐘的時間,你會如何因迷失方向而無法移動。你將手溜至她穿的絲質白衫正面,食指一一碰觸每一顆堅硬的白色鈕釦。她的乳房隨著呼吸而波動,你將手滑進她的上衣。你摸得到她胸罩的蕾絲,還有它所裹的柔軟肉體。你移動手指,找到乳頭。你忽然升起一股慾望,你想捏它,你想扯掉她的乳頭,用你的嘴將她的夢窒息。但你抗拒衝動,移開了手。緩慢地。你必須緩慢地得到。
她穿藍色的亞麻套裝,同色的外套,長度剛好在膝上的裙子。她穿膝上襪還是褲襪,你認不出來。你知道你可以看,只要把裙襬往上推就行了,不過你不會這樣,因為你知道你有用不完的時間。更何況讓這些人自己脫衣服有趣多了。她被下藥後,要剝光她、讓她醒來時一絲不掛,那是全世界最簡單的事情了,可是你從經驗知道,這樣這些人只會感到恐慌,你得花好一段時間才能讓對方冷靜下來。方法在於堅定但禮貌地向這些人解釋對方必須聽命行事的原因。對方很快就會理解。
你已經脫掉她的鞋子了。那是黑色的細高跟鞋。你喜歡看女人穿高跟鞋,她們會拉長腿部後方的肌肉,繃緊背部,讓她們走起路來搖曳生姿。你把她鏈在床上時,就脫掉了她的鞋,因為鞋跟銳利到足以當作武器,而在對方完全瞭解自己的處境前,永遠都有攻擊的威脅性。鞋子在樓上,跟她的手提包在一起。
她咳嗽起來,想用右手背掩住嘴巴,但鏈子阻止她這樣做。她的眼皮微顫,再度舔舔嘴唇。她醒來的時候會口渴。她們一直都會。你走到浴室,用紙杯裝了冷水。馬桶上沒有坐墊,牆上沒有鏡子,沒有浴簾或毛巾架,沒有可以用來當武器的東西。你是付出代價才學到這件事的。你以為把鏡子釘在牆上就夠了,可是其中一個人砸破鏡面玻璃,然後撲向你,手中拿著鋸齒狀的破片、鏡片匕首,一邊左右揮舞,血一邊從她手上滴落。那一個搞得一團亂,而你學到了教訓。現在房內沒有任何銳利的東西了。
你把紙杯放在瓷磚地板上,再度在床上坐下。床有金屬床架和黃銅床頭板,溫和的拱形裡是垂直的黃銅柵欄。你把床頭板和床架焊接在一起,這樣就沒法拆開了。鏈子將她的手臂鏈在床頭板,短到足以將她限制在床上,長到足以給她一些活動空間。她的手腕和腳踝有小扣鎖,另外還有同樣的扣鎖將鏈子固定在床上。鏈子閃亮地像外科器械,而跟扣鎖一樣,它們是全新的。
她咳嗽,一絲唾液從嘴角流出來,細細淌至她的下巴。你從牛仔褲後面的口袋拿出手帕,用它輕輕按著那一灘泡泡。她將頭挪開,眼皮再度微微顫動。她很快就會醒來,你的心情因期盼而搖盪。首先你必須對她解釋規則。接著你就可以開始玩了。
* * *
紐約市總能引出我心中的連環殺手。這個城市最適合殺人,完美無瑕,一千五百萬居民把市裡擠得水洩不通,大多數人根本不甩彼此的死活。沒人想惹禍上身,沒人關心對方,多麼妙不可言。走在萬惡大蘋果的街上,唯一會和你目光相接的人,只有搔首弄姿、企圖攬客的妓女,不然就是伸手要錢的乞丐。
無論走的是不是合法途徑,要弄到槍都很容易。你可以光明正大將槍掛在手臂上,不然就纏在後方褲腰。這裡不像某些國家,若無可成立的理由,美國警察不能把你架到牆上搜身。這一切都要感謝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其內容大致如下:「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財物的安全,不受無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權利;此項權利,不得侵犯。」唯一例外是警察提出所謂「可成立的理由」,換句話說,警察得有好理由。我愛美國。 只要我不特立獨行,隨波逐流,我就可以整天把上膛的槍插在褲子後腰到處晃,假裝自己充滿了殺人慾望。當然實際上是沒有。
世界上還有哪一個城市能提供如此豐富的受害者?我不光指數量,種類也是:這裡有富人、窮人、名人、小卒、黑人、白人,各種色調的有色人種。紐約市什麼都有,這裡是連環殺手的自助屠宰場,成功的訣竅是別太貪心。如果你老是仿效「山姆之子」、轟掉青少年的腦袋,或是寫信給媒體或警察,跟他們說:「是我幹的,但你們永遠抓不到我」,很快就會有一個專案小組盯上你,把受害者的身分釘在布告欄,接著你坐牢就只是遲早的事了。不能那樣,成功的連環殺手都富有耐心、慎選受害者,而且盡可能保持低調。
換句話說,訣竅就是隨波逐流,讓數字自行擺平一切。數字?沒錯,就是數字。你不用把受害者埋起來,或者用強酸溶掉他們、把他們切成碎塊,用垃圾袋裝起來,扔到市區各個角落之類的,根本不需要這樣。你可以直接把他們藏在數字裡。紐約市有一千五百萬人不是嗎?差不多吧。所以大致估計一下,就先假設人的平均壽命是八十歲好了。對,我知道,女人活比較久,男人比較早死,但人的平均壽命差不多是八十歲,就像我剛才說的,現在只是粗估。假設一千五百萬人平均活到八十歲,那就代表紐約市每年幾乎有二十萬人死亡。二十萬人,等於平均每週死四千人左右吧。請看,這四千人的死因,包括車禍及大量的自然死亡,但也有不少人死於謀殺與自殺。認真的連環殺手耐心等待,慎選下手的對象,接著就盡可能將罪行隱藏在每年龐大的一般死亡人口數字裡。首先,你必須瞭解一件事:死亡在都市生活中是很正常的一部分。每週死四千人,每天就死六百人。雖然一般美國人不喜歡思考這件事,他們寧願想像自己永遠不會死、只有少數人會真的離開人間,但實情是:每個人遲早都會死,誰都一樣。只要讓受害者看來像在淋浴間滑倒、失足跌落窗口,或是自己打定主意喝下漂白劑,你就有機會逃過法律制裁。你可以用這種方法將多數受害者處理掉,不過偶爾呢,真的忍不住的時候,你依舊可以將其中一個肢解,然後把屍塊裝進垃圾袋裡。
喂,不要誤會。這些都是我的想像好嗎?我不是殺手,我是作家,我永遠在構思情節。這麼做是為了寫作,我才不會真的變成殺人狂。嗯,應該不會吧。
總之,紐約市就是如此,到處都是陌生人,每天還有更多陌生人湧進來。我最愛的景點之一,就是中央車站對面。站在那裡,我可以看著陌生人抵達,看他們像螞蟻般爭先恐後地爬出蟻丘,四散去尋找食物。他們每個人都可能受害。就在我初次抵達這個城市時,我經常隨意找個女孩來跟蹤,目的是找樂子,也為了讓自己運動一下。我站在車站對面,舉目四顧,然後就隨機選一個女孩。我會暗暗決定要跟蹤第十個出現的女孩,或是第二十個、第三十個。接著,我就開始數來往女性,跟上中標的幸運兒,然後能跟蹤多久就跟多久。有時對方會坐上計程車,這樣就沒戲唱了。有時我也會在地鐵上跟丟對方。但是,偶爾我也可以一路跟蹤對方到家。天啊,站在這些住家外,知道她們就在裡面,這讓我覺得自己無比強大。你知道嗎?從沒有人發現過我在跟蹤她們,從來沒人轉頭來看,從來沒人注意過我。有時我自覺像盯上斑馬群的獅子,斑馬愚蠢又溫馴,蠢得要命,在獅子的利爪撕裂牠們的喉嚨、讓牠們血如泉湧之前,斑馬根本不會注意到自己身處險境。我的感受並非仇恨,而是鄙夷。可是呢,這只是田野調查,懂吧?
這些人睡著時,看來永遠脆弱無比。如此毫無防禦。你可以很輕易殺掉這些人,割開喉嚨,或把刀插進胸膛再轉動,而且這些人或許永遠都不會曉得。你有時會好奇這件事,你想知道睡著時死掉會怎麼樣。你會繼續作夢嗎?死亡的那一刻會延展去填補空隙,讓夢永遠持續下去嗎?還是逐漸消逝成一片黑暗?如果夢永遠持續下去,是快樂的夢,亦或夢魘,有不同嗎?一個是天堂,另一個是地獄?
她在床上挪動著身體,嘴巴張開,舌頭舔舔上唇,嘴唇就濕潤且發亮起來。一縷金髮落在左邊臉頰,她抬起左臂要拂去,但鏈子阻止了她,限制了她的動作。她在睡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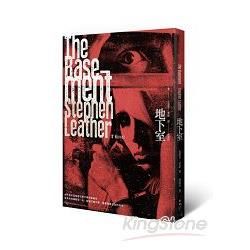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