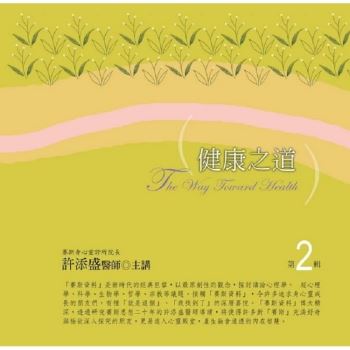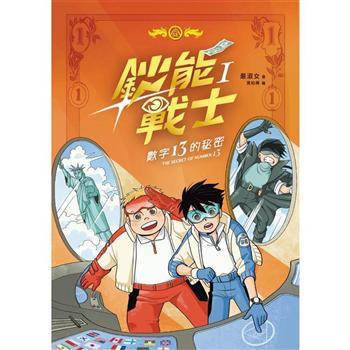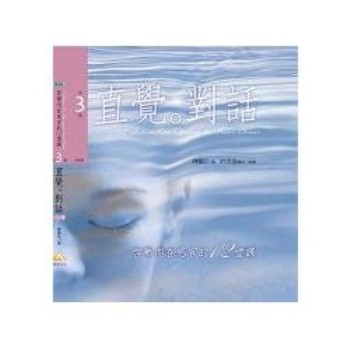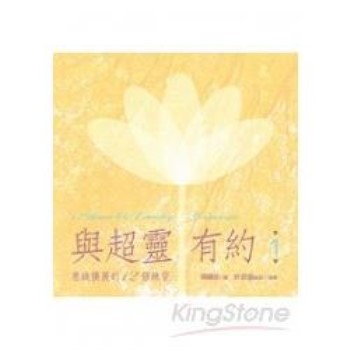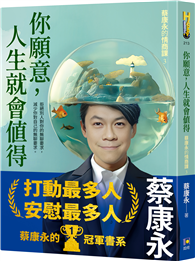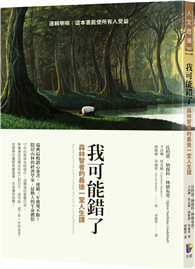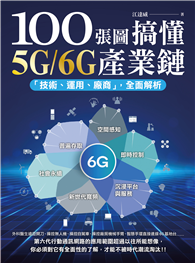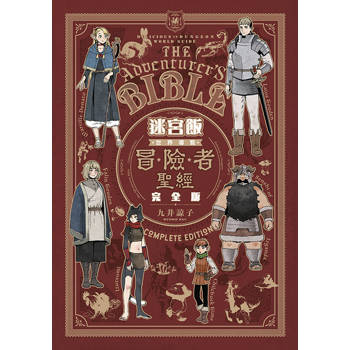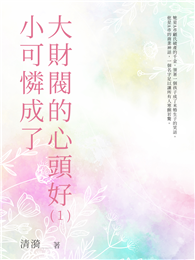推薦序一
「正因全世界都在反對你去實踐一個夢想的時候,這夢想便成為最有實踐價值的一件事。」
在實踐夢想的路上,總會有支持、反對、阻撓、吐槽、不以為意等等的聲音出現,但這些種種都是將我們正在實踐的故事「精淬」成更實際、更獨特的夢想。
回憶起與時暢相識的經過,只是與我們的共同好友──真輔的日常談話中,有意沒意的提起這位正在世界的某個角落騎著單車的朋友,後來真輔的臉書成為我認識這位流浪漢的故事頻道,包括在挪威雪地裡的掙扎,以及之後真輔出發印度、尼泊爾進行每年固定的單車繪畫之旅,與流浪漢會合後一起為環遊世界劃下句點。後來在雲林故事館──唐麗芳老師的走讀台灣活動中來訪鹿港,才真正見到流浪漢本尊。
但這些故事都是相當片面的。直到最近知道時暢把流浪的故事出版成書,請小弟幫忙寫推薦序,才有機會一睹三年半流浪旅行的完整故事。人生的旅途能有多長,唯有活在當下才能遇見最精彩的風景。
時暢的故事,讓我想起二○一四年在彰化進行移地訓練時,來到鹿港拜訪的DIY團隊(紀錄片《夢想海洋》的獨木舟團隊,以獨木舟環遊世界展開冒險)。其中帶隊的蘇達貞教授(拖鞋教授)提到了毛利人的祖先來自台灣。我們的祖先對於海洋的認識有限,一艘獨木舟就奔向海洋出發,就開創了另一個文明;現在我們藉由科技可知道世界有多大,卻不再出發冒險了。
不管是時暢還是夢想海洋團隊,他們都是偉大航道上的夢想實踐者。在閱讀這些冒險故事的同時,又讓同樣身為夢想實踐者(其實更希望被稱為流浪漢)的我,開始計畫下一趟冒險!
張敬業
(筆者為「鹿港囝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創辦人、「保鹿運動」共同發起人)
推薦序二
大約兩年前,時暢的旅途結束回到台灣,剛繞地球一圈的他,除了一絲疲憊之外,令我驚訝的是從他身體深處溢出的簡單。在我的想像裡,騎單車環遊世界的人不是都有某種耀眼的光環嗎?在小康之家出生的我,某個層面來說是相當缺乏自由的,而在這種情況下去想像自由,其實反而相對簡單。就像當我們是小員工時,對於怎麼當個好長官總有許多看法,但真的輪到自己當長官後,才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看到時暢的第一眼,就清楚的意識到我對他追尋自由的想像,已經偏的非常離譜。
當時的我,正處於拼命累積自己的階段,第一次商業藝廊展出、進入畫會、面對複雜人際關係,白天工作晚上創作,內外在都承受著各種改變,就為了讓自己能持續在創作這條路上,以為那些交際那些畫展,是我追尋藝術帶來的成果,當看到時暢的一瞬間,我心裡就知道自己似乎在某個關鍵錯了方向,他外表黑了瘦了,依然沒變的溫柔與靦腆之下,舉手投足都讓我強烈感受到他從未有過的沉靜與樸實,不「像」是曾經環遊世界的人!就像我曾經認為,藝術家也應該穿著時尚的華服,帶著強烈個人風格橫掃眾人,就算耀眼不如日月也可閃耀著星光,但他就是沒有那些光環,這跟我的想像完全背道而馳,除此之外還有更令我跌破眼鏡的,他環遊世界回來後的工作,除了書寫畫圖以及到處演講外,他選擇到雲林的鄉下種田……WTF !
諸葛亮《誡子書》:「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我認為是給這個選擇一個滿好的註解,等價交換的原則下,當他選擇了花三年半的時間,冒著生命危險與饑寒交迫中追尋他自己時,命運回贈他的東西,大概就是這一切的原因,而這些原因通通都藏在這本書裡。如果你是個有勇氣追尋夢想的人,那這本書會讓你在這條路上多一位夥伴。如果你是沒有勇氣追尋夢想的人,那也許你能從這裡找到些火苗,釀成生命中一場美好的大火。如果生命從來沒能讓你有喘息的空間去追尋夢想,那也許這本書會給予你勇氣做出改變的決定。
27元藝術創作者 魏瑋廷
作者序
小時候在海邊長大,總喜歡在海邊看星星,曾有人告訴我:「可知道你眼中的星光,其實是幾億萬年前的光芒嗎?遙不可及的距離連光都要跑上幾億幾萬年,當此刻的光芒照進你眼底的同時,或許那顆發光的遙遠星星已經在這億萬年旅途之間毀滅了。」回想,學校的作文題目中「我的夢想」,寫下長大想當科學家,可以學到這些星星上的故事,但就算活到八、九十歲,又如何解構眼前星光的旅途,於每個紀年裡發生的故事呢,無論怎麼想都太過於超現實。時間太過於巨大又無所不在、漫長又迅速,當初看星星時,應該為眼前的星光而哀傷。
有一次在家庭聯絡簿上寫了一個問題給老師,依稀記得是這樣:「假使我只能活到二十歲的話,那麼做什麼事才是人生最有意義的事,人活著到底為什麼目的?」老師在課堂上公開責備著幼小的心靈,要求我別想這麼笨的問題,因為不可能只活到二十歲。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口服心不服地接受這個答案,日後卻怎樣也無法妥協,二十歲和八十歲,不就是一分鐘和四分鐘的差別而已嗎,老師唬人啊!後來在大學接觸一點美學理論,才發現自己也許從小就是個虛無主義者,遺憾當時沒有留個龐克頭,實在對不起自己那段本應該叛逆的光輝歲月。
也因老師的唬爛,這點芝麻綠豆大的小事,放棄念書的本業,念書無法解決疑惑,索性就放給它爛吧,學業只應付父母,成天無所事事,像具喪屍,凡事父母說東我就往西,閃避社會價值的能力,和籃下的Lebron James差不多靈活,反正世間萬物,在無邊的時間軌道中透析之後都會消失,又何須如此在意社會強加的價值觀呢?
高中有段時期沉迷神話故事,尤其是日耳曼神話,閱讀北歐神話可說是非常快樂的時光,北歐神話中,角色的行為愚蠢又可笑,有著類似情節,例如:先知對眾神斷下的預言,全是真理或不可逆的命運,無法違背也不可能扭轉,這和現實中的時間有異曲同工之妙。既然先知預言悲淒的結局,這些故事角色們依然想盡方法去抗命,徒勞無功又為何要奮鬥呢?縱然是千篇一律的類似故事,我依舊讀得很開心,因為向不變的命運對抗的情節,其實有種愚蠢到十足熱血的感覺。人生一點都不意外,該發生的無論是好是壞,一定會出現在生命中,只是形式不同,人生不是意外,意外才是人生常態,重要的不是結論而是過程。
不過總要為自己無意義的人生找個位置存放,同樣,在自己人生故事裡,先知也預言,這是敘述一個不學無術,高不成低不就,沒有天賦、沒有才能,凡事失敗,十足愚蠢的傢伙,邁向可笑人生的冒險故事。雖然故事難以令人期待,但所幸平凡又無用的自己,能去實踐學生時代的理想,放逐自己的心靈。放逐自我並不會令你得到什麼或學到什麼,相對的,也不會失去什麼或丟掉什麼,人在生於世上是賺到了,也是停利點了。
於是,二○一○這一年,連親友都不看好的情況下,六月一日單車環遊世界的計劃與理想,強迫自己上路。朋友在機場送機時,雙方的心理態狀很兩極,我心想:「該怎麼辦?什麼都不懂!」親友心裡或許這麼想:「放心!他一句英文都不懂,只有台幣二十五萬,可能下星期就飛回來了,最多撐一個月吧!」臨走前不忘安慰我說:「嘿,下星期一起騎淡水八里啊!」老實說,我非常喜歡這種調侃。
然而二○一三年十二月完成旅途,再度回到台灣後,除了父母以外,再也沒有朋友質疑我想做的事情了。人最大的問題就是不願意面對自己,因此夢想永遠流於夢想,若是如此日復一日,那還不如別下床了。外在因素是一種意志的過濾網,它有存在的必要性,沒有這些質疑與否定,就沒有辦法篩選出自己心中真正想做的事,正因全世界都在反對你去實踐一個夢想的時候,這夢想便成為最有實踐價值的一件事。任何事都會有成功或失敗等結果,但前提是必須報名參賽,否則流於圍觀者,這果實永遠不會是自己品嘗。給自己一個參賽的機會,至少擁有一個失敗的結果,而穩賺不賠的是,這過程一定會留下一個努力奮鬥的故事,一個無憾的故事。
流浪期間,總有一些信念支撐,《異鄉人》是其中之一,將它奉為看待人性道德的圭臬,由衷地崇拜著卡謬,旅程結束迄今,仍然以流浪漢自稱。
流浪漢 吳時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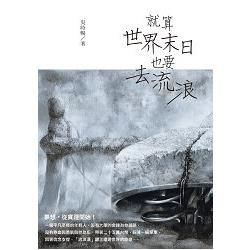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