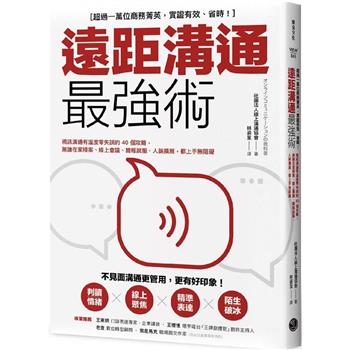★ 「愛呆西非」連加恩感動推薦!
被遺忘在有聲世界之外的耶魯高材生,
前進向來不被世人關注的非洲大陸,
貢獻己力拯救無辜性命,感受非洲人民真摯的熱情與單純的笑容……
這本篇幅不長的小書所描述的,是一位自幼失聰的年輕人在大學畢業後,志願加入和平軍(Peace Corps)兩年,前往非洲尚比亞(Zambia)境內一個偏僻的小村落,協助進行探勘水井等工作,同時在當地生活的種種歷程。
這位年輕人在抵達當地首日,即得知在這個以疾病、暴力、貧窮為現狀的國度中,該村落更以巫術與腐敗著名。儘管面對簡陋的生活環境與強烈的文化衝擊,這位年輕人在認識當地一位阿根廷醫官,並與他成為朋友後,在自己平日探勘水井的工作之餘,他開始前往醫療站協助這位醫官照顧村民。漸漸地,這位年輕人發現自己的聽障在當地已不再成為障礙,在此同時,他也慢慢融入當地生活,最後找到自己的第二故鄉。
作者喬許‧史威勒天生聽力不佳,五歲失聰。在成長過程中,他不時自問許多由於自己失去聽力,所衍生的人生疑問。畢業於耶魯大學後,他決定加入和平軍前往非洲尚比亞,本書是他的第一本作品。
一名年輕人欲接受自身失聰的事實,旅居在遼遠的非洲村落,經歷了一段美麗與暴力交織的崢嶸歲月。
作者簡介:
喬許.史威勒(Josh Swiller)
有先天性中度聽障,四歲時全聾。他畢業於耶魯大學,從事過形形色色工作:守林員、木工、拖鞋推銷員、生食主廚、禪宗見習門生、記者、教師等等。二○○五年八月,他移植耳蝸,手術成功,恢復了部分聽力。目前,史威勒常常發表演說,討論融入常規社會生活之失聰個體所面對的議題。他目前在紐約布魯克林一間收容所工作。請參觀他的網站:www.joshswiller.com
譯者簡介:
呂玉嬋
生於台北,藝術碩士。喜愛藝術、電影及旅行。曾譯有《偷書賊》、《第十三個故事》、《動物之神》、《生命饗宴》、《星期三的信》、《罪與償》等書。
章節試閱
耶誕節
來到姆努加之後,九個月過去了。早上我到衛生所工作,為幼兒量體重,替感染傷口與腸蟲潰瘡綁繃帶,將維他命限量配給營養最差的人。在家吃過午餐後,我不是回去衛生所,就是舉辦與會者寥寥無幾的集會,說明造井計畫,或是教導巴媽優們如何防止感染疾病散布。而奇蹟中的奇蹟,我們居然在卡賽克聚落開始挖掘水井,將負責翻譯的傑佛森、十字鎬與鏟子,以繩索一起降到現有的洞之中。他從底下傳回一桶桶的泥土,還有一根人類的大腿骨,它由於某種理由被扔進水井中,大概與恩多西有關吧。工程進行遲緩,因為井底幾乎全是花崗石。不過,至少在進行了。
如果我的和平工作隊義工經驗應該與造井有關,那麼,一輛鑿孔卡車與幾百萬美金,幾乎就可以搞定全省的用水問題。想想看:只要這麼做,五十萬人口就可免於因飲水而染上嚴重疾病。但是,那並不是當義工的目的,我努力參透這一點,好歹少去想這件事情。與村民日常相處能分散我大量心思,除了工作以外,我與傑爾喝酒,與齊魯巴及她妹妹打情罵俏,還有教導馬拉馬打撲克牌。
教他打牌不容易,因為他偷雞的概念難倒了他,如果我的牌比他的好,他總會說:「哦噢。」
「你說『哦噢』,就唬不了人。」我告訴他。
他說:「抱歉。」
「不要抱歉,唬我!」不過,他下不了手。
有些週末,我把馬拉馬抱上摩托車後座,騎上東向道路,溯流到一片小水瀑,在飛沫下游泳。水中長滿了會輕輕啄人的魚,我們游得很快,以免有鱷魚埋伏。怎樣都讓人精神為之振奮。
將近感恩節時,克里斯與我一起到辛巴威的哈拉雷(Harare)旅行。我們跟著一個年輕的拉斯特法里派信徒走,他答應要帶我們到一間前衛的夜總會,結果十五個男的猛然撲上來。我們殺出一條路,跳上路過的計程車,可是這群人圍著車。克里斯那頭的窗戶沒關,有人伸手進來抓他的眼睛。我用拳頭攻擊最靠近我的三個男的,狠狠地揮過去,打得拳頭都痛了,於是所有人都跑走。我們的車開走,然後我發現那些傢伙跑了,不是因為我們打架的技巧,而是他們已經摸走我的皮夾了。克里斯跟我昏頭轉向,走進一間旅館的酒吧坐下來。一位美麗的妓女把我們迷了半個小時,解讀我們的掌心,解釋我們的命運。我們兩人都嚴重發抖到說不出話來;她的身軀厚實豐碩,看似健康,但是我們無法採取行動。一直等到進了飯店房間,我們才發現克里斯有兩團黑眼圈,而我的肋骨斷了一根。
但是我們沒兩下就不把那當一回事情。「非洲嘛。」我們說,拿起南非啤酒為這片大陸乾杯。
非洲:這隻受傷的異獸。非洲:十分容易重新想像自己的地方。非洲:死與笑相距不遠。姆努加村民埋葬孩童,就像小狗埋骨頭。但是你習慣了後會發現,比起你曾期待認識的任何族群,他們笑容更燦爛,煩惱更少。當然,有例外存在,最明顯的就是博尼法斯。然而整體而言,村民友善親切,我很感激能稱呼姆努加為家。
接著,在耶誕節,一切變了模樣。
耶誕夜時,我給父親寫了封信,跟他說明一切安好,接著閒蕩走去參加臨時為衛生所員工舉辦的聚會,地點就在傑爾的因沙卡。到了那裡,我喝下相當過量的香蕉酒,傑爾為慶祝假期釀造了特濃的酒,連續在發酵酵母中加了十四天的糖,正常只加三天。每呷一口,我就感覺到牙齒搖鬆。不消說,鄉下傳統以喝到爛醉來紀念上帝之子的誕生。雨季的衝擊已經過去了,嚴重至極的疾病爆發,可是我們依然存活,這是我們慶祝的動機。我們隨著南非雷鬼音樂跳舞,相互舉高,命令自己的腳步移動。腳步不聽從使喚,帶著我們朝因沙卡的泥磚矮牆上跌過去。在亭子外面,醉漢宛如迷航的太空船,在烏漆漆的村莊中遊蕩。
突然之間,我們開始熱烈地反覆討論白種女人的性癖好。
「我聽說,她們結婚前,跟許多男人睡過。」傑爾說。
「有些是這樣。」我說。
「你得幫我找個這樣的人。」衛生所資淺的年輕員工派屈克說。
傑爾靠過去,抓住派屈克手臂。「派屈克,動動腦吧你,」他說,「喬許上哪給你找一個白女人?到市場去找?」
派屈克露出堅毅的神情,他的臉色永遠像在期待壞消息。「他會找到一個的,他可以的。」
傑爾看我。「喏,喬許?你去哪裡幫派屈克找一個白女人?」
我努力想說些風趣的話。耶誕酒與舞蹈讓我心情放縱無拘,但香蕉酒的麻煩處是,喝醉才一個小時,你就開始感覺到宿醉,頭痛欲裂,像是腦中有架廢物壓縮機。已經超過一個小時,我無法思考。
「我說的沒錯吧?」傑爾對派屈克說。
派屈克搖頭。「你錯了,傑爾先生,我對這個烏姆孫谷有信心,他可以的。」
「我很感激,派屈克,」我說,「為了你,我會找兩個。」
「兩個?」傑爾揚起眉毛,「兩個給派屈克,我一個都沒有?」
「沒有,你一個都沒有。」
接著,有個男的出現,靠在傑爾耳邊低語。傑爾邊聽,邊斂起笑容,打手勢要派屈克關掉音樂。有人剛在市場上被殺死了。
我們於是緘口不語。傑爾解釋,死者跟另一人在酒吧外吵架,接著名為奇通多(Chitondo)的對方僥倖(或是不幸)揮了一拳。第一個男人的鼻骨直接被打進腦子中,人像撕開的玉米袋垮下。一開始他們以為他在假裝,接著認為他被打得不省人事,然後發現他的眼角積了一灘血水。奇通多跑去躲起來了。
每十分鐘左右,就有人出現到因沙卡,帶來更多消息,情況越來越糟糕。首先,一票流氓想替天行道,尋找奇通多。這幫人尋不著他,洩氣之下,堵了他兩個朋友,殺了他們當替死鬼。他們想殺第三個朋友,不過他逃開。最後我們聽到的消息是,他朝著坦尚尼亞(Tanzania)的大方向而去,赤腳跑過荒野雜林。他不是在那裡開始另一段人生,就是在途中被土狼吃了。無人曾再見過他。
就那樣,三個人死了。這種作法無法無天,難以想像。我們雖然醉茫茫,依舊試圖想要弄懂這件事情。
「我看過奇通多嗎?」我問傑爾。
「看過,」傑爾說,「他來衛生所幫忙搬過幾次東西,這傢伙個頭高大,肌肉碩大,像這樣――」他在空中比了一個身形,「脾氣暴躁,總是想討錢,想起來了嗎?」
「欸。」我說。其實我想不起來,傑爾剛才形容了十來個人。「那群暴徒是怎麼回事?」
「有人帶頭就會有人參加。」
「誰帶頭?」
他掏出手帕,抹抹頭。「有謠言。」
「是誰?」
「他們說可能是你的朋友,博尼法斯先生。」
「博尼法斯?不會吧。」
傑爾沒有再說半個字。派屈克比以往更緊張膽怯,起身離開,回家關在草屋中。
約莫午夜,有關這票逞兇之徒進展的最新消息終於逐漸減少。我蹣跚走回茅屋,倒到床上,緊抓著床頭板,直到房間停止旋轉。我睡了,夢到苦哈哈、血淋淋的夢,這是吃下抗瘧疾藥所帶來的副作用,藥丸灼燒如點燃的炸藥,吞下後在我的無意識中爆炸。夜,充滿了吶喊、煙霧、滴油淌血的裸身。
後來,有人把我搖醒。馬拉馬。他從沒有鬧醒我過。
他看見我張開眼睛,說了什麼,而我只見他的嘴在動。
「走開啦。」我說。
馬拉馬搖頭,嘴唇又上下開闔。「助聽器。」我指著耳朵說。
他看看床,看看地板,找找上了亮漆的樹樁所做的床頭櫃,接著去了起居室,在我的夾腳拖鞋附近找到了。他鵝蛋臉露出興奮熱切的表情,潔白牙齒閃閃發光。我以前沒見過他這麼活潑旺盛。
我用嘴濡濕一片耳模,塞進耳朵中,頭留在床上沒抬起。
「好啦,說吧,」我對他擺手示意,「不,等等――」我喉嚨還有香蕉酒的味道:令人作嘔的甜味,帶有顆粒又酸溜,像是酷雷牌(Kool-Aid)人工果汁混了煤油與沙粒。「給我點水。」
馬拉馬衝去廚房,拿了一杯水回來。我坐起身。
「什麼事情,馬拉馬?」
「巴•喬西,你一定要來!」他說,「你一定要去看!我們抓到兇手了,要拖他死!在索蘭奇(Solange),他們,現在抓他。」
「兇手?」
「對,兇手。」
「你是說奇通多?」
他抓起我的手臂死拖活拉。「對,走啦。」
於是,耶誕節清晨七點半,我們匆匆趕去市場。抵達時,市場空無一人,賣香菸的男孩、巴媽優,一個也沒有,沒有客戶,沒有遊客、沒有攬客的男童,沒有人。沒有攤子擺賣,沒有魚販,沒有煮菜油的推銷員。感覺好似世界結束後的那個早晨,好像伊波拉病毒(Ebola)終究從薩伊雨林傳過來,在睡夢中奪走每個人的性命。一陣和風自河流徐徐吹來,芒果樹與樹薯田清翠鮮綠――雨季帶來的好處。遼闊的天似乎一如往常,相當自負不凡。
「大家都去哪了?」我問馬拉馬。他抬頭看山丘。
眼睛看到之前,耳朵清楚聽到之前,我先感覺到了。一種寒毛直豎、心臟停止的感覺,像是猝然被噩夢搖醒。馬拉馬的手一指,我轉頭看到人群在山丘高點,他們沿著通往市場的路,浩浩蕩蕩,滾滾而來,又是手足舞蹈,又是尖聲呼嘯。這行隊伍的頭,也就是指揮應該的位置上,有兩個男人拖著一具赤裸的身體。在崎磊的路上,身體宛如巨型的彈力球。
那是奇通多。
失聰有個特點,會培養出依據肢體觀察的直覺。身體語言、姿勢、動作、神情,洩漏太多祕密。女人揮手告別的寂寞;男人拳頭一鬆一握的憤怒。人,是攤開的書,無時不刻在洩漏祕密,從端詳自身倒影的樣子,從查看時間的姿態。重點是,當村民行進隊伍走過山丘的那一刻,他們的活力,在眼見耳聞之前,我已經感受到了那份活力,那份活力純潔無染,感覺好似快樂的心情。
第一道曙光出現,這群暴徒就開始搜尋奇通多。他們搗毀他往北幾哩遠的住家,威脅將他母親放逐到薩伊,將她妻子踢到她放聲痛哭,踹到她停止呼喊。天光明朗了,他們總算找出了奇通多,他蜷縮在一位女友茅屋的屋頂橫樑上。他們對他扔石頭,把他砸到地面上。他要求饒命,提議給他們一千美金,如果他們放過他。一千美金!他們誰都沒有見過這麼大筆的金錢。
「奇通多想去哪弄一千元?」事情結束後我問傑爾,「他是幹小偷的嗎?」
「他沒有那筆錢啦,什麼都試試看,他知道他麻煩大了。」
「他們幹麻不收下?」
「什麼都不可能阻擋他們,」傑爾說,「他不是善類,不過這個下場有點太離譜了。」
暴民把奇通多連拖帶拉從他女友的茅廬拖出來,之後將他衣物剝得精光,以繩子綁手腕。群眾之中,最勇敢的一個往前衝,拿條帶子環繞他的下巴。接著這群男人把繩子盤繞在自己的手臂上,輪流將他拖回姆努加。三哩遠的路,他們走了一個小時。他們奔走之際,天亮了。赤道的黎明總乍然而現,陽光左推右擠灑落而下,像是在躲避蛇的人。暴民經過馬拉馬與我站立的市場時,奇通多已經斷氣了,這票人馬依是連拖帶拉著他的屍體,氣喘吁吁,汗如雨下,每百碼路就換手拉繩子。聚眾跟在後面,載歌載舞,朝著顛簸的屍體吐口水。小狗尾隨在後,靠到敢靠近的地方,狼吞虎嚥吃下剝離的碎肉。
我幾乎無法呼吸。我看著馬拉馬,他笑到合不攏嘴。
「他們在唱什麼?」我問他。
他望著我,神色遲疑。「我們殺了凶手,兇手死了。」
「我們殺了凶手?」
「對。」
「那是一首歌?」
「對。」
「太精采了,馬拉馬。」
「對啊。」他又說,依然笑著。諷刺與偷雞雙雙都難倒他。
遊行隊伍隨著街道對面的寬弧道而行,接著在一排商店後面切入一片泥地,有三個死人躺在芒果樹下:奇通多揍的人,奇通多兩位不幸的朋友。馬拉馬同我走過去。成千上百的人亂哄哄地在四周推擠,在屍體間興奮走動,如同學童在博物館欣賞填塞動物。婦女成群結隊,憨笑指點,笑時掩起嘴來。父親把小男孩舉到肩膀上,以便看得更清楚。兒啊,那是大象,那是住在雨林深處的猴子,這是一個臉上有十六塊相異碎片的男人。氣氛愉快滿足。此時此地,正義難能可貴得以伸張,位於曼沙的政府沒有為姆努加做過一件事情;檢查哨酩酊大醉的士兵被喚醒後,只會收取過路費與賄賂金;整個雨季,痢疾與瘧疾肆虐全村。但是,現在村民獲勝,殺手已死。
奇通多的屍體赤裸躺在地面上,手臂如老鷹翅膀展開,遭道路磨破的巨大陰莖落在左大腿上,彷彿皮剝了一半的芒果。一株波羅蜜的樹蔭落在他腿上,微光閃閃。而臉呢,他只剩下一張模糊的臉,一張剛打好草稿的臉。馬拉馬與朋友在人群中衝進衝出,查看每一具屍首,指指點點,竊竊私語。我見到博尼法斯抱著手臂站著,下巴朝天,村民為他讓出一處寬闊的佇立處。他對我點點頭,我凝視著他,然而如果這是他的所為,他沒有露出表示。
一個男子從人群中站出來,拿著大鐮刀站在奇通多身旁。他穿著一件歌頌尚比亞民主的白T恤,上面寫著:我愛多黨政治。這人略為前彎,接著把二呎長的生鏽刀身高舉過頭。在這時候,我轉身離開,從人群中擠出。我關掉助聽器,因此我沒聽到――謝天謝地――刀子砍劈身體的聲音,鏘鏘鏘,第二次揮刀,鮮血噴出,奇通多的內肚猶如大量髒水瀉湧到泥土上,汪汪叫的小狗蹴腳向前,大快朵頤一番。
回到我的草屋,我一屁股沉坐到沙發上。好長一段時間,我光只是坐著。我明白,這裡有殘忍的事情發生,小孩隨時會暴斃,但是我毫無疑問相信,我認識的人不會謀殺他人,也不會拿他人的肝臟去餵狗。我錯了,這群暴民在主要通道的中央留下一條血跡,人人信步來去,帶著幾乎如性交後的喜悅。馬拉馬從敞開的門進來,背著門框,在地板上坐下。我觀察他,而他避開我的凝視,嚼咬他的膝蓋。這天早上他沒穿上衣,瘦稜稜的肋骨突出,皮膚閃著汗水。有八個月的時間,他睡在沙發上,吃我的食物,看我的雜誌,寫信給我兄弟以練習英文。但是,我不瞭解他;而如果我不瞭解他,我怎麼會了解村裡的任何事情呢?
「你要幹嘛?」我查問。
他略為結巴。「你――你想今天吃依撒比(isabi,魚)還是因可可(inkoko,雞)?」
魚或雞?我手指著他,責難他。「馬拉馬,你不做那種事情,你不要對人做那種事情,那不是好事,你沒蠢到做那種事情,絕對沒有做那種事情的理由,絕對沒有!你不應該開心的。」
「但是他殺了人?」
「又怎樣?你不能隨便就殺人耶。」
「為什麼?」
「因為――」我想不出要怎麼表達。暴民之中,我認出好多好多張臉孔,我信賴的臉孔。木邦加(Mubanga),幫我造了茅廁;路奇(Lucky),把這間茅廬租給我一年,以五袋水泥為租金;穆塞卡頭目,因為啤酒而親了我。「因為,那樣會讓你變成什麼,馬拉馬?如果你殺了兇手,你會變成什麼?」
「那不一樣。」他說。
「錯,沒有不同――你想想看!」我已經在叫吼了,「那樣會讓你變成什麼?如果你殺了人,你到底會變成什麼!」
他畏縮靠著門。「好啦。」
我以手背拭眼。「好了,你只是想順應我,馬拉馬,可你最好想想我說的話。」我們無語坐了片刻,我希望他離開。
「魚吧,」我說,「告訴齊魯巴,我們今天吃依撒比。現在你走吧。」
那一夜晚餐後,我到傑爾的因沙卡找他。我們坐著注視棋盤一個小時,一只棋子也沒有動。他始終把沉睡的美麗抱在腿上,柔情撫摸她的手臂。在村裡的那段歲月中,我沒見過這樣無所隱避的親情。
「你有看到屍體嗎?」我問他。
「我不想看到。」他答道。
「但是你看到了嗎?」
「那不重要。」
「你到底看到了嗎?」我提高音量又問。我需要聽見他說,他是我的真相來源,他的話會證實烙燒在我記憶中的事情。他的目光越過田地,朝衛生所看去,鐵皮屋頂在月光下閃爍。他的圓臉縮緊,我見過那個神情,常常在量嬰兒體重時出現,總是很快消散。但是,那次的表情有所不同,我無法看清楚。我費了一會兒工夫,才弄清楚那是什麼,是恐懼,他在害怕。
「我看到了,」他說,「這地方瘋了。」
耶誕節來到姆努加之後,九個月過去了。早上我到衛生所工作,為幼兒量體重,替感染傷口與腸蟲潰瘡綁繃帶,將維他命限量配給營養最差的人。在家吃過午餐後,我不是回去衛生所,就是舉辦與會者寥寥無幾的集會,說明造井計畫,或是教導巴媽優們如何防止感染疾病散布。而奇蹟中的奇蹟,我們居然在卡賽克聚落開始挖掘水井,將負責翻譯的傑佛森、十字鎬與鏟子,以繩索一起降到現有的洞之中。他從底下傳回一桶桶的泥土,還有一根人類的大腿骨,它由於某種理由被扔進水井中,大概與恩多西有關吧。工程進行遲緩,因為井底幾乎全是花崗石。不過,至少...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