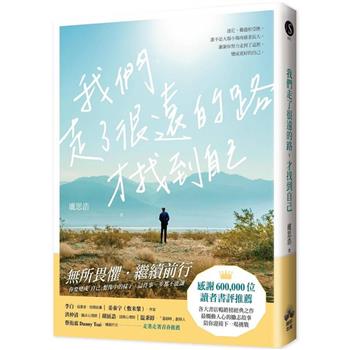序
高貴而獨特的匠人精緻料理
應該是2015年12月的某天早上,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張照片。照片圖說寫著那是一道「法式肉派」(pâté croûte)。它呈現閃亮或漆皮般的赤褐色澤,完整而精雕細琢,既深沉又豔麗,就像是被好幾代的主人珍惜並擦亮的古董家具一樣。這就是我想像中安東尼.卡漢姆(Antonin Carême)宏偉構築的模樣,那些主要、沉重及高貴的裝置,來自過往的年代,彼時的一切盡皆輝煌而衰落。
然而,「法式肉派」卻不是我特別喜愛的一道菜。它的傳統內涵讓我感到窒息,酥皮堅硬但易碎,既乾又潮,餡料的質地和味道也不穩定。那張照片裡的一整塊肉派讓人無法猜透它入口的質地會是如何,也讓人無法得知餡料摻雜了什麼。許多問題在我的腦海中反覆迴盪。它是否易於咬嚼、好入口、好吞嚥?酥皮會不會和它美麗木質家具般的外表一樣堅硬?第二張照片呈現的,是擺放在一只盤子上的一塊肉派切片。中間有一輪完美的肥肝,加上精美散布的肉塊和油脂。另外還有規則排列成兩行的六粒蔬食,不曉得是開心果還是蘑菇。這樣的幾何排列好入口嗎?美味可口嗎?這種完美的對稱難道不會像一坨硬塊,就好比一條放久了的凍腸嗎?
我讀了照片底下的圖說。
「卡倫.托洛桑是布魯塞爾波札餐館(Bozar Brasserie)的主廚,他於2015年的『法式肉派世錦賽』中,以比戈爾(Bigorre)產黑豬肉、鴨肉及鵝肝製成的『貴族法式肉派』摘下冠軍頭銜。」得主是亞美尼亞人?在比利時?誰會把「法式肉派」做得比艾斯可菲(Esco er)更道地?
布魯塞爾之旅
從那天起,我在哪裡都會看到一張照片。總是這同一道「法式肉派」,看來有著難以置信的完美無瑕。然後有一天,一道「庫利比亞克」(koulibiak)出現了。它威嚴而龐大,比「法式肉派」要大得多。我不得不搜尋我的記憶,因為縱使這名稱我不陌生,但只有在翻開艾斯可菲的《烹飪指南》(Le Guide culinaire)時,我才遙想起幾十年前吃過一次「庫利比亞克」。那是一種軟熱的派餅,切開後有過熟的鮭魚和菠菜,上面覆蓋著濃稠的醬汁。這是一道過時、陳舊的菜餚,很久沒有人會做了。
但是這位先生所製作的「庫利比亞克」顯然非常酥脆,呈現出「國王派」般夢幻的金黃色澤,餡料也不同,原本的米由我無法辨識的黑色穀物取代,而且鮭魚似乎外熟內生⋯⋯這愈來愈讓人感到好奇。
一年過去,突然間,有一張「皮蒂維耶酥皮餅」(pithiviers)的照片出現在我面前。不久前,我和主廚埃里克.布里法(Éric Briffard)合著了一本書。對我來說,他的「皮蒂維耶酥皮餅」堪稱法國美食史上的註冊商標,與之齊名的,還有保羅.博古斯(Paul Bocuse)的「季斯卡黑松露酥皮湯」(VGE)、阿蘭.桑德朗(Alain Senderens)的「阿彼修斯香料血鴨」(canard Apicius)以及貝爾納.帕科(Bernard Pacaud)的「黑松露千層酥」(tourte de truffe noire)。我品嚐過無數「皮蒂維耶酥皮餅」,沒有一個能夠與布里法的「皮蒂維耶酥皮餅」相提並論。我的好奇心到了頂。
我傳了一則簡訊給這位布魯塞爾的主廚。
「我可以到您的餐館用餐嗎?我對您的廚藝非常感興趣。」
主廚很快就回覆了。
「這將是我的榮幸,我是您最忠實的粉絲!星期五嗎?您想吃什麼?」
「我不知道耶。您的『法式肉派』讓我很感興趣。我已經40 年沒有吃到『庫利比亞克』了。而您的『皮蒂維耶酥皮餅』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會在星期五的12點30分等您到來。」他簡短地回答。
這就是我來到波札餐館的緣由。這地點從外頭看很低調,客人甚至會懷疑入口在哪裡。不過一推開門,餐館的室內空間則讓人訝異。內部呈現出建築師維克多.奧塔(Victor Horta)的裝飾藝術風格,1928年即已建成,以前是作為酒吧/吸菸室,其偌大的空間令人驚歎。它占地218平方公尺(66坪),在所保留的原始結構中劃分為兩部分,側邊擺有幾排長凳,中央放置圓桌。後方有一個開放式廚房,裡面有幾位廚師忙碌著。
「您好,女士,歡迎光臨。」他們對我說道。接著帶我到幫我保留的那張桌子。我正要坐下,但主廚已經等在那裡了,他張開雙臂,好像我們已經是世上最要好的朋友。有別於外場中那些身材高大且偏金髮的男性服務員,主廚身材健壯結實,毛髮十分黝黑,行走的姿態就像一個世故的人,一條毛巾就掛在廚師服肩上。
「您的火車是幾點呢?」他劈頭就問。
「您不用擔心,我們還有時間。而且我很餓!」
我在波札餐館的第一頓餐點就這麼展開……我既見識到又品嚐到精確的典範。我上一次見到對料理如此挑剔、嚴謹、偏執於完美者,可追溯到1996 年的侯布雄(Joël Robuchon)餐廳。
開胃菜是一個小泡芙,外表看起來很簡單。可能加了帕馬森起司。當我天真地一口咬下時,頓時感到訝異和驚奇。酥脆……一名記者朋友告訴過我,他被禁止使用這個形容詞。我們確實用它來形容任何輕浮的糕點或者任意一種炸食。但是卡倫.托洛桑的泡芙外殼重新定義了這個形容詞,或者該說,他重新賦予這個形容詞屬於他自己的意義。它的酥脆令人瞠目結舌。它在口齒間抗拒了短短一瞬。接著,牙齒輕柔而堅決地將它咬碎。它既不鬆軟,也不會太乾。它既不會太硬,也不會太潮,沒有絲毫瑕疵及不均勻之處,這泡芙殼質地絕對均勻。
然而,它的均勻口感無論何時都不會令人感到乏味。要如何做到如此規整卻又不乏味?它高貴、單純且絕對完美,它的輕盈讓人想像製作它需要多久的思考時間。意味深重,卻也輕如鴻毛。這顆泡芙非比尋常。撇開卓越之外,還有別的,是一種比好還好的品質。是精確度?是純粹度?還是化不可能為可能?
不過下一道菜接著上桌了。「萊芒湖(Lac Léman)白鮭,類似醃製鮭魚(Gravlax),搭配番茄、薑及香菜。請慢用!」主廚說道。我拿起湯匙,悄悄地在盤內攪動一番。底部有一層薄薄的膠凍。在還沒嗅到香氣並嚐上一口之前,我就為番茄著迷了。黃色、紅色、橙色和綠色,大小不一的番茄都已經去皮,甚至連最小的櫻桃番茄也不例外。如此細心處理,它們看起來就像彈珠一樣。你見過剝皮後的番茄那種略為粗糙的表面嗎?噢不,這裡可沒有。它們光滑無瑕,就好像經過拋光。可是沒有皮,這也太神奇了吧?
魚肉的質地純淨、緊實。風味也是同樣澄澈,但維持著一派優雅。或許我潛意識預期的是更粗獷率性的口味,畢竟是出自於一名專長在肉派的主廚。但實際上它卻像一個小小的祕密湧泉,從岩石裂縫中流出的泉水,一切都如此清澈且細緻。
「小牛頭肉佐小灰蝸牛(petit-gris)、香料草汁。請慢用!」小牛頭肉的烹調非常出色,膠凍部分在恰好從稜角開始失去形狀之前,便出現該有的入口即化。我再度對這口味的澄澈感到驚豔。有些人可能比較喜歡味道更濃烈的小牛頭肉,更有肉風味。不過沒人能否認這道菜的精緻程度,它絕對是一道高級訂製的招牌菜。
「『庫利比亞克』待會就上桌,它已經在爐內烤好了。我在這個空檔為您端上一些小東西,以免您覺得無聊。」主廚說道。
「已經上了好幾道不小的小東西了(份量完整且大方)……請問您特地為我做了什麼『酥皮』類餐點?」
「當然是『法式肉派』!還有『庫利比亞克』,和一個『皮蒂維耶酥皮餅』」。
「這麼多!」我大叫,有點驚慌失措。
「您從巴黎來,我可不會讓您空著肚子回去。」主廚說道,他的雙眼閃爍著笑意。
我不會描述那個在比利時境內乃至歐洲都聞名遐邇的「法式肉派」。世界各地的美食家都前來品嚐它。當我離開幾個月後,我開始有點忘記它了。畢竟,見異思遷的我告訴自己,它就是個「法式肉派」而已。不過只要我重新品嚐這道菜,我就會再度臣服。酥皮的質地鬆脆、輕盈且緊緻。餡料的口感隨著切片由上而下循序漸進,變得愈來愈深刻。膠凍雖薄,卻帶有濃郁風味。總之,每一口吃到的質地都有所不同,從酥皮的柔順和輕盈,開心果的柔脆,肥肝的豐腴滑順,鴨的肉感,再到把這些部分結合起來,三三兩兩一組分別取用,或把豬肉餡料所黏著的所有部分一起入口。醃漬胡蘿蔔和球莖甘藍時而呈現螺旋狀,時而呈現碎末狀。還有我最愛的醃黃瓜(卡倫說是「我和我女兒在放假期間一起採摘和準備的」),我好像從中尋得了主廚的根源。它們略甜而不會鹹,所以並不完全是甜的,且帶有些微的蒔蘿味,恰到好處的酸度在口中產生愉悅的清爽口感。
「庫利比亞克」和「皮蒂維耶酥皮餅」
起初,卡倫.托洛桑想成為珠寶師傅,但種種情況造成了不同的轉折。因為家境並不富裕,他13歲時為了賺點小錢而進入提比里斯(Tbilissi)的一家速食店廚房工作。他為了維生而在不同的廚房間往返奔波,直到他們一家移民到比利時。當時他18歲,一句法語都不會講。他的第一個職位是在伊克塞勒(Ixelles)的一間大餐廳當洗碗工。後來他升為廚房助理,但對這份他沒得選擇的工作並沒有熱情。至於法語嘛……他是周旋在成堆工作中去上夜校學的。
這名亞美尼亞年輕人在布魯塞爾發現了什麼呢?我們都知道亞美尼亞的歷史,它是前蘇聯加盟國,在柏林圍牆倒塌後,東方集團(bloc de l’Est)的解體過程經常是暴力的。卡倫經歷過這段歷史上的複雜年代,但他很少提起。直到我勤快地去他的餐廳用餐2年後,我們成了朋友,我才得知他的母語是什麼。純粹是因為他的母親打電話給他,而我聽到他們的對話。
「你跟你媽媽說俄語嗎?」
「是啊!我跟我爸爸和姊妹們講話也是用俄語。妳知道,我是在蘇聯出生的。」
「啊……這倒是。我從來沒想過。」
「我是在共產主義時期長大的。愛國歌曲、每所學校裡都有列寧雕像、晚間新聞時會播放蘇聯國歌⋯⋯這些都是我的童年。」
「你是喬治亞人嗎?還是亞美尼亞人?」
「啊,才不是呢!我不是喬治亞人。我雖然是在喬治亞的提比里斯出生,但我是亞美尼亞人!」
我感覺自己好像犯了很嚴重的錯誤。
「這就是為何我會熟悉俄羅斯的文化。『庫利比亞克』就是從那裡來的。艾斯可菲把它帶回法國,但他加了米和白醬。不過,雖然俄羅斯的米很多,卻不是土產,米源自中國。而「卡莎」則相對是本土的。所以我又把蕎麥加了進去。不過我保留了法式版本的酥皮(feuilletage),比俄羅斯的皮羅什基塔皮麵團(pâte à pirojki)更美味。我覺得酥皮真的比布里歐許麵團(pâte à brioche)還要好。」
酥皮滿覆著奶油及香氣,在炙熱狀態下外皮酥脆,內心柔軟濕潤。餡料豐富,同時保留著一股鄉村田園般的香氣及若干綠意,且口感變化無窮:酥皮的柔軟度雖然不是很飽滿,卻仍然充足,菠菜纖維柔順,略微的苦味與蕎麥極輕盈的粗糙口感交織結合。每一顆蕎麥粒的外皮都在咬合間微妙地抵抗著,不過隨著愉悅地咬入核心,便帶出令人驚訝的雅致。透過極為專業的烹調,鮭魚顯得鬆軟,且同樣展現不同層次的質地,每一層都蘊含著倍增的風味。外圍熟透,未熟的中心溫潤……對絕對需要經過長時間在烤箱烹調的派餅來說,是什麼樣的神蹟才能做到如此程度?驚人的幸福口感伴隨著風味的變化,而這變化彼此間具有無盡的細微差異。這裡所談及的滋味遠遠不只是鹹或甜、多汁或海鮮而已。
我從未想到艾斯可菲的經典作品可以如此純粹且精緻。是經典恆久遠嗎?不止,少說也是永流傳。我感覺置身於一個複雜到令人敬畏的樂高遊戲前,它是由一個瘋狂的造物主所組合而成。經典料理萬歲……
「女士,這是用莉莉安.布爾戈飼養的鴨所製作的血鴨鴨胸加鵝肝做的『皮蒂維耶酥皮餅』。餡料部分由紅酒油封鴨腿肉和沙地蘿蔔做成。請慢用!」儀態優雅的外場經理對我說道。
烹調,厚度,餡料,風味,香氣,聲音,輝煌,奢華。
我置身於另一個世界。儘管餐廳座無虛席,嘈雜的聲音卻像魔法般消失了。如此美麗……這種體驗很不真實。
卡倫告訴我他熬夜學習埃里克.布里法的「皮蒂維耶酥皮餅」。「我把書讀了一遍又一遍,試著理解它。突然間,我抬起頭,因為我聽到鳥兒在唱歌。我整晚都專注在『皮蒂維耶酥皮餅』上,甚至渾然不覺。」卡倫的「皮蒂維耶酥皮餅」與大師的版本有所不同,也許更現代化。在風味上,因為使用的是鴨而不是野味,所以味道沒有那麼濃烈。但除此之外,一切都面面俱到。鴨肉多汁。肥肝帶來法國料理中不可或缺的獨特風味。這道菜有輕盈、蓬鬆、豐富的絕佳酥皮,派皮上的溝紋不是徒具裝飾性而已。這些條紋有其意義,不單純只是生麵團在烘烤時膨脹而延展的物理現象。金黃色的帶狀部分在初次觸碰時觸感光滑,隨即轉為鬆脆,在酥鬆中帶有空氣感。它的淺色處細長,且「烤得不算太熟」,就像在麵包店看到的長棍麵包一樣。一如床的彈簧那般,兩種質地的交替,讓風味變得更加複雜且完整。圍繞著圓頂酥皮外殼的軸環狀裝飾細緻之餘,還更堅固,使圓頂外殼得以挺立並完整接合。沒有絲毫僥倖。一切細節都考慮周到。貌似「小耳朵」的可愛突出物完美膨起,吸附豪華的佩里格松露醬汁(sauce Périgueux),極具奢華美味。用手指拿起,啃咬鬆脆滋潤的滋味……
増井千尋 CHIHIRO MASUI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