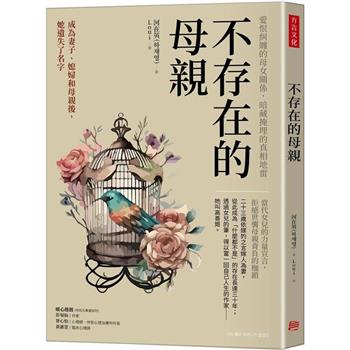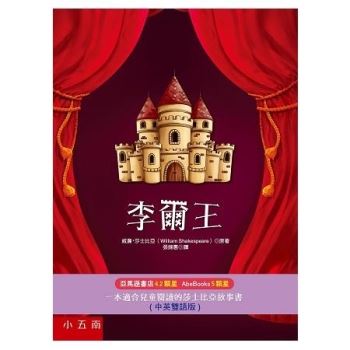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3 項符合
夏春錦的圖書 |
 |
$ 0 電子書 | 鲍廷博传
作者:夏春锦、沈思佳 出版社:中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5-03-20 語言:中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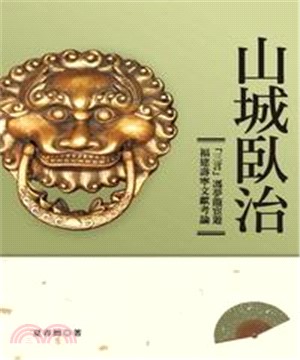 |
$ 189 | 山城臥治:「三言」馮夢龍宦遊福建壽寧文獻考論(電子書)
作者:夏春錦 出版社:秀威資訊科技 出版日期:2013-08-16 規格:1版 |
 |
$ 189 ~ 243 | 山城臥治:「三言」馮夢龍宦遊福建壽寧文獻考論
作者:夏春錦 出版社: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8-16 語言:繁體/中文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