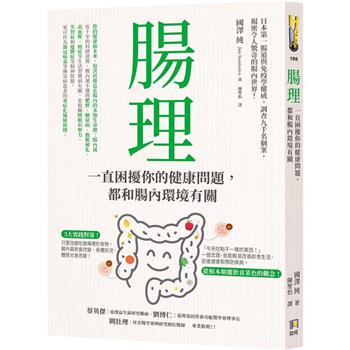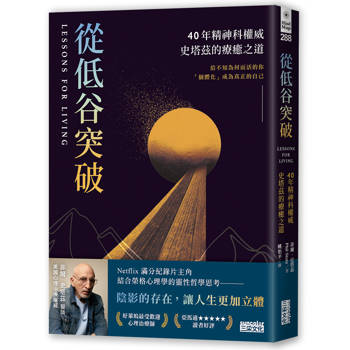推薦序
憶母怨母--大衛.里夫的《泅泳過死亡之海》
三年前的三月三十日下午,我抵達卡內基音樂館的贊凱爾廳。手持蘇珊.桑塔格助理寄來的邀請卡,出席一代才女的悼念音樂會。演奏的是桑塔格生前好友,享譽國際的古典鋼琴家內田光子。演奏會前見到觀眾席上的桑塔格的「遺孀」安妮.萊博維茨??名流攝影家,成名作是約翰.藍儂擁抱小野洋子的那幀裸照??與紐約文化圈的來客寒暄。
主持的是桑塔格的獨生子大衛.里夫。他簡單地解釋,悼念音樂會是桑塔格的遺願,節目表上的晚期貝多芬的弦樂四重奏(編號一三二)及鋼琴奏鳴曲(編號一一一)都是她個人的要求。
沒有冗長的頌德的演辭。大家默然聆聽逝者要求我們關注的西方音樂精品,靜靜地離開音樂廳,踏出暮色四合的第七大道之前,工作人員派發一本安妮.萊博維茨特別印製的紀念攝影集桑塔格在沙漠中的童年,穿唐裝的少女時代,反越戰示威被警察逮捕,在塞拉耶佛燭光下圍讀《等待果陀》……
整個悼念項目真的高雅、別具格調,我當時想。而特別佩服桑塔格在陰冥中操控自己身後「形象」的能力……這當然只是幻覺而已。
儘管桑塔格二十六歲離婚,帶著七歲的兒子與身上七十元的現金到紐約闖天下,又甚至拒收贍養費的豪舉,為女性主義者津津樂道。但她生前並不諱言自己雙性戀。與萊博維茨的關係長達十五年。
把私隱留為私隱??即使被當代同志運動視為政治不正確??大概是桑塔格做為「普遍性的知識分子」的態度。我記得自己與她的對話時談起「自傳」時她一臉厭惡的神情。
但○六年春季布魯克林博物館大肆宣傳一個安妮.萊博維茨的題為「攝影家的人生」的個人展,展出不少她最廣為人知的名流照片??畢.彼達,世界先生變州長的阿諾.史瓦辛格,老布希總統的太座芭芭拉。但插雜其中的卻是她偷拍的桑塔格彌留病榻、不成人形的「生活照」。此舉引來不少非議,評家說她借此博取「嚴肅、有深度」的同情分。
如今大衛.里夫出版的回憶錄《泅泳於死亡之海》對這批照片更絕不容忍。他寫道「若有一個仁厚的神,欣然插身人間事,庇護我們最深的恐懼的話,那我母親應該因心臟病發猝斃,而不應是緩慢痛苦地因血癌亡故……她不會有時間驚恐、沮喪??再幹不到她想做的事,過她期望的生活;她不會有時間為自己哀傷,面對自己也無法辨認的衰敗的軀體,更毋須死後受到侮辱??被安妮.萊博維茨的名流之死的嘉年華會影像『追思悼念』。」
許多對安妮個展的劣評,其實以「美學」為理由否定,儘管她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攝影師,但她無法從蕪雜的現實中找到藝術的時刻,令這批桑塔格的生前身後照淪為業餘無趣的「家庭相簿」。
在這狗仔隊、現實電視、自傳記錄片的時代,怎樣是不侵犯私隱,如何不「利用」私人素材是微妙的,但也彷彿是過時的藝術與現實的課題。但里夫依附的是個悠久的人文傳統,他在書中聲言,母親大去期間他不曾撰寫筆記。若這令他的態度顯得誠懇的話,誠懇也是不足夠的創作標準。《泅泳於死亡之海》觸及了許多現代社會的課題疾病與現代醫學,死亡與社會。感人之餘,這也是一本令人困惑的書,也許因為裡面有愛怨難解的情意結。
里夫早年曾是母親的編輯,寫過一兩本反應平平的非小說。他的突破是九五年出版,大受好評的《屠宰場:波士尼亞與西方的失敗》。此後他寫的有關人權及聯合國的書和文章都很受重視,雖然有人揶揄他是「專業的滅族屠殺觀察家」。九二年我訪問桑塔格時,她只淡然告訴我「我的兒子是位記者,他叫我往波士尼亞視察。」然後她解釋在危城導演《等待果陀》的來龍去脈。有些閒話我沒有寫進訪問中,例如她說我可以住在別的地方,可以住在巴黎。但我住在紐約,因為我的兒子住在這裡……」
桑塔格母子關係密切的一個神話也可追溯到影射她們的小說《嬉戲》(Caracole),書中虛構的母子密切得儼如有亂倫傾向。但《泅泳於死亡之海》內,里夫自責「為人感情冷漠」。談到母子之間的關係,他只隱晦地形容為「困難,緊張」。其實可以想像名母之子不易為,何況母親是這麼的一位才女天后?
桑塔格激賞的前輩女作家瓊娜.巴因斯(Djuna Barnes)在她的傑作《夜林》裡說過「人是對自己的死才感到突如其來,在別人眼中,我們一直朝向死亡。」桑塔格之死較許多人更有跡可尋,因為可以查考她的癌症病歷。
桑塔格在七五年患上乳癌,里夫才二十三歲。而醫生是向他宣布這壞消息,那年代醫生不會向病人直言,因乳癌基本上被視為絕症,但才女不會坐以待斃。於是往法國求診,與醫生設計出當時並不普及的化療程序,並接受了割乳手術。里夫說,她胸前的疤痕令桑塔格的性生活從此受創,令她的私生活成為「不快樂、哀傷」的泉源。但她的抗癌經驗令她寫出了對全球文化也影響深遠的《疾病的隱喻》一書,譴責社會醜化疾病患者,令她們感到咎由自取。而病者應坦然地視病為病,尋求療方。
但里夫引述她當年(仍未出版)的日記,披露她苦澀的心態:「一週兩次,我拖著自己重返醫院,把我晦暗的肉身向黑醫生或綠醫生展示,好令他們告訴我我的近況。一個推、拉、按,欣賞他的手工製品,即我的巨大疤痕;另一個把毒液泵進我體內,目的不是殺我而是殺死我的病……我覺得我就是越戰,我的身體在侵略,進行殖民戰爭,而他們向我施用化學武器,而我必須歡呼……」
桑塔格與癌症第一次交手,逃脫了,痊癒了。但里夫多年之後回想母親的「緩刑」「除非因意外橫死、或被謀害,人多半會因某種疾病殞命;如何調協人壽有限與富裕國的假設,即每種病都有治療的辦法,今天找不到的話,未來總會辦妥?前者的邏輯是接受死亡,後者視死亡為一宗錯誤,而某天我們可以糾正這錯誤。」
桑塔格在九十年代末第二次患(子宮)癌,而這次的「康復」更只是匆匆數年的「緩刑」而已。治療她子宮癌的化療破壞了她的骨髓,導致一種稀有的白血癌。她大概也感到大勢已去。她曾尖叫、飲泣,並沮然地向里夫說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不是一個例外。」但她渴求延壽,甚至羨慕也曾患血癌的薩依德最後痛苦的數年,「因為他多幹了那麼多工作。」她遂孤注一擲地花了一千五百萬元的訂金,往西雅圖一家醫院進行骨髓移植手術。對一名年過七旬的女人來說,機會當然渺茫,而且肉身與精神的磨折也是難言的吧!
里夫對別人眼中桑塔格雄風赳赳,頑抗死亡的反應是此書最複雜微妙的部分,他感到被迫去矇騙母親,每天哄說她精神好了,「我母親經常認為自己對真相的渴求是絕對的。診斷之後,那渴求仍在,但她絕望地尋索的已是生命,而不是真相。」
也許這片段已顯示出,《泅泳於死亡之海》的悼念愁緒之下隱含一份譴責。里夫反覆地問「可以為母親做什麼?」但他迴避了另一個重要問題「母親最後能為他做什麼?」這份難以啟齒的需要反映在里夫引述的,母親歿後的一封醫生來信「大部分人在那處境中會不再搏鬥,接受那必然的終結—也許出於睏倦、恐懼或他們希望能把有限的餘生給予生者更多的回憶。」
最後的一點的欠缺大概是里夫不願明言的遺憾,所以書中許多有關母親「不接受死亡」的幽曲怨言,儘管他無奈慨嘆:「這是她選擇的死的方式。」他也引述北島的話:「一個人的思想,只要說出口,寫下來,就會形成另一種生命,不會隨著肉體一起被消滅。」做為「其人既往,其文克定」的安慰。
里夫把母親棺木飛往巴黎下葬,令桑塔格成為沙特、波特萊爾、貝克特的墓友,讓世人憑弔。
陳耀成,文化評論家及電影導演。他的最新作品《康有為在瑞典》榮獲《南方都市報》頒發首屆人文生活(二○一一)年度電影大獎。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