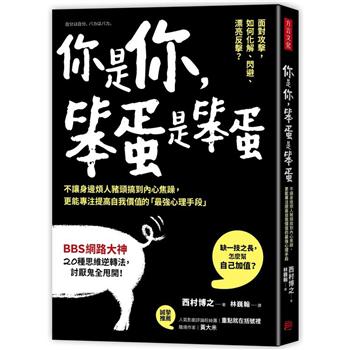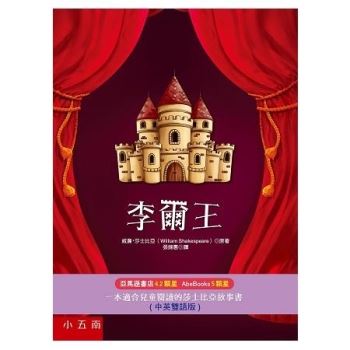發現黃金存摺
老包
將近三個月前,國民黨的馬政府利用政治打手特偵組,汙衊前總統李登輝在十七年前,曾有「貪污」嫌疑時,我寫了一篇文章反擊這些小人莫名其妙的指控。
文章出來後,一家相當有規模的新聞網站,一位年輕的女記者打電話找我,希望能夠引用我文章的觀點,來當她報導該重大新聞事件的價值判斷。同意之餘,我也有很深的感慨:因為女記者顯然被我文章中所舉,某些顯而易見卻被社會長期忽略的事實,所震撼而覺得必須加以引用,以免年輕一代的資訊工作者,繼續活在不清不楚的資訊迷霧中。
我那篇文章主要是說:台灣的民主環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有一大半是李登輝當年自我限縮權力去換來的──包括總統任期六年改為四年、取消可以無限制連任、廢除可以整肅異己的方便法律、裁撤可以當自己超級武器的警總、把用簡單的公開收買手法就可當選連任的總統選舉,修改成充滿不確定性的人民直接選舉……;因此,馬先生和特偵組的社會地位,根本就是來自於李先生的民主路線,現在反過來對李先生進行鬥爭,這種有悖天理的政治操作,是不可能獲得社會認同的。
果然這個事件引起社會強力反彈,就連馬陣營的一些深藍朋友,也覺得此舉實在太過分。現在我們就從這個地方切入,來問自己:李登輝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到底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我認為對一個創造歷史的人,我們必須先有一顆細緻的心,才可能正確認識。以我個人的經驗,雖然在一九八八年李先生開始擔任總統時,就撰寫報紙每日專欄,而有了節奏密集的政治觀察,但一直到一九九九年五二○當天,我才算是有了「正確認識李登輝」的入門準備──這就好像我在三十歲那一年,一個作家朋友告訴我,我們時常掛在嘴邊的台語「隨便啦」、「都可以啦」,其實就是帶有古意的「請裁」,而不是被粗糙引用的文化淺薄;從那個時刻起,我對自己的母語,才開始有了縱深的思考與觀察。
一九九九年正是李登輝擔任民選總統的第三年,那一年政壇最關切的一件事,就是李先生會不會參選隔年將舉行的,第二屆民選總統?按修憲後的選制改變,李先生並非沒有參選空間,且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有不少本土化改革未竟事宜,接班問題連宋之爭愈演愈烈,不少人希望李先生能出面參選,穩住陣腳……。李先生對續任與否遲不表態,國內外猜測的聲音四起。到了五二○那天,李登輝親自撰寫的《台灣的主張》新書,正式出版(日文寫作,再製作為中文)。在該書的最後一個章節,題目是「李登輝不在位後的台灣」,這幾個字已經清楚說明了一切──原來李先生早就決定不競選連任,但他希望人們從他的新著中去明確探索這個訊息,以便更能清楚認識他的心路歷程。而就在那個最後章節,當我讀到以下的文字時,內心是有著無比的震撼:
………………這股愛台灣的熱情,在我變化莫測的人生中,時而燃燒,時而潛沉,支持我走過這七十多個年頭。省思今日的台灣,就像歌德的《浮士德》中動人的一幕,我不由得很想吶喊:「停下來,妳是多麼的美麗!」但今後台灣還得面臨許多的挑戰,接受各種的考驗。台灣的歷史,還要繼續寫下去。………………
這是一段熱情洋溢,有如大海澎湃的文字,我從這裡看到的李登輝,並不只是創造台灣民主奇蹟的政治家,更是一個試圖超越時空限制,而有著豐富才華的文學家、藝術家──在李登輝時代尚未開展之前的台灣人,其面貌圖像事實上是相當模糊的,任憑一再更迭的外來政權粗魯操弄;到了李登輝時代,他全新貫注,將台灣人的形貌雕塑出來,台灣人的可貴生命力,因而開始顯現,並有了多元光采。因此,從某方面看來,說他是類似羅丹那樣的雕塑家,也不為過。
然而以台灣內部流通的資訊,並不足以讓我們認識李登輝,這個世界級的傳奇人物。這主要是語文的問題,李先生在表達他思想層次的訊息時,似乎日文才能呈現該有的縱深。舉例來說,日本的大文豪司馬遼太郎,就能從他的口中,掏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這樣的內心話,但台灣本地的訪談者,卻沒這個本事。這乃是歷史變遷對台灣人的捉弄;我們的父執輩曾出生為日本人,以日文在表達生命的喜悅與哀愁,但到了我們這一代,我們卻被迫要以中文為表達工具,與日本文化的連繫受到阻撓,甚至須切斷與父執輩的深度情感連結。
李登輝退休後,我曾有幾次機會和他聊天,有一次他很感慨的說:「可惜你不會日文」;我是一個文字工作者,我當然曾想過要學好日文,但是這三十年來,人生的精華都用在和台灣的中國文化霸權周旋上 有些願望就必須擱置了。我的經驗其實也是我這一代普遍的經驗,那這樣說來,我們的損失可大了──李先生快九十歲了,我想知道他留給台灣這塊土地,以及這個浩瀚世界,是什麼樣的資產?就好像我們的父執輩,留給我們一本厚厚的黃金存摺,但我們卻遍尋不著,那種懊惱乃可想而知。
簡單的說,描述李登輝的書籍不夠多,而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就政治表相在敘述評價的;對我來說,那些並不足以描繪出一個線索,來告訴我們「黃金存摺」在哪裡?有一次我和李先生聊到類似的話題,我說某某人又寫了李登輝故事的書,看來是有花不少心力在寫作,但我怎麼看,都不如《台灣的主張》這本書,能帶給我啟發。李先生說:「那不一樣啊,我自己寫的書當然會有差別」,然而這沒有完全說服我,因為當事人和一個敏銳的詮釋者,所能提供的線索有時還是不同。
舉例來說,李先生有個在生活上相當親近的友人,同時也是我的好朋友。四年前有一天,這個友人告訴我:「老先生最近心情很低潮,常出現不尋常的感嘆;因為他很欣賞又聊得來的一位學者,去世了」,這位去世的學者,當時才四十二歲。照理說,像李先生這樣見過大風大浪的政治家,是不太可能會為這麼一件事而陷低潮,但我當時卻感到「能夠理解」,而印象特別深刻。因為在二千五百年前,亞洲有兩個偉大人物,也有相似的心路歷程:佛陀最得意的弟子早他去世,或大儒孔子的弟子顏回去世,都曾使大人物悲痛神傷,體會世之無常,而令人發現一個偉人身上的共同「密碼」──那就是他們擁有一顆多感的心靈,但總是運用突破人之極限的意志力,時時刻刻在加以超越。
有較多的機會和李先生聊天後,常會發現他談到對台灣土地的愛,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時,語帶哽咽、眼眶泛著淚水。我認為這些必須透過文學、藝術,或甚至是音樂,才能深刻描繪出在老先生身上的「時代的悸動」。退休後的李先生,很喜歡接觸年輕人,也急切地想要了解現在年輕人,內心在想什麼,因此他會相當有耐心和相差一個甲子的年輕人交談;不斷提出問題,也傾聽年輕人用當代流行的術語說明。我每次在一旁看到這幅景象,總是特別感動,因為這個擘畫台灣民主路線的老人,很顯然是在年輕人身上 發現了多元民主為這塊土地,所帶來的真切生命力,而有著無比的欣慰。這是一幅散發生命光輝的畫像。
李登輝的存在,就如同台灣這塊土地的存在,是令人讚嘆的奇蹟──北回歸線穿過台灣,但在一天之內,人們卻可以在這塊特殊的地理,發現生長在地表的熱帶、亞熱帶、溫帶與寒帶等四種特色植物!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只用政治的語言去解讀李登輝,縱深也會有所不足。因此這十年來,我一直期盼有人能夠從較宏觀的視野,提供我們探照「李氏寶藏」(我前面所說「黃金存摺」)的動能與線索──套一句現代科技的用語,也就是提供一種3-D畫面,來探索李登輝的生命故事,與令人驚艷的精神世界。而按照我的觀察,這個人必須要有深度日文素養,以及濃厚的台灣情感,才能真正觸及李登輝的內心世界,並填補李先生和我們這一代之間,殘酷的歷史斷層。
所有的傳奇,終究會找到詮釋它的主人。台裔日籍的大文豪黃文雄先生,顯然也感受到了我們這十年來,所急切散發的念力,就在李先生將近九十歲,而他自己七十三歲的這一年,終於完成了這一本日文原著的《哲人政治家李登輝》,從哲學領域探索李先生的精神世界。看完這一本著作時,我久久不能掩卷,內心許多苦悶與疑點,終於得到了解答。套一句中文的說法,算是「打通了任督二脈」。按照黃先生在書中所稱的,「李登輝可以說是在美日中文明衝突與文化摩擦中,成長出來的代表性人物」,這一本書要帶我們去探索真正的李氏寶藏,這個使命是多麼不容易。
我因此很好奇這個過程的繁複,有一天當面問了黃先生,到底花了多少時間對李先生作訪談?黃先生說:「就是這十年啊,十年來和他對談的結晶!」我大受感動,人生有多少個十年?黃文雄先生用十年的工夫,為我們留下了可貴的文化元素──我相信將來會有更多文學、藝術的創作者,運用這些元素,去詮釋更豐富的關於李登輝,這個偉大哲人政治家的價值。
而更重要的,台灣的形貌,也將由於這些元素的注入,更顯明亮耀眼。是以為序。
自序
我經常受邀到日本參眾兩院的台灣關係讀書會當講師。與會的國會議員認為,政治家的模範或值得尊敬的政治家,除了吉田茂和岸信介之外,還有李登輝。
世界上有名的政治家非常多,戰後有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戴高樂,另有為世界新秩序鋪軌的超大型國家美國的歷任總統。然而為何日本人傾慕的,是亞洲小國的台灣前國家元首?
我經常會如此反問。針對理由究竟為何的大哉問,我身旁的日本朋友通常會出現這樣的回答:「台灣是個小國,但做為主權國家在國際社會,並沒有完全被認知。而李登輝不但沒有屈服於來自中國的恐嚇,還勇敢面對它、為堅守台灣的尊嚴而奮鬥至今。我們對其勇氣給予最大的尊敬。戰後日本已經不再出現那般有勇氣的政治家,所以我們想把李登輝當成自己的楷模。」
我每次聽到這樣的話,都非常感動,甚至眼角發熱。他們還會推崇「尊嚴」和「勇氣」,證明在日本,武士道精神依舊存在。近年來每到國政選舉,就會有人高喊「生活、生活」,而訴說國家大事的政治家卻越來越少了。不過,在日本還有政治家注重「尊嚴」和「勇氣」,這讓我對日本的未來還抱有一線希望。
仔細想想,日本是一個主權國家,是和歐美並駕齊驅的大國。但關於自身教育的歷史認知,以及屬於心靈和靈魂的靖國參拜,卻無法堂堂正正地貫徹自己的信念。
李登輝是一個已經從政界引退的民間人士,但他的訪日,因其「還有影響力」而被拒絕入境,造成很大的轟動。原因在於日本政府從頭到尾都受到中國的控制與指示,連來自中國的「現場指導」都甘願吞下去。
若從此事來思考,李登輝時代的台灣和戰後的日本形成明顯對比,那是很自然的。日本文壇的大老阿川弘之,甚至還曾想「請李登輝來當日本首相」。其言感人肺腑。我在日本居住已快半個世紀,那感受更加深刻。
眾所周知,被稱為「台灣民主之父」的李登輝,他的政治貢獻已在近、現代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頁。李登輝雖已近九十高齡,卻還在街頭手握麥克風,站在民眾的前方,看到這種景象,誰不會深受感動呢?
李登輝在政治上的成就,已讓台灣和全球刮目相看。關於他的相關書籍出版品相當多,然而令我在意的,竟然沒有一本深入探索支撐李登輝個人行為和思想、心靈與精神世界之根柢的書。特別是在台灣,用世俗眼光評價李登輝的人還是佔大多數。
在日本,人稱李登輝是「亞洲的哲人」。小說家兼立法委員,也是我的好友王世勛,則大大稱讚道:「他不僅是亞洲、而是世界的哲人。」我第一次從李登輝聽到有關「我」的省察與思索,是在台灣哲學會的會員大會上。
李登輝的政治力泉源,來自他的生長背景與教育環境。他非常喜好讀書,博學多聞,又有自身獨特的哲學思想。這也是我尊敬的台北高等學校出身的諸前輩們所共同擁有的特質,同時也是扎根在如同母親的台灣這塊土地才能孕育的人文素養。
李登輝在總統時代,以「心靈改革」為目標,經常提起「場所」哲學。而那帶有使命感的行動,或許是因為和夫人一樣都是虔誠基督徒的緣故。
我所知道台灣立法委員當中,最有學問、最勤奮,且是民進黨第一任秘書長的黃爾璇,以及前輩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他們倆人都曾向我表示過「像李登輝這樣的人物,在台灣史上大概不會再出現」的類似意見。因此我才會想以鈴木大拙說的「超個己一人」那樣的宗教意識和使命感,來講述偉大的政治家李登輝,並告訴後代子孫如同大地母親的台灣的未來動向。
李登輝不是「亞洲的哲人」,而是超越亞洲的「世界的哲人」,關於其在台灣與近現代史所扮演的歷史性角色,後世子孫又該如何學習?我想我們有必要闡明的不只是那些可視的外象,還有那些不可視的內蘊。前者是李登輝做為國家元首的言行舉止,後者則是他的心靈世界。本書試圖以多角度的視野,並透過和李登輝的對話,來探究他的「我」的哲學、「場所」哲學、「超越」哲學,以及他的生死觀與歷史觀。
本書所要談的不是政治的世界,而是心靈的世界,因此盡可能避免浮面的、模稜的訊息。希望會有許多年輕人透過此書,來瞭解李登輝的內心思惟及人格修鍊,並向他學習。
關於本書的完成,除了有李登輝本人的協助外,另外還有小說家高村圭子、日本李登輝友之會事務局長柚原正敬等人的幫助,在此向所有關係人致上謝意。
2011年7月吉日
黃文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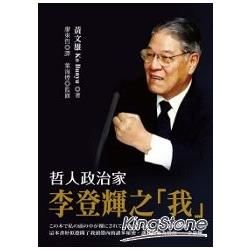

 共
共